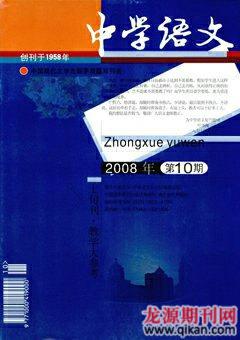一直走到天边——《后赤壁赋》备课札记
徐 彦
在高中语文教材的改革中,各种版本都先后选入了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可以比较学习。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和教学中,大家对“前赋”的看法趋于相同,对“后赋”则各持己见。甚至,后赋的主旨也众说纷纭,教师在课堂上,也是不甚了了。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供大家参考,供学生学习。愿意通过本文,和大家共同探讨。
苏轼,是横卧旷野的矿脉,我们应该去挖掘去感受,寻求那个隐隐约约藏在千年背后的答案。我不能奢求还原苏轼,因为“羽化登仙”的他只给人间留下了一个无可企及的背影。此刻,面对这篇神奇的文字,我半自信半心疑地,一字一山一句一河地跋涉着。
有人说“前后赋”是姊妹篇,金圣叹还说:没有“前赋”,“后赋”就不知道诉说了些什么;没有“后赋”,“前赋”又叫人糊涂了。如此说来,这两赋是断不能分开的。从第一感觉看,这双姊妹竟是天壤之别,那姐姐风姿绰约,丰腴温润,如天上神女,又宁静神秘,沉着舒缓,如深夜海边飘来的月光曲,怡目怡耳,悦情悦心;可是这妹妹,喜怒无常,足立难稳,像个神经病者,又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像黄昏时节还颠簸在山路上的牛车发出的叹息。
实际上,两赋的主题都是关于人生与社会关系的探究,内容上是言与行的关系。“前赋”是口头上的理想,华丽流畅;“后赋”是双脚下的行动,苦涩艰辛。“前赋”是理论,“后赋”是实践。
其乐为何
苏轼自己说此文写于1082年的农历十月十五。那一天夜里,跟着两个朋友,从雪堂回临皋。途中心情极好,就又想游赤壁了,也就真的去玩了一番,惹了一肚子的痴想回来,一夜无眠。
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经历过沧桑的人,会深深理解其中的味道。现在我能知道的,在“二客”当中,有一位应该是苏轼的知己了。杨世昌,一副神仙骨格的道士,与苏轼是老乡,长年隐居在长江中下游的水边山林,闲云野鹤般自由。当苏轼被贬黄州,自然而然地,两人你唱我和,形影不离,身伴神随,如胶似漆。前赋中那杨道士箫管呜呜,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凶猛的蛟龙也婆娑起舞,多情的孤女更泣泪涟涟,惹得苏轼也悄然黯然了。一曲洞箫余韵千年,不知引出多少情多少怨。然后又侃侃而谈,对话苏子,大道与至理扑面而来,帮衬着苏轼成就了一段绝世名篇。“后赋”中,杨道士的地位不甚显赫,但是苏轼实际上给了他更为神奇的境界,让他化鹤成仙,入梦出梦,点染出一片苏子亦不知其妙的妙境。
有这样的好友相随唱和,苏轼怎能不乐呢?此时的黄泥坂,枯枯的木叶飘落在莹莹霜雪,霜雪染白了人影,人影融进了明月。是清风吹抚了月光,还是月光抚慰了诗心?尽管有些萧索清冷,但幽然宁静。反正苏轼高兴了,酒兴诗兴游兴,浓浓地涌来了。良宵美景,如何能轻意消磨。于是鱼来了,是苏轼最喜欢的松江之鲈,有诗为证:“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此诗题为《携白酒鲈鱼过詹文君》,苏轼把吃鲈鱼品白酒盛赞为此生的真事业,可见其对鲈之爱,超过其他佳肴。
读到这里,我心中不禁有了疑问,那杨世昌话外有意,若是松江之鲈,就不是“状似”,若非,则何必提起呢?查了材料,得知鲈鱼生活在天气和暖,草长莺飞的五月。日出日落之际,水面平阔,水波不兴,驾一叶扁舟,轻举银网,网得无限生趣。苏轼著文时节已是十月之望,哪得鲈鱼呢?思量再三,觉得此处是杨道士有意说了假话。虽然所得并非鲈鱼,但是假借品鲈鱼之兴味,调制今晚的赤壁之游之乐,又有何妨?
既得佳肴,下面就是要寻找美酒了。谪居黄州的苏轼生活拮据,无钱沽酒。杨道士给了他一个制酒秘方,苏轼按秘方调蜜酒以待客,此时家中还有无剩余呢?须问夫人去了。
夫人的回话很妙:“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一个贤惠温柔善解人意又善于持家的女主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位女主人就是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苏轼赞扬她贤德敦厚,极具儒家所倡导的妇德。照顾丈夫,爱护孩子,富贵时不骄横,贫贱时不抱怨,勤劳朴实,始终如一,深得亲朋好友的赞誉。在黄州期间,亲手开垦东坡,种谷种豆,又蓄养家畜,喂食治病。不要说富贵女子,就是一般的农妇,恐怕也要钦佩三分。这样艰苦劳作的生活,并未消磨去王闰之心中的书香。在月辉满枝的良夜,她建议夫君设酒约友,欢聚一堂,吟诗对句,雅兴之浓,绝非农妇可比。此时,她将珍藏已久的美酒捧出,来助苏轼游兴,足见她心中亦有一片诗情画意的天地。苏轼将其甜胜蜜酒的回答收入名文,流传后世,也是对王闰之报以无疆大爱的明证吧。
时过景迁
雪堂正建未成的一段时间,苏轼一家人还都住在临皋亭,白天去东坡耕地建屋,夜里回临皋休息。一日大雪飘飘,染白了东坡,装点了房屋,令苏轼心气一爽,笔起字现,东坡雪堂自此得名,此文也就是这段时间所写。那么,时间不仅是在初冬时节,而且已经有雪飘过。景色必将与十月既望的“前赋”迥然不同了。
想必苏轼对此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到了赤壁之下,还是无法接受,心上口上都生生打印着不相信,不愿相信。“时间才过去了几天,我的清风徐徐,水波漪漪的赤壁跑到哪里去了?”眼前江涛喧嚣,天地之间怪石嶙峋峥嵘,温柔的月儿还是圆圆的,却被高高的山峰隔开,离人间那么遥远,我哪里能触摸到你的柔暖的光辉呢?
在苏轼心中温润了三个多月的柔美丰盈的乐曲彻底变了调,“不兴”之水成了“有声”之浪,“水光接天”成了“水落石出”,“白露横江”成了“断岸千尺”,“月出东山”成了“山高月小”,硬朗、突兀、高峻近于荒凉,恰似贝多芬《命运交响》的序章。
奋然登高
我一直在想,依苏轼的性格,登高也许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没有退路。
兴趣盎然地准备好了酒食,准备好了心情,准备好了前行的脚步,若无功而返,岂不可惜?泊在江面,风景再无可赏之处,饱览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美景之后,消瘦、荒寒、裸露的长江索然无味,岂不可叹?
于是苏轼奋然攀登了。
登高是古人的爱好,历经几世几代,成了习俗,也沉淀了厚重的文化韵味。据说最早的登高是为祭天封禅,从上古的黄帝延续到清代。君王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都是上天赐予的,所以登上王位后,都要到泰山封禅祭奠,感谢上天的恩德,帝王自称天子,他的命令就是上天对下界的旨意。这种观念从古至今,未曾有人怀疑,即使圣人孔子也坚信“君权神授”,他宣扬臣民必须服从君王,君王则应恩赐臣民。
大约从晋代开始,又有了重阳登高的活动。南朝梁人吴均之说,重阳登高可以避灾免祸,此后大为盛行,只是渐渐地,避灾免祸的色彩淡了,作为一种家庭的集体活动流传下来。
读过古典诗词的人都能够清晰感受到,文人墨客游子思妇,登到高处,常常要表达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忧伤之情。他们吟成大量诗文,汇成一条凄美的河流,浸润着华夏儿女爱家爱国眷恋故土的心。“楼高莫近危栏倚”,频频告诫自己,不要登到高处,楼越高越不要登上去,即使登上了也不要凭栏,更不要伫立久久,不要柔肠寸寸,不要粉泪盈盈,“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是人性中最温柔的深处,也是最迷人的情愫。如果说女儿情长,那么男儿更是情深,“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抒发着江湖漂泊,茫然无可奈何的忧愁,归思千缕万缕,纠缠不休。
也有人昂昂然唱着高亢的歌曲登上山顶的,杜甫是他们的代表。“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了建功立业的高远志向。杜甫彻彻底底继承了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衣钵,将登高理解为积极进取,是儒家奋发有为思想的体现。还有王之涣也是高唱“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豪迈地前行在远古的旷野,给人无穷的力量。
还有许多古人,登上高山,攀上高塔,往远处一看,就悲哀惆怅。最著名的是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涉世未深的少年,本应很少烦恼,为了装得深沉些,就登到高处,做出个愁苦很深的样子,写出一些“无故寻愁觅恨”的“新词”。同样是杜甫,《登高》诗中“百年多病独登台”,则表达了愁家愁国愁自我的浓浓悲情。
说到这里,有一首诗一定要提及的,就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似乎我们的理解已成定论,诗人表达的是孤独。旷古的孤独浸透了纸背,人的心也要融化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了。诗人站到了至高点,前人不曾达到,后者也不可能达到,前人后人皆不见,诗人独处天地之间,一滴孤独泪从古落到今。但是解到此处,我总觉得还有没有解出的味。一首好诗的审美内涵十分丰富,不可能答案唯一。诗中的“天地悠悠”,说明陈子昂是面对天地发出感叹,饱含着对天地的敬畏,对个人生命渺小的无奈。因为渺小,所以无力,所以欲求同伴。可以说陈子昂是在感喟时间和空间的博大,天之不老地之不荒,而人又能奈何?
突然,我心中豁然开朗,苏轼不就是四百年前的陈子昂吗?请听仲秋之夜的悠悠歌吟:“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高处”的寒凉孤独,是诗人久已深刻体会的。在后赋中,再次浓浓的渲染,并且进一步升华,诗人攀上栖鹘的危巢,向天地众神“划然长啸”,顿时“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大自然的雄伟的力量在渺小的个体生命面前,是那么的崇高宏阔。人,只像一粒纤尘,个人的喜与悲,是多么的卑微。苏轼没有像陈子昂那样痴痴地原地挥洒涕泪,而是有所做为,悄然肃然地生悲生恐,悲恐之中又感悟出“不可久留”,即刻“反而登舟,放乎中流”了,这就是苏轼的性格。他不会像杜甫“凌绝顶”而小众山,觉到的,是自己的无限高大伟岸。杜甫是把泰山假想成了自身的一部分,将外物化为己有,天人合一。如此,面对自然和宇宙,就不会自卑,不会敬畏,不会孤独,即使走上绝路,也至死不悔。陈子昂知道自卑,知道敬畏,知道孤独,却不知返路,不知回归自我,所以他至今还站在那里下泣。
苏轼,第一次自救!
划然长啸
说到长啸,我总觉得是远古初民遗留下来的一种自卫的方法或通讯方式。当他们被强大于自己的野兽袭击,就向天长啸,以期吓退凶猛的敌人,同时也向同伴传达危险的信号。后来打猎中追逐猎物也大声长啸,慷慨激昂,气势博大,壮了自己的胆,助了自己的势。到了晋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最善于长啸的高人,就是阮籍。他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与悲愤,就经常潜在高山深谷的竹林中“弹琴复长啸”。
啸也是古代道家一种吐纳练气的内功法门,运气极有功法,需苦练方得掌握。得道的仙师“月下披云啸一声”,会传三十里,怎的了得。苏轼与杨道士为好友,难怪划然一啸,“山鸣谷应”了。只是苏轼不是在练功,而是在发泄心里的孤独苦闷。
夜半鹤飞
在一次讨论中,我问唐宝康老师:“时夜将半,还有鹤飞吗?”唐老师沉吟了片刻,说:“可能是苏轼的船惊动了水鸟。”无论怎样,都是苏轼撒了个弥天大谎,骗了痴情的读书者一千年。可是转念一想,本段亦真亦幻,亦幻亦真,梦里梦外之间,何必追问其有其无呢?诗人物为心所役,凭空臆想一孤鹤,扑面而来,掠舟而西。鹤是道家的文化符号,西方又是快乐的所在,下文进一步点明用意,鹤化道士,揖“我”探问,是在点化俗子开悟。“我”心神往之至,欲随去却又止,惊怪之间,一切归于自然而然,不要刻意。这是苏轼的智慧。
问答之妙
苏轼睡了,没有了客,没有了鹤,没有了赤壁和小舟,一切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这时,道士来了,“羽衣翩跹”,立在熟睡的苏轼身边,轻轻问道:“此次赤壁之游快乐吗?”苏亦问:“仙师何方高人?”道士点头不答。苏轼不答道士,道士亦不答苏轼,答非所问,问非所答,在这只问不答之间,竟有无限的妙境。只有慧根深厚之人方能领悟。可叹的是,苏轼毕竟是苏轼,“哎呀呀,你就是昨夜那只飞过我舟的仙鹤!”道士笑了,苏轼彻悟了,精神随之羽化而去……
苏轼,第二次自救!
本文中,苏轼两次自救,意义深远。第一次是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从高高的治国救民的理想中解脱出来;第二次是战胜了道家思想的诱惑,放飞了思想的执念,放下了精神的枷锁。苏轼要成为世间最自然最自由的一个人,一个凡俗之人,也是一个感悟了大道的人,也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诗人不再年轻,他成熟了,诗心成熟了。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一次次贬谪,诗人坦然地面对,淡泊而且从容,达观地活着,一直走到天边。
《后赤壁赋》是苏轼对人生进行哲学式思考的至高点。对精神的思考到这里戛然而止,从此以后,苏轼不再轻易表露这方面的探究,更没有再写出这方面的文字,他的精神生命隐居了。
[作者通联:深圳龙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