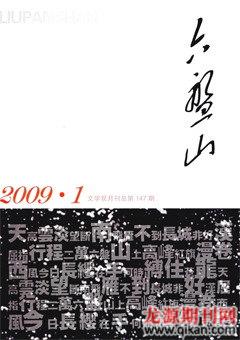贼事不能说
任立新
一
三九天的夜冷得真能把砖冻破。
鹞子下意识地把屁股从两块越坐越冰冷的砖上挪开,索性蹲着。砖是他上平房屋顶时顺手从山墙下搬来的。这是干他们这行临时用的家当,要么用来应急,要么用来吓人,要么跑时用来使绊子,特别在楼上更管用。
鹞子摸着两块冰冷的砖心里竟有些失笑。他想到那次顺着楼上人家的防盗窗栏攀上了四楼一户人家的情景。当时,要不是怀里早揣了块应急的砖,恐怕已经栽了。那样的话他就没有缘分认识条儿了。他隐约记得那户人家的男人当时还没睡,正温情地给女人说了句什么。没想到就在他翻身入窗的一瞬间竟踩在了一个皮球上,一下子摔了个仰面朝天,闹出很大的声响。那男人在大喊谁的同时拉亮了灯,他便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了灯光下。男人光着身子惊愕地看着他,他也瞪着那男的,女人已惊恐地缩成了一团,但还没忘了拉被子盖在粉白的光身子上。他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举着那块砖,男人没敢动,他斜着眼做出要砸的姿势一边寻找门的位置。让他由紧张转为镇定地是男人的裤子竟挂在门旁衣架子上。他举着砖边看边退,就在打开门的同时顺手拽上了裤子。老实说,出了门他没有丝毫的紧张,而是很专业地把砖摆在了楼梯转角处,那是人下楼时脚刚好会碰到的位置。就在他刚把砖放好之后,那男人手里不知操着个什么东西追了出来,他却不紧不慢,还没出楼门,楼道里就传来了重重的摔绊声和砖碎铁器落地的声音,紧接着是男人痛苦地哎哟声。
想到这,他竟然有些忍不住险些笑出声来。他突然想到了半夜里精屁股追狼把没羞当胆子大的这句话。
二
人世间的好多事原本就是一场缘。
鹞子至今坚信就是缘让他和条儿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如果不是那晚看到了那个粉自身子的女人,他也许就错过了条儿。
得手成功回到租住的单元楼,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这可是离开同伴,自己第一次单独出道就得手,而且有惊无险。他自己都不相信当时怎么那么冷静,竟有了自己就是干这行的想法。那个裤子口袋里装着一叠钱,不多不少,整整六千元,应该说既收获颇丰又非常吉利。可接下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为自己放砖使绊子的技巧而得意。他想到了那男人光着身子看他的丑态,那哪是个男人,简直就是一堆不规则的烂肉。他想到了那个粉白的身子,那可是一个真正的粉蛋,团起来纯粹就像个雪白诱人的大馒头。猛然间他有了饥饿的感觉。
他真的饿了。巷子的尽头是一家很有名气的泡馍馆,这是他到这个城市后吃上瘾了的东西,上顿下顿,越吃越香。他找了个临近窗户的位置坐下,边掰馍边看外面。他想找一间不错的发廊去轻松轻松。这也是干他们这行的讲究,既冲晦气又养气神,也能打发白天漫长的时光。
他和条儿就是这么认识的。其实刚进去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条儿那漂亮洁白的鸭蛋脸和镶嵌在鸭蛋脸中的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干他们这行一般是白天睡觉,晚上整夜上班,有时候真的感觉很累。他闭着眼,尽情地享受着头上或重或轻的按摩,特别是那尖尖的指甲很有节奏地在头上挠着,就像一根根针刺在头上,舒服极了。他想认识她,索性就固定一个专职洗发师,每次来时就叫她洗。但就在他睁开眼时却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看到了两条雪白的胳膊,他以为自投罗网,碰到了昨夜那个粉白的女人。他慌忙静神,想从对面的镜子看个明白。
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身后洗头的姑娘似曾相识,但绝不是昨晚上的那个女人,只是肤色和那女人一样,粉白粉白的。
他又想到了昨晚的那个女人。原本只有五十元的洗理费,他也说不清怎么就大方地甩下了一千元。潇洒走出门后,他感觉那双乌黑的眼睛盯得他后背有点酥。
三
等待比拥有往往更需要耐心。
鹞子在平房顶上已经蹲了快两个小时。小平房里的夫妇倒躺在炕上看碟片,丝毫没有要睡的意思。
这是一个四合院式的人家。他爬上的屋顶是一幢大平房。蹲在大房屋顶上能从窗户中把屋里看得一清二楚。蹲在高处看低处,能看得清,这叫登高望远。同样,蹲在暗处看明处,能看得见,而站在明处看暗处,却什么也看不到,这叫暗能躲而明不能藏。他正是凭着对这些浅显道理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才一次次地轻易得手。
他想无论如何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向来信奉兔子不吃窝边草。况且在这个小县城里,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不认识的,说不准谁与谁打断骨头连着筋,莫名其妙的是亲戚。如果一旦失手,那他骗家人骗村里人说他在一家公司里当推销员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今后还怎么做人,特别是让条儿知道了,他更无地自容。为这最后一次行动,他自己跟自己较量了一番。要不是条儿坐夜班车明早就到,要不是在这个小县城买啥东西都要到临近省上的市里去,时间来不及,他才看不上为铺的盖的东西贸然出手,他做的可都是大生意。也怪母亲为他和条儿结婚缝制用的褥子被子土气不说,还太薄了。条儿在他心中是既漂亮又圣洁,一想到结婚后条儿脱了衣服就像剥了壳的花生一样,容不得碰着垫着,他心里就堵得慌。为了条儿,他决心最后一次出手。他破天荒地下午到县城踩了几处点,这家是他选定最好下手的地方,从正面看,两排平房对称均匀地摆出了一条不长的巷子,每一家都是独门独院。这家在巷子里最后的一排,后面没有其他建筑物,应该是空地,一旦被发现还容易脱身。
天冷得更加厉害,两个砖头像铁一样,冰冷地粘手。他感觉腿有点麻,换了换蹲着的姿势。
四
心中的爱人大多都藏在自家的门背后。
鹞子坚持相信条儿就藏在自家门背后,用不着去梦里寻她千百度。像是自己心灰意冷回到家里把门关上,条儿在自家门背后站着一样,一把把她从门背后拉出来,理所当然就是属于自己的女人了。
没来这个城市之前,他也曾有过几次谈婚论娶的事。但现在想起来,都是执拗不过村里好心人的关心和母亲的着急,礼节性地见见面而已,最终不是他嫌人丑,就是人嫌他穷,很快拉倒了。唯有邻居二旦的表妹曾使他心动过。在他看来,那个姑娘不高不低,身材胖嘟嘟的很匀称,脸蛋就像屁股蛋一样,圆圆的。母亲说,生孩子过光阴能压住福。每次来到二旦家,她总是隔着院墙在二旦家院里大声说话,银铃般笑出声来,有事没事还总爱沿着他家门前的小路晃过来晃过去,两条垂过屁股的长辫子一度时期甩得他心里痒痒。
都怪二旦多事,把表妹在他家门前屁股扭得异常有力和他偶尔看她时的异样揣摩了个清楚。二旦爹就自告奋勇当了个媒人。那个早晨,他执拗不过母亲的哀求催促,二旦爹的连欺带骂,就提了四色礼随二旦爹到二旦舅舅家去相亲。原本想这门亲事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二旦表妹曾亲口对二旦说过,她愿意过来永远做二旦家的邻居。但谁想二旦舅舅是个二百五,张嘴要了五万块彩礼不说,还让他答应把他正在上学的大妹妹换过去给他儿子当媳妇。他被激怒了,别说把他大妹妹换过去,就是五万块钱对他家来说也是无力承接。他知道是二旦舅
舅了解他家的情况,不想答应婚事,故意刁难他。这极大伤害了他的自尊,他发誓这辈子挣不到钱就绝不再丢人现眼相什么亲,让人横挑鼻子竖挑眼。
二旦表妹的事就这样很不愉快地过去了,但在他心里却结了一个想解也解不开的疙瘩。他常想,二旦表妹有什么好,除过脸蛋屁股圆圆的,能不能压住福还需要考究外,脸还有点红,活脱脱的一个红二团。再说遇上一个二百五老丈人,将来还不把人气死。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心里就好受多了。他也常想,自己未来的女人,身段大概和二旦表妹差不多,但皮肤应该更白,眼睛更大,而且乌黑有神。
突然遇到了条儿,他的眼前一亮。他不敢相信,这世上竟然还有从自己想象的模子里托出来一模一样的姑娘。他心里的火又燃了起来。
五
有意思的事经常在不想观看中出现。
小平房里的夫妇不但不睡,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大吵了起来。那男人激动的从炕上跳下来,点了支烟,很生气的在地上来回踱步。女人依旧倒躺在炕上,指手画脚,声嘶力竭。
鹞子又挪了挪身子,选择了个看到小屋里情况的最佳位置。两块砖冰冷得已不能再碰。他隐约听出小房内的男人和女人是在为男人家亲戚过事行礼的事而争吵。他想这下可有意思了。他知道在夜晚这个时候,两口子狂风暴雨之后,一般情况下是难有的晴空和温柔,也是他下手的最佳时间。
他突然间又想到了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女人粉白的身子,更想到了条儿,想到了有一次在那个城市进入一户人家的事。
那是一个阴天的夜晚。他顺着院墙爬进了一户二层楼的人家。这是白天仔细踩过的点。进入院子后,他就听到了楼内姑娘轻微的哭声,他靠近窗户想从窗帘缝隙中看清屋里的情况,但窗帘罩的很严。屋里有男人来回踱步的声音。他听到那个姑娘在说让男人离婚的事,还听到说家里要钱,明天要让一个亲戚带回去。男人很生气,声音粗壮,语言极不文明,姑娘哭的更加伤心。争吵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他一直蹲在楼外窗户下面听着等着,他注意到临近自己身体的是窗户下—个不错的狗窝。
城里的女人就是贱,二奶更贱。就在那姑娘哭闹得异常伤心时,他听见了男人却孩子般温情地哄起了姑娘,声调语气就像楼内换了一个男人,而姑娘把哭声变成了像猫叫,让人肉麻。不一会,猫叫声也没了,屋内传来男人喘着粗气很沉重地上楼脚步声。接着又从二楼窗户里传出姑娘猫头鹰般的怪叫,他差点忍不住将怀里揣的砖顺窗给砸上去。
猫头鹰的怪叫好不容易停了下来。整个小二楼死似地寂静。就在他刚准备动手时,那男人却突然从楼内走了出来,他躲闪不及顺势钻进了狗窝。好在那男人并没有发现他,径直走出了大门,然后他就听到发动汽车的声音。
门竟然没有锁。这让他有些激动,但更让他激动的是,打开灯后屋内茶几上除过有红酒和各种水果零食之外,还放着一叠钱和一个男士小黑包。他并不急于把钱装上,也不急于翻包,他想这些都已经毫无疑问地属于自己了。他悠闲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慢慢倒上红酒,开始品起酒来。他知道,这个时候那男人一定是赶在天亮前回到老婆身边哄老婆去了,而楼上的姑娘死猪一样睡不到中午不起床。
酒喝着,零食水果吃着,钱就在面前放着,他有种异样的满足。他索性顺势躺在沙发上,他想睡一会再走。就在他闭着眼睛迷迷瞪瞪想条儿的时候,他听到了开大门的响声。他急忙爬起身,这时候才发现天已经大亮。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应付,门里已横着进来一个很胖的男人。看到他在屋里,那男人先是一惊,接着用眼角瞟茶几上的钱和包。大概是见钱和包还在,竟客气地问了一句:你来了。他脑子一片空白,只好随声应了一句:来了。那男人又说,我上楼去拿个东西,你先坐。还没等那男人上到二楼,他赶紧拿起钱和包飞也似地跑了出来。
那次收益最好。桌上一万不说,包里装着整整两万。后来他猜想,那男人多半是把他当成帮姑娘带钱回家的亲戚了,要不然还那么客气。
六
金钱在现实中确实比才智更起作用。
鹞子和条儿进展的非常顺利。有了第一次大方出手,第二次去洗头,还没等他坐好,老板娘就叫条儿过来了。他注意到,这次条儿给他洗头也多少有些不自在。她一边用力地在他头上挠,一边有意无意地从对面镜子里打量着他,乌黑的眼睛飘出了一份悠悠的神情,还多了一份难有的温情,就像二旦表妹偷偷瞄他时一样。
这之后,他就彻底收不住自己心了。他几乎每天都到发廊里去,每次去不用老板娘指,也不用他叫,条儿就主动过来给他洗头。日子久了,他和条儿熟了。他告诉条儿说,他在一家公司当推销员,隔三岔五要回公司一趟去结账。他担心天天去洗头,会引起条儿对他的怀疑。但爱上一个人,心里就想的不行,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还是每天去,好在每次条儿问他,他都能天衣无缝的编出个理由让条儿相信。
有了钱,他觉得条儿的心就牢牢和他粘在了一起。有了钱,他也就有足够的能力把条儿打扮得光彩照人。他经常带着条儿出入商场、饭店、卡厅,最高档的服装他也舍得掏钱去买,最好吃的东西他也舍得花钱去吃,最有档次的卡厅他也有钱能进。钱来得容易,花起来自然也就不心疼。城市生活的气息让他陶醉,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
日子久了,条儿离不开他了,他更不能没有了条儿。他们自然谈到了结婚的事。尽管条儿早就告诉他,自己是因为当粮库主任的大姐夫给他介绍了一位在粮库当会计的对象,她不愿意,才逃婚跑了出来。而且父亲见钱眼开,已经花了人家送来的一万块钱彩礼,他去很可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劝他不要到她家里去,先结婚把生米做成熟饭再说。但他还是坚持要去,他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他想把事情做到前面。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和条儿从那个城市出发,经过两天的路途颠簸,终于来到条儿背靠黄土崖,怀抱黄土山的家。迎接他们的果真是条儿母亲粉白脸上横着堆起来的一撮子沟壑和条儿父亲白羊肚毛巾下竖着翘起来的一把山羊胡。第二天,条儿当粮库主任的姐夫和那个会计就来了。他们用敌意的眼光看着他,让他恶心。他知道,在农村诸如此类人都是典型的能不够,凭着几个不多的臭工资,好像啥都知道,对啥又都一知半解,往往却最爱煽风点火。条儿她姐夫还装模做样的显出了满腹经纶,竟文绉绉地骂条儿是猪头昏,不知道坐着洋房子让养上享清福,鬼迷心窍地要跟着去太阳紫外线非常强的鬼地方活受罪,就不怕几天把白皮脸晒红晒黑脱了皮。他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突然顶上了一句,狗屁的话,狗的那个东西常年装在套子里,没见太阳光,却红地像个大辣子。条儿他姐夫噤了声,脸上的酱红肉一棱一棱的鼓涌起来。他没有注意到条儿他姐夫本来就是个大红脸。他们差点打了起来。
对立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好在条儿寻死觅活的护着他,为了条儿,他也豁了出去,他什么都没怕。他重重地将五万块彩礼钱甩到了桌面上,他要那
个会计也拿出来和他争一争。
七
最精彩的表演通常是在复杂的情节之后。
鹞子此时倒不觉得怎么冷了。他顺手拉了拉羽绒服上的拉链,那是条儿送给他的,一想到条儿,他心里就暖和多了。
小平房里男人和女人终于停止了争吵。像他判断的一样,那男人在小屋里丑态百出,一会儿跳上炕去,一会儿跳下炕来,不一会儿就站在地上将身上扒了个精光,然后站在炕沿边双手抓着女人的两条裤腿往下拽裤子。
他觉得更有意思了。这最后一次,莫非真的遇到了活神仙。小平房里男人脱女人裤子的表演实在让他惊讶,他不由又想起了回家前在那个城市的一次遭遇。
那夜他原本没有想着做,他是赶着去会条儿的。他要和条儿商量回家结婚。究竟咋办才好,当然他心中还有下定决心吃了白馒头的想法。条儿在他心中是圣洁的,圣洁得他至今连碰都不敢碰一下。有时候他甚至怨恨自己,反正条儿就是自己的人了,想干啥就干啥是顺理成章的事,结婚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做给人看罢了。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想过,也不止一次被这种想法折磨得心里难受。但一见条儿的面,一看见条儿粉白漂亮的脸,他自己都奇怪怎么就不敢了。他想,像条儿这样粉白的馒头,不经过洗手等一系列程序,就不应该随便动手给吃了。
那晚他是经过充分思想准备的。他有了说服自己的理由:白面馍馍谁不想赶紧吃?反正也只是迟早几天的事了。但就在他下定决心去会条儿的路上,一辆高级轿车擦着他的身子过去,停在了他前面的人行道上,目标奇迹般出现在了眼前。借着路灯的光,他发现从车上下来的男人屁股后面鼓得厉害,这让他眼馋,他由不得停了下来。不一会,他注意到临街三楼的一扇窗户灯亮了,窗户下的一楼二楼窗户都安着防盗栏,而且亮灯的窗户是开着的,紧挨窗户的还有一排枝大叶茂的树木,他着实想走也就走不动了。
一切奇妙地如同事先安排好的一样。那男人的裤子就像是他的,只是错穿了一会儿。他爬上三楼的窗户,没用下窗台进入房间就发现那条裤子放在紧挨窗台的床头柜上。他换了换手,将粉红色的纱窗用左手轻轻移开,用右手去拿裤子。就在他准备把裤子拉过来时,一条白色的小狗却突然狂咬着扑了过来,惊得他差点背身从楼上掉了下去。他挪了挪蹲着的姿势,蹲稳当。小狗是城市人的玩物,好玩不管用,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不止一次遇见过,可以不理。他用力想把裤子拽来退下楼去,小狗不可怕,但紧挨床头柜的大床上还睡着两个大活人,条儿还等着呢。裤子却拽不动,他抬头这才发现床上的一对男女不知什么时候已死死拽住了另一条裤腿。他知道,这个时候手是绝对不能松的,你退他进,何况自己还蹲在窗台上,根本就没有退路。相持之下他用尽了浑身的力气,想一把把裤子拽过来,始料不及的是裤子被一撕两半,他失去重心从三楼窗台上翻了下来。好在紧挨楼房的树枝让他化险为夷,只是胳膊被划出了血,感觉有点痛。他顾不得太多,爬起来拿着拽来的半条裤子拔腿就跑,却不想情急之下被一同拽下来的纱窗绊了个狗吃屎,下巴被磕破了一条口子。
那晚条儿那里没去成,他至今还在后悔。但收益颇丰,仅拽来半条裤子后袋里就装着一万五。
八
长久笼住女人的心首先要给她一个不错的窝。
鹞子从条儿家回到这座城市后,条儿对他更好了。然而,他心里却拧了个块,始终觉得就像是二旦舅舅羞辱了他一样,条儿他姐夫和那会计羞辱了他,而且这次羞辱得更重,想放都放不下。他骗条儿说他得回公司去把工资领了,把帐结了,请一段时间假好准备结婚的事。
他背着条儿,又来到条儿的家乡。他很快打听到了条儿她姐夫和那个会计所在的乡下粮库。经过仔细踩点,在一个夜晚他摸进了粮库院里,把主任室和会计室翻了个遍,能撬的全部都给撬了,钱尽管对他来说不多,只有三千多块,但足以让他出口恶气。出门之前,他还没忘了在两扇半开的门上给放上两块砖,让他们晚上回去自己推门砸自己。走出粮库院子,另一栋房子里的麻将打得正响。
他开始为他和条儿结婚的事而忙碌。他带着条儿到处去看房子,他要先租用一套像样的住房把条儿安顿下来。有了条儿在她家里寻死觅活护他的经历,他更爱条儿了。他可不愿意再让条儿两个白馒头手再在别人头上挠来挠去,让别人舒服,他要把她养起来,他要她的皮肤更白,他还要让条儿当主任的姐夫睁大眼睛看看啥叫洋房子。他要把条儿领回家体面地把婚结了,让可怜的母亲乐一乐,让庄里人瞧一瞧,当然更要让二旦他舅舅看一看,让他脸红和后悔。然后,他就领着条儿到城里来,洗手开始做正经生意,和条儿好好过光阴,生孩子,永远做一个城里人。
条儿对租房住的事却并不赞同。她劝他要租就租一间门面房,既能住又能做生意。她想用在发廊学到的技术开一间发廊,索性当老板,雇几个人干。她可不愿意一辈子坐着享清福,让他没日没夜的去为公司拼命跑推销。
条儿感动了他。在一条还算繁华的街上,他很快租了两套门面房。他告诉条儿,一间用来开发廊,还有一问上下楼,楼上他们结了婚住,楼下他自己开个泡馍馆。他决定辞掉推销员,守着条儿,和条儿并肩干。
原本是要和条儿一起回家的,但发廊设备还需一天才能装完。眼看给母亲说的要回去结婚的日子只剩下三天,他干脆先一天回家准备结婚的事,让条儿隔一天再来。他担心母亲把啥事准备的不好,让别人笑话,让条儿寒心。这不,铺的盖的就出了问题。
九
倒霉的事总是瞬间和人撞个满怀。
小平房里的男人光着黑不溜秋的身子总算上炕了,女人却提着裤子下炕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院子里的花园边尿起尿来。
鹞子既好笑又生气。他真想把这个没脸的女人两砖给砸了,一走了之。要知道,在平常碰到女人尿尿放屁的事本来就不吉利,何况干他们这行如果真的碰到更讲晦气。但他瞬间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心中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报复计划。他感觉到自己的肚子也有点胀。
女人总算回到屋里熄灯上炕去了。小平房里很快就传出了女人的鼾声。他知道下手的最佳时机到了,猫一样轻巧的从房顶跳到了院墙上,又从院墙蹦到了院子里。大房门上安着防盗门,他掏出钢丝等撬锁专用的小家当,他早从一位同伴那学到了一手开门撬锁的好手艺,一般的防盗锁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他有些意外惊喜。这最后一次,小平房里的夫妇不仅为他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他遭遇过的一些精彩片段,竟然还把钥匙插在门上,好像知道他要来,专门欢迎他。屋里有些黑,他摸出微型手电找到床的位置,像是到了自家屋里一样,舒服地一个仰背躺在了上面。他用手捏了捏身下的毛毯床罩,手感非常好,软软的,很绵。他想这么好的东西真应该和条儿那胖嘟嘟的身段和粉白的肤色相匹配,让那个大黑屁股女人用着确实有些糟蹋。他又想到了条儿,这个时候她大概正在夜班车上睡觉呢,抑或是也正在想他。他估摸大约再有三个小时条儿就到
了,时间刚好,约好去车站接条儿的车五点半才到他家门口,从这栋房子到他家也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回去后还有时间把床铺好。等接到了条儿,就让她先绵绵的、软软的舒服睡上一觉,然后再到县城找家理发店化妆打扮。
小平房里传来像把牛宰了一样的呼噜声,他听出是那女人的。他心里又来气了,还有女人打呼噜这么地动山摇的,真苦了那瘦猴男人。他起身把灯开开,毛毯果真不错,枣红的底色上面印着一朵金黄的大花,非常喜庆。床罩更不错,颜色和条儿粉白的皮肤有些相近,紫罗兰小花一朵连着一朵,若隐若现,就像条儿看他时的眼神。他干净利落地把床单扯下来铺在地上,把床上所有铺的盖的统统裹在里面,用劲扎了个包。
十
生活总是给憨厚老实的人开出不幸的支票。
鹞子根子上确是一位憨厚朴实的农民。如果不是他父亲意外撒手走了的话,他也许现在快要大学毕业了。从小到大,他聪明伶俐,懂事可爱,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尖子生,尽管高一只上了一学期,但各门学科在全年级三个班中名列前茅。他不会忘记父亲为了供养他姊妹四个上学去打松籽,从悬崖上掉下来的那悲惨一幕。没了父亲,就像房子没了大梁,一切都塌了下来。为了能够继续供养三个妹妹上学,他毅然弃学回家和体弱的母亲共同撑起了将要倒下来的家。
他强忍着失去父亲的悲痛,每天早出晚归,把家里已退耕还林的地又整了一遍,搞成了林草间作。他求爷爷告奶奶,总算从信用社贷了两千元,买了两头小牛犊让母亲喂着,他自己到县城一家建筑工地干活挣钱。他聪明,有文化,很快就学会了砌墙,绑钢筋,支模板等技术活。眼看着几个妹妹大了,学习也还不错,家里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算过的去。
要不是母亲经常催的话,他才不会急着去相亲。他心中有一个让妹妹们上大学的梦,他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二旦表妹的出现多少有点改变了他的生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本是平常事,再说一家女百家问,事情不成仁义在,这也没什么丢人的。但谁想自己的热脸却贴了个冷屁股不说,还受了羞辱。二旦他舅舅做出的事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想,自己的智商并不比别人低。为了争一口气,他决心离开家乡,只身来到这个城市打工挣钱。他要活出个样子来让别人看看!
城市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陌生的比小时候电影里看到的更加繁华与噪杂,这让他眼花缭乱。他先找了一家卖糊辣汤的饭馆打零工扎住了脚。月工资六百元虽说少了点,但管吃管住,干的好每月还有奖金。他想通过自己的诚实与吃苦多挣些钱,他拼命地为饭馆干活。然而,饭馆老板并没有因为他的踏实与勤快而开恩,因为干活时不小心撞倒打碎了一摞碗,月末奖金没挣上,工资还被扣掉了二百。他觉得老板太不近人情,找着去评理,被扣的钱不仅没要上,还差点挨了揍。他一气之下走人,索性不在饭馆干了。
他凭着在建筑工地学到的手艺,很快在一家工地找到了活。说好的是按小时计工,他算了算,只要自己肯吃苦,每月吃过最少还能落个两千多元。于是,他不分白天黑夜,别人不干的活他都干,为多挣些钱,他经常加班加点。但谁想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包工头在发工资前却卷着钱跑了,自己的血汗钱一分没拿到。
无奈之下,他又租了一辆三轮车,跑起了搬运东西和运送小货物的活,他有的是力气。可命运似乎是有意和他过不去,他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城管逮住罚款,还老遭受货主和城里人的白眼。一次去给一户搬了新房的城里人送东西,主人说的只有五公里路,但走了却不止十公里,中途说好到了多加五元钱的运费,但到了地方主人却耍起赖来,不仅不给总共才十五块钱的运费,还掏出一叠钱说他要抢,一帮城里年轻人围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将他狠狠打了一顿,他算是受够了城里人的欺负。
十一
侥幸往往会滋生出意想不到的危险。
小平房里的呼噜声依旧如雷。鹞子背着包慢悠悠地来到了大门前,就在他要开开大门出去的时候,一辆车突然停在了巷子口,灯光直直的把巷子照了个通亮,巷子口的夜空还有一闪一闪的红光,不时把黑沉沉的夜色划出光环,他还听到有人说往里面走着看看。他急忙将大门在里面反锁住,用力把包甩上小平房,然后迅速顺墙爬到小平房屋顶,一脚把包从房顶后面踢了下去。他有足够应付一切复杂情况的心理素质,他并没有急着跑,冷静地蹲在小平房顶上,开始观察巷子里突然出现的情况。夜色黑沉凝重,就像他把床上的东西用床单裹了个严实的包一样,周围浓浓的夜色把他和这户人家的房子紧紧裹在了里面。巷子里四个穿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人排着队,正顺着车的灯光向巷子这头走来。巷子口停着一辆警车,警灯一眨一闪的。
他下意识地趴在了小平房顶上,习惯性用手去摸身边。他心里一惊,竟然把顺手拣来的两块砖忘了没有揣上,丢在了大平房顶上。这让他感到心里没底,这最后一次咋就丢三落四的。这个时候手里拿着砖,不论对于脱身,还是给自己长精神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巷子里进来的四个人离他趴的小平房越来越近,他急忙爬起来转身,猫着腰从小平房屋顶后面跳了下去。这最后一次了,可不能过了大西洋太平洋,在小阴沟里把船翻了。
十二
命运就像一个手摇的轱辘用力向上松手下滑。
在饭馆干活的那段时间里,鹞子意外碰到了同村几个没上学早年就外出打工的伙伴。他们每天上午准时来吃糊辣汤,说是下了夜班来吃早点,个个西装革履,牛哄哄地,一副城里人的派头。还上班呢,他笑了。他其实早知道他们在干啥,他曾从心里鄙夷他们,他始终告诫自己离他们远点。但经常受欺负,特别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人打了一顿后,他实在是冤气难出。他想城里凭什么就随便罚人款,凭什么就任意扣人工资,凭什么就卷着别人的血汗钱轻松跑了,又凭什么随便打人?难道农村人进城来真的就这么贱!他窝着一肚子委屈找到了他们。
他当时心里想着只是让同伴们替他报复一下那个拿着钱显阔,给他栽赃,让他挨打的主儿。他牢牢地记着那个地方。但就在同伴们轻易得手之后,他感觉自从进城以来心里拧成的一个硬硬的东西不见了,一下子通了气。他想,十五块钱不给,拿来他一万五,这活做得漂亮,痛快!在这之后,他竟不知不觉地和同伴们一起干了。
起初他只是干踩点、放哨、接应的活。
放哨接应的活他没用学就比其他人干得好。他有点文化,脑子自然就活,他机灵,点子自然就多。其实这些活比踩点要容易多了,也很安全,关键是要多个心眼,善于观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伴们在踩好的点出动以后,他每次都特别警惕附近周围的动静,有警车来,就要赶快发出事先定好的信号,以防同伴在楼上受到上下夹击,被逮个正着。当然对一些老年人也要特别注意,他们往往爱多管闲事,还有不怕死的精神,让他们发现,还真不好对付。接应主要是动作要快,反应要活,楼上有东西撂
下来,要接得住,跑得脱。同伴一旦被发现,还要能及时地打好掩护,帮助逃脱。
刚开始和同伴们干的时候,他也常常会在踩完点接应同伴们得手之后,莫名其妙地自责起来。他想,这样干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但一想到被人欺负,被人整,他很快就心安理得了。他宽慰自己,城里人被整是自找的,睡觉时就不知道把窗户关上,有时候连门都不锁。好好的一幢楼房窗户为什么有的人家非要安上防盗栏,自家安全多了,而让别人家又多了危险。他也常想,城里人是活该被整,不要看个个有眉有脸,心里却乌七八糟,互相攀比,不服人,势利眼,狡诈,还爱装大气爱显阔,有钱没钱裤兜里总爱装个钱包,不装钱包也要在裤袋里装上一叠钱。也难怪只要出动顺手拽来一条裤子,十有八九就收获不错。
和同伴们一块干了不久,不知是嫉妒他,还是嫌他老干着轻松安全的活,他就感觉同伴们对他有些不满。分钱时,给他分的明显少了。有时在楼下接到钱包,他的确没有看里面到底有多少,但他们总怀疑里面少了点,言下之意就是他抽走了些。他可受不了这样的气,他离开同伴们的活动区域,在这个城市的另一处租了套单元楼住下来,自己单干了。没想到第一次单独出道虽有惊险,但得手成功,这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十三
平淡的故事最终都是无言的结局。
人生的路走错不得,跨出危险的第一步,想收有时候都来不及。鹞子跨步从小平房顶上往下跳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不对劲。他想收住已跨出去的一只脚,将身体所有的重心放到还没离开房顶上的另一只脚,后倒在房顶上。但已迈向空里的那只脚的裤腿就像被谁拽了一把,一下子将他整个身体带向了空中。他慌乱地举起了双手,试图抓住什么,但两手很轻,什么也抓不着。这上去一下子就到了屋顶的高度,跳下去却没有了底。他惊恐地从内心深处喊了一句我的条儿呀!然后就没了知觉。
这座小县城紧倚着一条宽阔的河道。由于千百年来河水的冲刷,河堤已高出河道许多。尽管往日波澜的河水已接近干涸,但小县城的人们却习惯于把正房面河修建,依河而居,紧靠河道的许多人家为了院子里宽敞些,都将小房墙背沿河堤而起。那户人家的小平房后墙恰好就是顺着河堤砌上来的,房后面足足有二十多米高,这是鹞子踩点时没有搞清楚的。
他还不知道,晚上来到巷子口的警车和巷子里进来的四个人并不是冲着他来的。那年,县里新上任了一位政法委书记,他积极探索推行县城、乡镇、农村、警务四道防线,其广泛开展巡逻的综治经验,在全国综治会上被交流推广。一时间,全县从农村到县城,广泛开展传牌巡逻,警民互动,单位联动,构建起了一个立体防范网络。晚上进入巷子的是从各单位抽调履行夜间巡逻的联防队员,其实他们还并没有发现他。
天蒙蒙亮的时候,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三九天的早晨不仅冷得能把砖冻破,冰冷的气息还让人觉得冻在身上,冷在心上。
这个时候,从那个城市发往这个小县城的夜班车准点到达。车站里人头攒动,一位肤色粉白,眼睛乌黑有神的姑娘在不停地东张西望,红色的羊绒大衣,洁白的貂皮围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显得格外耀眼。
薄薄的霜将小县城映衬得清晰可见,三九天的清晨显得异常肃穆静寂。一辆警车正呼啸着向河道方向驶去,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责任编辑: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