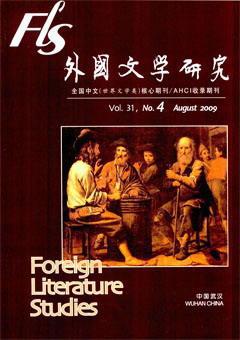生活的意义:爵士乐队精神
徐方赋
内容提要:伊格尔顿《生活的意义》从列举古今对生活意义问题的种种质疑和解答入手,通过分析“意义”和“生活”所含玄机,揭示了“内在论”和“构建论”的本质和历史渊源,提出了生活的意义在于爵士乐队精神的理想。
关键词:伊格尔顿《生活的意义》内在论构建论爵士乐队
200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特里·伊格尔顿的《生活的意义》作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一种哲学反思,纵古论今、旁征博引,气势恢宏、语言诙谐,一经发表便引起热烈反响。英国作家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指出,伊格尔顿以其傲视历史的勇气和睿智犀利的笔触,铿锵有力地回答了生活意义的问题。该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Questions and An-swers”从探讨生活意义问题的性质人手,回顾了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质疑和解答。“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不同于“象牙是什么颜色”等关于具体事物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语言的问题。语言表达基于一定的结构,许多看似相同的结构,其含义却可能大相径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挖掘这种差异、揭开其中的谜团、揭示语言的涵义,德里达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解构”。关于具体事物或语言结构的问题同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有的可能有答案但无法找到,而有的根本就没有答案。越是如此越容易引发各种解答。
在古希伯来人看来,生活意义的问题如同是否相信上帝的问题一样,让人愕然。对他们来说,耶和华及其训诫即生活的意义。而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几乎所有传统价值观念和机构都遭到怀疑,“生活意义”的问题日渐凸现,并出现了西方文化、乃至全人类的命运等最具探索性的问题。现代人们没有完全扼杀和抛弃上帝,只是将其换成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新名词,如自然、人类、理性、历史、权力、欲望等等,后现代主义将所有这些都归为“文化”。20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存在主义和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后结构、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不再探讨人文主义和人类生活等基本问题,而是聚焦于文化差异、地方特色等具体问题。传统认为至关重要的人类生活的共同表征,如宗教、文化和性爱遭到边缘化、碎片化,由公共生活维度蜕变为个人生活维度,并趋于产业化和商业化,探索生活的意义成了有利可图的产业,一些对当代金钱崇拜的社会不满的男男女女纷纷转而著书立说,为人们释疑解惑,提出关于生命意义问题的种种解答,从中大赚其钱。由此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传统信念的丧失导致生活意义问题的凸现,生活意义问题的凸现招致众说纷纭的解答;而这些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的解答莫衷一是、令人眼花缭乱,反而削弱了其本身的可信度。
第二章“The Problem of Meaning”从意义的三类涵义人手,探讨“meaning”一词所含的玄机:1、主观意欲(What do you mean?)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2、客观所指(What does the wordmean?),即特定语言结构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定指向;3、前两类含义的综合(somethingsomeone intends to signify),即主观意愿希望通过客观载体所表达的功能。这种区分表明“生活没有意义(meaningless)”是一个认识论命题,而不是逻辑命题。比如莎翁笔下的麦克白抱怨人生短暂和空虚,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认识论涵义,人类生活只是一场空虚的戏剧,也许饱含意义,但都带有欺骗性;二是语义涵义,所谓生活没有意义,就如同说了一通空话。严格地说,这两层含义互不相通。
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其著作中创造了一台名叫“沉思”(Deep Thought)的计算机,用于计算宇宙的终极含义,“沉思”花750万年算出答案为42。这等于将生活意义的问题数学化、逻辑化,将其归为某个事物,如权力、情欲、吉尼斯、巧克力等等,因而是荒谬和滑稽的。那么生活的“意义”是否属于第三层涵义呢?除非你信仰上帝,否则就不是,也没必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多为无神论者,但都认为人类生活乃具有某种意义的模式,其背后不一定有超人的力量。乔治·艾略特等现实主义作家不信教,却更注重发掘生活本身的逻辑。而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则认为,生活本身并无意义可言,因而无从挖掘,而是由个人赋予的。
认为世界或由上帝赋予意义、或者完全没有规律的观点是一种伪无神论。生活本身可能具有某种意义模式,但这种意义并非来自于某人的意愿;同样,我们可以认为,生活本身没有意义、混沌一片,但有某种力量使然。叔本华就认为,整个世界(不只是人类生活)是“意志(Will)”的产物和工具。“意志”通过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不断诱使我们相信生活饱含意义,以维系自身之繁育。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衣钵,认为真理往往令人生畏,人类拥有艺术即因害怕死于真理。弗洛伊德将叔本华的“意志”改称为“欲望(Desire)”,认为没有幻想和欲望便没有生活。这一观点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用“意识形态(ideol-ogy)”取代了虚假意识。
在叔本华看来,了解生命的真谛后,却发现它十分可怕,会使人陷入困境,因而只有傻瓜才会思考生命意义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叔本华的许多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历史上匮乏、痛苦和剥削的元素确实多于文明和启蒙的元素。
第三章“The Eclipse of Meaning”以剖析“内在论”和“构建论”为脉络,考察生活意义丧失的历史渊源和影响。契诃夫等现代主义作家的怀旧情结令其对于生活意义的丧失感到愤懑。而后现代主义认为,幻想世界具有某种内在意义的人一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即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要获得自由,必须抛弃幻想。
贝克特作为介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作家,通过《等待戈多》指出,生活有一定意义,但不存在“终极意义”;生活不一定有某种稳定意义,但并非没有意义。事物本身有其意义,无需个人“构建”;各种意义相综合,即可构成整体意义。这种“内在”意义表现为各种真理性的人类行为和一种社会默契,是个人和现实交互的产物。如诗歌,既有本身蕴含之义,也有读者诠释之意。所以探索生活的有效意义,必须尊重社会的本质和结构,这便构成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基础,从而区别于“构建论”。“构建论”认为生活的意义由个人添加。这种看似激进的观念实际上同西方的意识形态心照不宣:即个人为了自身目的而设计的意义最为重要。
“内在论”和“构建论”之争可追溯到中世纪晚期。争论过程中“内在论”逐渐让位于“构建论”,原因在于内在论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事物本身具有其内在意义的观点有碍上帝发挥其绝对权力;而生活本身没有意义的说法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当今世界充满了解读的自由,牧师们不再在解读生活意义的王国中独领风骚,善男信女们亦无需理会上帝赋予世界的各种意义。圣经中关于“所有物理元素都象征了某种精神”的训诫让位于世俗解读。由于现实世界本身没有任何预设意义,人们即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欲望进行解读。施莱艾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解释学(hermeneutics)由此应运而生。
伊格尔顿认为,关于个人可以决定自身生活意义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个人生活离不开他人、离不开社会,因而他人对生活的诠释势必影响到自身对生活的选择。任何有意义的人生规划,如果离开血缘、社会、性爱、死亡、娱乐、哀伤、欢乐、疾病、劳作、交往等等元素,必定行之不远。
第四章“Is Life What You Make It?”从分析“生活(life)”的玄机人手,提出生活的意义在于爵士乐队精神的命题。首先,究竟是否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人类生活(human life)”的现象能够承载某种统一的意义?有人认为无法对人类生活进行抽象概括,因为要抽象就必须走出这个圈子。尼采曾言,我们无法判断生活本身是否有价值,因为判断标准来自生活本身。而伊格尔顿认为,正如批评英国社会无须跑到新西兰一样,对人类生活进行抽象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人类属于同一个自然物种,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威胁自身生存的各种挑战。
如言生活的意义在于追求人类的共同目标,则这个目标便是追求幸福(happiness)或称福祉(well-being)。但对幸福的理解各有不同。伊格尔顿集中介绍了亚里斯多德的幸福观:1、幸福即践行美德,而美德具有社会性,因而幸福乃一种生活方式,即有德之人可从行善而不是作恶中得到快乐;2、幸福是个人能力的自我实现过程:残疾人较难获得幸福乃因其发挥个人能力的途径经常受阻;3、个人“幸福感”受制于“虚假意识”:身为奴隶的人,你可以告诉他身为奴隶很幸福,而其行为却表明他并不幸福。综上,个人幸福感要求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自由发挥其创造力。除此而外,其他许多元素均可成为生活的意义:权力、财富、爱心、荣誉、真理、快乐、自由、理性、自主、国家、上帝、内省、克己、欲望、死亡、功名、自我牺牲、遵从自然、开怀大笑、为最多数的人谋取最大幸福、同伴的尊重、获取尽可能多的体验等等。而对于多数人来说,生活的意义还在于同亲人(伴侣和子女)关系融洽。
在很多人看来,以上各种元素作为生活的意义有些过于琐碎、过于工具化,如权力只是一种资源,而财富只是生活的手段。弗洛伊德开始将“欲望”、后来将“死亡”作为生活的意义,认为了解自己必将一死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的缺陷,从而有助于勇敢地、真实地生活。这听起来有些沉重,实际上却是人们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心理基础,传统上称之为“爱心”。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认为,生活的意义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非形而上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不但离不开生活,而且是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不一定非得在诸多关于美好生活的元素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所有元素可以共融。如同爵士乐队,它同交响乐队的明显区别在于其成员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意愿,而每个队员的随意演奏进而成为其他队员随意演奏的基础,从而达到一种复杂的和谐效果。每一个乐手都在“整体美(the greater good of thewhole)”中发挥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无需自我牺牲、而源于乐手的自由表达。这里有自我实现,但这种自我实现以自我融人整体为前提;这里有自我成就,但这种成就感不会引发自大狂。相反,这种成就——音乐本身——成为乐手之间和谐关系的载体。如果人人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即可将人性发挥至最佳。
伊格尔顿最后指出,将爵士乐队精神扩大为生活的意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关于生活意义的争论仍将持续、且会富有成效。人们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难有共识,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危险,如果一味争论而无法找到共同的意义,则种种争论与其说催人奋进、不如说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