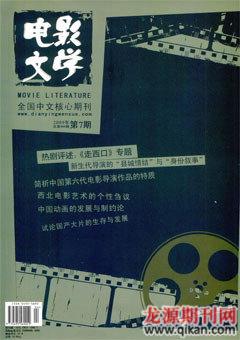新生代导演的“县城情绾”与“身份叙事”
邴 波
[摘要]出于自觉的艺术选择与“县城”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地位,有一些“新生代”导演开始让“县城”在影片中发挥重要的叙事功能,这实际上是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及焦虑的投射,是“新生代”导演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叙事策略。
[关键词]“新生代”导演。县城情结,身份叙事
当第五代导演迷恋于主题严肃、风格阳刚、节奏跌宕、画面壮丽、色彩缤纷的大制作,越来越注重视觉奇观与消费语境时,有一批“新生代”导演表现出与前辈完全不同的审美旨趣。他们在小制作的压力下把电影的视觉背景从城市转向了乡村,从历史拉回到现实城市边缘青年漂泊和游走之地,以平民的视角、纪实的手法、粗糙的影像向人们讲述着现实的无奈。其中,尤其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县城”作为叙事背景开始在银幕上显示出它的强大魅力,尽管在中国电影史上,以“县城”为空间来演绎人情世故的电影有许多,如费穆的《小城之春》、谢铁骊的《早春二月》、凌子风的《边城》和谢晋的Ⅸ芙蓉镇》,但如此大面积地出现且真正让“县城”在影片中发挥叙事功能的应该是新生代的重要发现,典型影片包括: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任逍遥》和《三峡好人》,章明的《巫山云雨》和《秘语拾柒小时》,王小帅的《二弟》和《青红》,顾长卫的《孔雀》和《立春》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新生代导演发现的“县城”对传统影像有“补白”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新生代”导演从事电影创作时基本上都生活在大都市北京,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就地取材,而是选择“县城”作为电影生涯的起点,这里面有经费紧张的考虑,因为“不同环境产生不同成品。第二世界美学意识,在开头,往往是为了克服器材和技术上的困难,想尽办法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达方式。……你可以把不利的环境转为自己所用,创制出属于这个环境才会有的形式风格”。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这种选择是“新生代”导演自觉的艺术选择。“新生代”起于一种自觉的反对,反对“第五代”过分的形式主义。由于他们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及其对世界的感觉与“第五代”大不一样,在“第五代”的“宏大叙事”和“寓言化模式”成强弩之末的时候,他们便集体转向了与主流文化不一样的边缘性立场和视角,所以他们的影片中没有“中心话语权”,有的只是对所体验的世界还原,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的关注,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度关怀和理解,体现了电影的人文本质和艺术营养,也包括对中国电影美学的开拓。而这种关注才是真正意义的终极关怀。贾樟柯在回答拍摄《小武》的动机时这样说道:“在接近四年的学习过程里,我们每个星期会看到两部新的国产电影。这几年看下来,我看不到一部电影跟当下有真正的关系,看不到一部电影跟当代中国人的情感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电影能够跟县城、跟处于城乡交界的那样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所以我感觉这种生活是被遮蔽掉的,是银幕上缺失的东西”。章明在谈及他以故乡巫山县为背景的影片《巫山云雨》的动机时也说:“现在电影有很多空白没有人填补。很常规的、很普遍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最能代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的人,他们希望什么?在寻找什么?他们想干什么?想象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中国就是由这样一批人构成的。这样的关注就是对中国整个命运的关注”,而“从各个角度来讲有代表性的普通人正是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小城镇。”由此看来,这其中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由于“新生代”导演审美视角的迁移所带来的场景变化。
其次,这种选择是由县城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县城在地理位置上背靠着乡村,紧依着都市,注定了它与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县城一般是介于城市与农村居民点之间的过渡型居民点……大多数处于大中城市和农村的交错地区,与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从县城的发展历史来看,县城应该是乡村的经济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演变而来的,它是连接众多乡村的结点,因此在文化品格和精神内核上或多或少带有乡土的特色。但也与乡村存在着差异,一方面它是乡村面向都市的窗口,另一方面又是周围村落的商业中心。与乡村相比,县城与都市在工业、商业等很多方面的密切联系,使县城又具有了与都市相通的开放现代的一面……尤其在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还很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程度相比差距很大,所以这种从乡村到都市过渡的县城,也还是大量地存在着——它们既没有大都市的繁华热闹,也没有乡村时期的贫瘠,而是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县城是乡村和都市的联系纽带,是乡村和都市的过渡空间,是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带,更是秉承了乡村与都市的双重特点。尤为重要的是县城在中国社会地理上的双重附着性,赋予了它文化身份中的特殊性,从而成为乡村与都市之间的一块极富弹性的文化中间带,不仅传统与现代、昨天与今天、先进与落后、边缘与中心在这里融会和碰撞,而且还见证了各种历史演绎和文化变迁,见证了社会转型期乡土中国和都市中国在这里的抵牾、冲突和融合……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县城在文化的价值选择上具有双重逆向性:一方面,它是都市文化的受益者,接受着都市文化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洗礼。另一方面与传统文明的血脉相连,使得它在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又较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文明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个性人格。因而,生活于此的人也就具有矛盾又协调的背反特征:乡土性与现代性对立同一——这恰恰是转型期中国人最典型的心态特征。
贾樟柯所构建的“县城”作品体系就矗立在这样一个“中间带”上,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发生激烈变化的中国内陆县城所独有的地域面貌与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且带有强烈的共性特征。影片中的山西汾阳县城以独特的城乡接合部文化形态成为全中国任何此类处所的一种缩影,狭窄的街道、游走的小贩、高音喇叭的扩放、喜欢看热闹的人群、无处不在的录像厅……影像上模糊粗糙的“灰色”,已成为其因背负沉重历史枷锁而无法迈出豪迈步伐的隐喻。重要的是,汾阳县城在影片中不仅仅成为“小武们”的中转站、故事发生的地点,它俨然就是影片的主角——生活在县城中的人们背负着和县城一样的遭遇,尽管努力尝试着突围,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和回归。“小武们”的身份、“小武们”的流浪青春因为回归冗长乏味的生活而最终变得格外尴尬,“小武们”经历的数次失落:友情的失落,亲情的失落,爱情的失落,最终也都成为一种对“县城”的隐喻——县城在拥抱现代性冲击的同时,同样也在忍受着失去一些东西的痛苦,譬如传统的伦理关系、人际格局和道德体系。所以。毋宁说,“小武们”就是县城的化身,县城的悲欢离合与“小武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县城滞重的阴影见证了县城青年落寞、无奈和孤寂的成长体验。我们说不清是人衬托了县城还是县城衬托了人。
比较而言,王小帅与顾长卫的作品更像是对贾樟柯
“县城情结”的一种延续。《青红》就是一个关于“围城”的寓言,作为逃离对象的县城在老吴等父辈眼中简直就是罪恶的表征,它欺骗了他们的青春,制造了他们的屈辱,最终也残酷地埋葬了青红和小根的爱情。他们试图“出城”的努力,也最终化为泡影。尽管影片结尾,老吴一家人终于回上海了,但上海也未必就是幸福生活的目的地。顾长卫的“县城”与贾樟柯的“县城”有异曲同工之处,《立春》中的年轻人与“县城”角色处在同样的尴尬位置上,生活在县城中的“王彩玲们”梦想跳出“生活在别处”的幻觉,却始终无法抗拒体制带来的束缚,最终,对北京的想象演化为一场白日梦——黄四宝放弃7关于北京的所有冲动,毅然南下深圳,王彩玲不再渴望谎言置换带来的短暂快乐,以收养孤儿的母爱放逐了艺术。这样的叙事策略实际上就是县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形象化表述:作为边缘尽管从不放弃对中心的强烈渴望,但他们注定是首先要被忽略和牺牲的。
之所以县城会被“新生代”导演重视,正是由它在中国整个转型期中所凸显的文化典型性所决定的,同时,这样一个含混的、介于文化中间带的地域身份适时地与“新生代”导演的叙事身份互为表征,暗合了这些“县城造梦者”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县城”进而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焦虑投射。
何谓“身份”?身份(identity)是指社会个体的社群归属和文化角色。“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身份提供了一种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已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身份确定了个体对自我的定位,也确立了个体和社会文化语境关系的自我想象图景,它为个体解决了“我是谁”的社群归属和文化角色。但事实上,这种身份意识的和谐和稳定是非常不可靠的,它随时面临着内在平衡的被打破。就像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就是说,所谓稳定的身份意识只能是封闭语境下的产物,一旦作为参照物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发生变化,个体就会面临“身份”统一性和稳定性的断裂和破碎,陷入无所适从的“身份危机”(an identity crisis)之中,产生身份的焦虑。
“无论是在自己的导演生涯。还是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贾樟柯们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浓重的‘红小兵情结。从政治身份上看,他们既不像‘红卫兵,是当代文革政治意识的创造者,同时又是这种意识的反叛者,也从来没有负载过多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无论是政治神话的‘建构还是‘解构,抑或意识形态的皈依与反叛,都与他们无缘。他们没有壮烈的历史可以反思,没有极端的现实可供批判,供他们成功的机遇少之又少,因而只是生活在红卫兵的阴影下无法命名的一代。”这段话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新生代导演的经历和命运的准确描述。他们曾经经历过“文革”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只是旁观者而已,并非真正的参与者。当他们开始电影创作时,整个社会文化和电影体制、语境又发生了变化,他们迅速失去了可资依傍的文化身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代人一直是时代的疏离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带有农村文明的小城市与大都市北京的文明碰撞中一出场就不得不接受历史给予的“边缘人”身份。贾樟柯、章明、王小帅甚至顾长卫都是如此。正像王小帅在谈到《扁担·姑娘》这一外来工题材的选择时所说的:“这种状态跟我自己比较接近,我在哪个城市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亲戚朋友也没有多少,老有一种外来人的心态。”
这种身份焦虑在贾樟柯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贾樟柯自述他拍摄《小武》的动机时谈道:一方面是汾阳现代化的改造景象刺激了他,关键是他自认为在汾阳找到了“当下”和“在场”的感觉。这种感觉似乎和他在北京找不到“归属感”是一致的,但仔细体会,他恰恰反映了贾樟柯对自身的身份焦虑——我们如何指认1997年的贾樟柯的身份?
文化人类学的“主位与客位”理论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主位(emic)与客位(etic)”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提出的。“主位”指用该社会的本土观念理解对象社会的行为或思想的做法,是从文化负荷者、传承者的立场和视角去解释某种文化现象,代表着族内人(insider)的世界观;“客位”指用局外人眼光理解这些行为或者思想的做法,从外来者、旁观者的角度对某种文化做出评价或解释,代表族外人(outsider)的世界观。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贾樟柯,我们发现一方面他是地地道道的“县城人”(边缘人),因为多年以来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所谓“县城人”的身份,没有离开脚下那片属于他自己的土地而去拥抱“外面的世界”,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是“主位”,由此决定了他身份叙事的对象大多是游离于社会边缘的或社会底层、缺少职业或文化归属感的人群,换言之是缺少身份认同的“边缘人”。正是由于缺少“身份”,他们才需要不断地获取某种身份认同,表现于具体的叙事策略,便是“寻找”——寻找人物的社会身份定位,寻找人物身上被忽略的社会价值,寻找“县城人”身上的人性光辉,而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所以,离开了县城的贾樟柯,在此刻找回了“县城人”的感觉,恢复了“县城人”的身份,他与他的县城兄弟小武共同开始经历和体验着县城的变化·但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贾樟柯在许多场合表述过他和大都市的间离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拍摄《小武》时的贾樟柯,是离开家乡并获得一些成功之后,以一个成功者的身份回到家乡拍摄电影的,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又是“客位”,体现于站在导演立场上使用从电影语言中得来的不同范畴和规则来对拍摄客体做出阐释。所以。《小武》虽然看起来像是纪录片,其实都是想象的产物,是完全虚构的作品。它既不动声色地呈现出了小城的“原生态”,也表达了作者对某种秩序的反抗和蔑视。毕竟,贾樟柯通过他的镜头展现出的是“他”的记忆,呈现的是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特的记忆。它包含着贾樟柯确证自我身份的努力——以“边缘人”获取话语权的精英意识和精英的“世界观”,表明了作者身份叙事的动机和意义。
当然,文化人类学认为,主位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主观的。客位的看法也不见得是客观的。族内人易陷入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跳不出地域表层的束缚,未必能真正地把握文化本质,这时就需要族外人引进新的思维方法,站在客位的立场上去解释他们所看到的文化,两种视角的相互转换才能更接近事实。而“主位与客位”的身份在此时的贾樟柯身上已全然成为一体,所以,一方面是手拿摄影机的“县城人”,另一方面是掌握了电影话语权的贾樟柯,这个既是insider又是outsider的暧昧身份其实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县城”在社会转型期的中间地位,由此也决定了《小武》的独特性。或许也正是这样一种间离的审美态度,最终决定了贾樟柯的成功。
“县城情结”与“身份叙事”的相互指认源于“新生代”导演在社会中暧昧不明而又不断边缘化身份的深刻体会,这使得他们一直处于这种谋求身份认同的尴尬处境中,自然而然在创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身份意识输入其创作过程。所以,“新生代”导演的“县城情结”影片实际上成为他们确立被社会认可的“真正的自我”(县城人)和“真正的我们”(导演)的混合叙事,是“新生代”电影导演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如何由边缘走向中心?即在没有话语权、没有代言者,甚至没有相对清晰的文化形象状况下,如何不停止对生命的本质思考,如何在困境中创造奇迹,在绝望时成功突围。正像张颐武在评论贾樟柯的电影时曾写道的:“贾樟柯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经验,一种中国内地小城镇的文化经验,一种混合了压抑和梦想,混合了发展的冲动和失落的恐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