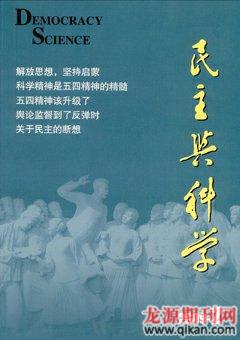关于民主的断想
梁晓声
一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必修课。正如世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独裁是独裁者们的日日操,专制是专制者们的“养生功”。
但是倘一个国家挺富庶,足以养民于无虞,则独裁就不需要太铁腕,专制也就显得不怎么黑暗。在那一种情况下,独裁是可以独得比较漂亮的,连皇上和国王都愿意表现自己是明君。
唐玄宗李隆基坐天下时,宰相叫韩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休,对自己唯一的“顶头上司”也每有冲撞和冒犯,多半是由于皇帝做了什么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故玄宗若欲放纵一遭,每问左右韩休知否?皇帝何以惧宰相呢?盖因韩休治国有方略,很负责任,使李隆基免操不少心。也有人暗中撺掇李隆基将韩休罢了或干脆杀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啊。唐玄宗却说出一番话——罢休杀休,反掌之事。但他替我将天下处理得如此太平,我怎么能轻率地除了他呢?
杀之随时可杀,这便是独裁肯定专制的规律;不杀是看在有用的份上,这便是所谓“明君”的真相。
后来韩休识趣,主动辞职了,怕李隆基迟早会找碴儿杀他,终日声色犬马,力图给皇帝一种再也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使其放心。按西方民主的内涵来说,他成了个没有“免受恐惧”的权力的人。
故,说千道万——不理想的民主制度,那也显然比似乎很理想的独裁制度理想一点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事实上,民主当然也是全人类社会的生命。
而另一个事实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并非必修课,只不过是选修课。专政才是必修课,曰“人民民主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就很尴尬。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逐渐重视起民主来。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政治课,民主在中国,由选修而必修,上升到“国课”的高度了。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看西方某些国家的民主,仍觉得像是“戏”,像是“秀”。我们中国人是崇尚庄重的,什么事有“戏”的成分了,有“秀”之嫌了,往往质疑其意义,认为比之于“戏”,比之于“秀”,干脆将某些事仪式化倒还严肃些。
这是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西方的竞选吧,五年一次,从第四年起,便紧锣密鼓,风声鹤唳,你方唱罢我登台,可不像“戏”,可不像“秀”嘛。
且慢取笑。那像“戏”、像“秀”的竞选,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像”,在人家,那是面向全民的公开答辩。
然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年复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年后,公民们对于政治那也必然会心生冷漠的。这叫“民主冷感症”。
一个民主国家一生出这种病,全民在精神上往往会“睡过去”。
竞选也罢,议会里的争吵也罢,政治人物们的互相批评、指责乃至攻击也罢,其实也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能动性的体现。为的是证明给人民看——我们
充满活力。也为的是暗示人民——别不关心啊,我们的国家可是“公民社会”,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你们都有责任参与。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代表你们进行,为你们进行。
民主国家全靠了五年一次的竞选,对民众的“公民神经”进行必要的刺激。全民的公民思想意识,才不至于在“民主后”漫长的无动感年代麻木了。
“五四”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被视为“东亚睡狮”?
叫我们“狮”,乃因我们人口最多。
叫我们“睡狮”,乃因我们真的是长睡不醒。
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地球西侧正是国国争相实现民主、社会变革天翻地覆之世纪。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自己却大睁双眼睽瞪国家,唯恐哪儿有人没“睡实”,或假睡。谁如果大声说:“中国怎能这样!”他们便砍谁的头。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么一种情况,谭嗣同才宁肯用自己的血惊醒中国人。可他被砍头时溅出的那点儿血,又哪够惊醒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
加上秋瑾的血,加上许多想要惊醒中国人的人的血,也只不过使少而又少的中国人醒了过来。
而使更多中国人醒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坚船大炮……
故我对于什么“康乾盛世”之说,是很讶然的。
比照一下历史看看,不正是在那么一种所谓“盛世”前后,西方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吗?
人家猛醒了,我们还睡眼惺忪的,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处在“盛世”里,这样的些个人,似乎至今还没完全睡醒……
人家在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的时候就从王权的摇篮曲中彻底醒了,并且最不愿看到的,便是“公民”又在民主的摇篮曲中“睡过去”了。
“睡过去了”,民主也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生命”了。
我们比人家醒得晚,晚很多。
故我们看人家,有时看不大懂。
民主也是使一个国家不在精神上“睡过去”的一种方法。
他们深谙此点。
我们则应多一份虚心,虚心地看,虚心地想。即使并不打算照搬,那也还是要虚心。
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人民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政治冷感心理?
这是一个有必要思考的问题……
二
民主曾是一种主义。
故当初热爱民主的人,被称作民主主义者。
肯为民主奔走呼号之人,被视为民主人士。
那些为民主而不畏强权、不屈于迫害的人,谓民主斗士。这样的人,在1949年以前,在中国,真是不少,几乎个个是大大的爱国者。
为民主而被砍头,而被枪杀的,自然是民主烈士。
如李公朴,如闻一多……
胡适起初也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自从他当了北大校长,便一心一意只做学问家了。然有许多资料可以证明,他至死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只不过他后来
成了一个沉默的民主主义者,做学问是他对民主失语后自认为唯一可做的正经事。幸而他仍有一番学问可做,否则今人不会对他敬意依然。
他的弟子傅斯年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蒋介石对他可算厚爱有加,然而他抨击起国民党高层的腐败来毫不留情,口诛之,笔伐之,更是在国民参政会上历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种种贪赃劣迹,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设宴劝导他说:“你既然信任我,便应信任我所用之人。”他却说:“因为信任你似乎就该理所当然地信任你所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承认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
他是信任并尊敬蒋的,然跟蒋说话并不“您、您”的,他是个平等意识很强的人。真的民主主义者,大抵如此。他与他的老师胡适的不同在于,官照做,民主之声照发,并不沉默。所以他人虽已亡,在今日之台湾,口碑却仍良好。
胡适一心一意做学问后,有一句当年流传很广的话是——“少谈些主义,多思考些问题”。此话也有另一种版本,即“少谈主义,多做学问”。
多思考些问题也罢,多做学问也罢——都是为了劝好友和别人少谈些主义,包括他自己骨子里也始终信奉的民主主义。
胡适何以会变得如此,非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事。
以我的眼看来,以我的耳听来,今日之中国,似乎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当年的胡适,所恪守的也都差不多是胡适那一种主张,但应改为“少谈民主,多做学问”。民主是少谈了,做出的学问并不多,还时有学问丑闻。
并且,都不如胡适般磊落和坦白。
因为胡适既那么主张,毕竟公开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今人却是不说,不写;闷在心里,闷成圆圆滑滑的一定之规。
但私下里,民主又是多么热衷的一个话题啊!
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呢?
夜深人静,每自问,愧作难当,潸然……
我辈如此暧昧,在狷性上比傅斯年、比梁漱溟不知矮小多少;在学问上,恐怕也是再难出一个胡适的吧?因为即使做学问,活得自然些的人,那也肯定是比活得不自然的人做得好的。
诸种国是,掰开了,揉碎了,说来道去,弊端不往往与“民主”二字关系密切吗?
总书记在作每次国是报告时,不是也一再地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吗?
熬过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将面对一扇怎样的势必要推开而入的门?
它除了是民主之门,还会是一扇别的什么门吗?
这将是国是中的国是,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却为什么“大是稀声”呢?
故,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责任、有使命为中国公开谈谈民主的人,只要其谈得理性、真诚,并非哗众取宠,我都是心存敬意的。哪怕,我不完全甚至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民主思维……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