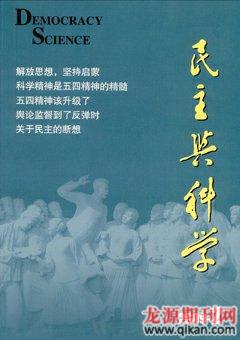谈我们对民主的错误认识
魏行进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在于民主制度建设。有道是“治民先治官,治国先治吏”,世界各国政治实践表明,要治好官吏,根本之道在于实行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指出,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是一个“人民民主”,即“权力公有制”的社会。《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经济公有制”,也要消灭政治权力私有制和意识形态私有制,从而全面搞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今天,我们对民主的一些错误认识阻碍了我们的民主建设和“政治公有制”建设,因此,要搞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中共中央提出的“民主执政”的理念,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民主。
一、对民主含义的错误认识
其一,有人常常把“开明”当成民主,这是错误的。
民主的实质是民作主、民决定,它由一系列的制度构成,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民主是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而只有“民选”才能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以“民选”是民主的根本。光有民选的制度还不是充分的民主制度,但没有民选的制度肯定不是民主制度。
一个领导者、决定者,在决定之前让下级和人民多说话并发表意见,这叫开明,不叫民主,因为最终的决定权不是在民而是在官,不是“民作主”而是“官作主”,这只能叫“官主”而非叫“民主”。
如果把开明的“官主”当成“民主”,那么中国封建专制的开明皇帝唐太宗比现代的许多人还“民主”,但唐朝是民主制度吗?!
当然,政治的开明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民主本身,开明之后由谁决定、决策、立法呢?这才是民主与否的关键。
其二,有人常常把分散、散漫、“无政府主义”看成是民主的表现,认为讲民主就不可能有统一、集中、高效的行政效率,这也是对民主十足的无知。
“民主集中制”这句话很容易让一知半解的人认为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其实,民主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集中是相对于分散而言的。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一样都既有集中也有分散。
从某种角度而言,民主就是最大程度的集中,因为民主政治是集中最大多数人民意志行事的政治;专制政治才是最不集中的政治,因为专制政治根本没有真正集中过人民的意志。
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现象,但它们不是民主的本质属性,而恰恰是反民主的,是无法无天的行为,是民主社会法治不健全的表现。可见,“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不属于民主好坏的范畴,而属于法治好坏的范畴。
二、对民主性质的错误认识
有人认为民主是有阶级烙印的,这种认识是十分荒谬和有害的。
温家宝总理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30年前,我们在经济上把市场经济、股份制等均看成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认为它们姓“资”不姓“社”。今天我们认为它们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只要它们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对提高国力有利、对人民生活有利,社会主义就可以实行。同样,在政治上,我们对世界各国具体的政治制度的认识也应当以邓小平提倡的这“三个有利于”为准则。
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人民主权”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政治原则,而“人民主权”就体现在“民选”上,没有民选就没有人民主权。恩格斯早在1891年的《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就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首先,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在这里,恩格斯为未来社会主义政治体确立了两个最根本的制度,一是普选制,二是任期制和弹劾制。很可惜,后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均没有实行这两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苏联和东欧的早期社会主义实践中,“民选制”变成了“官选制”,“任期制”变成了“变相的终身制”,政治的腐败和无能就成为必然。这最终导致了苏东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灾难。
三、对民主地位的错误认识
有人认为,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建设决定民主建设,因此,我们的建设始终应当以“经济建设为首”,而不应当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重点”,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决定政治,这是从本源和“应然”的角度而言的,从“实然”的角度而言,意识也反决定物质,政治也反决定经济。在早期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垄断一切,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这种权力上层建筑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
今天,我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民主法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的、关键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良好与公平的经济结构是基础,诚信与平等的思想体系是保证,优美与良性的生态系统是条件,科学与民主的权力制度是关键。建立和谐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权力民主化的问题,一个社会正如不可能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经济和谐一样,也不可能通过“计划政治”和“计划思想”来实现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和谐。
社会大系统的正常的良性的运行,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这些子系统之间保持相对的均衡与协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民主民选的“政治权力公有制”,那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就必然会存在着矛盾。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犯罪问题、经济无序问题、道德价值扭曲问题、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的存在,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领域政治权力构建的缺失,与经济、文化等系统不协调,导致社会大系统结构失衡,从而产生不和谐。
因此,中国有没有可能最终建立起和谐社会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是看能不能在发展起来的良好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起一个科学、民主的政治上层建筑。
可见,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地位是一样的,两者都是一个国家建设的头等大事,绝不可偏废。
四、对民主条件的错误认识
有人常把我国生产力落后、国民民主素质低下当作不应实行民主的借口,这是错误和有害的。
古今中外,在民主实践中,均有人以此来攻击民主的实行。早在二百二十多年前的美国民主初创时期,保守派就以人民缺乏文化、素质低下为借口极力反对民主派的民主改革,美国民主的奠基人杰裴逊总统大声指出:“我认为除了人民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是社会终极权力的保管者,而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还不足以用健全的判断力行使他们的控制权的话,补救之道不在于从他们手中夺走这个控制权,而在于靠教育来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在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人民反对袁世凯实行帝制,袁世凯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民智未开,民权怎么建立?我想当皇帝,还不是为了救中国吗?”袁世凯看似是多么认识中国国情和民主的条件,但这种思想是正确的吗?!
民主意识、民主素质、民主的经济基础对民主的实践一方面有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民主条件也只有在民主实践中才能得到发育、成长和发展。离开民主的条件,民主很难实践,同样,离开民主的实践,也就不会有民主建设的理论和丰硕的果实。只看见事物之间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事物之间的能动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就以黄豆为选票来民选领导人,难道现在的中国经济和人的素质还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吗?!认识国情与民情固然重要,但认识国情与民情只能作为变革的依据而不能作为不变革的借口。我国许多乡村已进行了村民直选的实践,我们必须坚持探索并不断总结经验。
五、对民主内容的错误认识
有人把“议行合一制”等当成民主,也有人把“两党制”、“三权分立”等当成民主,这显然是把民主的手段当成了民主的内容和目的,是不正确的。
民主的内容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之中。民主的本质和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一国里,人民怎样来达到自我作主呢?在一个国家,公意的表达是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政府来实行的,民选是民主的根本,民选越少民主就越少,民选越彻底民主就越真实。
“权力源决定权力责”,即权力的来源决定权力的责任指向。政府官员的权力是人民选举授予的,它就会首先对下级和人民服务,“为民作主”,如果它的权力是上级任命和授予的,它就会首先对上级负责,“为官作主”。要想做到“权为民所谋”,必先做到“权为民所授”。因此,民主选举是民主的根本内容,而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法制等仅仅是民主的手段或条件。
民主的手段和条件可以多样,但本质和目的只有一个。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三权分立也好,五权分立也好,一权之下再分也好,这都是形式,它们的好坏需要实践的检验和修正。难道多党制就一定能保证人民自己作主吗?!难道一党制就不可以进行民主选举吗?!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今天,一切忧国忧民的中国人必须牢记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人民民主”的宗旨,在追求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要批判各种错误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探索前进。
(作者单位:浙江省象山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