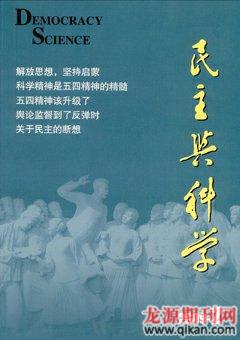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传统
蔡朝阳
傅国涌先生这本《大商人》,以事实的描述为主,着眼于那些带有历史体温的细节,读者可以从多重角度去读,每一个角度都可能找到你想寻找的东西。美国小说家辛格曾说,观点会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过时。《大商人》里面呈现的事实,为我们勾画了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两代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群像,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他们之所以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非传统商人的那种质的变化,这些事实密集的聚合在这本书中,叫人肃然起敬而又有恍然隔世之感。这种企业家精神,原来我们也曾有过!同时这些事实也突出的呈现了他们创业的艰难,作为在一个专制国度里生长出来的民营企业,他们一直游走在权力垄断和民间社会的狭窄中间地带,在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社会启蒙,甚至缺乏现代契约意识的条件下,他们游走在权力的狭缝里,像摇摇欲坠的走钢丝者。或许你可以说他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这只因为你对他们的处境缺少同情之了解。个中辛酸,岂足为外人道哉?
在张謇的实业之路上,官方权力扮演着复杂的两面角色。试与盛宣怀相比,张謇和盛宣怀已经是两类商人了。盛宣怀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其办实业仅是一种进身之阶,意在官场,而张謇办实业便是其目的本身,用实业带动地方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甚至达到地方自治。这是张謇的伟大之处,这个人是读古书的,从旧体制中走出来,最终能有宪政民主之思想,并对中国的政治进步有重大影响,即便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便无法绕过。所以,盛宣怀这样的官僚企业经营者,虽然也对中国的工商业发生过正面的影响,但其影响仅仅是客观上的,是一种副产品。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应该是从张謇这代人开始的。
但这里的所谓“私营企业”,也不是说,张謇办实业就跟官方一点关系也没有。当时,从制度的准备到社会的成熟,都还不构成私营企业普遍的自由成长的基础,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权力结构还是大一统的金字塔。事实上张謇办实业本来就有张之洞建议的因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促发力。当然张謇自身认知原因更重要,他开始筹办企业时,已经43岁了。但他多年来目睹官场的腐败,深知依靠老官僚,这个政府无法获得新的生长点,而兴办实业倒有可能是一条兴邦之道。
张謇的企业,一开始便跟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不是清廷一些政策性的鼓励经商办实业的措施,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实质性瓜葛。张之洞委任张謇为“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个头衔会给他一定的方便。刘坤一更是在1897年直接过问张謇办实业事宜,盛宣怀也是筹办时的股东之一。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官方背景在张謇开办大生之初给他的帮助。当然,最后盛宣怀的承诺未曾兑现,张謇筹款仍是十分艰苦,这是后话。但毕竟,张謇的大生公司启动了,翁同龢为之题字:机杼之发动乎天地。从此,通海一带旧貌换新颜,一个崭新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南通,逐渐酝酿成长。
大生公司后来盛极而衰,原因很复杂。傅国涌先生引用当时人概括大生失败的原因为“二无二差”,曰:无计划,无制度;舆论差,团结差。这些诚然是重要原因,比如其中的制度。对于一个近代化的企业来说,必须有一种近代化的制度来作为保障,企业制度和整个社会制度都有互相生发之作用,大生公司在这个方面做不到位,这是先行者的悲剧,我们无法责人太过。时至如今,江浙一带的家族企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与是否建立这个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摆脱家长制,也有深刻之关联。
同时,傅国涌先生还发现,晚清到民初,高度集中垂直向下的官方权力对企业的干涉,也给大生公司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因为官僚集团也是投资方,他们需要获得收益。即便在公司资金最为困难的时候,张謇也不会拖欠官方的利息,甚至不惜抽调股本,因而造成企业本身的运转不灵。大生一向获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约定为8厘,这是那个时代企业的通病,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也是如此。但这恰是现代企业的一个要害。弗里德曼曾言,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而现代企业需要的正是政治上对公民自由的保障。从张謇对官股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侧面看出,官方的一举一动,会对这个所谓的民营公司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张謇死于1926年,即此粗完一生事,我觉得他未必不带有遗憾。
对荣氏家族来说,垄断权力对于他们的染指和侵害,毋宁说是一场噩梦。荣氏家族本来是开钱庄的,他们建立带有近代化特征的企业集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荣家兄弟,是将生命的全部,托付在了企业之上,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荣氏家族的黄金时期,出现在晚清到北洋政府这一时间段。其全盛时代,荣德生说,衣食上,我拥有半个中国。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国际大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中国民族企业获得了第一个飞速成长的黄金时代。其次则在于荣氏家族的经营有方,他们步步为营,不断扩张,从面粉到纺织,都成为当时著名的品牌。再次,此时政府为弱势政府,尚无暇控制民营企业。
但树大招风,荣家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官方。1927年,国民党势力到达长江流域,摊派“二五”库券,要上海的华商纱厂认购50万元,荣宗敬时为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不愿接受摊派,结果是蒋介石恼怒,密令无锡县政府查封荣氏在无锡的产业,并严令缉拿荣宗敬。经多方斡旋,华商纱厂如数认购库券,才得以解围。这是对荣氏家族的一个沉重打击。到1936年,由于纱贱花贵的日子绵延不止,荣家再次进入困境之中。而宋子文则趁机想吞并荣氏集团。他对荣宗敬说,申新这么困难,你就不要管了。原来宋子文一年前就密谋,要吞并申新,改组成有限公司,而由官方资本来控股。由于银行家陈光甫和李芸侯的坚决反对,宋子文的意图才没有达成,荣家逃过一劫。
最蹊跷的是1946年荣德生被绑架事件,索要百万美金的赎人款,后经讨价还价,降至50万美金。此案扑朔迷离,从种种蛛丝马迹看来,后面有军警特的介入,是一起官匪勾结的敲诈案件。经此一案,荣德生骨瘦如柴,加之获得释放后各地军政要员索款借款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穷于应付,荣德生如惊弓之鸟。而这仍不是荣家最惨重的损失,1947年,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荣家的巨大家产一夜之间贬值。荣德生愤然写到:课税横征猛于虎。
这一类面对政府垄断权力的逼迫无能为力的事件,几乎在每一个商人实业家身上发生过。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曾遭军阀绑架勒索。刘鸿生的火柴厂一直被宋子文觊觎,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让宋子文得逞。后来宋子文又想吞并他的华东煤矿,亏得刘鸿生聪明,懂得利用宋子文与孔家的矛盾,才幸免于被吞并的命运。穆藕初稍微好一点,大概因为他有很长时间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原因。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学史笔记》中引用霍布斯的丛林学说解释民初经济政治状况,认为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若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那么它就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可惜“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两难的途径过程中,逐渐滑向具有一个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的失效,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而掌权的军阀,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身上还保留了专制制度的遗毒,他们普遍相信国家机会主义,相信权力和武力。即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也是无可奈何,他们在这个博弈中,最终输多赢少。
而最有寓言性质的是卢作孚,他白手起家,于1925年在家乡药王庙筹办民生公司,起初连一艘小轮船都买不起,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成亚洲最负声望的轮船运输公司之一,创造了中国轮船运输史上的奇迹。1938年,他指挥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光是这件事他便可以名留青史,永垂不朽。新中国成立后,他本应对国家有所作为,但是他挺不过政治运动。1952年2月8日,重庆“五反”运动刚开始,卢作孚在临时借住的金城银行家中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59岁。当时的新华社内参用的是“畏罪自杀”这样的词语,而卢死后仅6个多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成为全国第一家公私合营公司,毛泽东曾说:公私合营“要学习民生公司的榜样”。从此,中国私营企业的风流在一个时期内成为绝响。
(傅国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