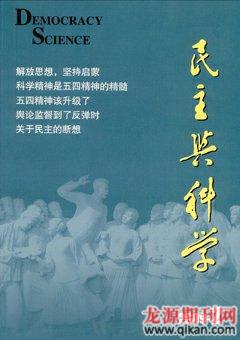建立“第四权力”的一种努力(外一篇)
游宇明
怎样约束不当权力,是优秀知识分子经常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不懈探索,才有了“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才有了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的弘扬,也才有了号称“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
在中国近代史上,媒体与权力博弈的事情并不少见。历文发表在2009年2月17日《扬子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1903年,沙俄拒绝履行中俄两国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肯从东北分期撤兵,并提出新的不合理要求。慈禧不敢抗争,希望与沙俄缔结一项密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在密约即将签订时,供职于某日本报纸的沈荩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了相关内容。他将密约草稿寄给天津《新闻报》提前发表。密约内容被揭露后,舆论一片哗然,密约自然订不成了。慈禧狗急跳墙,下令抓捕坏了她“好事”的沈荩,并密令有关官吏杖杀他。沈荩被害后,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大公报》则连续发表七篇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追踪,舆论批判的焦点是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行刑的行为和对言论犯罪的重刑判决。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一书谈到杨绛父亲杨荫杭先生一件旧事。杨荫杭先生早年分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法律,有非常强烈的法治情结。民国初,他担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时,依法传唤犯罪嫌疑人,搜查证据。然而,许世英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物,他曾担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等职,上级官员为他说情的不知有多少人。许世英被拘传那天,杨家的电话整整响了一夜。司法总长张耀曾在杨荫杭准备查处许世英时就出面干预过,要求其停止侦查,杨荫杭没有理睬。张耀曾恼羞成怒,在杨荫杭传唤许世英的第二天就停止了杨荫杭的职务。尔后,司法部又呈文给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由,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杨荫杭无辜受处分的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申报》更是活跃,1917年5月25日、26日,它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新闻时,将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和杨荫杭的申辩书全文同时刊出,使“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杨绛语)。两年后,杨荫杭被迫离开司法部,他辞职南下那天,来火车站为其送行的人山人海。
相对于居住分散,时间、精力和财力都非常有限的公众个人,媒体具有更强的获取事实真相的能力。假若媒体能够秉承新闻良知,不被金钱、权力等外在力量绑架,它就有可能成为每一个公民延伸的眼睛和耳朵。而当公众明白了事实真相,自然也就知道了谁对谁错,懂得自己应该在某一事件中采取什么立场。专制权力害怕媒体,害怕的就是媒体可能把它千遮百掩的真相披露出来,使其谎言大白于天下。
时常有人说起“公民社会”这个词,我这个人知识贫乏,不知公民社会应该如何定义,但凭我粗浅的理解,真正的公民社会应该让媒体有充分的披露真相的权力。因为媒体的力量太弱,权力就可能胡作非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就难以得到保证,社会自然就难得变成“公民”的了。晚清和民国初年当然不是公民社会,但可以看出那些先进的新闻知识分子梦想建立公民社会的一种努力。
报刊的操守
一个社会永远需要两种规则,一是外在的规则,一是内在的规则,法律制度是外在的规则,道德操守则是内在的规则。操守不仅仅对个人而言,作为舆论代表的报刊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人的操守表现在一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态度,报刊的操守则体现于它如何面对权力的威压和金钱的诱惑。
徐百柯《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给我们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国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本叫做《良友》的大型综合性画报家喻户晓,即使在最偏远的云南省也不乏它的热心读者,手头拮据的读者寄来头发编成的表链,希望可作为订阅的费用,信里说,如果这不行,他将改寄火腿或大头菜(都是云南著名土产)。《良友》还发行到了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是当时“国内唯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出版物”,《良友》对这一点也颇自豪,它曾在画报上印有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良友》的销地,并在地图上写着“良友遍天下”。著名作家李辉认为,《良友》不仅有新闻的敏感性,而且有文化的丰富性,“它尝试过努力过的许多创意,在我看来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良友》的影响这样大,想在上面登广告的企业自然如过江之鲫,然而,这本杂志做广告却非常慎重,看起来不可靠的广告不登,涉及色情、性病的不登。
当年的《生活周刊》也有这种面对不该得的金钱岿然不动的操守。《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11日,1926年起由邹韬奋任主编,徐伯昕负责刊物的经营。由于刊物内容轻松生动简洁雅致,发行量达到15万份,广告一天比一天多。这在战乱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据知情者回忆:徐伯昕对所刊广告限制极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
办刊物总是想赚钱的,赚不到钱,刊物就开不了编辑、记者工资,买不到必要的设备,编辑好的稿子也进不了印刷厂。然而,刊物的利益有两种,一是短期的,一是长期的。一个报刊毫无顾忌地做广告,可以在短期内获取大量资金,却可能因为引起读者反感,导致发行量下降,损害长期利益。《良友》、《生活周刊》坚持不做不良广告,自然有对自己长远利益的考量。
《良友》、《生活周刊》不乱登广告,坚守刊物的品位,更与主事者的文化眼光有关。刊物永远是由人来操作的,刊物的操守,说到底就是在这本刊物说话算数的那几个人的操守。在《良友》和《生活周刊》的主事者看来,自己的刊物登载广告,等于向读者推荐某种商品,刊物对读者负有一份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何况,任何刊物都要向读者传达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输出,既表现在刊物发表的文字中,也表现在刊物的其他行为里。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刊物才有可能真正深入人心。
于是又想起时下流行的一个词:名报刊。在有些人看来,名报刊就是有人写文章捧场,政府评奖的时候有一席之地,其实,真正的名报刊永远是靠自己创造的,它必须有操守有品位有足够的发行量。而操守又是报刊的重点之重。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