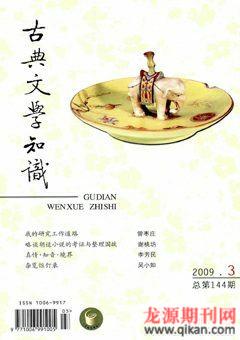真情.知音.境界
李芳民
《学林清话》是傅璇琮先生为学界友人的学术著作所作序文的辑集,共收录了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去年(也即2008年)初二十多年间所作的序文73篇。书序这种文体,不仅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特点,即使在当代,它仍然显示着很强的生命力。不过,就这种文体本身特点而言,它先天地也潜藏着某种可能滑向世俗乃至庸俗的危险因子。因此,序文之好坏优劣与是否有价值,实际上也最能考验出执笔为文者的品德与功力,套用古人的话说,它实际上也是一种“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曾巩《寄欧阳舍人书》)的文体。在《清话》的“自序”中,作者曾明确说到他为人作序,一是抒“淡如水”的友情,二是叙“切于学”的旨趣。
友情是人类最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之一,但友情也是有着层次上的差异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先哲的箴言,也是作者为文作序时“抒友情”的基调。不过作者写“淡如水”之交谊,并不意味着感情的淡薄,相反,在“抒友情”时,他总是灌注着一种诚挚笃厚的真情。可以说书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有这种诚笃真情的体现,但如果具体点,我觉得在叙及与吴汝煜先生的交谊时,文中的诚笃之情尤使我感动。作者在给孙映逵的《唐才子传校注》、吴在庆的《杜牧论稿》、胡可先的《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等书的序文中,曾多次提及他与吴汝煜先生相交相知的过程以及吴先生的人品学问,收在本书中写给吴先生著作的序文,即有两篇,即《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及《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序》。在这两篇序文中,作者对两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以及学术贡献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不幸的是,昊天不仁,吴先生过早地去赴了天帝的玉楼之诏。在给《全唐诗人名考》作序时,吴先生已因病住院,序文的末尾,作者引述了陶渊明《答庞参军》“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欢心孔洽,栋宇为邻”的诗句,然后深情地回顾了他们1984年在厦门的一段学术交往情谊:“我们时常面对远方的水天一色,畅叙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共同的爱好与志趣。但他在徐州,我在北京,除了几次参加学术会议,很少见面,比起陶诗所说的‘栋宇为邻来,相差实远。但书信是不断的,他给我的信总是那么谦逊、周详。现在他积劳成疾,以后要编写著作恐怕是很困难了,什么时候我又能为汝煜同志的新著作我所能作的一篇小序呢?默诵‘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我实已难以为言。”我想读到这样的文字,无论是谁,都会为作者这种诚笃真情所打动。
作为给同道学人学术著作的序文,切磋学问是作者极用心力之处,这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切于学”的旨趣。在好几篇序中,作者都曾引到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一段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确实,序文中对著者作品的价值、意义做出精到的揭示,客观公正地指出其欠缺与不足,不仅是作序者的学术良知的体现,同时对凡是真正热爱学术的著者以及读者来说,也都会因此而获得一种高山流水般的欣悦。作者为序时,确实是以一种严谨认真、从不苟且的态度来着笔的。他不止一次说过,他有一个习惯,“为友人作序,虽然不过一二千、二三千字,但总要翻阅全书,有时不止看一遍。”正因为如此,作者的序言,往往使人感到准确精辟,没有虚语陈言。在给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的序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话:“我读这本书,以及读《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笔者按,后者是吴的另外两本学术著作),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在给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的序中,作者在概述了尚君先生的学术成果及学术成绩后,又从治学路数与研究风格的角度,概括其治学特点,认为“尚君先生治学,一是勤而博,一是细而精,这两者往往是结合的。就是说,要搞一个专题,总要在这一专题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内,尽可能求全求实,同时在资料搜集考辨的过程中,细心发现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抉隐发微,提出新见”。
另一方面,作者的序文所述,还不仅仅限于著者知音的层面,他常常总是超越著者作品本身,从整个学术界研究的范式、视野、方法等角度,揭示某些著作所具有的开拓、创新意义,并通过推奖与引导,来推动整个学术研究的更新、发展与进步。就本书序文所涉及的范围,其中有三个方面是比较明显而值得特别引起注意的。
一是他对资料搜辑与文献考据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与倡导。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有相当一段时间由于过分强调研究中对规律等的揭示与概括,因而将资料搜辑与文献考证诋为琐屑而极为轻视。作者显然是不赞同这样的观点的,书中有好几篇序都表示了他对此的看法。写于1988年夏的《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中曾明确说:“编制索引和整理资料,是学术事业中的服务性行业,它有着强烈的利他的性质。但是它要服务得好,其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即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研究者。”写于1990年9月的《吴在庆<杜牧论稿>序》中,则针对鄙薄考证的观点作了有力的批驳。而在1997年春给《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序》中,通过对尚君先生考证成果的分析又讲到:“从这里,我倒有一个想法。过去往往对史料考证不够重视,认为考证只不过是限于文献资料本身,无关宏旨。不说别的,仅从上述尚君先生的几篇考证文章,就可看出,资料的考证往往与作家作品的整个思想发展,与某一时期文艺观念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交叉联系。而考证,从治学路数来说,并非只是所谓饾饤之学,实是一种细密、清晰的理性思考,没有对某一学科的整体的把握和考察,没有具备一种综合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工作程序的。”把对资料考证的认识提到这样的一种认识高度,我不知道作者是否为当代学界的第一人,但这样的认识,无疑可说是学界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学人的知音。现在,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富有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与考据成果,我不能说这是具体个人推奖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结果,但作者很早就倡导并坚持奖引这种研究方法,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则是不容否定的。
不要以为作者只是重视文献考据之学,其实,他也一直在倡导资料考据与文艺学的细致分析相结合等富有价值的治学路数。在1991年1月所写的《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序》中,他曾敏锐地指出著者在其著作中体现的两点使人感兴趣的方法,即“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把作者大量搜寻到的材料,用统计、数学、表格列出”,认为“这样做,不仅醒目,更重要的是加强我们作文学研究时的科学观念。”其次是“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限于一些理论著作,而是尝试着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并由此对著者所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和古典文献研究所养成的“在文学的审美研究中加强现代科学思维训练的学术品格”表示赞赏。作于1990年秋冬之际的《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序》中,他对罗先生的文学思想史与士人心态研究所体现的研究思路同样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肯定,这自然都可以看出作者在治学方法上所体现的敏锐眼光与开阔弘通的胸襟。而在我看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7年3月给《日晷丛书》所作序中对中国大陆古典文学学术研究转型期及其研究范式转化的揭示所具有的意义。他说:“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这是20世纪前80年所未曾有过的。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这确实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术研究范型变化的一种非常精确的把握与概括,体现出作者对学术研究态势的一种高屋建瓴的统摄眼光,而且这种立足于学界研究现状的概括与把握,反过来也引导着年青一代学人的选题与研究方向。
二是呼吁对海外研究成果的重视与引入。由于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影响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海外的汉学研究状况与成果是非常隔膜的,因此,在新时期之初,中国大陆的读书界、学术界都非常渴望了解与借鉴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1987年,贾晋华女士翻译了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的《初唐诗》,傅先生应邀作序,在《欧文<初唐诗>中译本序》文中,他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演进的角度,介绍了近现代西方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认识的深化历程以及现当代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状况,指出“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从宏观上对日、美两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做了概括,由此他对欧文先生《初唐诗》的研究特点与成绩也做了精到的点评。同时,从更高、更远的角度,他想到了如何更好地借鉴海外研究成果的问题,指出,“由欧文先生的著作,使我进一步感到,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结构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现状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我相信,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还有不少,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误失,也能促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些误差的原因,加深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也将会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结构起到积极的协调作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已看到了不少海外汉学研究著作的译本,而这些也许正是作者设想与呼吁所带来的结果。到了20世纪之初,作者则与海外学者联合,主持编撰了《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的大书,其中海外部分,对台、港、澳地区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了系统的介绍,从而更全面地促进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
三是对古典文学研究工程中重要课题的提出、规划与设想。作者曾主持、规划并完成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大工程,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人都非常清楚的,无须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的相关序言中作者及时提出或设想的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课题,对作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工程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有些不仅在当时看非常重要,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如此。作于1989年春的《点校本<五代诗话>序》文,作者由清代乾隆年间李调元的《全五代诗》中的一些问题,指出“从理清基本事实来说,五代文学需要做的事情实在不少”,并设想在“从头由理清材料着手,踏踏实实地把五代文学中存在的问题搞清楚”的同时,“选择一些前人已经下过工夫的著述,如李调元的《全五代诗》,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等,作一些必要的整理,加以出版,供研究者参考”。五代文学长期被作为晚唐文学的延续,应该说学术界的重视是不够的。作者这里提出五代文学及其事实清理的问题,确是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课题,而所做的初步的研究设想,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此外,在1986年11月所作的《<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中由黄庭坚研究引出的关于宋代文学及黄庭坚研究的三个问题,2003年5月所作的《<全宋笔记>序》引出的关于笔记研究如何建立科学体系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具体课题设想的建议等,都无不体现出其学术工程建设总体设计规划师敏锐的学术战略眼光。
无论是抒“淡如水”的友情,还是述“切于学”的旨趣,《学林清话》都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即一种由真情与真知相交融而达致的境界。前者是作者品德的体现,后者则是作者作为学者的学识的呈示。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作者作为大学者所具有的宽厚谦逊以及奖掖后进如恐不及的美德。书中序文中所涉及的著作,不可能个个都完美无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者作序时,并没有对一些不足之处作有意的规避,而是本着对作者、对学术负责的精神,以长者的宽厚,采取商榷的态度,向著者提出自己的意见,绝无一点骄人的盛气。至于作者的谦逊之德,更是常常映现于序文之中的,读了《<李白在安陆>序》、《<浙江十大文化名人>序》、《<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序》等文,定会对此有深刻的印象。而作者对于学术上有创见、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所体现的奖掖之勤,则常常又会使人联想到一千多年前北宋文坛一代宗师欧阳修的风采来。这些都是作者在书的《自序》所述的意旨之外而又流漾于文字之中且能够为读者所感受到的文外之意趣。本书是按写作年月的先后排列的,因此,透过书中文字,读者又无疑等于重温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经历的学术观念、思想、方法、范式的演进过程与学术研究视野不断开拓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熔铸进了近三十年学术演变而带有“史的印痕”。若干年后,人们从这本书中,将不仅可以看到作者对学人的友情、作者的学术见识与人格风范,而且藉此也可以追寻近三十年来学术发展的轨迹。
作者将此书命名为《学林清话》,本于陶渊明《与殷晋安别》中之“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的句子。唐宋文人述及交往的文字里,常常出现“清话”一词。每读到这样的字眼,总有一种温馨、亲切而又古雅脱俗的感觉。读了《学林清话》,感到书名真是太恰切了。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