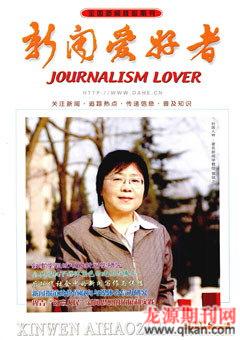解读约翰·斯坦贝克《菊花》的女性主义
宋利存
摘要:本文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20世纪著名的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著名的短篇小说《菊花》,主要分析了小说的女主人公伊莉莎,揭示了她的心路历程,渴望以及梦想的破灭,以此来探索女性的命运以及斯坦贝克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斯坦贝克《菊花》女性主义伊莉莎
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蜚声美国文坛的作家和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声誉主要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联系在一起,而他的短篇小说亦同样出类拔萃。《菊花》被世人称为是“斯坦贝克在艺术上最成功的小说”。《菊花》多被人们从象征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笔者试从女性主义来解读,来探索妇女的命运,挖掘斯坦贝克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菊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斯坦贝克的故乡——南加州的萨利纳斯峡谷。女主人公伊莉莎·艾伦是一位能干的35岁的家庭主妇,她十分擅长种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过着一种平淡如水的生活。但伊莉莎内心充满勇气和渴望,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走出峡谷去领略生活的风光。一天,她碰到一个四处流浪、过着自由生活的补锅匠,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最后,伊莉莎送给补锅匠的菊花被弃之路旁,她的梦想彻底破灭。
小说开篇渲染的环境气氛,标题《菊花》的象征意义以及斯坦贝克着力塑造的伊莉莎的人物形象,都蕴涵着女性主义思想。正是这三方面的共同作用,才推动了伊莉莎心理活动的发展,使其女性身份由被界定到自我发现的完成。
环境的暗示
斯坦贝克把故事的发生地定在萨利纳斯峡谷,然而,他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峡谷旖旎的风光,而是一幅沉闷的备受压抑的画面。“厚重的、灰蒙蒙的法兰绒般的冬雾紧紧笼罩着萨利纳斯峡谷,仿佛要与天空、与外部的整个世界隔绝开一样”,而“这冬雾像扣在山峰上的铁锅,使得整个峡谷看起来像一个紧密扣实的锅盖”。“紧紧笼罩”,“锅盖”,“紧密扣实的铁锅”,以及紧接着的“苍白的冷冷的阳光”、“焦黄的柳树叶子”等意象词无不暗示着伊莉莎生活的地方是多么萧条衰败而毫无生机。它衬托出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者说当时社会的大气候给人的一种压抑,无形中摧残着女性内心的渴望,使她们像伊莉莎一样迷失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她们不得不安于“家庭中的天使”一般的角色。“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女性身上”。这里的“社会”当然是指男权统治下的社会,它将女性身份狭窄地界定在女性个体与父权制家庭之间。很显然,故事开端的伊莉莎就是这样一位被界定的女性。家庭就是她的人生舞台,屋舍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户擦得“光亮夺目”,甚至放在前门台阶上的草垫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由此可见,伊莉莎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家庭主妇,但她又与一般的家庭妇女不同。她生活在这么一个闭塞的环境里,除了家务事和种菊花之外没有其他事可做。因此,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出去透透气。但遗憾的是,她所生活的世界是男人给定的。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哪有属于她或者说整个女人的世界呢?所以,故事的开端所渲染的消极与沉闷意在暗示:女人们深隐于一个被男人包围着的无望的境地,她们想挣扎、摆脱,但那微弱的向往自由的呐喊声终究被湮没在男人的包围中,包括伊莉莎在内的女人的梦想必然会破灭。
菊花的象征意义
小说将“菊花”作为标题,说明其具有不同寻常的作用。而以“菊花”为切入点评论此篇小说的文章也不少:新西娅·比利认为,伊莉莎和菊花的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体现;托马斯则从性需要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伊莉莎种菊花的行为特征;马科斯认为,菊花弥补了伊莉莎与亨利婚姻中孩子形象的缺失等。本文仅从菊花的象征意义来探讨菊花与伊莉莎以及女性的关系。
小说中的伊莉莎在当时社会的男人眼中可谓典型的好女人形象,她善于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很干净。更重要的是,她还是种菊花的能手,但这一点却不为男人们所称道。这是因为,在当时,对男人们来说,种菊花还不如种水果来得实惠。而种菊花对伊莉莎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料理菊花,伊莉莎倾注了她几乎全部的情感与心血。她种的菊花在附近一带是长得最好的。当亨利谈论起她种的菊花时,伊莉莎的脸上乃至语调中都洋溢着沾沾自喜的骄傲。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菊花象征着伊莉莎的梦想和渴望,也是她的全部价值所在。她渴望外面无拘无束的世界,即使自己走不出峡谷,只要她的菊花能被带出去,也就等于自己走了出去。在她心里,菊花就是她自己。所以,菊花备受伊莉莎的呵护、宠爱。同时菊花也象征了伊莉莎作为女人的天真。伊莉莎之所以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是因为她对男性世界充满了好奇,她渴望走出去,总以为外面的男性世界能够接纳她。但男人们既然已经为女人们界定好了身份,当然也就不希望她们能逾越这个身份。故事的结尾,伊莉莎送去的菊花竟被补锅匠弃之路旁,而花盆却被拿走了。至此,男人的自私、虚伪、欺诈已经完全打碎了伊莉莎的梦想,也摧毁了她的天真。事实上,不管菊花是代表伊莉莎的梦想也好,还是天真也罢,其结局只有一种:破灭。也就是说,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总是处于被打击被摧残的弱者地位,女人是属于男人的,在男人心目中,女人是没有感情、没有发言权的。
伊莉莎的女性心理发展
冰心曾在《<关于女人>后记》中说过:“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个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所以,女人是整个生命世界的一半,缺少了女人,这个世界就会残缺。女人与男人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但遗憾的是,在男人居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女人一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她们被遮蔽在男人身后,成为一个沉默的代名词。但女人毕竟在成长,她们不会总是“沉默”。美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伊莱恩·肖瓦尔特从女性经历的角度出发,对由女人组成的文学亚文化进行了三个发展阶段的定义:(1)对主流传统流行模式的模仿以及对其艺术标准和社会角色观点的内化。(2)对这些标准和价值观的抗议。(3)自我发现阶段,这是摆脱了对对立面的依赖之后向内在的转化,是对身份的寻找。而《菊花》中伊莉莎的心理发展过程正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模仿(男人)——反抗(男人)——发现(自我),只不过其间伴随着痛苦和挣扎而已。其实,在伊莉莎的成长过程中,模仿阶段与反抗阶段的界限并不分明,而是交叉进行的。一方面她希望自己能像男人一样做想做的事;另一方面她又不满意男人为女性设定的角色,并试图挣脱这种角色的束缚。因此,她总是在无意识地模仿,同时又在有意识地反抗。伊莉莎有一颗不安的心,正是这颗心才驱
使她不认同当时社会规定给女人的应该安于家庭。相夫教子的戒律,她希望女人(至少她自己)可以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外部世界,与男人平起平坐。这种强烈的愿望从伊莉莎与补锅匠的一段对话中可见一斑:
“(这种生活)肯定非常精彩,我希望女人也能过这样的生活。”(伊莉莎)
“对女人来说。这并不是合适的生活方式。”(补锅匠)
“你怎么知道?你又怎能这样说?”(伊莉莎)
在男权社会里,女人被捆绑在家庭牢笼中,她们不仅要做各种家务琐事,还要照顾丈夫、孩子,即便是活着,也是为了丈夫、孩子而活,完全失去了自我。伊莉莎并不想做这样的女人,她挣扎着要摆脱家庭的束缚,但这谈何容易,她面对的敌人是如此强大——一个由男人控制着的社会。
故事开头作者用“强壮”一词描绘了伊莉莎的外貌,而她一身男性化的装扮,使其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有的“温柔、文静、脆弱”等特质在她身上荡然无存。或许伊莉莎在其潜意识中把自己当做了男人,希望自己与男人一样,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模仿着男人。殊不知,女人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一定要像男人一样强壮,模仿男人事实上就是在迎合男权统治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样无形中使得女人成为一种虚无、一种“空洞的能指”,不利于女性价值体系的形成,甚至会阻碍女性身份的找寻。
故事中的伊莉莎与亨利并没有孩子,“母亲”被认为是一个女人的天职,但伊莉莎并未去履行她,这或许是伊莉莎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言反抗。当亨利向伊莉莎炫耀他生意上的成功时,伊莉莎的回答可谓精辟:“好,对你而言!”是的,成功是你的,却不是我的。她不愿把自己看成是丈夫的附属品,和丈夫与荣俱荣、与损俱损。而当亨利提议去镇上吃顿饭、看个画展以庆祝生意成功时,那种商量的语气——“我想”,“你看呢”,这些字眼似乎在表明亨利对伊莉莎的尊重以及他们之间的平等地位。但小说结尾时,亨利的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语却道出了他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我应该经常带你去镇上吃饭,这样对我们俩都好。”伊莉莎想要出门还得由作为丈夫的亨利领着才行,这是多么残酷,又多么不公平啊!不管你多有能耐,你只能跟随在男人身后,这仅仅因为你是女人!对此,伊莉莎一方面靠模仿男人来证明自已并不比他们差;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反抗这样的不公平。正是在这种愤愤不平中,才促使伊莉莎的心理活动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寻找自我。转折点就是当补锅匠把她的菊花带走之后。
菊花代表着她的梦想,菊花走出去了,伊莉莎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而潜藏在她内心的作为女性的灵魂也复苏了。“她回到屋里洗澡,准备与丈夫去镇上吃饭。当她擦干身子站在起居室里的一面镜子前时,她观察着自己的身体,她收紧腹部,然后长出一口气,她转过身子从背后看她的肩膀”。此时的伊莉莎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欲望格外强烈,在镜子中反观自己,力图通过自己的目光来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淹没的自我。这时的她已发现了自我,虽然肉体上的她不能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但精神上的她至少是独立的,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里不再是男人与女人的两性战争,而是她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没有输赢,只有漫长的自相交战过程,而人性的矛盾本质使伊莉莎在自我审视中前行,但同时又在自我发现中徘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却不知自己应怎样得到。在去镇上的途中,她看到被补锅匠弃之路旁的菊花之后:“她像老女人一样哀哀地哭泣着。”此时的伊莉莎更清楚地意识到:男人的世界不容许女人踏入,女人的价值对男人来说微不足道,根本不被男人重视。至此,伊莉莎的梦、伊莉莎的天真被彻底击碎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自省、顿悟,以及她无助的徘徊。
结语
伊莉莎在模仿与反抗的痛苦挣扎中,完成了她的自省,但自省之后,伊莉莎作为一个女人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呢?一连串的问号摆在她的面前。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曾经说过:“为了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和男人一样平等,女人一定要走进男人的世界,正如男人也要走进女人的世界一样,一切应该是完全对等的交流。”
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她不主张女人与男人对立起来,而主张建立一个两性和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仅需要女人们的努力,也需要男人们的参与。但在那个以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男人们愿意或者说会和女人们一起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吗?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