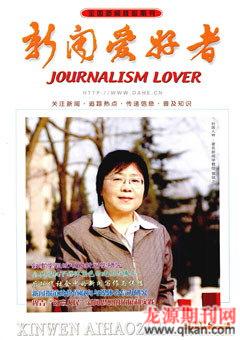孔子音乐思想考略
陈 薇
孔子与音乐
孔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幼喜爱音乐,尤其是对传统性的音乐特别喜欢。他好学不倦,不耻下问,因此掌握了多方面的音乐技巧。他会击磬、鼓瑟、弹琴、唱歌、作曲等。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叔,学琴于师襄等人。他不管学习什么知识都很认真、刻苦。他跟乐师师襄学弹琴曲《文王操》时,从音乐的各个角度探索音乐表现力。师襄一再说:“可以益矣。”然则孔子却一再用“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为人”的谦虚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孔子以“精辟微妙之义入神化”的娴熟技巧向老师汇报演奏了这首曲子,使得师襄佩服得“避席而拜”。
孔子音乐理论
孔子在大量的音乐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论语·泰伯》中曾记述了孔子与鲁国太师师挚、师冕相交往的事迹。“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后之,而反和之”。(《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学习唱歌时谦虚态度的真实记载,可见他学习唱歌多么用心。孔子在鲁国与乐官谈论乐曲时曾这样说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瞰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的演奏要有层次感,在乐曲的开始时应是合奏,渲染情绪,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开始。接下来乐曲的旋律进行则是像小河淌水一样,流畅奔放,旋律既要优美动听,节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扬顿挫,悦耳感人。音乐只要达到三方面的要求,就能使乐曲丰满和谐,感人之肺腑。这大概是当时贵族宴饮场合中常用的一种演奏程式。孔子的这一高论,对乐曲结构的规律,作出了简明扼要概括性的说明。孔子把“可知论”首次用在音乐上,这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也为以后的音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汉代儒学家的一些音乐基本理论,便来源于此。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述,孔子在音乐研究中,要求渐次达到“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的境界。所谓“得其数”,就是要探求音乐的一般规律。所谓“得其志”,就是要探求音乐中丰富饱满的思想感情。所谓“得其为人”,就是要探求音乐中充满活力的人物形象和做人的道理。这也就是说,音乐所表现的主题,应当是丰富的、有血有肉的,不仅要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而且要形象地再现人们的语言行动。这就注意到了音乐的生动性、形象性及其所表现的意境,说明孔子已经在探求音乐的内容与其所体现的境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书于汉代的《礼记·乐记》中某些关于音乐的基本理论,就其发展脉络来看,其实可以在孔子那里寻到其渊源。因此,不言而喻,孔子对古代音乐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地位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孔子音乐美学
孔子认为,音乐的本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这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礼乐”、“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突出标志,也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礼”与“乐”是“六艺”的组成部分,也是音乐美学的综合概念,这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有着完整的阐释。《礼记·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就是正,就是合适、合宜。“和”就是和谐。中和之美要求处理好文艺内部的各种因素,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而要和谐适度,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关键是“中节”,人的情感不可尽情发泄,要以礼义加以节制,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使人成为彬彬有礼、温柔憨厚的君子。“中和之美”这一美学思想,是孔子中庸哲学在美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美学思想。孔子认为音乐是“美”与“善”的完美结合,这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a孔子承认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善”和“美”来评价音乐家,凡合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孔子对中和理论的发展和基本成形起着重要作用。他有如下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知知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中和之美的典型反映,后来成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美学原则,经长时期历史沉淀,也成为我们民族审美情趣的一个特色。
孔子音乐教育
据《周礼》规定,八佾本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舞蹈,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为二佾。作为鲁国正卿的季氏,依礼只能享有四佾,却享用天子才能享用的舞蹈,无怪乎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会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感叹。西周时有“礼不下庶人”的规定,加之那时的音乐教育以“官学”为主,教育的对象是不会包括庶人的,同时也是想通过乐教的等级制度来体现礼的等级。然而孔子在教育上却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乐教等级观念,提倡有教无类变无教为有教”,这在乐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教无类”思想的实质就是“在教育对象上,无有贵族与平民、华夏与华夷之分”。这也是他的音乐美学理论与音乐教育具体行为上的矛盾体现。孔子的乐教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孔子对音乐具有“兴观群怨”、“移风易俗,安民治上”的社会功能的充分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中“六艺”的“乐”置于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极力主张发挥音乐的作用,以获得应有的社会效果。他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文之以礼乐”,为人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用音乐来修身养性,涵养人的内在品质,并以“成于乐”作为人格完善的最终目标,所以,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中,乐教既是内容也是手段,既是过程也是目的,具有严谨完整的逻辑系统性。孔子的乐教内容,是建立在“礼”、“仁”、“中庸”三大范畴基础上的礼乐道德功利论。尽管他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对象上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的限制,但他是以周之礼乐制度的等级规范,作为其乐教的内容和准则为前提的。他对季氏用天子之乐,“八佾舞于庭”所表现出的愤慨之情就是突出的例证。虽然他以“仁”施行乐教,但却要“止于礼”,即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就是说,“视、听、言、动”都要合于“礼”的规定,才是“仁”,才能“复礼”。他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就是要求乐教之乐的“思”合于“礼”是以礼限乐。因此,“礼”是本、是目的,而施“乐”不过是“复礼”的手段与过程而已,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他所崇尚的“周礼”。故《论语·卫灵公》记“颜渊问邦。子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候人。郑声淫,候人殆”。这就是孔子对礼之乐教的道德内容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定位。孔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教育
完成的全过程,并把“成于乐”视为教育的终极成果。孔子之所以如此崇尚“乐”是因为“乐”与“礼”一样,在周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把外在的礼的规范性要求,通过音乐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体的心理中,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内在要求。即受教育者学习音乐,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再加上心智聪慧与意志体魄这些成人的必要条件,又在礼的学习中学会各种社会礼仪、行为规范,使之内外统一,就是“成于乐”了。显然,这时的“乐”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由“道、德、仁、艺、诗、礼、乐”的教育逻辑过程,最终所形成的完美人格之“乐”了。即孔子所说的:“如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在评价音乐演奏时认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记》)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一观点对当前的音乐教育有着现实意义。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
孔子音乐社会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之名”。“兴”指感发意志,就是教育作用。“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孔子音乐社会功能着眼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中,重视音乐协调人际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合理性。子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成……”(《论语·子路》)这种重视道德与社会伦理的音乐社会功能在以“礼”为人本时,必然导致以人为本的声情自由抒发和发展的不足,也使音乐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对音乐内在的实质认识缺乏一种客观性。无论是内在的思想还是外在的形式,都力求避免情感的激烈和外露,而倡导含蓄、适度、节制,强调情感和理智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与个体身心的均衡。“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孔子推祟“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赞赏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郑卫之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及“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表现了他音乐思想的保守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贬斥郑声新乐的思想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看不起民间新文艺,把戏曲、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低贱之作的重要根源之一。孔子“家国同构”的儒家思想渗透到音乐中,使音乐异化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以乐辅礼,治理国家”。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当孔子的学生颜渊问怎样才能治理国家时,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冕,乐则《韵》、《武》,放郑声。在这种思想的礼乐之国中,一切都为了国家的和谐和稳定而服务。
总之,孔子的音乐理论体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以“和”为中心的审美态度,对我国的音乐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把音乐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穷极人生的途径。孔子认为审美与艺术的作用就在于感发和陶冶人们的情感,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片面强调音乐反映思想情感为内容的指导思想,忽视了对音乐这一人类情感载体的本质认识,暴露了儒家思想在音乐自律论上的缺陷,严重束缚了音乐,使之不能自由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要求音乐不以“人”为目的,而以“礼”为目的,不是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而是成为统治人民的手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音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失去了本身的独立性,影响了人类对美好情感的表达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带有政治功利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严重阻碍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