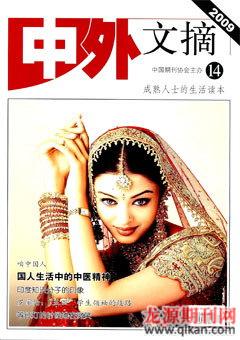我的书房
龚鹏程
读书人谈他的书房,就像女人谈她的首饰盒,是要惹人嫌厌的。
何况,据报馆里的朋友们分析,20岁以上的人,有百分之六十一,这半年来几乎没买过任何一本书。另外,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在选择礼物赠送亲友时,从来都不把书考虑进去。剩下那些虽或想到可以选朋友一两本书的好人,当然大部分并不曾真送了书,因为他的朋友恰好就是不读书的。因此,所谓书房,恐怕是上古遗留下来的名词,一般人既未见过,建筑业中似乎也早已没有这一项规划啦!
尝读明人陆绍珩《醉古堂剑扫》,他形容书房的条件是“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潇湘雨、彭蠡烟、广陵涛、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此种书房,于今大概只能求之于故宫博物馆,根本难以想象。
即使标准不这么高,即使陆绍珩谈的也只是他理想中的书房,古人一般书斋大概距此水准并不太大。例如写《陶庵梦忆》的张岱,他家里就有好几个书房。什么“梅花屋”、“不二斋”、“琅嬛福地”……光听名字,就令人魂销。这些书房,真是“房”,外面有“前后空地,后墙坛其趾,西瓜瓢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西溪梅骨古劲,滇茶数茎妩媚。其傍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璎珞”之类,屋里,那就更不用说了。
以此为标准来看,现下谁有资格说他有书房呢?所谓书房,若未绝迹,大约也只是工作室的别名罢了。小孩为准备考试、写功课交差,需要一张桌子、几册参考书(参考书的消费颧,是台湾图书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女人,不幸而为教最文人,为了餬口,不免干些家庭手工业,必须伏案抄辑,所以也得有个堆积遇稿的地方。这些地方,便常宣称为书房。
房中大低什物堆积、纸卷杂沓。一灯荧荧,伴我两眼昏花。不复为张岱之琅嬛福地也。
我家的书房,更是如此。其实亦无所谓房。早先住在桃园,屋子总共十坪大,除去床浴厨厕,便是书。起居藏息,皆在其中。书架是我自己买了木头扛回家,敲敲打打一番就搭起来的,连木面都没有刨光。书插上去,旁人看着寒酸,我则颇为得意。迁居台北,书架自仍移来,甚便我工作。但有一天我去淡水上课,台北大地震,妈妈正在午睡,听得轰然大响,忙跑到房间一看,书架震倒了一面。书呀书,堆得满坑满谷。累我整理了一个月。幸好人不在里边工作,否则恐难幸免。过了一阵子,清晨大地震,又是乒乓一通,震垮了另外一面……
事实上,“书多压死人”,绝非虚语。朋侪中,我的书不算顶多的。但已有些不相熟的亲戚,会拉着老婆悄悄问“你先生是开租书店的吗?”言下若不胜其痛悯。老婆当然也对我的买书恶习,至为不满。她常威胁着要把这些垃圾丢出去。因为乱七八糟的书,堆得一塌糊涂,既碍观瞻,亦不便行动,“都是一斤两块钱的东西!”她嘟哝着说。
其实我的书算什么?陆放翁之书,号称书巢。巢就是蜂巢。据说进出书房,都得像蜜蜂在巢中曲折钻动,甚至匍匐转侧,乃能成功。而放翁在宋朝,还称不上是大藏书家哩!
我的书,更远不够资格冒充藏书家。然而只此便已令人头痛了。每找一书,辄翻箱倒箧,遍寻不获,只好上街再买一本。所以到底有多少重复的书,自己也搞不清楚。幸而书不管重不重,都常使用,非充门面假装潢而已。我几乎从不上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里面长什么样子都不晓得,更不用说什么“中研院”的罕秘珍藏了。这当然是因个人治学方法特殊,从来不必仰仗秘本,也是因为性格乖张,自以为我没看过的书,大概不会有什么价值;更因为我自己的书用来顺手,既然足供采摭,自然不必旁求。
我想这大概就是在现今公立图书馆发达时,人们仍愿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的原因。虽然如前所述,这点卑微的心愿,有时不免只是梦想。但去图书馆毕竟如逛博物院,奇珍异宝,众呈毕列;却总不及自己家里一两样破铜烂铁——虽不可能打理得整齐光鲜,然而蓬头垢面,却不妨晤面相亲。老婆与书房,道理都是一样的。
(摘自《中外书摘》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