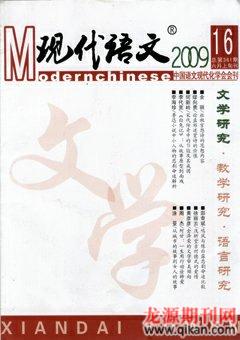蝉联对比,因果不爽
摘 要:项羽、刘邦是秦汉时期楚、汉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二人事迹在司马迁著的《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中蝉联,形成鲜明对比,清楚地揭示了刘胜项败的因果关系,向世人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和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本纪 对读 项羽 刘邦 成败兴亡
两千年前的楚汉相争,最初能料定汉胜楚亡的人恐怕不多。楚、汉力量对比悬殊的双方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戏剧般变化,让人百思有味,生趣无穷。
通过描写项羽、刘邦这两个领袖人物的形象,展示导致楚、汉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存亡兴灭的原因,这应该是司马迁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的动机。两篇《本纪》在《史纪》一书中蝉联,形成对比,再加上在其他篇章中的刘项二人事迹,清楚地揭示了刘胜项败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使世人看到了那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和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
《史记》首先从刘邦、项羽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和个人品性写起。项羽,其先人“世世为楚将,封于项”,其祖父项燕“为秦将王剪所戮”。楚国破灭后,叔父项梁带着他“避仇于吴中”。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观秦始皇游会稽时口吐狂言“彼可取而代也”。由此可知,项羽出身于楚国的世袭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知识、军事知识、军事技能的熏陶,个人武艺高强,同时与秦王朝有杀祖、灭国、毁宗的深仇大恨,因此他具有自觉而强烈的造反动机,是秦王朝潜在的一个大敌。而刘邦平民出身,“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以至酒债累累,却不思偿付,每到年终,酒家只好“折券弃债”;赴吕公的宴席,“不持一钱”,却要萧何在礼单上给他大书“贺钱万”(此举竟赢得吕公赏识而以女妻之,是为吕后);“徭咸阳”、“观秦皇帝”时,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些行径,使人们认识到,少时的刘邦,只是一个游手好闲、横行无赖之徒,但却对富贵荣华有着强烈的向往。因此,沛县人杀了县令造反后欲推选出领袖之时,因“萧(何)、曹(参)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众莫敢为,乃立季(刘邦字)为沛公”。时代形势把刘邦推向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刘邦流氓、无赖的心性也使他勇敢地站到了时代大潮的风口浪尖之上。
当秦王朝在反秦战争的烈焰中灰飞烟灭之时,项、刘二人分别成为两大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但其实力,不可同日而语。政治上,项羽因钜鹿战功已成为各路反秦义军实际上的统帅。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政由羽出”,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以瓜分全国土地,成为秦朝之后实权上的天子。对此,大多数诸侯是承认并拥护他的。而刘邦,虽有“先入定关中”之功,却被项羽剥夺了“王关中”的资格,被安置到巴、蜀、汉一带的偏僻崎岖之地。刘邦对此,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军事上,项羽有四十万同秦军打过硬仗、恶仗的精兵,而且还能号令其他各路诸侯军队。刘邦入关时虽有十万军队,但到去做汉王之时,项羽却只“使卒三万人从”(硬夺去了七万卒,还很可能全是精锐),另外“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两部分人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十万之数,而且编制散乱,将不知兵,兵不知官,战斗力不强。在这种劣势情形之下,刘邦集团内部又开始出现了不稳倾向,“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此时的刘邦,可以说处在他投身社会运动以来的最低谷,其前途真是岌岌可殆哉!
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项、刘双方本质上的优劣势却是潜伏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斗争的演进,这种潜伏着的优、劣势便逐渐浮现出来并最终决定双方的命运。
历来天下纷争之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道理很好懂,但参与争夺天下的人,真正能够做到的却不多,所以许多英雄争不到天下(如东汉末的袁绍、唐末的黄巢、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许多争得了天下(如西汉末的王莽、明末的李自成)或半个天下(如东晋时的前秦王符坚、五代时的唐庄宗李存勗)的人,他的天下最终被别人夺去。刘邦和项羽,在争取民心上,存在一个鲜明异常的对比。
早在反秦战争之时,刘邦就约束部下“诸所过毋得掠卤”,因此,在诸侯中赢得了“独沛公素宽大长存”的美誉。及至咸阳,则不失时机地向秦人宣布“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等主张,几句话便把亡秦的各阶层人士安抚得妥妥贴贴。因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食军士”,而刘邦又“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于是“秦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争取民心的工作刘邦做得非常好。在楚汉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刘邦又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实行土地改革,“诸故秦苑囿园地,皆令人得田之”使一大批无地农民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同时,又两次“大赦罪人”,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以上说明,刘邦集团从起兵之初,就比较注意民间疾苦和人民愿望,所以采取了许多延揽民心的措施,其直接效果,就是他在第二年八月东出陈仓、还定三秦之时,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此外,从政治策略上来说,刘邦在力量尚弱之时,注意掩饰自己的长远战略目标,以此来麻痹项羽,争取在政治上的主动权。当他刚从汉中偷渡陈仓、占领关中之后,张良就送书给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使项羽认为刘邦不过是想实现当年的约定,称王关中而已,因此不把刘邦放在心上,而跑到北方去镇压造反的齐王田荣。刘邦则乘机东进,一举攻占中原重镇洛阳。在洛阳,刘邦听到项羽杀死义帝的消息,则 “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不道,寡人……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这恰到好外地抓住项羽政治上失策的把柄,把自己出关东向,蚕食诸侯王地盘并进而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略目标,巧妙地变成为义帝报仇,为诸侯王雪耻的堂堂正义之师了。
项羽则不然,他一生信奉的是“以力征经营天下”,自恃“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因此时时处处以杀伐立威,直到垓下突围时,仍以自己的英勇无敌骄示部属,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政治上延揽民心。起兵之初,项羽叔侄便毫无道理地杀死主动找他们商量起兵反秦的会稽守殷通,并其门下数十百人。在进攻襄城时,由于襄城军民“坚守不下”,便在攻克之后,把守城军民全部活埋。钜鹿大战后,项羽收编了投降的二十多万秦军吏卒,等到西进至新安时,那些投降的秦吏卒因不堪忍受诸侯吏卒的“奴虏使之,轻折辱”发出了许多怨言,项羽便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万新安城南”。以当时的情形而论,这确实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诸侯吏卒之所以欺辱秦吏卒,是发泄他们当年征发到秦中时所受到虐待的愤恨。项羽对此事前没有预防措施,事发时也没想到、或者也没有能力制止。而“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这就威胁到项羽集团自身的安全。当时的历史,还没有妥善处理这类事件的成功先例,但却有四十年前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四十余万而终于灭赵的榜样。待到进入关中,与刘邦在鸿门宴见面以后,项羽即“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项羽这一坑一烧,直接的效果,是弹压住了秦朝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不满或反抗;而其长远的效应,却是在他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才显现出来。汉之二年(公元前205年)冬,彭城大战,刘邦惨败后,逃至荥阳,“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未登记服兵役名册),悉诣荥阳,复大振……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稳定了刘邦的后方根据地。汉之四年(公元前203),在广武一线,两军相持数月,“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漕”,而刘邦方面,却因为“关中兵益出”形势逐渐演变到“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疲食绝”的局面,刘邦终于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并很快进行垓下决战,彻底消灭了项羽集团。关中人民对刘邦集团的态度是全力支持,对项羽集团的态度是拼死抵抗。
在军事上,若从战术上相比,行军布阵,冲锋陷敌,斩将搴旗,项羽远远地超出刘邦(彭城大战中,项羽以轻骑三万奔袭击溃刘邦五十六万大军足以证明),可是在战略上,项羽却犯了一系列错误,完全是一个莽夫。
这首先表现在项羽不都关中而都彭城,放弃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优胜之地,却为衣锦还乡的虚誉而建都于四战之地的彭城;而刘邦在第二次夺取关中后,则一直以此为根据地同项羽抗衡,并且在夺取天下后,建都关中,形成虎踞龙盘、俯瞰山东之势(关于建都关中,项、刘二人都先后有人向他们提醒过,但项羽是“烹说者”,刘邦则采纳之)。其次是在楚汉战争全过程中,项羽都采取四面出击的方式来对付反抗他的诸侯。而没有集中力量打击刘邦。汉元年,他派兵南击彭越;汉二年,项羽率兵北击田荣、田横,二田未灭,刘邦攻占了彭城,他又自率精兵三万回师救彭城,结果同刘邦僵持在成皋、荥阳一线,而北方田横复振;汉三年,“项王自将东击彭越”,让刘邦巩固了成皋阵线;汉四年,广武相持未决之际,项羽却派大将龙且北击韩信以救齐、赵,又落得个损兵折将的结果,“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他第一次产生了恐惧情绪;同年,项羽经不起彭越在后方的骚扰,把生命悠关的成皋战线交给庸将曹咎防守,再次东击彭越,结果让刘邦攻破成皋防线,在“兵疲食绝”的情况下,不得已接受了刘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的议和,而刘邦却乘“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之际,违约乘机“追项王至阳夏南”,并迅速调集韩信、彭越、刘贾、英布、周殷等各路大军“皆会垓下,诣项王”,完成了对项羽的最后包围。在同一期间,刘邦采取稳定关中,坚守成皋—荥阳战线,确保战略后方安全的战略,然后派韩信北击燕、代、赵、齐,派彭越(后又加派卢绾、刘贾)骚扰项羽的战略后方下邳,努力把战争打到敌占区去。刘邦曾在荥阳突围后,率兵南下宛、叶,引诱项羽南追,东救下邳,疲于奔命,而刘邦又掉头北上,恢复巩固了成皋阵线,致使项羽一方面不能牢固控制自己的后方,一方面又陷于三面作战的危险之中。最终军事较量的结果自然是刘胜项亡。
刘、项之所以在政治军事战略上有如此优劣之差,同他们个性及人才战略有关。项羽的个性,若从个人道德方面看,自然也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但他作为一个参与群雄角逐的政治家、军事家,其性格的主导方面,却存在着严重不足。他极端迷信武力而刚愎自用,因此他便听不进、听不到许多极其有益的意见,从而错失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灵计妙策和大略雄才。当时两个最优秀的人才在经过对项羽的观察分析后得出过结论:“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劳当爵者,印玩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这是韩信去楚归汉后,被刘邦破格擢拜为大将时对刘邦说的话。而韩信之所以去楚,乃是因他曾经“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另一个也是去楚归汉的人,对项羽的评论则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陈平)乃去楚”,“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这是陈平在楚汉相持荥阳时,为坚定处于困境中的刘邦信心而对刘邦说的话。综合韩、陈二人的话,我们看出,他们认为项羽致命的弱点有:①匹夫之勇;②妇人之仁;③残暴好杀;④任人唯亲;⑤意忌信谗;⑥注重虚誉。《史记》中多处描写了项羽的这些性格特征。钜鹿大战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惴恐,莫敢仰视”。以诸侯将领的表现,写尽项羽以武骄人的情态。鸿门宴上,因项伯的一句“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的劝说而许诺不杀刘邦,放纵自己最大的潜在敌手不辞而别,“妇人之仁”、“恭敬慈爱”之情莫此为甚。入关以后,“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其愎谏之心昭然天下(此后谁还敢向他献计献策!)。陈平使反间计后,“项王果大疑亚父(范增)。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时刘邦被困城中,朝不保夕),项王不信,不肯听”,白白丢失了一次捉杀刘邦的绝好机会。
项羽手下,原是人才济济。韩信、陈平因出身低微,在以六国旧贵族为领导力量的项羽集团中没有立足之处,加上项羽全无人才意识,二人毫无进身之阶,遂先后去楚归汉。张良本韩国贵族,项羽分封天下后,张良也跟韩王一道随项羽东归。但后来项羽先是限制韩王去他的封地,后来又无端杀掉韩王,逼得张良只好逃跑,“间行归汉王”。这三人后来成了刘邦打天下、安天下最得力的股肱大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万世英名。除此三人,项羽营中就只范增可用。但这范增投效项羽叔父项梁之时,已“年七十”。虽然《史记》上说他“好奇计”,即也只是“好”而已,始终未见他有过“奇计”。相反,在一些大事上,他不是默默无闻,便是出馊主意。举凡坑秦降卒,屠咸阳,焚秦宫室,分封诸王,弃关中而都彭城,弑义帝杀韩王,军事上四面出击等项羽的一系列错误之举,均不见范增有一言半句的谏说建策。其余龙且、钟离昧、曹咎、司马欣等辈,均为一介武夫。项羽自身个性和才智学识如此,而对人才战略又不重视,其暴兴暴亡,实是理所必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出版社,2006.
[2]巴城.中国历史故事总集上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3]韩兆琦.韩兆琦《史记》新读[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4]王立群.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M].重庆出版社,2008.
(余晓萍 四川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 646005)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的其它文章
- 古典诗歌中的绘美二法
- 敦煌文研究综述
- 《惜诵》发微
- 军礼与《诗经》战争诗
- 爱情与婚姻的背弃
- 灵魂在“流观泛览”中诗意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