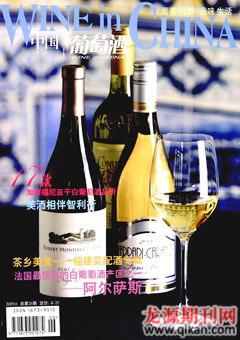踏遍青山人未老
张雪超
在亘古与当下两个时空中穿梭,他计量时间的单位是万年。行走在荒山、戈壁,埋头在书斋、实验室,与离体的牙齿、单块的骨骼、破碎的头骨化石对话,寻找着数不清的世代前与我们有着血肉传承联系的我们的远祖,探索着茫茫史前黑暗中人猿相揖别的故事。蓝田人、和县人、巫山人,当代中国古人类考古界的三次重大发现,都与他的名字相关。让我们走近古人类学家黄万波,与他一起倾听远古人类的回声。
我们是谁,又来自何方?这是人类从首次仰望星空开始就一直被深深困扰的问题。
在神话中,大地是人类起源之处,女娲、马杜克、宙斯或者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就了人类。
19世纪,人类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一个人、一本书,重新解释自然规律和生命演变,成为现代生物进化论的象征。20世纪以来,站在进化论的基石之上,人类起源的话题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重大科学热点。古人类学家们努力工作,在泥土中寻找人类起源的依据。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用化石连接起人类长达六七百万年的历史,试图更加完整地告诉我们关于自身的来龙去脉。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就是这群探索者中的一员。作为东亚最古老的人类——巫山人的发现者,2005年,经过对中国长江三峡地区巫山龙骨坡长达20多年的考古发掘之后,他提出“东亚型”人起源于长江三峡的学说。
2009年春花开得正艳的时候,也正是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各项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有幸在北京回龙观采访到这位在古人类学领域成就卓著的科学家。
走进古人类学世界很偶然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登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这是地质队员们几乎人人会唱的《勘探队员之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矿产资源十分匮乏,国家急需培养一大批年轻地质找矿人才。黄万波当年正是在李四光精神的感召下,毅然报考了地质学院,怀着为祖国寻找宝藏的梦想,从长江边宁静而古老的四川省忠县新立乡来到了东北的黑土地上,如愿以偿地成为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查专业的学生。
在学校期间,尽管当时交通条件恶劣,山路崎岖难行,但他仍然对野外实地考察课程非常感兴趣,跟随着老师们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考察了不少地方。没想到,这些地矿知识,却为他推开地学的另一扇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黄万波毕业了,但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全班30多位同学,都分到了各个地勘单位从事地质找矿工作,唯有他一个人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这令年轻的黄万波怅然若失。做了千百次的找矿梦就这样戛然而止?但是那个年代,黄万波也没有再多想,“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黄万波来到了当时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报到,也就此来到了一个新专业的门槛前。
没想到的是,到这里的头一个晚上,他就被来了个下马威。
我国虽然是举世公认的仅次于非洲的世界第二大古人类资料蕴藏地,但50年代的时候,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古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也是从相关专业抽调而来的,其中有学生物的,有学地质的,有学医的。由于单位的宿舍太远,第一个晚上黄万波被安排到一位出差在外的同事的办公室暂住,而这位同事是大连医学院解剖系的教授。年轻人好奇又好动,晚上一个人闲来没事,黄万波就观看起办公室里的标本来。随手打开一个标本抽屉,发现里面竞有十几个真人头骨。一直学习地矿的他哪见过这样的标本,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在这间办公室一宿没睡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第二天怎么也不肯在这里睡了。
就是这样一个见着人的头骨都睡不着觉的年轻人,几年后,自己也拿起了解剖刀。“不学不行啊,”黄万波说,到了这里真正开始工作后,由于专业的距离,知识有很多的盲区。为了尽快进入角色,他努力自学医学、解剖学知识,还到北京大学进修了两年,才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而让黄万波备感幸运的是,他来到中科院后被分到了裴文中先生那里,并且一直跟随着他做科研。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于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裴先生不仅传授知识,并且培养黄万波科学的思维、严谨的态度,让他终生受益。他对黄万波说,作为一个古生物研究者,关键是要自己去寻找化石材料,而不是关在书斋里纸上谈兵。这些话对黄万波的影响很大,几乎成为他几十年科研生涯的指针。为此,他特别注重野外考察,北上南下,孜孜以求,寻找“自己的”发现。
1963年,黄万波与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发现相遇。当年7f14日,黄万波一行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黄土地层发现了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化石,同年7月15日,他们又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的黄土地层发现了蓝田猿人头骨产地,填补了我国古人类80万年至115万年这一阶段的空缺。这也是继北京猿人发现之后事隔34年再次在东亚地区发现的猿人化石,而且又是首次在洞穴外的黄土地发现的。
1980年,黄万波和他的同事们在安徽和县发现猿人头盖骨。距今二三十万年的和县猿人头骨,成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保存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对于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南北方猿人的特性与差异,长江沿地的发育史以及古地理、古气候等方面,提供了极其珍贵和重要的依据。半生心血付与“巫山人”
黄万波一生中最大的发现还是在他的家乡大三峡地区。
多年来,在黄万波的心里始终有这样的猜想:在中国南方还有更早的古人类化石。
这个猜想来自蓝田人的发现。蓝田猿人跟北京猿人处在同一个进化阶段,但时代却早了一倍以上,这使黄万波大胆猜想;在中国,能不能找到更早的古人类化石?如果有,又该到哪里去找呢?
伴随着蓝田猿人化石一起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有几十个品种。在仔细研究后,黄万波感到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些动物品种,几乎都是生活在南方的种群呢?另外,从蓝田遗址的地质剖面来看,在距今一百多万年以前,那一带是黄土堆积,根本不适合原始人类安家落户,繁衍后代!
这个猜想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黄万波的脑海中:蓝田猿人的故乡可能不在陕西,他们很有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从秦岭以南迁移过来的。果然,在蓝田猿人发现后不到一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出土了两颗人类牙齿的化石,后来又找到的石器证明,元谋猿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数字,它把中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又往前推进了。这个发现也再一次坚定了黄万波的决心:他要在中国南方寻找更早的人类祖先。
而这个猜想的破题之处就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的一个小山坡上。
1984年,黄万波等获悉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地农民在巫山县龙坪村西坡地耕种时挖出了大批“龙骨”,即哺乳动物化石。黄万波随即率队进行了调查,在当地赤脚医生牟之富带领下,他们找到了盛产龙骨的西坡地,“钻进一片刚刚吐缨的玉米地,发现地面上满是当年挖掘后废弃的龙骨渣。”面对这一情景,黄万波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蹲在地上就开始拣拾,一块、两块、三块……不一会儿便拾到了十余块“龙骨片”,它们像出土的宝石,像出海的珍珠闪烁在黄万波眼前。看着这些“龙骨”,听着当地人对这面山坡往事的回顾,“龙骨坡”这个名字从黄万波的脑海中浮出。从此,这面山坡有了自己的名字——龙骨坡。
经初步断定,这些化石来自于剑齿虎、鬣狗、小种大熊猫等,它们都是我国华南早更新世的代表物种,其生存年代远远超过北京猿人,甚至比目前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原始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还要久远。这个时间所带来的诱惑是难以抵挡的,在那时,除了这些动物之外,会不会还有更进步的、类似人类的生命?
黄万波隐隐感到,龙骨坡有可能改变“东亚型”人演变的历史。
1985年深秋,龙骨坡的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了。按照惯例,考察队一般工休时才作化石分类,但10月13日这天中午,黄万渡却一反常规,上工不久便在各个竹筐里挑选起化石来。突然,他发现一节骨头有明显的人工加工或使用痕迹,职业的本能使他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有古人类活动。当挑选到H9探方的竹筐里时,他见到了一块含有动物牙齿的钙质结核,当他把附着在牙齿表面的黏土清除后,发现这竟是一段灵长类动物左侧下颌骨,其上保存有两枚牙齿。从其齿冠形态看,有些性质与古猿相似,有些特征又接近能人或直立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啊!黄万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几乎高兴得在工地上跳了起来,并将这一特大发现马上告诉了在场的全体发掘人员。
后来,经鉴定,巫山猿人化石的年龄在200万年左右!它成为东亚地区时代最早,性状最原始的一件古人类化石!“东亚型”人的演变历史,在黄万波的挖掘中,被整整提前了100万年!
此后,黄万波和他的同事们在巫山龙骨坡又发现了数百件打制石器和100多种动物化石。经过多年的系统深入研究,他发现三峡地区保留着人类200万年来连续演化的文化系统痕迹:巫山人及其周围地区的建始人、官渡人、河粱人、大溪人、奉节人等,体现了人类活动的传承性和完整的演化过程。2005年,黄万波正式提出“东亚人起源于长江三峡”学说,改写了科学界对“人类演化史”的认识。
踏遍青山壮心未已
“每一个人类学家都梦想发掘出人类远古祖先的一副完整的骨架。可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死亡、掩埋和石化等变化莫测的因素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记录的贫乏和破碎。”这是被誉为研究古人类学的“第一家庭”——利基一家中,儿子理查德·利基在他的著作《人类的起源》中所写下的一段话。它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有太多的人在为寻找人类祖先的化石努力着,但其能够找到的概率就像是购买彩票。
黄万波并不否认这一点,他说,古人类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气,说得科学一点,也就是机遇。但黄万波更相信,产生机遇的前提,是长时间孜孜不倦的积累。
“机遇是在扎实的基本功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比如你走路遇到一块石头,你没有足够的史前考古学知识,很可能会认为它碍事,就把它踢到一边去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石器。机遇的本身,就在于时间经验的积累,你知道认识某个东西了,你碰到了,然后你就把它拿起来,就这么简单。”黄万波发现蓝田猿人的经过或许就佐证了他的观点。在黄土高原考察期间,有一天下大雨了,黄万波和几个科考队员一块儿往回走。走着走着,他被不远处的景象吸引住了——黄土坡上由于当地老百姓挖水沟,露出来了一个剖面,剖面上竟有好多化石。黄万波一边看一边琢磨:这些化石比较破碎,非常凌乱,不像是水冲之类的外力形成的,是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根据多年黄土地区考古工作经验,黄万波进一步判断这些化石应该早于新石器时代。按照当时的考古计划,他们的科考队当晚就要结束这个点的工作,开往另外一个工作地点。在黄万渡的坚持下,考古队不久之后再次回到了这里,对黄万波所发现的剖面进行发掘。在发掘工作进行的第三天,举世闻名的蓝田人化石出土了。如果说发现蓝田人是机遇的话,那么这种机遇正是来自于他多年积累形成的基本功。
积累,对于黄万波来说,除了书本学习之外,更多地来自于野外考察。黄万波和他的同事们出野外一般一次是三个月,最长的时候达到八个月。曾经,在缺水的黄土高原上,住在一个靠村里六个劳动力从200多米深的井里打水上来给全村人喝的地方,他学会了如何把一盆水用到极致;曾经,睡不惯北方火热的炕头,他想出了用十多公分宽的两块木板架在炕上睡的笨办法;曾经,在海拔6000米的高原突发严重的心动过速,在大雪山上从翻覆到沟里的汽车里爬出来,在横断山深处危机四伏的黑森林里夜宿……。野外考察,一次次让他吃尽苦头,又一次次地“增益其所不能”;一次次地令他失望,又一次次地带给他无限憧憬和希望。
如今,黄万波足迹已遍及包括台湾在内的我国所有省份。但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眼前这位瘦削但精神矍铄的77岁老人仍然经常跑野外,甚至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因为事业中的一些谜题仍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关于巫山人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古老物种与年轻物种的演化关系,很难以零星、不全的化石得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1985年巫山人左侧下牙床化石出土之日起,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这块骨骼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一些学者认为这段骨骼的主人是猿而不是人。但除去这一小块骨骼化石之外,黄万波没有找到其他部分的骨骼化石,尤其是能够判断脑量,进而能够对其归属进行界定的头骨。
不服的人负责质疑;新的化石最能叫人闭嘴。要结束这场争议,还必须找到更多的化石。“在三峡地区找到比较完整的古人类化石,是无数外国学者和中国老一代古人类学家的一个理想,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理想。从理想回观现实,现在所完成的工作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黄万波对长江大三峡这片考古学的处女地寄予了厚望,他相信这片厚土中埋藏着人类进化的秘密。过几天,他还要再赴大三峡地区,启动对长江支流乌江流域的考察。他笑着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一直跑到85岁!”
不羡温柔乡,最爱青山好,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是属于这位古人类学家的执著的情怀。
不断地解题,又不断地创造自己也为之神往的谜题,并把一生沉浸其中——这是属于这位古人类学家的充实而快乐的人生。
我们相信,他,会让古老的三峡绽放更多古人类学的灿烂之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