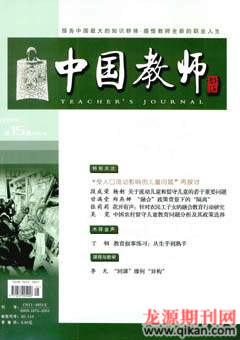善用农民工家长社会网络,提高流动儿童受教育质量
陈翀蔚
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农民工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子女受教育的可能性和质量高低,因此,研究农民工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行为对推动提高流动儿童受教育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农民工家长教育行为研究的领域中,社会网络是一个新兴且极具价值的研究视角。家长的社会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在家长的教育行为中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农民工家长群体获取信息、分享价值的渠道较少,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性较高,因而社会网络对他们的教育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并分析他们运用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影响教育行为的过程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于其教育行为有很大影响
1.社会网络是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
社会网络分析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的研究。从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使用“社会网络”这个概念以来,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以自身的努力充实社会网络理论,完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最终使社会网络分析成为当今社会学界最热门的分支之一。[1]
总体上来说,社会网络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行动者或主体以及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关系的结构。[2]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从关系出发,进而回归到关系,认为关系优于属性,应该根据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来理解观察到的社会行动者的属性特征,而不能简单地利用属性特征来解释人们的行为。社会网络分析所秉承的信念和持有的视角不仅是更有解释力的,也同样是更有生命力和更具价值关怀的。
2.社会网络视角对于农民工教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流动儿童教育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多遵循社会结构的观点,注重分析农民工的经济条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属性特征带给家庭教育的影响,并且主要指出了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种种缺陷。这样的分析是必要的,但由于农民工的属性特征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基于社会结构的观点,他们子女的家庭教育状况也就无法得到改善,这样的结论较为悲观。更重要的是,基于社会结构视角,以往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和建议多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力图通过政府行为提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质量。“自上而下”的建议固然重要,但“自下而上”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其生活、经验直接相关,基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研究及其结论与建议更加切近现实,基于此视角的建议,学校以及教师更容易把握。
二、农民工家长的社会网络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
1.农民工社会网络状况
目前,大多数农民工进城与资源获取既非依靠市场(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也不依靠正式组织(组织增加了农民工的进城成本),而是依靠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言是根本性的,是从传统延续下来的根,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稳定、平和的关系,使社会成员在低成本、少风险的情况下互助发展。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来说,社会关系网络是不可或缺的生活途径。
在流动中,农民工社会生活场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论述了农民工是如何通过关系资本来进行地位获得的,认为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主要依赖了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像当初农民进入乡镇企业时把这一网络移植到企业中一样,现在又把这一网络移植到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圈子。[3]
有研究发现,流动农民的社会网规模较小。流动农民社会网规模总体上不仅小于农村居民,也小于城市居民。在网络关系构成中,流动农民依赖父母、配偶等血缘姻缘关系,基于兴趣、经历等而建立的朋友关系力量突出,而同事、邻居等交往频率较高的关系力量下降。[4]
综上所述,农民工社会网是一个规模较小、初级关系比重较乡土社会有所提高、功能重要和互动频率紧凑的网络。在农民工社会网的关系构成中,朋友关系的比重最高,以下依次是血缘关系、工作关系、居住关系和管理关系;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等次级关系的比重较乡土社会有所提高,可见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己经不同于乡土社会中的关系构成。农民工社会网的功能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部分网络成员给予他们物质支持、精神支持。
2.农民工社会网络对于子女教育行为的影响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深刻影响了农民工的教育行为。城市生活为农民工增加了社会网络和信息渠道,为农民工的家庭教育增添了优势也带来了烦恼。
在现实生活中,多数农民工对于子女的教育规划(如读大学还是早就业,留在城市还是回到老家,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是否上辅导班等)、教养方式(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方式是专制、民主还是放任)深受其社会网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城市生活给流动儿童教育带来了正面影响。城市生活改变了家长的教育观念,为儿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很多家长到城市后对孩子的期望提高了,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家长不仅重视儿童在学校的受教育情况,而且重视家庭的教育环境,尽力为孩子提供好的学习条件。城市还给家长提供了家庭教育的榜样。比如,城市的学校都有家长会,有的还有家长学校,这不仅可以给家长提供一些教育的知识,而且为家长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有利于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和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5]
农民工家长的教育资讯通常来自于市井闲谈,这些资讯都经口耳相传且与现实有一定差异。而农民工家长因忙于生计,他们往往直接接受这样的资讯而很少求证资讯的准确性。在笔者对于农民工家长教育行为的访谈中,“听说”一词的频率很高,而“打听”一词却很少出现。可见农民工家长对于讯息的接受较为被动,并且他们对讯息很少做进一步的分析,盲目接受的情况较多。同时,在访谈中,“亲戚”一词出现的频率远高于“朋友”“老师”,这也显示农民工家长信息渠道的来源较为单一,他们的教育信息获得依赖其社会网络。有许多研究指出了城市生活给流动儿童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一项研究根据南京市有关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背景,指出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教育投入注重功利性、教养方式缺乏民主以及对孩子期望值较高等[6]。农民工家庭教育问题的同质性不仅受限于其社会经济地位,更多受限于其社会网络的局限性以及他们获取资讯过分依赖社会网络。
若能够了解农民工家长社会网络的特点,以及因此产生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优缺点,并以此为基础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学校和教师定能更积极有效地与农民工家长互动,培养家长正确的教育理念,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相信经过这样的努力,流动儿童教育质量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的提高。
任何人的行为都会受其社会网络的影响,农民工也同样如此。农民工子女教育网络对其教育子女的行为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农民工拥有提高子女受教育质量的动机和一定的能动性,同时这种能动性受到生计、自身能力等各方面的制约。研究表明,针对家长教育行为的培训往往不会凭空得到接受或拒绝,但当这些培训在家长已有的社会网络中引起讨论时,却能事半功倍。因此,对于家长教育行为的干预若能进入家长社会网络将更加有效;同时,干预项目应当直接针对家长社会网络而非单独的家长个体。[7]因此,作为力图提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质量的学校、教师,应当了解影响农民工教育行为的社会网络,并基于此为他们提供便利并且易于获得的教育信息和教育建议,以促进流动儿童教育。
参考文献:
[1][3]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J].改革,2006,(5).
[2]Martin Piotrowski.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s at Origin Communities on Migrant Remittances: Evidence from Nang Rong District[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006,(22).
[4]王毅杰,童星.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J].社会学研究,2004,(2).
[5]邹泓,屈智勇,张秋凌.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发展与需求调查[J].青年研究,2005,(2).
[6]赵娟.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状况[J].社会,2003,(9).
[7]Susan K.Walker, David A.Riley.Involvement of the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as a Factor in Parent Education Effectiveness[J].Family Relations,2001, (50).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