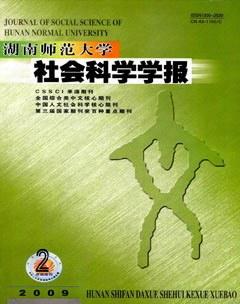崇力:鲁迅以力为美的审美取向
詹志和
摘要:鲁迅的审美取向可以提挈为四维:“尚新”、“主用”、“崇力”、“弘真”。“崇力”,即“以力为美”,是鲁迅审美化cc社会话语”的主旋律,是鲁迅关于“美本质”问题的深刻体认,也是鲁迅创作风格的显著征象。鲁迅‘‘以力为美”的审美取向迎应了中国近现代救亡、启蒙的历史使命的吁求,有久远的感召力和型范意义。
关键词:鲁迅美学;以力为美;《摩罗诗力说》;《野草》
中图分类号:G4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2-0103-05
鲁迅毕生致力于鼓铸审美一艺术新风以激扬国民精神伟力,开拓中华文明新运。鲁迅的美学,其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可以提挈为四维,即:“尚新”——以“新”为美;“主用”——以“用”为美;“崇力”——以“力”为美;“弘真”——以“真”为美。鲁迅的审美取向迎应了他所处时代的吁求,体现了正大的民族精神风貌,对于弘扬富于中国气派的审美一艺术风尚有久远的感召力和型范意义。笔者拟对此“四维”展开系列探讨,本文着重申论“崇力”的一维。
一、“崇力”,是鲁迅审美化“社会话语”的主旋律
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要由“力”来推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空中,由于“天崩地解,大变将至”的时代呼唤,涌动起一股从龚自珍那里肇始并在百余年间风起云涌绵延不绝的“心力主义”、“意力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对于中国近现代驱逐魔魇走向光明的历史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原动力和精神鼓舞力。鲁迅堪称近现代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在审美一艺术的领域里对这股思潮鼓动最力的学人,其“崇力”的审美价值观正是心力主义、意力主义思潮在文艺美学中的反映,与救亡、启蒙、开拓中华文明新运的历史使命此呼彼应、息息相通。
李大钊于新文化运动肇兴之际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宣言《“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倡言“青春中华之创造”有赖“力”与“美”的联手擘画:“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这里呼吁的能“勃兴”“新文艺”并进而“诞生”“新文明”的“一二哲人”,当具“四力”:一者敢“犯当世之不韪”,二者勇于“发挥其理想”,三者“振其自我之权威”,四者“为自我觉醒之绝叫”。概言之,就是呼吁具有高尚雄强之伟力的“精神界之战士”创造具有同样伟力的“新文艺”“先声”,以“惊破有众之沉梦”,“创造青春之中华”。可以说,鲁迅以自己“精神界之战士”的一生恰好回应了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的呼吁,他致力于新文艺和新文化的开拓与建设发出了强有力的“先声”。
正是遵“青春中华之创造”的时代使命,标举“力之美”、弘扬“美之力”,成为鲁迅的审美化“社会话语”的主旋律。鲁迅内心世界中属于“私人话语”的那一隅也满蓄着温情。如他早年以《别诸弟》为题的一组律诗中抒写了颇为感人的游子思亲之情;他晚年咏虎的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爱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也表现出为人父者内心深处的舔犊之情;他还曾在给挚友的信中借剖白内心矛盾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至爱深情:“我有一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鲁迅书信集·180820致许寿裳》)但是,一旦涉及“社会话语”,鲁迅表达出来并想传染、感召于人的,总是“崇力”的一面。他留学日本期间发表的专论文艺美学的长篇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就是这种话语最早也最鲜明、最强烈的直接表达。文中,青年鲁迅对拜伦式的充满强力的人格诗魂热烈礼赞:“索诗人一生之内秘,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前顾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文中于综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摩罗诗人”的共性时说:“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大其国于天下。”出于“崇力”,文中甚至认同将“摩罗诗人”之初祖追溯到拿破仑,将拿破仑一生功业称为“最高之诗”。末了以“摩罗诗人”之人格诗魂和救世热忱反观中国,呼唤中国有“精神界之战士”出,以“善美刚健”的“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成就“第二维新”之大业:“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苟有此种“精神界之战士”出,则“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摩罗诗力说》论及众多美学问题,关涉的历史、文化内容甚为广博,但其主旨,正如其标题所示,乃是推崇“诗之力”与“力之诗”,呼吁“精神界之战士”以“刚健不挠”之声、“殊特雄丽之言”,“令有情皆举其首”,“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说》表明,“以力为美”的审美取向和“新国”、“新民”的救世热忱,在青年鲁迅那里完全是同气相求的关系,而且,鲁迅对之毕生奉行。他晚年写的那首气韵沉雄的七绝:“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透露出来的心声、意气,仍与《摩罗诗力说》一脉相承。
探讨鲁迅“以力为美”的“社会话语”主旋律,将他与周作人进行对比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察见真谛。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侧目,原因复杂,论者亦多歧见,但若从“社会话语”的审美取向来看,很可以称为在“以力为美”问题上的不相调和。鲁迅1933年写杂文《喝茶》,讽刺了津津乐道于品茶趣味的“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感觉”变得过分的“细腻”、“敏锐”,实在是“生命进化中的病态”:“感觉的细腻和敏锐,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有鲁迅研究专家指出:“鲁迅晚年有些文章是以周作人为对象的……鲁迅的《喝茶》就是和周作人的《苦茶随笔》针锋相对。这篇文章十分精辟地勾勒出在大动荡时代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那种回避现实、不敢使自己的灵魂粗糙起来,却又变得具有病态的敏感、细腻,以致不能经受时代风暴考验的怯懦性格。”显然,在鲁迅看来,他这个兄弟太缺少阳刚之气、雄健之力。而周作人也确实于大动荡时代“不敢使自己的灵魂粗糙起来”,虽然早年也写过有“力”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和《谈虎集》、《谈龙集》中另外一些有“力”的文字,但后来却一味标举温文闲适、中正平和的审美向度,同当时一些“西化”的“绅士文人”所标榜的“费厄泼赖”精神相与唱和。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相与鼓呼
堪称双璧的“周氏兄弟”,便在随后接踵而至的、一波强于一波的“大动荡”中离心离德、愈行愈远了。平心而论,若放到大的时空范围里看,周作人所标举的审美向度无疑也是多元中的选项,于和平年代尤可伸张。但是,在光明与黑暗殊死较量的年代里,要驱逐黑暗,争取光明,更需要的无疑还是“粗糙的灵魂”、“弥满的精力”,而不是中正平和的“费厄泼赖”精神。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鲁迅的睿智与深刻,他绝不贬斥真正的“费厄泼赖”精神,但是,此种“精神”不合时宜,必须“缓行”。其杂文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缓行”二字,用得实在是格外的精审。历史剧变的“大动荡时代”,更需要的是“精神界之战士”,而不是“精神界之绅士”。同出一源,鲁迅对列夫·托尔斯泰设想的用温和、克制的宗教道德去弭暴安良的救世主张也颇持怀疑态度。1936年,冯雪峰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文译本作序,在论及外国作家对鲁迅创作的影响时,提到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看后,涂去了这两个名字,对冯雪峰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刘半农曾作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品藻鲁迅,“托”指托尔斯泰(“尼”即尼采),鲁迅亦颇不以为然。应该说,对于托尔斯泰博爱情怀的美好性和真诚性,“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是并不怀疑的。但托尔斯泰提倡的一味用宗教道德去消弭暴虐、拯救乱世的主张,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看来,显然不能作为风雨如磐、历史巨变的“大动荡时代”的救世良方,而也只能在“缓行”之列。这里,必须特别注意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全面理解认识鲁迅,而不可将他推人云端,又依据后来不断变化的“时尚”去定调毁誉。事实上,在鲁迅所说的“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里,审美一艺术行为要想为驱逐魔魇争取光明的事业效力,是必须“缓行”同不合时宜的“费厄泼赖”精神相与唱和的审美言说,而着力弘扬“令有情皆举其首”,“大其国于天下”的“刚健不挠”之声、“殊特雄丽”之言的。这已为记忆犹新的历史所证明。
二、“崇力”,是鲁迅关于“美本质”问题的深刻体认
“美”具有何种性状,或者说何种性状为“美”,是“美本质”问题中关乎审美主体认知感受方面的重要问题。对此,不同的审美主体有不同的体认。儒家以温柔敦厚为美,道家以清净无为为美,李诗豪放飘逸,杜诗沉郁顿挫,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丑为美、以颓废为美的作派。鲁迅则是“崇力”,“以力为美”。这是鲁迅的美学有关美本质问题的最深刻、最独特的体认之所在。如果说,鲁迅也有某些思想观念是“与时俱进”或者“彷徨”于“两问”的,那么,他“以力为美”的审美体认,却是一以贯之,从来没有过变化和动摇的。19、20世纪之交,西方发端于叔本华而以柏格森、克罗齐为代表的生命直觉论美学倡言“美在生命”,此种美学观念在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中影响甚大。但在鲁迅看来,这个命题还必须加一个“力”:“美在生命之力”,或者说“美在有力之生命”;“力”之于“美”是不可或缺的,仅有“生命”不一定美,只有富于“力”的生命才美!前述鲁迅的杂文《喝茶》讽刺在“享清福,抱秋心”的闲适生活中感觉变得过分“细腻”、“敏锐”的“雅人”乃是表现出了“生命进化中的病态”,于此亦实可反观到鲁迅在美本质问题上“以力为美”的价值取向。在曾经有过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常常用鲁迅说的“焦大不爱林妹妹”来申论他的阶级论美学观。其实在说这话的鲁迅那里,恐怕还有一层更深的、超乎阶级论之上的意义在:那位弱不禁风、以泪洗面、凄凄切切葬花的林妹妹实在是缺少了村姑的壮健和弥满的精力。
鲁迅对于萎靡、委顿的对象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乃至对于迹近柔弱的“优美”、“秀丽”也似乎带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怀疑、警惕而与之保持小心的距离。在鲁迅的作品中,“风花雪月”也偶尔露头,却往往带上了讽刺、调侃的意味。其《朝花夕拾》中的散文,除写“百草园”的那篇外,实皆无“花”可“拾”;其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前记”摆出一付欲谈“风月”的架势,可接下来的60多篇“正文”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令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是《野草·一觉》中的片段。本来令人赏心悦目的对象,在鲁迅营造的语境、氛围中,都失去了“美感”。鲁迅对“优美”、“秀丽”确然是颇有成见、不欲亲近的。当然,他绝非不能感知、不能写之,其《社戏》中寥寥几笔点染出来的江南水乡、《故乡》中如同夏夜田园牧歌般的月下瓜地,是何等明媚,何等令人神往!但这类与婉约毗邻的美,在鲁迅笔下仅属偶露峥嵘,只是成为了表明鲁迅能写之,而且写得非常出色却不热衷于写的证据。
“崇力”的美本质观在鲁迅的审美心态中扎根甚深、扩散甚广。鲁迅可谓有一个“以力为美”的“英雄情结”,青少年时代到辛亥革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时,他就曾请友人刻了三枚图章——一为“戈剑生”,一为“文章误我”,一为“戎马书生”;此间他还“经常策马在明故宫一带疾驰,并与南京城内的八旗兵竞赛”。在日本留学时,他在同学中第一个割辫断发,并留影馈赠亲友,在赠给好友许寿裳的那张上题诗述怀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03年,沙俄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意欲鲸吞之际,鲁迅在留日学生办的《浙江潮》第5期上发表《斯巴达之魂》,赞扬“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呼吁“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当“掷笔而起”,戮力抗暴,借古代异域英烈以抒发“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辛亥革命期问,鲁迅邀约同人创刊《越铎日报》,亲撰《(越铎>出世辞》,亮明该报宗旨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一般人看来,湖光山色是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鲁迅却以为“也会消磨人的志气”。鲁迅翻译外国人名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则:“不在女性人名上加草头女旁。”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鲁迅称赞白莽的诗“是林中的响箭”。在为自己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所写的广告词中,鲁迅将这部早期苏联文学名作比喻为“新文学的一个大炬火”。谈文艺作品的地方色彩时,他说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鲁迅书信集·547致罗清桢》);谈作家、作品和读者、观众的关系时,他说:“有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众,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鲁迅论“美”,几乎总要言及“力”。其杂感《秋夜纪游》中因深夜闻犬吠而生起的感受,也有“以力为美”的深意在:“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者就是。倘或偶经生疏的村外,一声狂嗥,巨獒跃出,也给人一种紧张,如临战斗,非常有趣的。”因“犬声如豹”而“闻之神怡”,因“危险”、“紧张”而“觉到自己生命的力”,这种极为罕见的“感受逻辑”,恐怕只有
在鲁迅那里才可能发生、成立。
探讨鲁迅“以力为美”的美本质观,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他晚年对木刻(版画)艺术的倾心扶掖。鲁迅被尊为“中国新兴木刻艺术之父”。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如果说鲁迅有两项空前绝后、无人可以比肩的功业,那么就是他在杂文上树立的丰碑和对木刻艺术的倾心扶掖。用“笔”写的杂文和用“刀”刻的版画,堪称鲁迅特别看重的两件有非常之“力”的“文明的利器”,这正是鲁迅“主用”与“崇力”合一的美学思想的鲜明体现。从社会功用上看,鲁迅提倡木刻的原因非常现实,甚至可说非常功利、非常单纯:“木刻不仅容易通俗而普及,而且材料容易办到,即使到了战争的时候,也是可以继续宣传的”,“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新俄画选)小引》)。而从审美取向上看,此举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鲁迅“崇力”的审美价值观。他之所以特别看重木刻艺术,完全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木刻乃是“全方位”地将“力”与“美”直接结合的最佳艺术门类。在1929年写的《(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中,他对木刻艺术的独特风格做了简明直截的指认,称之为“有美”、“有力”、“有力之美”的艺术:木刻“是以刀拟笔”,“是画家执了铁笔,在木版上作画……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细,然而这些之外有美,有力”,观众也可以从中感受到“有力之美”。在1934年为《无名木刻集》所写的序言中,又说木刻艺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充满新的生命”。不乏论者如此认为:“鲁迅之所以大力提倡木刻,提倡用木刻作文学作品的插图,一者因为和油画相比,木刻更易于着手而便于流传,再就是木刻作品具有一种‘力之美,而这后者,正是鲁迅先生所喜爱与欣赏的。”(《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6日)木刻(版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艺术生力军作用,尤其在延安“鲁艺”,它几乎成了“美术门”里恰逢时运、独领风骚的骄子,直至五六十年代,它仍堪称中国艺坛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门类。木刻(版画)之所以有此种作为和兴盛,推究起来,一个重要的缘由,乃是得力于鲁迅特别器重“力之美”的慧眼和他敏于“顺时倡艺”的卓识远见。
如此种种或显或隐的征象,虽各有不同的因缘变现,但其中的一个“通则”乃是:皆为崇尚“力之美”的表现,皆为标举“美之力”使然。“美”与“力”在鲁迅那里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说的关系,以至有鲁迅研究专家评说:“鲁迅在理论上固然不否定人的和谐,但他更强调‘偏至,强调向恶的方向的偏至,他喜欢‘恶之声,在审美选择中强调恶的美,力的美,狂暴的美。”如果说,“不否定和谐”与“喜欢恶之声”实为两极,而鲁迅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其实又并不能简单地以“偏至”概之——另有论者就认为,“(鲁迅)价值取向的独特品格表现为既偏至又圆融”;那么,在审美价值取向“既偏至又圆融”的意义上说,鲁迅真正看重的乃是可以折冲此二极的“力之美”和“美之力”,所谓“在审美选择中强调恶的美”、“狂暴的美”,其实是用“偏至”的话语彰显了鲁迅“以力为美”的美本质观。
三、“崇力”,是鲁迅创作风格的显著征象
正是“力”与“美”结合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审美效应,使鲁迅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新文艺主潮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创作,在题材和表现方式上做过多样化的探索,这是他“尚新”的表现,但是读其作品,不论是何种题材何种表现方式,都有力透纸背、撼人心魄的震撼力和穿透力。在《狂人日记》中是对于“古久先生的流水簿”记载的“吃人”历史的激愤控诉;在《药》中是对于愚昧的被拯救者与孤独的拯救者的无限悲悯;在《孔乙己》中是对于冷漠与迂腐的同时鞭挞;在《阿Q正传》中是对于麻木与自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祝福》抨击了“礼教”与“神权”对善良弱小的无情绞杀;《高老夫子》、《肥皂》以“诛心”之笔撕破了道学先生双重人格的假面;《故乡》中记述的“我”与那月下瓜地里手持钢叉刺猹的少年闰土的友谊,原是用来谴责沧桑的无情和更无情的人间尊卑秩序;《伤逝》中可爱的“油鸡”和依人的“阿随”也随同主人的爱情婚姻悲剧一齐叩响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警钟!鲁迅的作品中还经常用石雕、铁铸般的意象去构造比喻刻画人物。如《故乡》中在生活的重压下神情变得麻木呆滞的闰土:“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孤独者》中因祖母去世而悲恸至极的魏连殳:“他却只是兀坐着号眺,铁塔似的动也不动。”《故事新编·奔月》中愤怒的后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故事新编·理水》中执着的治水大臣:“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一样。”此类“石像一般”、“铁塔似的”、“岩石一般”、“铁铸一样”的比喻,与其说是贴切生动地刻画人物的需要,毋宁说是鲁迅偏爱“力之美”的艺术思维惯性使然。鲁迅的古体诗也特别善于表现两种力量对抗时进放出来的激越和力量隐伏时蕴积的勇猛,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如磐夜气压城楼,剪柳春风导九州”;“横眉冷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至于鲁迅的杂文,他本人曾豪迈地自诩要将其打进“高尚的文学的殿堂”,而评家则称之为“投枪”、“匕首”,不言而喻,其生成的两个基础也是“美”和“力”。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更堪称“力”与“美”互相鼓铸、激扬的集大成之作:“绝望”与“希望”、“冰谷”与“死火”、“人间”与“地狱”、“复仇”与“杀戮”、“大爱”与“大恨”、“旷野”与“星空”、“石像”与“墓碣”、“过客”与“路人”、“庸众”与“猛士”、“战叫”与“沉默”、“光明”与“黑暗”、“生者”与“死者”、“过去”与“未来”、“大欢喜”与“大悲悯”、“大火聚”与“曼佗罗花”、“南方的雪”与“朔方的雪”、“铁刺般的树”与“小粉红花”……在字里行间奔突跳阆,旋转升腾,闪烁明灭。“激情”与“冷脑”营构的巨大张力在这里时而凝聚,时而喷薄,令人瞠目、噤声、骇觫、惊怖,但是亢奋、偾张,而绝无萎靡、怯顿。其中特别撼人心魄的情景,是《死火》中那幅可谓中国文学中绝无仅有的象征当时“精神界之战士”的严酷处境和抗争精神的“冰谷烈焰”图:
……有炎炎的形,但毫不动摇,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围……
这是极为独特的鲁迅式审美一艺术思维的结晶,其构想显然得力于佛经中明珠缀结、互相映现、重重影明、重重互现的“华严帝网喻”的启示。姑且不论其中寄寓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就纯粹的“美感”而言,这是一幅由高峻的“冰谷”
与热烈的“火焰”凝合起来的奇瑰景象,刚健之“力”与崇闳之“美”就在其中“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了!
《野草》中凡是投射着鲁迅的肯定性情思或者折射出其自身生命意志的形象,无不有“力”,连其中出现的一个最无力的“弱者”——《颓败线的颤动》中为哺育儿女付出了自己全部生命机能和人格尊严的孱弱老妇,其“形象”的最后定格也竟然是一尊立于荒野的“石像”。由于“后代”的嫌恶,“她”被迫离家出走,“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与毒笑”,孤独地立于深夜的荒野中,以“无词的言语”质问苍天。“她”那“石像似的”身躯在“颓败线”上“颤动”,“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颤动,仿佛暴风雨中荒海的波涛”。这“荒野”中的“石像”正是当时的鲁迅自况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处境及其内心世界的象征:在绝望、冷寂和孤独的底下,涌动着熔岩、地火和惊雷。
《野草》中偶尔也宕开一笔,点染出“优美”、“秀丽”的诗情画意,如《雪》中写到了“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雪”,描绘了“杏花春雨”式的温煦画面;《秋夜》中写到惹人怜爱的“小粉红花”在“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但前者是用以烘托那“闪烁”、“旋转”、“升腾”,敢于同“凛冽的天宇”搏斗的“朔方的雪”的美与力,后者则是反衬窗外那两株直指苍天的有着“铁刺般”枝干的“枣树”的劲健与昂扬,通篇用意仍然是渲染崇闳之美与刚健之力。
在《野草》的最后一篇《一觉》中,对托尔斯泰设想的一味用温和、克制的宗教道德去弭暴安良的救世主张颇为怀疑的鲁迅,却对托尔斯泰留给文坛的一则掌故——因有感于不可摧折的野花劲草而写下赞扬高加索山民之强悍生命力的小说《哈泽·穆拉特》——表现出了特别的经心和由衷的激赏,并生发酬唱:“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我记得托尔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动,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这里,正是对神圣不可摧折的“生命之力”的惊奇、憬悟和感动,使鲁迅同托尔斯泰这两位在救世主张上不相与谋的哲人却在“以生命之力为美”的观念上发生强烈共鸣。这个在《野草》中有“点睛”之意味功效的“野蓟意象”,实可引人领悟《野草》的题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野草》,其最激越的旋律,也是最深刻的思想,就是赞扬“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的顽强生命力。总而言之,这部堪称中国现代散文诗绝唱之作的《野草》,乃是鲁迅郁勃、偾张的生命强力所催生,是鲁迅“以力为美”的美学思想最为集中的艺术化体现和最为璀璨的具象化结晶。正是在“崇力”的审美取向上,《野草》与《摩罗诗力说》恰好构成了鲁迅的“创作实践”与“理论阐扬”之间的互相观照和彼此呼应。《野草》固然是鲁迅的作品中着意熔铸“力”与“美”的典范,但它的基质充盈弥漫于鲁迅的全部作品之中。批人是比较注重以温柔和煦之美去“育人”、“化人”的话,那么鲁迅更看重的则是以刚健崇闳之美去“撄人”、“立人”,去唤起人、鼓舞人、振奋人:“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顾瞻人间,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摩罗诗力说》中阐扬的这个“诗力”说,正体现了鲁迅的人格诗魂而且鲁迅将其奉行了一生,在风云际会、“新声争起”的中国现代新文艺、新文化史上,“他用如椽之笔,塑造了一个坚持战斗、自强不息,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巨人形象。这个形象虽不存在于他的小说当中,但从他刻画出各色各样人物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从他的著作中或赞扬或鞭笞的社会历史现象流露出来的爱憎来说,这个形象正是鲁迅本身——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向往的‘精神界之战士”。1936年10月,鲁迅溘然长逝,覆盖他的旗帜上大书“民族魂”三字。可以说,锻造这颗“民族魂”的重要元素,正是“美”与“力”,正是崇闳刚健的“力之美”与美伟雄丽的“美之力”。开创中华文明新运,复兴中华伟大文明的壮丽事业,呼吁这样的“民族魂”,需要这样的“民族魂”。
参考文献:
[1]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3]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5]宋庆龄等,鲁迅回忆录(一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6]钱理群,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7]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校:谭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