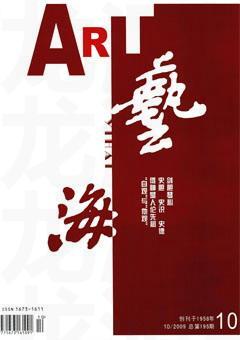史胆 史识 史德
文忆萱
我国历时三十年的十大部文艺集成、志书,在2009年10月份全部出齐。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史无前例的工程。《中国戏曲志·湖南卷》,为《中国戏曲志》之先行卷,于1989年9月出版,至今也过去了二十年。当年参与修志的同仁,不少均已辞世,我这幸存者,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从1981年开始接触编纂专业戏曲志书任务起,到现在整整二十八年,在这漫长岁月中,不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去回顾一下,既感到幸亏在那时编出来,总算完成了一项历史任务:也不无遗憾,以当时的认识水平,还达不到修志应有的高度。这遗憾,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认识的变化,似乎也在增多。
我的同辈人,都属于“老戏改”出身,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从事戏曲改革工作的专业干部。我们开始是从事辅导工作,日子长了,就在戏曲的文、论、表、导、音、美方面,拣性相近的一项研究开始,并逐渐专注于一行,自然而然就只在这方面探索。多年来,不但从来没人想过修戏曲志,连方志都看得不多,忽然要修戏曲专业志书,还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有点惶惶然、茫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不管怎么说,从事了三十年的戏曲工作,居然赶上了“盛世修志”,而且是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我们得以恭逢其盛,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再难也得承担。但激动是一回事,现实的残酷又是一回事。
我们省艺术研究所前身——湖南省戏曲工作室,在“文革”之前,积累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不仅有文字、图片资料,还有些文物;有各剧种主要唱腔的录音、记谱和各地方大戏剧种的全部脸谱。但“文革”期间,损失最“彻底”,片纸只字无存,什么也没留下。甚至一些个人的笔记、文稿,都在“抄家”时全部抄去,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没资料,修志从何着手?
当时,《中国戏曲志》编辑部,由汪效漪、薛若琳、周育德、刘文峰四位同志来湖南动员我们上先行卷。我们既感到荣幸、振奋,却实在畏难。那时我们首任所长金汉川同志也不敢轻易表态,只是反复和我们座谈、讨论。经过反复论证之后,才做出决定。作决定之前,老金还问我们:敢不敢立“军令状”?这是激将法,我们这辈人,自认修志责无旁贷,一致表示:愿立军令状,才接下这先行卷的任务。
所谓先行卷,也就是《中国戏曲志》中出版的第一本,先行一步而已。但“先行”就意味着没有可师法、借鉴之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前进。有些遗憾,可能就是“先行”所致。
我们第一步仍然是传统方法:从上到下,发动群众,先修剧种志,以便于动员更多的人来广泛地收集资料。
湖南全省有十九个地方戏曲剧种。我们动员凡有本地剧种、专业剧团的地、市、县文化部门,都组织力量加入修剧种志队伍,成立了十九个剧种志的编纂机构,全面地展开收集资料的工作。那时,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从省到地、县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业务骨干,不少都是落实政策回来的同志,没受太多“文革”流毒的影响,所以没什么大的阻力,很快就在全省铺开了工作。许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都是识途老马,凭记忆知道在什么地方还可能重新获取资料;各剧种也还幸存了一些老艺人,他们不但本身可以提供资料,而且还可以提供某些资料的线索;各地还有些老戏迷、老观众,也能够供给一些宝贵的资料。各级从事修志的同志,足迹不仅踏遍三湘大地,连邻近的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许多有关地方都去了,走访了一些幸存的老艺人和当地耆宿。同时,也几乎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档案室、资料室,爬罗剔抉,细心搜求。编纂、收集和受访对象,总人数在千人以上,这是一支庞大的修志大军。没有这支队伍,想迅速恢复大量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与此同时,我们从1980年就开始的各主要剧种代表性传统剧目的教学演出、录相工作仍在进行,也同时抢救了不少资料。这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特别是张庚、郭汉城两位前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我们那时哪有录相条件和经济能力,都是研究院的李愚、刘沪生率领录相队的同志,无偿地帮我们录制了200多个小时的形象资料。这些工作,当时只觉得是该做的事,事后回头一看,真是侥幸,总算抢得时机,不是抢得快,人亡艺绝,有些资料可能就恢复不了。几个主要的剧种志写出初稿时,就集中一批力量开始编纂省卷。编纂志书最困扰我们的是两个字:“直”和“志”。
“直”,志书是官书,是信史。我们对前人的志书虽读得少,史书还是读过一些,二十五史都是官书,但是否全“信”,治史者和读史者都知道。今天,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来写,应该成为名符其实的信史。我们如何面对这个艰难的标准秉笔直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界的风风雨雨,如何记述?给我们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要求:粗要能说明问题,细要不损害党的形象。说来容易做来难!
“志”,在文体上,必须写得像志书,而不是总结、不是调查报告,不是学术论文,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几十年已形成习惯的文体、文风,探索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二十世纪的志书新文体,这也并非易事。
有什么办法?摸索!我们试写了二十个条目的例文,从上到下反复地讨论,广泛地听取意见,不断地修改,《中国戏曲志》编辑部的同志也和我们共同研究。汪效漪等四位,记不清先后几下湖南;我们也派出多人次几上北京。经过广泛的、审慎的推敲,定下了第一批条目。这样,才正式着手全面编写。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拿出《湖南卷》的初稿。又经过两年的修改才算定下来。
1987年省卷交稿之后,我们既为完成原定计划,也因资料较多,不可能全部用于省卷,必须慎重保存。于是按照《湖南卷》模式,正式设计、编纂出全省十九个地方剧种志,出版了一套《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五集、230万字,并于1991年全部出齐,也算抢了个先,是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套全省剧种志丛书。
抢先,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留下来的遗憾可能比其他省卷多:因为时间短,收集资料难望更广泛:因为没经验,每走一步都在探索,考虑不周之处更多。
湖南卷1989年出书,全书98万字。但就在这时,这一卷的责任编辑汪效漪、机构部类主要编纂人陈青霓、表导演部类主要编纂人蔡倜先后辞世,陈、蔡二位只在病床上看到清样,不及见书。地、县编纂人员和提供资料的老艺人不少都没能见到成书,使我们健在者深感遗憾。
回顾这段历史,首先要感谢编辑部的四位同志,如果不是他们一再动员我们上先行卷,我们就很可能贻误最佳时机,不能即时抢救到许多资料,也不能得到这些识途老马的辛勤付出。如果晚修五年,难度不知要大多少,甚至有些资料可能无法找到。
修志的成果自然是主要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除二十五史官修正史而外,各种史籍浩繁;志书除大量的地方志、通志而外,还许多专业志。大概是地球上史、志类书籍最多的国家吧。但是,《中国戏曲志》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戏曲专业志书。虽说中国戏曲的出现,晚于希腊和印度,但自从发生、形成之后,不仅近千年从未绝迹于舞台,而且不断
发展、壮大,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全球绝无仅有的民族艺术独特现象,本应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在历史上却不被重视,不能登大雅之堂,于史无征。我们从正史上获得的资料,多半是反面记载:禁戏之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曲获得应有的地位——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得到党和政府特别的重视,终于有了第一部专业志书,开历史之先河。这件事本身就将载入史册。
湖南地方戏曲艺术,属于湖湘文化。但是,其遭遇和全国戏曲一样,不为历代官方重视,只有近代部分,湖南戏剧家的论著中涉及到。《湖南卷》这本志书,大体梳理出湖南三湘大地地方戏曲发生、形成、流布、发展的轮廓。在这之前,我们中虽没有专门研究戏曲史的人,但前人的戏曲史论著都读过。前人治史,大多是从书籍中发掘史料,而见诸文人笔下的多为城市戏曲活动的记载,民间的很少。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民间正式演出,只有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中元节”条内那二十六字的记载:“构市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东京梦华录》是记作者于北宋崇宁癸未(1103)到靖康丁未(1127)年间在北宋东京的见闻,和湖南扯不上联系。我们在修志期间,却在《浏阳县志》卷十六“职官”二的“政略”中,发现杨时在北宋绍圣元年(1094)知浏阳县事时,就曾有“凡酒肆食店与俳优戏剧之罔民财者,悉禁之。”的“政绩”记载。这被禁的“俳优戏剧”而且能“国民财”,明显是一种营业性的民间演出,却比孟元老入京早了近十年。说明在当时湖南浏阳就有营业性的民间戏曲演出活动。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个重大突破,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关于湖南戏曲活动最早的记载。这条史料进一步纠正了多年的一个误区:在这之前,不少人认为是明朝初年“扯江西,填湖南”,由江西人带来了弋阳腔,湖南才有戏曲;或者是明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时,各赐剧本,湖南地方戏曲由王府戏曲而来。这条史料以及我们辑录的夏庭芝《青楼记》中的一些元杂剧艺人在湖湘间的活动,都说明最早进入湖南的民间戏曲情况,为今后治史开阔了视野,它提醒我们应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民间的戏曲活动研究上。
通过修志,对全省的民间小戏剧种也作了一次科学地、严谨地规范。“剧种”一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正式广泛使用的。虽然在湖南“湘剧”和“祁阳戏”二词早就见诸文字,但并未被普遍运用,艺人和社会上都习惯称戏班班名或某地班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对湖南地方大戏剧种已基本明确、界定。但民间小戏却比较紊乱,如各地的花鼓戏,在解放前,湖南有些地方禁唱本地花鼓戏却不禁湖北楚剧,湖南境内一些花鼓戏班则改称为楚剧班。这种现象在1951年全省第一届戏曲会演之后,虽得以纠正,但各地习惯却只冠剧团所属地名,称某县(市)花鼓剧团或某地剧团,而没有标明所属剧种,使广大观众始终闹不清湖南有多少种不同的花鼓戏。经过十年“文革”,不少剧团已原气大伤,难以恢复,剧团数量大减,而且有不少剧团改称文工团(队),年轻演职员甚至闹不清楚自己演唱的属何种剧。通过编纂剧种志,得以为各地花鼓戏剧团正名,分别标明长沙花鼓、衡州花鼓、零陵花鼓、邵阳花鼓、常德花鼓、岳阳花鼓六种,使观众能对剧种有所区分。而花灯确有三种不同流派,因为已没有专业剧团,就作为一个剧种分别记述清楚。湘西阳戏则仍按习惯叫法加以记述。而少数民族的侗剧和苗剧,是在这次修志中才正式载入史册。这不但使湖南人了解到全省地方戏曲全貌,也使观众看戏时弄清了剧团的所属剧种,使各级文化部门的年轻人得到一次专业学习的机会。
由于参与修志的有大量从事了三十年戏曲工作的人员,都能认识到中国戏曲艺术的主要宝藏,不仅是留有浩瀚的文学剧本,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近千年的表演艺术。中国戏曲是以演员为中心的艺术,湖南戏曲也不例外,各剧种在表演上,有许多珍贵而独特艺术,是几百年来前辈艺人的毕生心血。我们统一的认识是:重在记艺。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多少民间戏曲艺术家湮没无闻。在这部书中,我们尽可能找到部分有代表性人物的业绩而立传,使后人知道前辈名家的艺术创造,就是这类历代名家的积淀,才有今天的丰富艺术遗产。找不到人的,则在其他一些条目中,基本贯串了这一要求,把历史上的一些表演艺术尽可能记录下来。许多戏已迹近失传,能为后世留下些可资探求的记载,也是好事。
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戏曲改革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作了相当有份量的记录。特别是“文革”前那些经过整理加工的优秀传统剧目如《琵琶上路》、《醉打山门》、《打猎回书》、《思凡》、《刘海砍樵》、《五台会兄》、《祭头巾》、《昭君出塞》、《打差算粮》、《捞月》、《盘盒》、《破窑记》、《李慧娘》、《追鱼记》等一大批优秀剧目,都成为长期保留的瑰宝,得以载入史册。这些戏,虽然是前人的艺术成就,但在历史长河中,蒙受了许多历史的尘埃:有的戏对人物有所歪曲:有的被强加以宣扬封建道德的主题;有的则留下一些低级庸俗的内容。在戏改工作中,经过戏曲工作者和艺人的通力合作,精心整理,不断地进行艺术加工,扬其精华,除其糟粕,使其重新绽放艺术的光芒,这是解放后五十年代戏曲改革的丰硕成果。至于“大写十三年”期间,确为优秀节目的《打铜锣》、《补锅》之类,也同样载入史册。在对这些剧本加工的同时,对音乐、服装、化妆、道具上的改进和舞台美术上的设计,都得到具体地反映。
修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全省资料搜集,查证、整理、分析、综合的过程。通过修志,为我们这个建立不久的研究所储备了资料,为全所此后的集体、个人的研究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作进一步研究开拓了视野,在成书之后的年月里,许多课题、专论都是由此引申而来。如我所建立过相当久的目连、傩戏课题,以及在剧种史、声腔、表演、脸谱、古戏台等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有一批人写出了不少专著、专论,都和修志积累有关。
我们所做过的工作,大概也就只有这些。但是,《湖南卷》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把所收集到的资料整理、精选、保存下来,既可使后来者略知概况,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和参考;也可为今后湖南戏曲的发展、创新作为借鉴。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编纂了本关键性的书籍。
近二十年中,一些业内人士在工作中以志书作为参考资料:一些湘籍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都引用了湖南这两种志书;同时,这两种志书也被海外汉学家所收藏,说明确实具有一定价值。
但是,回顾我们的《湖南卷》以及《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确实有许多遗憾。这里,只就《湖南卷》谈些个人的反思,因为《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是照《湖南卷》“比葫芦画瓢”完成的。仅仅增加了“全省各剧种传统剧目总表”和“修志大事记。”前者是为趁机留下一份剧目总册,而后者则是想使这么多修志人的劳动不至于湮没无征。
经过二十来年的反思,我提出这“胆、识、德”三个字,是有切身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