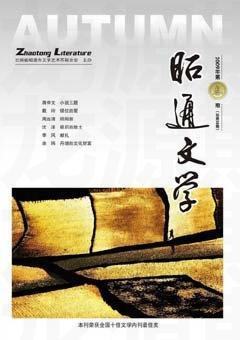如期来临的黄昏
蔡发玉
一
家具厂厂长到工棚里来通知开会的时候,看到正在干活的工人寥寥无几,偌大的工棚里乱糟糟的,工友们的马凳横一条竖一条地放着,地上的刨花好久没打扫了。厂长老朱知道负责打扫工棚的老许这段时间在闹情绪,有心想去说老许几句,但又想着厂里都好久没给老许开工资了,说起来还是不能怪人家老许,人家大老远的从乡下来到厂里,看厂都看了一二十年了,说起来还不是为了每个月那几十元钱。以前家具厂兴旺的时候,倒是从来没拖欠过老许的钱,每个月总是由老朱签了字,再从会计那儿支付给老许,可家具厂现在的情况比不得前些年,不要说老许看厂打扫工棚的钱,就是工人们干完活,都是先把做好的家具交给厂里,在会计那儿记着,要等家具卖出去了,然后再按照交活的多少领钱。前几天厂里的退休老工人们又追到厂里来了,一来就呯呯呯地敲老朱办公室的门,幸好当时老朱正好在厂区外围转悠,一听到动静就躲起来,根本不去跟他们见面。老朱知道,这帮老工人来找他,目的不外乎就是找他解决他们的退休金。因为以前厂里是答应过工人们,说等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厂里每月是要给他们每人发上三十来元退休金的,而且在厂里情况好的时候,也兑现过一段时间,可自从前年厂里资金陷入困难,这笔退休金就被自动废除了,以后再没人领到过一分钱。为此老工人们意见很大,隔三差五的跑到厂里来,一来就要找厂长老朱,说他们在厂里都苦了一辈子了,图的还不就是到老来有个靠头,怎么答应了的退休金,到最后却一分不给了。一开始老朱还给他们耐心解释,说厂里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不太好,等以后缓过来,再想办法给他们补齐。可老工人们不买老朱的账,他们说厂长说得倒是好听,等以后补齐?现在都不给,以后找哪个要?再说我们倒是想等着以后,可又不可能把嘴巴缝起来,等着以后再吃饭,都是些七老八十的人了,再等就等着钻土了。老朱晓得自己说不过这帮老工人,惟一的办法就是躲着不跟他们见面。为此老朱专门跟老许以及厂里的会计等人说,只要是这帮老工人找来,不管他在不在厂里,都要跟他们说开会去了,或者说他出差去了。老朱自此以后来到厂里,都是一个人悄悄摸进厂长办公室,一进去就把门关上,有人在外面敲门,老朱在里面连气都不吭一下,让敲门的人以为里面没人。老朱觉得现在当这个家具厂的厂长实在是有点穷于应付了。
老朱摸进工棚去的时候看到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在干活,都是平时经常在厂里的几个年纪大点的工人,其中有个王帮国,是六十年代那会儿跟老朱一起进厂的。跟老朱一起进厂的有好几个人,除了老朱后来被提拔做了家具厂的厂长外,其他的人都一直在厂里做普通工人,不过是虽是普通工人,但别人的路数都比这个王帮国宽,见厂子里的效益不好了,个个都到外面去找事情做去了,只有这个王帮国,就这样一直跟几个乡下木匠在厂里混,脾气还大得很,见什么都不顺眼的样子,一会儿说厂里的这不对,一会儿又说厂里的那不是,让厂长老朱心烦得很。本来嘛,你王帮国一个干活的,想来就来干点活,不想来就别处去想办法,反正也就是做点计件活,犯不上管这管那的,可这个王帮国偏偏就是想不开,总是要多嘴多舌的。老朱一走进工棚看见王帮国,眉头就不由得皱了一下。不过厂长很快就恢复了平时的表情,厂长老朱不想让王帮国看出他老朱不想见他,老朱想现在厂子里的事这么多,他不想再生事端,厂长觉得他一个厂长要有厂长的肚量,尤其是现在,正事都忙不过来,何必跟这个王帮国一般见识。
厂长老朱很快把晚上在厂里开会的事情说了,连坐都没在工棚里多坐一下,就站起来走掉了。老朱还得到好些工人家里去通知,说起来是开会,可就是那十来个工人,这会就未免开得太寒酸,简直就没有个开会的样子了,因此老朱觉得还是再去通知一下其他的人来,再说老朱还有好些事情要讲,不去把人些多喊点来是不行的。老朱一边走出家具厂,昔日热闹而今门庭冷落的厂区大门,一边在心里感叹,想不到过去红火的家具厂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想不到我老朱为了不跟几个老家伙照面而东躲西藏,唉,这日子都过到什么地步了!老朱想起厂子红火那阵子,那时候的日子是多么的舒畅,每天厂里有许多的业务往来,人们老远见了他,就热情地问厂长吃饭没有厂长今天忙啊,可如今,有哪个还会老远跟他打招呼呢,又有哪个工人会一看见老朱,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工具,等着厂长跟他握手呢。如今人们见了老朱,就跟见了一般的人一样,该走路照样走路,就仿佛他这个厂长不存在一般。老朱一边想着,一边觉得鼻子酸酸的,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啊,只要你势头一不在了,就再也没有人拿你当回事了,如今的人都势利得很,有钱有势他就认得你,等你没钱没势了,哪个还会拿你当回事!
老朱整整跑了一大早上,把心里记得的人家通知了个遍。老朱去到这些人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在,家里人听老朱说厂里开会,只说要得,等回来了我们告诉他。老朱晓得这些人虽然不在厂里做了,可人家出来照样是找了事情做的,老朱明白自己亲自跑这一趟是多余的了,可来都来了,该说的话还得说到。当然也有本人就在家中的,老朱就把开会的事情对他本人说了,还说一定要来,大家难得在一起吹一下,再说厂里也有些事情要通知,就当是到厂里来耍一趟。在家的人就答应了,因为已经是接近吃午饭的时候了,就带口留老朱吃了饭再去,老朱说不了。人家也不多留,老朱就告辞出来,一个人回家去了。
晚上老朱掐着时间到厂里。工棚里吊着的一只一百瓦的大灯泡亮亮的,照着马凳上三三两两的工人。厂子里都好久没这样亮堂过了。老朱看了一下,出乎老朱的预料,大多数的工人还是来了,三三两两的,抽的抽烟,吹的在吹散牛。老朱看看开会的时间都过了十来分钟了,想想没来的肯定是不会来了,于是就宣布开会。以前开会老朱都是有话说的,会开得也闹热。可今天一开始,老朱就觉得似乎找不到话。老朱酝酿了好长时间,大家也就静静地等着老朱。老朱独自一个人面对大家蹲在一只靠门边的马凳上,慢条斯理地说了起来。老朱说厂里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本来说起来是没有什么会可开的,可前两天局里面把各个厂的厂长召集了去,说厂子要么宣布破产,要么就要厂里把生产搞起来,像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局里面就要派人下来清点资产,银行要接收拍卖了。老朱说这话的时候工棚里闯进来一只蛾子,先是在人们头上东一阵西一阵地乱飞,好几个人站起来扑,却怎么扑也扑不着。后来蛾子掉在地下,旁边的林木匠趁机用脚踩死了,工棚里才又安静下来。人们继续听老朱讲话。老朱接下来说,要是让人家银行来接收拍卖,厂子也就不存在了,这么大的事,他一个人说了不算,今天把大家召集拢来,就是要让大家拿个主意,看看到底要怎么办。
老朱的话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开会的意思了。其实说起来,轻工局的单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基本上都是些垮台的集体单位,包括家具厂在内,绝大多数人都得出去自谋生路,不出去不行,在厂里拿不到钱,可一家老小要吃要喝,不出去找事情做日子就过不下去。赖在厂里一直没出去的,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人,他们的日子自然也就过得青黄不接的,日子很不如人。厂子对于大家来说,早就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按道理来说,大多数人也都不在乎厂子宣布或者是不宣布破产。老朱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也以为是走一下形式,到最后还是得走破产这条路。可令老朱想不到,当老朱的话刚一说完,包括王帮国在内的好几个老工人就吵起来:谁说要宣布破产了,谁说厂子就不存在了?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厂子,怎么说破产就这么轻易宣布破产了?一边是老工人们在竭力争吵,另一边是年轻些的人,闷在一边不讲话,看老工人们跟厂长吵。说老实话,老朱原本对于家具厂这个烂摊子,已经是没有抱多大的指望的了,老朱原本的意思是借开会把厂子宣布破产的主意拿定,却想不到老工人们会横插上这一杠子。老朱心有不甘,把头转向年轻些的人聚集的一边,问:你们看呢?初初问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讲话,脸上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等老朱问得狠了,才有人搭上一句,既然大家都不同意破产,那就不破产好了。老朱没想到开会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没办法,老朱最后说,既然大家都不同意破产,那就还是把生产搞起来,局里面等着我们拿出方案来,大家商量一下,看以后要咋个整,不要厂里面人影影见不到几个,到最后却说我老朱不关心厂子的发展。老朱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面是带了些气的,他早上去通知开会的时候,是把会计和出纳都通知到的,却想不到工人们来了不少,会计和出纳却连鬼影影也见不到一个,这真的是做得太绝了。想起来厂子红火那阵子,我老朱就从没亏待过这些人,每逢过年过节的,我老朱哪次给他们给得少了?每回不是一千就是八百,说出去都让人眼红,有好多次都是几个人悄悄分了完事,为的就是不让工人们晓得,可到最后人们还是多少知道了一些,为此厂里的工人都恨死我老朱了,还说这个厂子就是我老朱家开的,我老朱想给哪个发钱就给哪个发钱。想不到现在厂子不行了,我老朱说话没有过去管用了,这些人就不买我老朱的帐了,甚至连通知到厂里开个会都不来,真的是太没有人情味了。老朱心里带了怨气,又怕再得罪厂里这些工人,毕竟自己现在比不得以前,人家虽然只是厂里的普通工人,但说起来人家也是靠卖力气吃饭,帮厂里干活还不如帮外面的私人,所以就是跟你老朱争吵起来,也是威胁不着人家的,再说以前老朱得罪的人也太多了。本来厂里的人大多对老朱怀恨在心,虽说现在时过境迁了,但毕竟心里是有芥蒂的,说话还得注意着点。怀着以上的心思,老朱的话就说得有几分委屈,有几分推卸责任的味道。不过在场的工人没注意这些,他们有的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有的呢,则想着厂子要是真的宣布破产了,这以后厂子答应的退休金找谁要呢,都为厂里苦了一辈子了,眼看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厂里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呢?于是工棚里一片吵嚷之声,好些人说要让大家来厂里干,厂里也要开得起工资呀,像现在这样干了活都领不到钱,难道要家里人把嘴缝起来不吃饭了?应该说,工人们说的自有他们的道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这样的话是应该的。可这些话就给了老朱一个难题:局里面的意思是要老朱把大家重新组织起来,通过生产把厂子重新救活,可具体的问题摆在眼面前,不解决工人们说的问题,这生产又如何能够搞起来?不过老朱现在不想多找心来操,他想厂子不管是好是歹,他老朱都不想多管了,他只想把问题重新反馈回局里面,让局里面的领导来定夺。因此等工人们吵得差不多了,老朱就借坡下驴地对大家说,我老朱明天就把工人们说的问题向局里面反应。老朱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他现在是不想当这个厂长了,要不是局里面一定要他出来主持工作,他早就想撂挑子了,当这个烂厂长,有个球的意思!不过老朱没把这话说出来,他嘴上敷衍着,把个会草草结束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走了,这时外面传来吵嚷声,原来是退休的工人听说厂里开会,赶着堵厂长老朱来了。等他们赶到工棚里,人早都散尽,老朱听到风声,早就从值班室的后门溜走了。
王帮国混在几个工人中间,一边走一边想,其实局里面的想法是正确的,都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大家都不到厂里来干活,这个厂哪里还会有重新恢复起来的可能呢,其实局里面早就该拿出个方案来了,要不然任由厂子就这样半死不活地下去,国家就是不宣布破产,厂子迟早也就是个垮字。要按照他以前的脾气,他是见不得老朱这家伙的,要不是他私心太重,家具厂怎么会到这一步呢,说起来这个厂子都是败在他的手上。不过,王帮国还是从心底里希望厂子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毕竟大半生时间都在这个厂里过来了,厂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是对厂子抱了很大的希望的。王帮国按捺住心中的不满坐在一帮工人中间,听老朱把话讲完了,忍不住问了老朱一句:厂子里的事,说到底以后是个别领导说了算,想把厂子咋样就咋样,还是要把工人们聚拢来大家商量?也不晓得老朱是有意装没听见,还是当时太吵了,老朱的的确确是没听到,反正当时大部分工人都在争着发言,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朱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人注意到王帮国说了些什么。
二
那天晚上厂长老朱召集工人们开过会后,第二天就到局里面去把大家的意见向局里面反映了。局里面让老朱草拟出个方案来。老朱于是就对老局长说,他是不想当这个厂长了,因此拿方案的事,局长是不是重新找人干。老朱的话一说完,老局长当时就发了脾气,说你现在想撂挑子了,当时厂子红火那阵,你怎么不说你不想干,现在你说你不想干了?厂子出了这么多事情,说来说去,还不是局里面给你们顶了过去,可现在你却说出不想干的话来,你说说看,你现在不想干,有哪个想干得很!老局长的话一说就说到老朱心里去,因为前些年厂子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厂里跟外地人做生意,却想不到一下子被骗去三十万元钱,三十万元!这在当时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因为当时的许多国营厂子都有不起这个家底,而家具厂却一下子就损失了三十万元,这说起来还是厂里刚刚从银行抵押贷来的钱。厂里的工人晓得后,纷纷找到局里面去,要求追究厂长老朱的责任,说老朱还不是贪图人家的回扣才上的当。当时老朱都被公安局喊去了的,原以为自己无论如何都是逃脱不了判刑坐牢了,却想不到局里面硬是派人去作担保,说老朱只是改革心切,上了人家的当,其主观意图是好的,就这样左说右说才把老朱给开脱了出来。那件案子自那以后一直摆到现在,至今也没能破出来。老局长提到厂子里出的事,老朱自然心里是有数,而且老朱对局里面的老局长等人也是心存感念的。如今老局长硬要老朱继续当起家具厂的厂长,老朱虽说有心不当,可当着老局长的面,老朱是无论如何都不好意思再推脱了。老局长见老朱默不作声站在一边,以为老朱是想通了,口气放缓和下来,让老朱坐,还给老朱泡杯茶,并且宽慰他说,他也晓得厂里的事不好办,可再不好办也得有人干,要是大家都知难而退,那轻工局这一大摊子的事情还有哪个来做?老局长还引用了时下一句时髦的话,让老朱要“激流勇进”,不怕受挫折不怕摔跟头。老局长是个外地人,五十年代末期随工作队到这儿来搞土地改革,搞完土改后就留下来工作,并且还在这儿娶妻生子成了家。平时大家都晓得老局长是个头脑简单实在没有多少文化的好人,把什么人都往好处想,他认为老朱是他看着进厂并且一手提拔的,对于家具厂的厂长老朱他是了解的,因此每次老局长在局里面见到老朱后,都是不厌其烦地说上一通大道理。他觉得这是他对干部负责的表现。那天老朱在局里没有推掉厂长的职务,回家去后心里闷闷的,心想干脆来个不管不问算了,可又想着前些年发生的那件事,又生怕老局长一生气不管他了,他知道那件事至今都还没消案,要是厂里有人重新去顶着告,他老朱怕是就劫数难逃了。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个好的主意,心想只有硬着头皮先干着了。既然要干,老朱还得主动再去找厂里以前的几个干部,让他们都坐拢来,大家好商量出个主意,好歹好跟局里面交差。想到这儿,老朱忍不住长长地叹口气,心里面觉得做人真他妈的累,以前老朱听别人这样感叹时,还觉得太做作,既然都生成个人了,该咋个做就咋个做,有什么累不累的,想不到现在自己对这句话有了如此深的感受,老朱想起一句话: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他想我老朱现在真的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了,一方面要应付局里面和厂子里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要躲避退休工人们的围追堵截,难过啊,这日子!
在局里面的再三催促和厂长老朱等人的努力下,家具厂终于拿出了方案。说是方案,其实也就是些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老朱上报到局里的方案就是围绕着这两点来说的。可是说起来简单,等真正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你想想,家具厂为什么这些年来会被私人开的家具店挤垮?说来说去还不就是生产成本高过人家,技术也不如人家的先进,做出来的家具要看样没有看样,样式老土不说,价钱还比人家外地人的贵,如此的厂子,不被人家挤垮掉才怪呢。其实老朱也晓得家具厂的问题之所在,但家具厂说来说去毕竟不是他老朱一个人的厂子,局里面要老朱拿出方案,可老朱有什么办法呢,老朱想说除了他厂长外,厂里面的会计出纳保管等人一概免去过去的月薪工资,可这样局里面会答应吗,这些人都是局领导的三亲六戚,老朱要是这样说,这不是明摆着跟局领导过不去吗?他老朱才犯不着这样!老朱也想过是不是让厂领导出面搞促销,可厂子里的这些人,单单就拿会计李小会来说,你让她来签字拿钱倒好说,可你要是说让她去整点厂里的什么事,她一定是会找出一大通理由,又是娃娃小家里有事走不开,又是她娘家人有什么事等等等等,搞得不好事情做不下去不说,倒跟他老朱整些多余的话来说。老朱在心里算来算去,只有把单价再往下压和降低材料费一项了。老朱想,如果单从价格上来说,人家私人的厂子做得起的活路,厂子里也应该做得起,他老朱设计的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因此在把方案上交到局里后,老朱又召集厂里的工人开了个会,并且把厂里的新规定向工人们作了宣布。老朱对大家说,如今厂子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像以前一样了,关于这一点要大家理解,等厂子渡过了难关,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老朱还说到节省材料上,老朱说,为什么同样是做家具,可人家外地人能够赚钱呢,一则是因为人家做得好看,买的人就图个新鲜,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只晓得看着好看就行了。二则呢,人家外地人做东西很懂得节省材料,不像我们,一件家具实打实地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材料用去了,还又笨又难看,做的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老朱最后叮嘱保管,让他在给工人们发材料的时候,注意着点,该少给的就少给。老朱的意思,是要工人们学着节省材料。他说,像人家外地人做的家具,用工用料都是很节约的,外表看上去好看,里面的内容又看不见,我们就是要学学人家。老朱还让人去进了些次品料,而这些材料过去厂里都是扔掉不用的。老朱觉得,他这个厂长只要从今以后当好厂里这个家,说不定厂子的情况真的会重新好起来。
就在老朱调兵遣将对厂子进行整顿的时候,工人们在下面开始议论纷纷了。其实,不用老朱说,大家也晓得有些外地人做的东西是很差的。王帮国跟坐在旁边的杨槐奎讲,挨着他们家坐的一个叫小老虎的邻居,在结婚的时候到四川人开的家具店里去买了个矮柜,刚刚抬进门的时候看起来还可以,样式也新,可有一天小老虎在挪动屋子里的家伙时,不小心把矮柜面子碰掉了一块,小老虎看着心疼,于是就过来请他,意思是看能不能修还原。可等他过去一看,那碰断的地方,露出来的是被压过的木屑,原来那矮柜就是用人们常说的机压板做的,一坏了就无法修,原因是钉子钉进去根本吃不住力。王帮国说,其实年轻人买东西主要是不懂,如果是懂得的人,还是不会去买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的。王帮国说,自从那次到小老虎家看了那个矮柜后,他对外地人做的东西就反感得很。杨槐奎说他就是搞不懂,外地人做的东西这样假,为什么偏偏还有那么多人去上当?杨槐奎说怕是现在的人钱都多得找不到地方放了,买东西也不图个结实。王帮国摇摇头。这时又有人发言了,发言的人说外面开的单价都比厂里的高,像这样的活做下来,工人们是不是太不合算了?老朱说厂子里开出的单价是比外面私人的低,不过这就看各人的本事,如果你做的东西能够多省出点时间,那算下来还是差不多的。下面就有人开骂,说怕是找不到卵事情搓了,要到你这个厂子里来,老子还不如去帮私人做。不过说的人说得小声,因为他根本不是为了要说给老朱听。那天的会开过后,好些离开厂子到外面混的人还是照样没来。老朱也晓得人家不来的原因,像现在厂里这个条件,人家不来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老朱也不去动员这些人。
退休的人们终于在厂子里逮到厂长老朱。可逮到了还不是逮到了,老朱只说厂子现在像这个样子,他拿着也没办法。那次老朱就坐在他的办公室的小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任几个老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老工人们拿他无法,只好吵着到局里面去找。局长的回答跟老朱的一样:厂子现在的情况不好,实在拿不出钱来,他让他们回去,说等以后厂子好起来后,有了钱一起补发。一帮白发苍苍的退休老工人听了局长的话,晓得找不找都是没多少意思了,被局长连哄带劝地哄出来后,一个个灰了心回家去,该帮着儿女做家务的帮着儿女做点家务,家境好点的干脆就靠儿女养着,各人过各人的清静日子,对厂里以前答应给的那点不多的生活费不再抱任何希望。
厂里似乎比以往多了点活力,又有几个半老不少的工人回厂来了,工棚里的响动因此比以往要大点了。附近的居民看见家门口走动的人又多了起来。老朱每天来开了门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小屋里,出纳和会计自从上次开过会后也恢复了以往的正常上班时间,因为老朱在开会的时候说过,以后他们几个干部都要来上班,如果哪个不来,厂里每个月发的工资就取消了。为了每个月开的两百多块钱的工资,李小会还是每天到厂里来了,来了后就各人坐进各人的小屋,天气冷的时候把门一关,在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里面。李小会在这段时间织好了娃娃冬天穿的毛衣,还给自己的父母一人织了一条毛裤。工棚那边工人们干活的敲打声有一下没一下的传过来,让李小会觉得日子过得真慢,她忍不住用手捂着嘴打了个长长的呵欠。
三
家具厂接到学校来订做的两百套桌椅,是局里面介绍来的。两百套,就是在过去家具厂红火的时候也不是经常能够接到这么大的订单。那天老朱正在厂里面,局长突然叫人来喊老朱过局里面去。老朱去的时候以为局长又是像往常一样喊他去过问一下局里面的事情,等他走到局长的办公室,看见那儿正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老朱认识,是县一小的老师,老朱经常在来家具厂的路上遇到的,每次老朱都见这人提一只人造革的皮包,随着一帮小学生走进学校去,因此老朱就猜测,肯定是学校的老师。老朱一进来的时候就看见这只人造革提包放在沙发的扶手旁边,跟着就认出了提包的主人。老局长向双方作了介绍,又说了叫老朱过来的目的。原来是学校里要扩大办学规模,准备找厂里订做两百套桌椅。老朱接过局长递过的教育局写的介绍信看了,又跟两个老师握了手,双方开始商定做桌椅的事。由于是局里面介绍的,价钱上就没有像以往一样要讲价还价,而是按厂里原来收取的最低价,跟学校签了两百套学生桌椅的合同。尽管老朱因为这些人没有直接来找他,而是先找到局长那里去,心里面感觉到有些不快,但想着厂里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接到这么多活,今后两三个月内厂里就是不接其它活也没关系了,老朱还是由衷地舒了口气。
在跟学校的人签好了合同后,已经是下班时间了,老朱想着应该约上老局长和这两个学校的人到馆子里吃上一顿饭,这在过去厂里业务多的时候老朱经常是这样做的,这是生意场上的惯例,今天老朱签好合同后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点。没想到老朱刚一说出到外面吃饭的邀请,两个老师像被吓着了一般连连摆手拒绝,说不敢这样做,不敢这样做,还说要是让学校知道了,脱不了爪爪。两个都把吃一餐饭当做了了不得的腐败,连脸都变白了,看样子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再加上老局长也在一边说那就算了,老朱便只好作罢,大家一起出来,两个老师先告辞走了,老局长也各人回去。老朱一边走在路上一边想,怪不得社会上的人都说现在的老师无用得很,看来真是这样了,下下馆子都看得这样了不起,又想着这样的机会要是放在一般人的头上,那就不只是吃点饭的事情了,老朱在家具厂当了十来年的厂长,各式各样的人都见惯了,还从来没见过像这两个老师这样迂的,连送到嘴边的肉都不晓得吃,还一本正经地拿上介绍信,先找局里面然后才由局长来找他老朱。老朱这样想的时候感觉自己似乎对这两个人产生了一点怜悯,唉,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可他老朱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笨鸟,那胆子真的才有鸟的那么大,一小点事情都被吓得一惊一诈的,活该要饿得脸白寡寡的,一个个瘦长瘦长的了。
老朱打算把这两百套学生桌椅再转包出去,因为他在心里面算了一笔帐,这些桌椅要是由厂里面的工人来做,他老朱是一个额外的子也捞不着,都是要过明帐的,除去工人的工钱,再除去厂里面的提成,剩下来的简直就没有什么了,再说还有会计出纳那几个人,大家都看着的,你老朱难道说还好做什么手脚。以前厂子情况好的时候老朱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每当厂子里接的活多了,工人们做不过来时,老朱就把他认为不太合算的活计转包给外面的私人做。起初老朱也没发现这其中的好处,可有一次在老朱给人家结帐时,人家偷偷塞了些回扣给老朱,数目还相当的不少。从那以后老朱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似的,怀着喜悦的心情悄悄把厂子里接到的一些活转包出去,瞒天过海地捞了无数的好处。可惜后来厂子衰败了,再也没接到什么大宗的活,老朱就是想这样做也没什么机会,他也想着当这个厂长也什么油水了,却想不到老局长会把这样的机会再次送到了他老朱的头上。
想到这儿老朱简直是有点热爱老局长了,他想老局长真的是他老朱命里的贵人,自从老局长从一帮工人中把他提拔成厂长那会儿到现在,老局长都是一直罩着他老朱的,就是厂里有人到局长面前来反应他老朱的什么,老局长都是宁肯相信他老朱,也不听别人说三道四。老朱决定等过两天让妻子林淑美再给老局长家送一袋田湾产的糯米过去,因为老局长家人最爱吃田湾产的糯米,每次有人到田湾那个地方去,老朱都要请人带点那地方的糯米来送给老局长家,每次糯米送过局长家去,局长老伴都相当高兴。老朱晓得老局长是个好人,你要是送钱给他,他是断断不会要的,送点糯米么,不过是人情往来,联络联络感情。老朱跟老局长家的感情就是这样一袋糯米一袋糯米地建立起来的。说老实话,他老朱是打心眼里佩服老局长的,他晓得老局长不是个贪心的人,只不过老局长的家人喜欢吃他老朱送的田湾糯米罢了。
走在路上的老朱心情好起来,两眼都放出光来,脚步也轻快了,仿佛时光倒流,老朱又成为了好几年前的那个老朱。那时候的厂长老朱可以说得上是年轻有为,手下是有着百十号人的大厂,尽管那也是个集体的厂子,可是此集体不是彼集体,那时的老朱可是局里面的红人,厂里面的工人要想找点摊钱的活做,总得先把他老朱敬到了,等他老朱高兴了,然后随便派上一派,这人的目也应算达到了。那时候老朱还是岳父岳母面前的贵婿,老朱把小姨子带到厂里来,随便安个保管之类的职务,再安排一小间屋子作为小姨子的办公室,每个月小姨子就可以跟厂里的会计们一样领月薪工资了,日子还过得舒舒服服。要知道,厂里的会计出纳都是局里面那些人的三亲四戚,没有点关系是进不来的,可老朱硬是将自己的小姨子带进来了,还享受了跟局领导的亲戚一样的待遇,像这样的女婿又到哪里找!那时候老朱只要一到老丈人家里去,老丈人老丈母像见了活龙一样的,一家人都尊敬得了不得。老朱走在街上,经常都有人追着喊厂长您到家里来玩厂长你慢点走。可是,这样的情景有好久没出现过了?老朱的心情又有好久没这样快活过了?说起来,还不都是厂里的情况不好闹的。这段时间以来,厂长老朱的心情尤其郁闷,仿佛一个成天顶着个黑锅盖生活的人,走到哪儿心情都是压抑和绝望。老朱好久没体会到举足轻重的感觉了,老朱知道权力其实就是一个人握在手里的核桃,只要捏在手里了,想怎么捏弄就怎么捏弄,老朱都好久没体会到这样的感觉了,直到今天接到这一大批活,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回来的,是在老朱边走边想的过程中一点一点体会出来的,这个一点点体会的过程很好,像嚼一种回味无穷的东西,越嚼越有嚼头,越嚼越有味道,老朱甚至想,自己不久前怎么会产生不想干这个厂长的想头呢,那不是傻吗?
老朱感觉到消失了很久的自信像春天的草芽,在重新一点点泛绿,一点点冒出头,并且越来越茁壮了。
四
王帮国从保管那儿领来了两个三门柜材料,他一边走一边看着口袋里的半斤钉子,心想,就靠这半斤钉子,这两个三门柜要怎样才能做出来。王帮国这次是真的犯起了难:过去做两个三门柜,一般情况都要用去两斤多钉子,就是再节省,最少也要用个一斤半以上的钉子才够。可这次保管只给了半斤钉子,他想他王帮国就是手艺再高,靠这半斤钉子也是难得做出这两个三门柜来了。可人家保管说了,现在厂里要节省材料,工人们当然也就不能多给了。王帮国本来想跟保管吵起来的,他跟保管嚼了半天筋,可任随他怎么说,保管就是不再多给他哪怕是一颗钉子。保管说你又不是不晓得,前不久厂里才开过会,厂长都说了,家具厂现在必须要在节省材料上下功夫了。王帮国说,难道说厂长的意思是要大家跟外地人学习偷工减料吗?保管听了,不答王帮国的话,随他一个人吵。王帮国无法,只好拿着保管发的材料走了出来。王帮国想起开会的时候,老朱确实是说过要节省材料的,虽然当时厂长没有明明说出要偷工减料来,可厂长的意思明明摆在那里,意思就是要大家偷工减料,厂长还说这是形势的需要,说不这样厂子就无法生存。当时王帮国还没明白过厂长老朱说这话的含义来,以为厂长只是一般性地强调一下,意思是要大家不要浪费材料,真想不到老朱会是让大家学着偷工减料。王帮国跟保管说着这些的时候,心里突然明白过来,厂长的意思原来就是要工人们学那些偷工减料的外地人,这样看来肯定是厂长叮嘱过保管克扣材料的,这事怪不了保管。王帮国往工棚里边走边想。
放下口袋里的钉子,王帮国再去看了看堆在工棚外面围墙边的木料。王帮国一边看一边摇头,这些烂下脚料,哪里是做家具的材料,明明就是人家打水泥的工地上用过的料子!王帮国在里面找来找去,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几块像样点的木料。王帮国想要像以往那样下锯子开做了,可比划来比划去就是无法动手。他想自己做了几十年的木工活,还从来没有在如何偷工减料上动过脑筋,这叫我怎么做呢?王帮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为难。想想自己过去也是恨那些弄虚作假的人的,怎么现在自己倒要做起这种事情来了?王帮国想来想去,越想心里越不好过,他想自己是不是像人家说的那样,越来越落伍于时代了,或者真的像杨槐奎说的那样,现在的人不在乎家具质量的好坏,要的只是个样子?王帮国过去从来没怀疑过自己,他总认为做东西做得扎实和精致是第一位的,因为在他的印像里,人们做家具都不是想做就做,一般都是在结婚的时候,而且做一件家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家具做了都要用上几十年的,并不是像杨槐奎说的那样,三年两年看着不顺眼了,把旧的丢掉再买新的。过去一般人家做家具,都是把木匠请到家里来,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为的就是让木工师傅上点心,把家伙做牢实点,偶尔在搬动的时候不至于损坏。文化大革命中,厂子里停了生产,王帮国到外面混一家人的生活,就帮许多人家做过家具。应该说,他做的东西还是很令主人家满意的。运动结束回到厂里来后,王帮国也还是一如既往地认认真真地做,从不在细节上偷懒。王帮国和几个老牌木匠做的家具一度也是家具厂最畅销的,可现在是怎么了,怎么连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会卖不动了,会弄得厂长老朱要大家从省时省料上下功夫,而不是像以前,说起王帮国几个老工人,老朱的口气都是带了点尊重的。老朱现在说起家具厂败落的原因,几乎是把所有的过失全推在家具厂工人意识保守不懂得偷工减料上了。王帮国就这样一个早上都坐着琢磨这些问题了,因此就几乎没干什么活。杨槐奎一边用锤子敲打推刨一边问王帮国:老王,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了?王帮国摇头,说他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外地人做家具有什么诀窍,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做了几十年的木工活,怎么会到现在反而被说成不会做了呢?杨槐奎宽慰王帮国说,管他怎么说,反正也是这把年纪了,再说你老王还儿女成器,不靠着这个厂又不是没人给你养老。工棚里正在干活的几个人也停了下来,大家都说,是呀,反正就是这么个厂了,会做不会做都是那么回事,就是他说你做得好,说来说去还不是帮他们多挣几年。大家看看已经是中午了,干脆就把家伙收拾起来,回家去中饭去了。
王帮国回到家里,老伴已经把饭做好,一家人坐在炉子边,专等着王帮国回来吃。王帮国闷闷地推开门,老伴见了站起来舀饭。王帮国让老伴不要舀自己的,他说他不想吃。老伴见他这样,晓得他心里不痛快,于是劝他说,人是铁饭是钢,就是遇到天大的事情,这饭还是要吃的,要不然都这把年纪了,别饿出胃病来。王帮国听从老伴的劝告接过了饭碗,却怎么也不如往天吃着香。好歹吃完一碗,也不要老伴添,放下饭碗,一个人就走出去了。老伴在后面追着问他要去哪儿,他回答说出去看看,就自顾自走了,老伴拿他没法,只好回去继续吃自己的饭。儿女们说起他这段时间情绪不好,老伴说都是厂里的事情闹的。老大老二都说,干脆把父亲喊回来,让他不要去厂里了,都败落成了这样,还到里面去干啥。不过儿女们也晓得,一说起家具厂是个烂厂,一有人提起让他回来不要到厂里去的话,王帮国是肯定要发脾气的,他就是不允许家里人说他们的厂子是烂厂之类的话,至于别人怎么说,他王帮国管不着,可无论如何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家里人说,他想如果连他自己的家里人都说这个厂子没救了,那么这个厂子就真的再也无法重新站起来了,他一辈子最大的希望也就在瞬间落空了。王帮国觉得,厂子里以后无论是发多或是发少的生活费,都说明厂子还存在着,他们这一帮人还有个厂关心,可要是这个厂真的不存在了,那他们跟乡下来打零工的那些木匠有什么不同,跟社会上飘起的无业人员有什么不同!对于王帮国这一辈人来说,有个单位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单位是他们内心永远的依靠。
王帮国逛到了胡同外的一条街上,这条街隔王帮国家并不远,街的两边一家挨着一家做生意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对于那些花花绿绿的服装店,王帮国从来就不感兴趣,可这其中有两家外地人开的家具店,早几年王帮国就注意到了。以前王帮国从这些家具店门口走过时,他只是侧过头从外面看看这些店子,有时候看见里面摆放的床啦梳妆台啦,远远看去跟他们厂里做的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有时候也见到里面有人在相家具,不过这样的时候不多,所以那店子一般情况看上去也不是很热闹。以前王帮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走进这些外地人开的家具店,他历来都是自信的,他认为自己在小城里已经算得上是个有些资历的老匠人了,从学做家具那会儿到现在,都已经是一、二十年了,做下的桌桌柜柜少说也有几千万把个,从过去老式的柜子到后来兴起的新式柜子,包括近几年才流行的三门柜栏杆床之类,他都做得不少,无论家具厂还是社会上那些知根知底的人,大家都认为他王帮国做的东西从质量来说还是过得关的,再怎么说他也不至于要去向这些外地人取经,特别是邻居小老虎请他去家里修柜子那次,王帮国的这种想法就更加牢固了。那时候王帮国断定过这些外地人就凭着这种花拳绣腿的手艺,终究是站不住脚的,迟早点要卷起铺盖回各人的老家去,所以王帮国从来不踏入外地人的家具店半步。那时候的他是自信的,自信得底气十足。
王帮国在街上逛了好一会儿,感觉体力有些吃不消了,很想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可他不想回家去,本来心里就烦,再加上老伴没完没了地唠叨来唠叨去,没有人不发脾气的,可一发脾气吵起来,儿女们又都说是他的不是。王帮国在街边一处街坎上坐下来,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流,心里生出万般感慨,说起来小城比原来扩大了,可再扩大也就是那么几条主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怎么样扩都只是那么几条道道,心里总是有数的。他家一直在那条街上住了几十年,房子是老伴娘家的老房子,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了,儿女们一个个生出来,又一个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工作,他和老伴也就不知不觉老了。说起来,自己这一生艰难日子也过了无数,每次都咬着牙走过来了,从来就没有跟任何人低过头,想来自己反正都是靠卖劳动力吃饭,也犯不着去跟人低三下四。原以为都这把年纪,好歹又有个单位靠着,想不到单位走着走着就成了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而自己呢,又到了这一把年纪,要说老呢,还说不上,可说起来也是五十挂零的人,已经经不起多少折腾了。最令他想不通的是,他原本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一个技术过硬的老师傅,自己为了赢得这一称号也下了好多年的功夫,勤巴苦挣了好些年,可自从外地人涌来,他的江山就一点点丧失了,人们一天天忘记了他,不再把他的手艺当作一回事了,他预期的外地人卷铺盖滚蛋的结局也没能来临,倒是他和他的厂子,一天天变得被动起来,几乎都要到了栖惶的地步了,这样的局面没有人愿意相信,特别是像他这样的人,自尊自强了一辈子,要承认这样的现实,比拿小刀子一下一下挖自己的肉难受。可不承认有什么办法呢,现实就摆在那儿,不承认也无法扭转局面啊!
王帮国又想起厂长老朱说的话。老朱要大家学习外地人偷工减料,老朱总认为外地人的生意能够做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偷工减料,可王帮国总觉得老朱的这种说法实在是道理不大。这些年外地人不是没有做倒闭的,可绝大多数的外地人还是在本地站稳了脚跟,如果单纯把这说成是因为偷工减料的结果,王帮国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可如果不偷工减料,做什么都按着规矩一板一拍地做下来,大家都这样做,家具厂就没有理由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关于这一点,王帮国都在心里琢磨好久了,他有时候甚至想亲自到外地人做工的地方去看一看,到底这些外地人的活里面藏了什么秘密,为什么人家做了能够嫌钱的活,到了厂里怎么就嫌不到钱了。可是,每次王帮国都只是想想,他到底还是抹不开面子,说起手艺人,都多多少少存在一点骄傲的心理,王帮国更是如此,所以他每次都克制住了这种想法,硬是从外地人的门口走了过去。其实每次走过去后他心里都是有些难受的,这种感觉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去看一看你又损失了什么?王帮国像质问自己似的咕噜了一句,于是心里增加了许多勇气,这突然而来的勇气帮他把一直以来存在于内心的顾忌瞬间打破了,他左右看了一眼,现在是中午时候,街上行人不多,更没有一个熟人,王帮国立马站起身来,毅然走近了最近的一家外地人开的家具店去。
王帮国感觉心脏跳得呯呯地响,他以为人家如果晓得他是个本地木匠,说不定要呵斥他,于是他做好了痛击的准备,在他的性格里,原本就是受不得气的,他两只眼睛睁得像两个电灯泡,可见他此刻内心是充满斗志和决心的。可是当他走进去时,却发现在靠里的沙发上睡着一个人,见有人进来,懒懒地欠身看一看,口里问一句:老师傅要买沙发啊。王帮国听出人家喊他老师傅的意思,并不是说晓得他是这个行道的人,而是表示尊敬。外地人说完坐起来,两只眼睛还睡意迷朦。沙发店里的气氛又慵懒又安静,王帮国的如临大敌像一只蓄满了力的拳头捶在海棉上,显得可笑又无的放矢,于是自己暗暗把紧绷着的心放下来,答了句看看。外地人和善地说:师傅请随便看。王帮国的内心彻底放下来,眼睛里尖锐的光不见了,长久蓄积的敌意一下子消失,觉得自己以前很无聊,心里有一点愧疚,但面子上终于没有露出来,于是也看得不太仔细,很快就从那家家具店出来。
后来王帮国又走进好几家外地人家具店,所有的这些家具店里,老板一看见有人来都格外热情,一会儿问王帮国想买个什么家具,一会儿又向他推荐,哪种家具的样式好,哪种家具的功能齐全好用。王帮国不好对人家说他只是来看看,可又不能就这样走掉,现在他已经明了自己来这儿的目的。王帮国一边嗯嗯啊啊地应付着外地人,一边走来走去地看。最后外地人看出王帮国不是来买家具的,又不好赶他走,态度就冷淡了下来,并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只是让王帮国看着,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去了。王帮国也不管这些,他把这些摆放在店子里的家具都仔细看了个透,并且用的是专业的眼光,从用料到做工一样不落地仔仔细细看,像一个医生面对病人一样,用遍了望闻问切的手段。看完后王帮国出来了,遇到下一家店子又走进去,像在前一家那样,又把人家摆放着的家具研究个透。王帮国后来还钻进人家在店子后面干活的房里去,看那些外地工匠做家具看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王帮国回家来,也不对老伴说自己没到厂里面去,只接过老伴递过来的碗。吃过晚饭后,王帮国从家里找出一支铅笔,一个人坐在灯下写写画画的,有时又沉吟着,一个人陷入冥想。儿女们以前也看见过王帮国对着厂里交给的家具图纸思考过,却从没见他如此的用功,大家都很好奇,但又不敢问,因为他这段时间以来脾气都不好,大家不想惹他生气,只由着他一个人写写画画,后来才把纸收起来,似乎心里想明白了,才跟老伴讲起话来。老伴见这样,放心了,收拾好碗盏,儿女们都各人休息了,老两个也熄灯睡觉。
五
经过仔细研究,王帮国得出一个结论:外地人确实聪明,人家做的家具正如老朱说的那样,在用工用料上的确是很节省的,但节省是节省,但节省得是相当的得法的。就拿用料来说,在家具的受力部分,人家用的都是上好的花梨木之类,像那些烂泡桐板子,一般都是用在家具的背部或者是下面,外地人做的沙发,扶手的两边和两档部分,用的都是好料,而里面和下面就用点下脚料,做好后把面料一绷,用些小毛毛钉钉上,看上去又洋气又漂亮。在用工上,人家也是很讲究的,该省的地方决不用一点力,而不该省的地方,人家也是做得相当到位的。不过,在厂里做东西,如果像人家外地人这种做法是不行的,因为外地人很舍得在外表上下力气,可有些工艺所需要的条件厂里没有,再说厂里订的单价又低,因此就只好把这部分力省掉了。
王帮国把自己到外地人那儿去看的结果跟厂里的几个老工人进行交流,大家都同意王帮国的看法。杨槐奎说,如果外地人的家具真的像老朱说的那样,怕早就收摊回老家去了,像他们家那儿原先租房子的一家四川人,就是做了两年做不下去了,只好把房子转让掉回去。是呀,外地人中有偷工减料的,那都是自己堵自己的路,可别的那些懂得做生意的,人家就不这么做,所以现在街上有好多家外地人,生意越做越大了,钱也越赚越多。林木匠说。
几个差不多的老木匠都认为王帮国说的有道理,大家都觉得是该改一改过去的那一套了,但完全像老朱说的那样也不行,如果光只晓得一味的省时省料,图便宜图快,那家具的质量就难得说了。大家都说先做着看,合算就做,万一做下来不合算,实在不行,干脆就出去帮私人干,要么就干脆回家去带孙子得了。
王帮国在一堆木料中挑选来挑选去,老朱一进厂门就问王帮国:老王,活儿干得咋样?王帮国回答老朱:还没有动手做。老朱说咋还不动手呢?王帮国边捡起一截木料用手比划,一边回答老朱说,他在找好点的木料,因为再怎么将就,家具的受力部分还是要用好点的料子,要不然等人家抬回去用不了多久就烂了。老朱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一个人打开办公室的门,进去了。王帮国选了好半天,终于选好几根看上去比较恰当的材料,拿着走进工棚里。杨槐奎正在磨刀石上磨推刨,见王帮国进来,跟王帮国搭起话来。
杨槐奎说,这次厂里买的这批木料太差了,选来选去就是选不出几截好点的来。杨槐奎把嘴凑近王帮国的耳朵,悄悄地对对王帮国说,这批材料他听人说是老朱到人家工地上买的次料。王帮国一听这话就忍不住了,他想厂子都被吃成这个样子了,难道说这个老朱现在还忍心继续像以前一样乱整?王帮国问杨奎槐是听哪个说的?杨槐奎赶紧朝厂长办公室那边努嘴,意思是怕说大声了让老朱听到。王帮抬头往那边望去,果然厂长老朱正锁了门朝厂子大门走去。等老朱走远了,杨槐奎才说,他也是前几天听徐小田说的。徐小田以前也是在家具厂的工人,年龄比王帮国这一伙人要小十来岁,人头脑聪明,在厂里的时候就比较出众。后来厂子不行了自己出去找事干,在外面开起了家具厂,听说生意还可以。王帮国在街上也遇到过徐小田,徐小田也曾经好几次说过让王帮国到他的家具厂去干,可王帮国过去帮私人帮怕了,再说他总是觉得轻工局这个家具厂好歹是个单位,要是厂子不垮,等以后自己到了退休年龄做不动了,厂子还答应给个二三十元的生活费,虽说数量不多,但毕竟也是温暖人心的,比不得私人,他如果发了财,在你的面前不拿大就不错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王帮国一直都没答应徐小田。现在王帮国听杨槐奎这样说,心想是不是徐小田又想挖杨槐奎到他的家具厂去帮忙了,王帮国知道,这个徐小田总是想方设法要把厂子里技术好的几个老工人挖到他办的私人厂子去,因为像王帮国和杨槐奎等人,徐小田晓得他们做家具的技术是过得硬的,只是好些老工人的想法都跟王帮国差不多,家里要么有人做着事情,要么儿女都在单位上,不等着他们做那点钱回去买米下锅,他们也不想再出去看别人的脸色,到厂里来只是因为干了一辈子的活,突然歇下来不习惯,于是就到厂里来混着,做多做少倒不在乎。王帮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前几年老伴在街面上摆了个咸菜摊了,做了点咸菜每天在街上守着卖,一天下来也有好几十元的收入,中午或是晚饭时候还可抽空给家里人做点饭,王帮国所以才一直在厂里耗到现在。而厂子里那些单靠着一个人挣钱养家的,都早早地出去帮私人干活去了,没办法啊,一家老小要吃饭,就这样死守着这个破厂是不行的。王帮国听了杨槐奎的话,心里老大的不舒服,开口骂起老朱来。其他几个在角落里干活的人听到动静,都停了手里的活,问老王又有什么不痛快的了。于是老朱拿着厂里的钱去进次料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工人们都说这老朱太不是人,太没有人性了,厂子都吃垮成这个样子,到现在他狗日的还寸寸步步想着的都是吃回扣,这简直就是存了心要把厂子完全整垮掉!大家都说干脆还是到局里面去反应一下,请局里面把这个狼心狗肺的老朱换掉算了,要不然照这样下去,这家具厂迟早只能是个破产。
于是果然就有人告到了局里面。老局长把老朱叫了去,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老局长的面前,老朱大倒苦水,据理力争为自己分辨。老朱说,现在的情况局里面又不是不知道的,什么材料都贵,他处处想办法节约,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厂里,可工人们不说理解他,反倒认为他吃了回扣。老局长说,再说是为了厂子节约,也不能节约得专门进些烂材料,你这叫工人们怎么做出家具来?老局长让老朱还是去进些好木料来,让工人们搭配着使用。老朱答应了局里面。从局里面出来后,老朱满心的不快,心想肯定又是王帮国带着人来告他了,因为以往好多次都是王帮国跟他过不去。大家都是一路进的厂,可这个王帮国,眼睛里根本就没得人,说起来厂子里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可每次都是他开头跟他老朱过不去。好吧,你既然想告就告吧,以后我叫你去告个够。老朱在心里恨恨地想。
几天后厂子里果然又拉来了一车上档次的木料,就下了堆在那堆次料的旁边。老朱虽然对于工人敢于到局里面去告他的事很不高兴,但毕竟还是听了局里面的意见,又让人拉了一车好料来。老朱让负责保管的人把好材料关,说不能由着工人们,想用好料就专门用好料了,他要求工人们做每件家具都要搭配着使用,不能光图方便。
家具厂的日子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过着,老朱隔三差五到厂里面去,看看会计来没有来,看看出纳上没上班,偶尔也到工人做工的工棚里去转悠转悠。工棚里照例还是只有十来个人,稀稀疏疏地分布在偌大的工棚里。看厂的老许隔两三天打扫一次工棚,把每个马凳前的刨花木霄弄出围墙外烧掉。老许的工资总是要两三个月才能领得到一次,每次都是厂里卖出一部分家具了,老许听到消息,趁着老朱来厂里的时候追到老许的小屋里,请老朱把字签了,然后到会计那儿把钱领掉。工人们常常看见会计李小会坐在她一个人的小屋打毛线。家具厂的日子仿佛就是由工人们乒乒乓乓敲打掉的,是由会计李小会从一截一截的毛线上织出来的。
王帮国的两个三门柜已经做出来交到保管的手里,按厂长老朱的说法,还是要等三门柜卖出去后才能领到钱。王帮国做这两个三门柜用了将近七天的时间,本来可以做得再快一点的,可在做的过程中,王帮国时常停下来思考:本来该打榫头的地方省掉没有打了,只用两棵大钉子钉上,可等用了钉子后,王帮国又感觉到心里实在不踏实,仿佛是做了有亏于别人的事情,无论如何心里总是不安,又有点做了贼的感觉,生怕一不注意就被人家发觉了,将一张脸丢尽掉。左想右想实在于心不忍,干脆又拆开来重新打了榫头,重新用胶水好好沾了做过。在用料上,王帮国也是经过了再三的考虑,家具的受力部分他还是用了比较结实的好木料,只在一些不太关键的部位将就了一下。王帮国想,人家花了钱买一件家具,总不是为了买来三天两头换的,再说现在的人不像以前他们那时候那样,太过分在乎买家具的这几个钱,但他总还是觉得毕竟不是哪个的钱都来得容易得很,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做人不能太亏心,做个家具,总不能连钉子都省得不能再省。为了做这两个三门柜,王帮国还帖进去了半斤多钉子,主要是到后来他从保管那儿领来的钉子不够了,他去找管保,人家说,厂长吩咐的就给这么多,不可能再多给了。没有办法,王帮国只好自己去买了点钉子来加上去。王帮国在厂长设计的节省材料的方案上算是交了一次不合格的答卷。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吃亏的还是王帮国自己。
王帮国听说他们交上去的这一批家具已经卖出去了,隔天便去会计那儿问,是不是能够领工钱了,每次会计都说钱完了,怪王帮国不早点来,又说要等下一次了。王帮国觉得奇怪,明明刚才才见有人领了出来,既然会计却说没钱了,他也没有办法,心想会计说等下次,那就只好等下次了。王帮国总觉得这个李小会是故意跟他为难,但怀疑归怀疑,王帮国也没有办法,只有耐着性子出来。有一次王帮国发了脾气,一定要李小会打开装钱的抽屉给他看,李小会拗不过王帮国,才说了句:你去找厂长,是厂长吩咐的。王帮国气不打一处来,等着厂长老朱来了,去敲老朱的门,问老朱为什么他做了家具交上来,明明早就卖出去了的,怎么他不让厂里给结算工钱?老朱打呵呵说,是吗,等我问问会计。又说,可能卖出去的不是王帮国做的那一批,他听说王帮国做的家具都还放着,没卖出去。王帮国一听眼睛立马就瞪了起来,要老朱马上跟着他到仓库里去瞧,说看没卖出去的东西是不是他王帮国做的。老朱被逼得无法,只好当着王帮国的面通知李小会结帐,王帮国才算把这段时间以来干活的钱领到手。
这件事过后厂里的人再没见王帮国来厂里,老朱偶尔到工棚里来,四处转转,问其他人:这段时间王帮国没来吗?有人回答:都好久没来了,怕是到外面去帮私人做去了。老朱于是说:巴不得他不来才好,又不是离了他王帮国,家具厂就找不到人干活了。老朱说的是心里话,他现在只要一看见王帮国,心里就像吃了块生肉下去,相当的不舒服,老朱也知道王帮国不到厂里来的真正原因,老朱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王帮国走。老朱晓得,他要是不预先跟会计打招呼,让大家都想办法夹一下,处处跟他过不去,这个王帮国怕是说什么都不离开厂子的,他不离开厂子的真正目的,还不是专门找机会跟他老朱过不去。老朱想,你王帮国不仁,就别怪我老朱不义。老朱在工棚里说完那句话后,听着没人答自己的腔,一个个都吭哧哧埋头干活,老朱知道这些人是不好答他的话,于是就一个人出来了。老朱边走边吹着口哨,一边掏出腰里的钥匙打开门,一边想,跟我斗,你王帮国还差得远!脸上就露出了些得意。其实厂里的人不说,心里都明白,人家王帮国凭自己的手艺,就是不来厂里才好呢,还怕挣不到在厂里的这点钱。不过没有人说出来,主要是犯不上得罪老朱。王帮国那天来厂里收家伙,说是徐小田请他过去他答应了,主要是他难得看老朱的嘴脸。王帮国还关照正在干活的几个老伙计说,厂里要是有什么事,记着告诉他一声。大家都清楚王帮国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老朱再做出出卖厂子利益的事,他王帮国是要回来跟老朱斗的。于是大家都劝王帮国:算了,既然都想通掉要出去做了,干脆就安安心心的去帮私人,还怕说这个破厂有个什么稀奇的。王帮国说,稀奇倒是不稀奇,只是厂子不是他狗日的一个人的,再说都在这儿苦了一辈子,不能任由他一个人葬送掉。大家都觉得王帮国说得有道理,但又想着王帮国正在气头上,不能再火上添油了,于是就都说了些劝解的话。老朱倒是晓不得这些过程,只是觉得终于把王帮国挤走了,心里面觉得挺解恨,终于把长久以来憋着的一股子恶气出掉了。老朱打开了办公室的门,突然又想起什么,于是并不进屋去,而是转身进到老许的值班室,吩咐老许:下午林大军来,就让他搬家伙到王帮国的位置上。林大军是老许的家乡人,老许把他介绍来厂里来。,本来厂子外面来的人一般都是把干活的马凳支在工棚外的坝子边上,老朱却让老许把林大军喊进去,把王帮国原来的位置占掉。老许答应了老朱。
杨槐奎这一段时间懒洋洋的,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就是来了也不好好做,大部分时间都是拉着人瞎吹神吹。杨槐奎说他那个读师范的侄儿子回来了,说是一回来人家县委的就看得起,于是就书也不教了,留在了县委大院上班。林木匠于是问杨槐奎一句:你咋个不喊你侄儿给你找个不苦的活干?想不到杨槐奎不但不觉得林木匠这话是整他,反而挺自豪地说:侄儿说了,等以后县里的什么工程上马了,就给我说了去保管材料。林木匠想,人家杨槐奎不干活可以靠在县委工作的侄儿找好活计做,以后他老了怕他这侄儿还管得着他,而他林木匠,只有一辈子赖在这个厂子里了,好是这个厂,不好也是这个厂。想到这里,林木匠忍不住叹了口气,心里说,这就是各人的命了。
六
家具厂最近老是出事。一开始有人要求将买回去的家具退货。首先是附近乡下的一家人来家具厂买了个三门柜、一张床和几个凳子拉回乡下去,准备结婚的时候用。却想不到家具抬上车的时候没事,可在抬下来的时候就出了问题:那家具经过一路的颠簸,等拉到家门口往下抬时,三门柜的一只腿就掉下来了。这家人见了这个样子,心想又没人碰着砸着,怎么说掉就掉了呢,像这样的家具,质量显然是不好的了。于是干脆就又重新把家具拉回了家具厂,找到厂长老朱,说要求退货。厂长老朱一听说人家要退货,心想卖都卖出去了的,怎么可能给你退货呢?于是厂长老朱就说了,家具是在你们的手里烂掉的,怎么会赖得着我们呢,你说要退货,你倒是到处去问问,看给有卖出去了又退掉的道理。老朱只答应把掉腿的三门柜换掉。可凭老朱七说八说,这乡下人就是咬定了一条,坚决要求退货。厂长老朱见这个乡下人太强硬了,实在是说不动,心想干脆自己躲起来,看他找不着人,这货还怎么退,就不相信他天天在这厂里吵得起。于是老朱就趁乡下人不注意的功夫,一个人悄悄溜走了。乡下人吵着吵着,一转身就不见了老朱,晓得老朱使了金蝉脱壳之计,于是就把一大堆家具从车上卸下来堆在厂门口,几个人还进到老许的屋子里,坐下就不走了,在老许的屋子里开起了伙食,看样子是做起了长期驻扎的打算。那些家具堆在厂门口,每天招来附近看热闹的人,都晓得是家具厂卖出去后又被人家拉转来要求退货的家具,自此后轻工局的家具厂做出来的家具质量差的消息让好多人都晓得了。厂长老朱躲了几天,晓得人家告到了局里面,又把些家具摆来堵住大门,弄得厂子里的人连活都做不成了,没办法,老朱只好又回到厂里,通知会计跟人家把货退了,乡下人才偃旗息鼓,从别处买了家具拉回去,这事才算完结。
自此后家具厂遭到的退货接二连三,家具厂门市上隔几天就有人上门去吵,要求把买来的家具退掉。究其原因还是家具的质量不好,人家买回去后不是发觉用料太差,就是做工粗糙,看得到的地方还过得去,要是用眼睛看不到的部位,干脆就是能糊弄就糊弄,似乎这做的不是一件家具,是要用上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而是随随便便一样什么东西。其实这些家具都是厂里的一帮乡下木匠做的,这些人手艺本来不好,出去找不着活干,所以才会一直留在家具厂。家具厂原先有点技术的工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厂长老朱想,你要走你走你的,难道说离了王屠户,还要连猪毛吃了,我不信我老朱离了你们,家具厂就存活不下去了。老朱于是把家具厂的活包给了这些乡下木匠,虽然给的工钱很低,甚至比原先给家具工人的还要低,但这些乡下木匠也没话说,照样是把家具做了交给厂里来。本来老朱对这些乡下木匠的功夫就心里没底,但为了维持厂里的生产,也只好这样,却想不到会出这样的事。
老朱心里正烦着,又有人来找老朱了,是在厂里干活的乡下工人,来人对厂长老朱说,厂长我现在手里没钱,连伙食都开不下去了,是不是请厂长先支点钱用着,等家具卖出去了,再从我的工钱里面扣。厂长老朱这时候最烦的就是他们,做点家具连卖都卖不出去,就是偶尔卖出去了,还接二连三遭遇退货,都到这时候了,还好意思说支钱的事。老朱气不打一处来,说厂子里现在没钱,像你们做这种活,厂里不让你们赔材料钱就算好的了。这个人原本是个老实人,其实被人家退货的家具不一定就是他做的,但当时听老朱这么说了,还是一下子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因为厂子里只有这些人还把厂长老朱当个人物,自然在老朱面前也就显得低三下四,说不出什么话来。等这个人退出去后,厂长老朱立马通知了会计和保管,喊他们查一查,看退回来的家具都是哪些人做的,厂长老朱说,既然人家都来退掉了,当然就不能算钱给他了。老朱说了一句话: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羊都出不了毛了,这羊毛钱就说不上给,不喊他赔羊子的钱就不错了。
厂长老朱的烦心事还不止这些。局里面又要各厂把生产报上去了,特别是现在正在正常生产着的厂子,帐目要求一点都不要含糊。老朱晓得局里面的意思,说起报帐目,老朱就晓得这是局里面那伙人要各厂上贡给他们了。以前厂子红火的时候,在这方面老朱从来没有含糊过,该给的给了,局里面的人脸色也好看了,反正又不是拿老朱私人的钱,再说那时候那点钱,对于家具厂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老朱从来不会计较在这一方面拿出了多少钱。可是现在厂子里的这种情况,这帮人是晓得的,说起来是正常生产着的,可每天来厂里干活的就是十来个人,这对于曾经有着百十号工人的家具厂来说,还算得上是正常生产吗?可局里面不管这些,他们只晓得家具厂还没有纳入破产考察的厂子之一,而且生产方案是报到了局里面的,这样的厂子当然就算成了正常生产的厂子之一了,他们才不管厂子现在的经营有多困难,厂子里上班的人少,家具卖不出去,他们反正只晓得伸手要钱。哎,这些官老爷,真的是只管吊着兜兜捡鸡蛋吃,太不晓得好歹了。可老朱有什么办法呢,对于这些人,老朱是得罪不起的,既然局里面的意思都明确了,老朱就只有想办法先把这一方面应付过去再说。老朱一边想着是不是找人把工棚后面的仓库抵押出去,先从银行弄点钱来周转一下,顺便也好把局里面打发掉,一边在心里感慨,家具厂照这样下去,怕是再难恢复以前的红火了!
七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家具厂的工人越来越少,看厂的老许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无聊,想找人吹吹牛,却常常是一大早上过去了,厂子里还不见一个人来。老许老家在乡下,老许一个人在城里看这个厂都已经看了好多年了,自从老伴十多年前死了,老许就一个人住在厂子里,闲来无事了,就在厂子各处走走,工棚里有干活累了过来歇气的工人,老许就跟人家神聊白聊地吹一气,借以排遣孤身一人在城里的无聊。以前老许也把最小的孙子带了一个在身边,可后来那孩子到读书的年龄,被他父母接回乡下去了。老许虽然是看厂的,可说起来也算是厂里的工人,原想着就看一辈子的厂,等以后回乡下去,每个月有厂里给的几十元的生活费,这一生人也就是这样了。可令老许想不到的是,厂子到后来会成为这个样子。照这样下去,不要说等回老家,就怕以后连看厂的活都干得不长久了。前段时间厂长老朱把厂里的人喊回来,说是局里面关心厂子,要大家回来干活,老许还以为这下厂里可能有救了,却想不到这厂子在老朱手里,整来整去还是个半死不活,到后来干脆连原来一直在厂里干着的人都走光了,老朱也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地不来,几个乡下木匠据说做的东西质量差,做些家具出来卖不出去,算下来简直就做不到钱,也纷纷收起各人的家伙开路了。
老许正在厂子里面东瞧西瞧,想找点工人们丢下不要的下脚料做发火的木材,却听到外面有人来了,忙直起腰来看,发现是好久不见的杨槐奎。不久前老许就听林木匠说,杨槐奎到外面帮人家一个什么大单位看门去了,老许晓得,一般情况下,大单位看厂的差事是比较不好找的,老许想,肯定是他那个师范毕业的侄儿帮他找的活计。老许跟杨槐奎打个招呼,问怎么这么久不来厂里了?杨槐奎说他值班的那家单位忙得很,不经常看着不行,怕外面的人走进去,干扰了单位上的人办公,领导要不高兴。老许赶忙让杨槐奎到他的小屋子里坐,这时好几个人接二连三地来了。老许见厂里来了这么多人,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又想着这些人都是厂子里的工人,怎么今天来得这么齐。正想着,王帮国也来,肩膀上头发上都有一层木屑,看来是从干活的地方直接来的。大家进到老许的值班室,也不等老许让坐了,各人就找地方坐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讲起来。老许听到后来听了个大概,工人们今天来,就是有人听说了老朱把厂子的仓库和工棚抵押出去的事,于是就互相通知,约齐了到厂里来,一起商量这事要咋办。关于厂子抵押出去的事老许也听说过,是听厂长老朱跟会计说的,当时老许正到老朱的办公室找老朱签字领这几个月的工钱,不小心刚好听到了老朱跟会计李小会说的话。当时老许并没怎么在意,心想厂里的事情,他老许也不懂,于是就忘了这事,今天听他们说起来,老许才突然想起来,心想这些人的消息还灵通,怎么就晓得了这件事呢。不过老许没把这些话说出来,只一心听他们说。老许注意到王帮国的情绪最为激烈,王帮国说,大家不能就这样任由他乱来,想抵押就抵押了,想卖就卖了,说到底这个厂子还是集体的,怎么他一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呢。杨槐奎说,也不晓得他把厂子抵押掉,把钱拿到哪儿去了。本来这些人都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木匠,一辈子靠出卖劳动力生活,说话根本就不懂得抓住主要矛盾,这下听杨槐奎这样一提,大家马上就把谈话的焦点集中在老朱把这么多钱拿到哪儿的问题上。一伙人议论了一上午,最后一致决定,等到下午局里面上班后,大家一起到局里面去闹。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去“闹”,关于要怎样个“闹”法,没人提,也说不清楚“闹”的目的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点,大家一起去,去了向局里面反应老朱瞒着大家,一个人悄悄把厂子抵押出去的事情,当然,关于钱的事情肯定是要说的,每一个的心里都存在怀疑,这么大一笔钱啊!究竟老朱拿这么大一笔钱干什么去了。
一帮人于是就去了局里。局领导听说工人们来了,让人把他们叫到二楼的会议室去。局里安排了一个副局长接待工人们,可工人们不干,说一定要局长亲自来,他们好把厂里的情况当面向他说清楚。这个副局长说局长不在,有什么可以直接跟他说。有人说刚进来的时候明明就看见局长从厕所里出来,怎么会说局长不在呢。这个副局长无法,只好退出去了。一会儿老局长进来了,工人们七嘴八舌向局长反映。有的说厂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说来说去都是老朱一个人的责任,要不是他私心太重,把个厂子当成他家的,厂子也不会垮成这个样子;有的说老朱连进点材料都要想办法从中间吃点回扣,这个老朱心太黑了,太不是人了……这些人各人说各人的,都认为自己说到的一点才是老朱最关键的问题。突然老局长发脾气了,说你们反映你们厂长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有没有证据,有证据来反映是可以的,局里面也可以查,可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污告,法律上是要负责任的。一帮人先时还闹嚷嚷的,觉得自己说的都是确有其事的,都说无风不起浪,都搞得让大家都知道了,难道说事情还假得了?可当老局长说到证据二字时,一个个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并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因为人家老局长都说了,要重证据。证据,你有吗?于是,一时间大家都安静下来,气氛显得有几分的压抑,先还理直气壮的一帮人现在哑口无言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晓得该怎么说。停顿了几秒钟,终于,还是王帮国打破了沉默,王帮国说,局长,我们来的目的,主要还是想跟局里面汇报一下老朱瞒着工人们把厂子私自作抵押向银行贷款的事,局里面是晓得的,明明厂子现在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厂子再抵押出去,以后靠什么来还银行的钱?这不明明就是把厂子卖了吗!以后工人们再到哪里上班,老了还能指望哪里?王帮国的话一说完,老局长就捂着嘴咳嗽了起来,咳嗽完后,又等气喘匀了,才回答王帮国说:关于家具厂拿厂里的财产抵押货款的事,是经过了局里面同意的,老朱作为厂里的厂长,有权力作厂里的主,只要是局里面同意的,就算不上违法。老局长还解释说,厂子里本来就存在着债权债务的问题,这些问题局里面会监督老朱,他老朱用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局里面的审核。老局长让大家放心,说老朱一定不敢乱来的。老局长的话刚一说完,工人们就吵了起来,说他们不懂什么债权债务,就晓得好端端的一个厂子在他老朱的手里被葬送掉,现在连骨头渣渣都要找不到了,他们来这里就是要局里面给个说法,还工人们一个公道。老局长越听越觉得这些工人们太哆嗦,任他怎么解释就是听不懂,只晓得吵,太没道理了。老局长最后又发脾气了,说你们再不听解释,那就各人到县委那儿去反映,我没时间跟你们纠缠。老局长说完拂袖而去。先前那个副局长出来劝工人们回去,说既然厂子里没事干,家里面的人还要吃饭,不如各人去干各人的事,找点钱回去才是正事。想着在这儿也没多大的意思了,一伙人只好走出了轻工局的大门。
一伙人站在街边,有人问,要不要到县委那儿反映?去,怎么不去,既然局长叫我们到县委反映,难道说我们还怕不成?于是大家一起闹哄哄去了县委大院。到了大门口,值班的人拦着不许进去。于是又在县委的大门口吵,说他们来找县委反映点情况,怎么就不许进去呢。可任他们怎么说,值班的门卫就是拦着,只允许派两个代表,其他的只能在外面等。派代表?都是些下苦的人,哪个能出得起这个面代表大家?一时间大家没有了主意。这时王帮国开口了,王帮国说:我去。他说他就不信当个代表说几句话,还会被领导吃了不成。王帮国又拉杨槐奎和他一起进去,起先杨槐奎还推了一下,可经不住大家的劝说,最终还是跟着王帮国进去了。两人被值班的领到一间办公室门口,进去了,算是见着了县委领导的面。领导问他们有什么事情要说。两个把心里凡是能够想到的厂里的问题都向领导作了反映。领导一边听一边在一个小本本上作记录。等他们讲完,领导也记完后,相当和气地对两人说,你们反映的这些问题我记下了,接下来他会安排人去调查,如果家具厂问题确实涉及到犯罪,县委决不会姑息。不过,这个领导接下来说,一切都要经过调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领导让他们回去等着,县委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满意和合理的答复。既然人家县委领导都这样说,而且又说得这样合情合理,王帮国和杨槐奎两人再没有理由不答应,于是就都点了头,心服口服地出来了。
一伙人等在外面,见到两人,都赶紧问:给见着领导了?领导咋说?两人于是把跟领导见面的经过详细对大家说了。大家听了都说:人家县委的大领导都不说我们是无理取闹,只有局里面那个鸡巴局长说我们无理取闹,说来说去还不是被喂饱了。既然人家县委领导都发话了,大家也只好各人先去做着各人的事,以后再看结果。看看已经是中午了,杨槐奎邀大家到他家吃饭,说他早上出来的时候,他老伴说要煮包谷面稀饭吃,他说那包谷面是他兄弟从乡下请人带上来的,黄皮包谷,煮出稀饭来香得很。大家都说不客气了,这么多人,要是到你家去,怕你老伴用好大的锅煮都不够吃。于是大家告辞后,各人走了。
老朱也晓得了工人们到局里和县委那儿去告他的事情,当然了,十多个人闹嚷嚷地去了,老朱要不晓得才怪呢。老朱逢到有人问他这事,脸上总是带着胸有成竹的冷笑,说,让他们告去,怕他们还把我的鸡巴逮掉。老朱现在照样经常到厂里面去,有时还把会计喊来,让他找人处理厂里剩下的地块,处理仓库里积压的家具。会计于是找了几个人来,把仓库里的东西清了清,清的结果,无非就是些人们家里用来装衣服的衣柜,装碗筷的橱柜,还有好些年前就做了摆在那儿的桌桌凳凳。老朱随便批了个价钱,让会计带着人全部抬到街上,通通以极便宜的价钱处理掉了。
老朱又跑到局里面去,把厂里的一些单据跟局里面的领导作了个汇报。老朱晓得,他现在做事情,每一步都得小心谨慎一点,现在好些人都盯着他,他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把自己陷进去,老局长也跟他说过,从现在开始,他处理厂里面的每一件事,都必须跟局里面汇报,得到局里面的同意。老朱晓得老局长是好意,是出于保护他的意思。以前他老朱做什么,都是尽量争取局里的支持的。我老朱是谁?不说从人际关系上,就单凭见识,也比厂里面这些只懂得下死力的人强多了,要不,我老朱岂不是白在这世上混了。老朱知道,他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获得局里面的同情与支持,也就是过去人们常常说的,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组织才会给你打气,给你撑腰。老朱去的时候见到老局长正在拿着一把喷壶给盆里的花浇水,老朱走过去,老局长也看见了老朱,一边浇着水一边问老朱:厂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老朱恭敬地回答:正在处理仓库积压的家具。老局长放下手里的喷壶,一边招呼老朱进屋去。老朱听见旁边一间屋子里传来麻将的声音,老朱晓得,又是局里面的几个人闲得没事,凑在一起搓麻将了。老朱经常在局里面遇到他们搓麻将,有时候还会拉老朱陪着搓上几局。轻工局的屋子是以前修的木板楼,楼上楼下一有人走路,就整栋楼咚咚地响,隔着两三间屋子搓麻将,简直就跟在眼前一样,连有人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老朱早就听说这楼要拆除重建的,他晓得这楼确实是不行了,太老了,现在木结构的办公楼已经不多了,但真正什么时候能够拆除没人晓得,管他呢,早晚的事吧,老朱想。
八
家具厂还是破产了,不破产不行,不但欠着人家银行的贷款,还跟人家私人那里打了若干的欠条。家具厂是无力偿还这些钱了,于是就只好申请银行破产。听局里面的人说,家具厂欠的钱即使是厂子能够正常生产,也要还上好多年才还得清,没办法,只有破产一条路走。在这之前厂子里有好些工人到局里面去告,到县委上访,可像轻工局这类单位,好些厂子财务历来不正常,要是查起来,每家厂子都是乱糟糟一团,没有哪个查得清。所以上访来上访去,还是没上访出个什么名堂来。工人们都灰了心,各人奔各人的前途去了,不再对这些个破厂抱任何希望。局里面见厂子再没有活起来的可能,再加上老朱三天两头到厂里来哭诉,说厂子里过去的老人们只要在路上遇到他,三句话不对就开口骂,还有欠人家钱的那些人,一天把他老朱像堵个贼样的堵来堵去,要他老朱把厂子里欠的钱还清。局里面拿着这事没办法,又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还是申请破产,这样一来就一了百了,管它是私人的钱还是银行的贷款,反正家具厂就是那点财产,等法院去执行算了。工人们听说厂子准备宣布破产了,又跑到厂子里来一通大骂,不过骂归骂,也只是发泄发泄心中的怨气罢了,至于其它作用是没有的,人家老朱听不见,局里面的人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没多大的意思。工人们发泄够了,各人把留在厂里的东西全部收拾起来,该拿走的拿走,该烧的烧掉,于是人们在这个厂子几十年的痕迹算是彻底没有了,只有一些东一处西一处的破败,东一点西一点的零乱。
轻工局好些厂子破产的消息像决堤的潮水,一家连一家地传来,这其中也包括家具厂在内,随之而来的,还有的轻工局即将被合并的消息,听说文件都已经下来了,说轻工局即将被合并到工业局,这样一来,轻工局就不存在了。不存在就不存在了,拿这样的一个吃饭不管事的轻工局来干什么呢?听到这个消息的工人们都这样说,他们对局里面的那些人是相当有看法的,要不是他们跟厂子里的这些厂长串通一气,原来多么红火的厂子怎么会一个个说垮就垮了呢。工人们还听说,轻工局的老局长由于已经到退休的年龄,趁着这次合并,干脆就让他办了退休了。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局长骨子里并不是个坏人,只是没有多少文化,又刚腹自用的,除了他自己提拔起来的人,他根本就听不进其他人的一句话。于是大家都说,怎么现在才退休呢,要是早点让他退掉就好了。说是这样说,可哪个又有这个本事让他早点退掉呢?
王帮国是最后一个到厂里去收东西的。他原来还有些用不上的家伙放在厂里,原以为以后回厂要用,没想到再也没有回来用它们的机会了。王帮国本来没有想着还要把这些家伙拿回来,可经不住老许再三催促,老许三番五次地到家里,又找到王帮国帮人家干活的地方,让王帮国去把各人的家伙收走,说好腾出厂子来给人家。王帮国于是在一天放工后去了。进了厂子的大门,见厂子里到处静悄悄的,破败得很,像几十年没人来过一样。喊一声老许,老许从看厂的小屋子出来。两人走进一地乱糟糟的工棚,乱虽乱,却空旷得很,夕阳的光辉透过棚顶的破洞射进来,愈发显得凄凉。
王帮国于是在一地的灰尘一地的乱木屑中收着家伙,一边问老许:老许,以后打算咋整?老许说,以后吗,回老家吧,家里有地,有房子。老许说他以前的老房子还在,也没人住着,儿子们都各人有自己的房子,老房子就一直空着。王帮国本来想跟他说,人老了,种地种不动了,何不让自己息着,让儿女们给他养老算了。可王帮国却突然想起来,以前就听说老许因为一直在城里帮厂里看厂,家里的儿子们都跟他生分,这一下子回去,说厂里的退休工人算不上,因为连厂都没有了,说是到城里来挣钱吧,除了自己的伙食,老许现在怕拿出几十块钱都费力。老许自老伴死后,就一个人只顾得了自己,连像农村里的好些老人一样给儿女们带带孩子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脸回去让人家养老!想到这里王帮国把嘴里的话咽了回去,只是在心里叹息:这个老许,到老来才走到这一步!
王帮国收好家伙走出棚子,见天边几颗星星都出来了,老许一个人坐在小屋子的门外,手里拿着个大大的水烟筒一下下呼呼噜噜地吸着。王帮国突然想吸吸老许的水烟筒,以前他经常见好多人在值班室抱着老许的水烟筒吸,心想这些人真是无聊,这种水烟筒么,一吸就哗啦啦地响,还不就是让人吸个热闹,像老许这样的人,家人不在身边,一个孤老头子,哗啦啦吸一吸还可以,他以为其他人都是装装样子。可今天的王帮国却是非常非常地想试一试。于是王帮国放下背上的工具,从老许手里接过水烟筒,学着老许的样子,哗啦啦深吸下去。这一吸可不得了,王帮国只觉得一股苦得让心口冒烟的味道从烟筒直钻到肺里面去,把肺搅得乱七八糟,王帮国于是大咳起来,咳声直传到家具厂外面的居民区,把居民区外的天空咳得一抖一抖的,几颗星子于是掉下来,一直掉到城外的天边。
【责任编辑 杨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