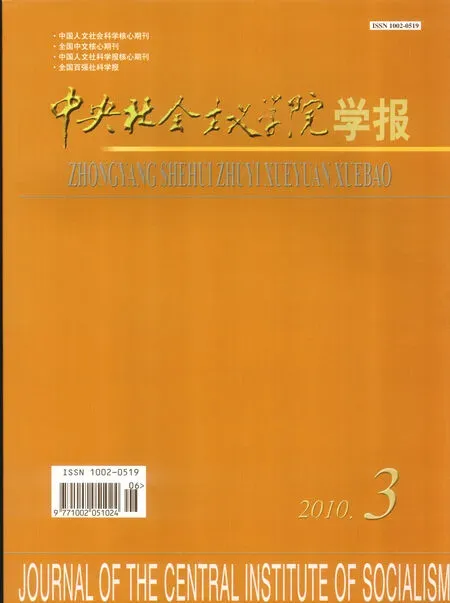列宁、斯大林处理群体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贺佃奎
(广东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列宁、斯大林处理群体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贺佃奎
(广东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列宁在处理工农群体冲突时,是以公平为理念、以满足农民的合理要求为出发点、以发展生产为目的、以合理妥协等方式来化解矛盾的;而斯大林则主要是以“贡税论”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为指导,用行政强迫的方式甚至以发动群体冲突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认真分析和研究列宁、斯大林的这些做法,对我们今天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体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群体冲突;社会矛盾;新经济政策;阶级斗争;两极分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逐步显现,群体冲突时有发生,所有这些,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如何正确认识并有效化解群体冲突,已成为摆在我们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前苏联两代领导人处理群体冲突的理论与实践,对当前我国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体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冲突,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认为,冲突是一种应得的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而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赛(Lewis A·Coser)则认为:“可以权且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1]由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刘易斯·A科赛认为,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物质性的,即权力、地位方面的不平等,以及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均衡;另一类是精神性的,主要是价值观念和信仰的相异。
群体冲突通常表现为群体性事件、聚众闹事等。我们认为,群体冲突是指某种松散的、或紧密的利益结合体,包括社会阶级、阶层甚至一些游离于社会组织和团体之外的群体,为了某种或某些实际利益结合在一起而进行的对现实的对抗活动。
群体冲突既包括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战争、镇压运动等阶级斗争形式,也包括小规模的群体冲突,如罢工、游行示威、群体集会、集体上访、极端个人行为等。就其形式而言,有劳资冲突、工农群体冲突、企业与居民的冲突、教派之间的冲突、政府与某些群体的冲突(官民冲突)、群体内部的冲突等等;就其性质而言,有政治冲突、经济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信仰冲突等等。在不同社会,群体冲突的表现形式和强烈程度是不同的,对抗的性质也是相异的。
群体冲突与社会矛盾有所区别。社会矛盾之内涵较群体冲突更为抽象,而其外延则更为广泛,它包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如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等。就人际矛盾而言,它不仅包括阶层矛盾,而且包括个人矛盾;不仅包括现实矛盾,而且包括思想方面的矛盾和价值方面的矛盾等。仅就群体之间的现实冲突来看,社会矛盾与群体冲突才是重合的。
群体冲突与阶级斗争具有属种概念的区别。阶级斗争属于政治类的群体冲突,是群体冲突中对抗最为激烈的一种,是群体冲突在阶级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群体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也有区别。当群体冲突表现剧烈,酿成了有影响力的后果时被称为群体性事件。因此,群体性事件是群体冲突的表征。但是,群体性事件并非是群体冲突的结果,有些群体性事件并非由群体冲突所致,如发生的火灾事故中衍生的群体性踩踏事件等。
马克思开创了研究和解决群体冲突的先河,他与恩格斯重点研究了剥削阶级社会两大对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群体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即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
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政策成了调节和影响群体利益关系的重要工具,而广大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也是一致的,从而消除了大规模冲突的可能。但是,人民的利益包括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如果国家的政策不当,就有可能使这二者之间出现局部利益失衡,从而引起部分群体的不满甚至导致群体冲突。此时,国家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正确与否就至关重要,它决定着群体冲突的解决程度以及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列宁处理群体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了俄国的政权,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根本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巴黎公社的初步实践、俄国当时面对的与帝国主义作战的特定情况以及俄国共产党的理想,根据列宁的提议,在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这一体制是对共产主义在落后的俄国的初步试验,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是,它同时也引起了两种群体冲突:第一种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与被俄共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体的冲突。这一冲突是剥削阶级的财富或者在既有的体制下被剥夺,或者有潜在被剥夺的危险。所以,他们拚命反抗,力图改变既有利益的划分格局。对此,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暴力方式加以解决。第二种是工农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实际上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用列宁的话说,这一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使无产阶级专政之政权不稳固。本文重点探讨的是第二种冲突。
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是指 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围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实行工业、银行、商业组织国有化,普遍劳动义务制,取消自由贸易,经济关系实物化,预备消灭货币,建立统一的分配机构“消费公社”以及余粮收集制等。列宁说:“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2]而当时所付的纸币都是一些急速贬值的“彩色纸片”,用它买不到什么东西。因此,这就近乎于无偿剥夺农民,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农民的潜在不满。
三年国内战争一结束,一切为了战争的情况已然转变,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农民起初的不满情绪随之显现,特别是广大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逐渐演变为普遍的骚乱和暴动。“在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处处出现了自发的暴动,参加暴动的不仅有富农,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农。即使在没有发生暴动的一些省份,农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明显。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粮食机关写了大量申诉信和请求书。”[3]并且不少农民前来莫斯科上访,甚至在 1921年出现了喀琅施塔得兵变。“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普遍现象”[4]。这说明,当时的群体冲突已经非常严重,是工农联盟即将破裂的信号,对新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对于当时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冲突,以列宁为首的苏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畅通沟通渠道,充分倾听农民的心声
列宁把农民的信件看作是农民情绪的最好“晴雨表”,他阅读了大量农民上访的信件,接见了前来莫斯科上访的农民群众。在列宁的笔记中记载了一次非党农民会议上的谈话,其中一位吉尔吉斯的农民说:“粮食被收集得像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5]列宁把这些意见分别转发给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参阅,要求他们重视农民的情绪和要求。通过这些方式,列宁充分了解冲突群体的意见与疾苦,为及时调整政策提供了依据。
(二)制定新经济政策,以政府对农民的妥协来消除冲突
1921年 3月,列宁在俄共(布)会议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提出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实物税、将国家垄断贸易改为自由贸易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必须在工农之间确立合理的经济关系,“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的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大多数农民阶级之间达成妥协”[6]。所谓“妥协”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益妥协,即大幅度减轻农民的负担,相应地减少政府的收入;二是政策妥协,即实行农民喜欢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当时的观点认为,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会后,中央通过新的法令,规定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实物税;实物税额应低于在目前实行的以余粮收集制方法征收的税额;随着工业的恢复,苏维埃政权将用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换取农民的农产品;完成纳税义务以后剩余的全部粮食、原料和饲料储备,归土地耕作者自行全权支配、自由流通。上述措施在施行后,化解了农民群体的不满情绪,迅速平息了群体冲突,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一年来 ,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 ,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几亿普特的粮食 ,而且没有任何强制手段……农民完全满意目前的境况 ……全体农民对我们完全没有什么严重的不满了。这是一年来取得的成就。”[7]
(三)以群众满意、调动生产积极性作为消除冲突的政策理念
在解决因余粮收集制而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群体冲突的过程中,政策的制定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是以头脑中固有的理想、主义为标准,还是以群众的满意度为标准?这个“主义”与“满意度”的取向,是当时尚处于年幼的苏维埃政权所面对的难题。列宁的做法是,要让广大农民群体满意。“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8]。而粮食税制与自由贸易政策,则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进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或动力”[9]。农民满意了,生产力发展了,群体冲突才有可能被消除。
(四)以公平的理念、市场交易的方式处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按照当时的情况,国家急需掌握大量的粮食。但是,粮食大部分在农民手里,仅靠农民交的实物税尚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此时,要想取得农民的余粮就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收取的办法;另一种是通过市场公平自由地交易的方式。前一种办法虽然效率高,但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会引起群体冲突;后一种办法尽管符合正义理念,但是,需要政府付出代价,即要更好地发展生产,生产出农民所需要的产品,也就是说,国家要有商品、有经营能力才能获得农民的余粮。列宁使用的是第二种办法。他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社的形式,用城市的工业产品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将农民手里的余粮收集起来,以解决城市之需。为此,列宁向全党发出了“学会经商”的号召。列宁还提出 ,作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必须具备“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本领”,要具备按先进的“欧洲方式”而不是按落后的“亚洲方式”做买卖的“文明商人”的本领[10],促使小农经济转化为真正的现代大农业。
(五)对于暴力性冲突采取坚决镇压的做法,迅速维护社会稳定
苏维埃政府为了避免流血,曾经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亲自前往喀琅施塔得解决暴力冲突,尽管他极力向士兵们进行说服和解释,但是,都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派红军才迅速平息了兵变。
二、斯大林处理群体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不久就废除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经济模式以工业化为目标,以近乎单一化的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以立法、行政、司法三合一的中央集权为依托,以单一的计划和命令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大海中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较快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
但是,斯大林计划体制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他在处理群体矛盾时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很大的失误。列宁逝世后,苏联面临着急速工业化的要求与资金积累短缺的矛盾,对此,斯大林采取的是剥夺农民、发动大规模群体冲突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以“贡税论”形成对农民群体的无偿剥夺,人为地增加群体冲突
所谓“贡税论”,是由斯大林提出的一种处理工农关系的理论。1928年 7月,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粮食收购危机问题,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积累源泉除了工人之外就是农民,农民必须为实现工业化而缴纳“贡税”,即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化缴纳“额外税”。
“贡税论”的提出与 1927年底至 1928年春的严重粮食收购危机有关,而此危机又反映了苏联经济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对此,斯大林不是从调整经济关系入手,而是采取了剥夺农民群体的办法来解决,这就不能不引起农民群体的强烈不满。
(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令农民群体组织集体农庄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斯大林违反了改造农民的自愿原则,而是用行政命令或变相暴力的手段强迫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各级政权为了完成命令,层层加码,有的地区的苏维埃机关,干脆规定农民一律加入集体农庄,凡拒绝加入者就没收其土地,并剥夺其选举权。有的州还提出:“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11]
在全盘集体化的高潮中,普遍将农民的住宅、小家畜、家禽、非商品乳畜等,统统加以公有化。各地农民因惧怕牲畜被集体化而滥宰滥屠。“1930年 2、3两个月内,屠宰掉的大牲畜约 1400万头,猪被屠宰掉1/3,羊被屠宰掉 1/4”[12]。这些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强制性的集体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体冲突。就政府而言,采取的是积极的冲突行动,即通过行政命令、组织处理、法律制裁的方式强令农民服从,强迫行为就是冲突的一种;就农民而言,他们采取的是消极冲突 (消极抵制)的方式,如在集体化运动中,“消极怠工、损坏劳动工具、忍痛挥霍多年的积蓄,几乎成为普遍现象”[13]。对于这种消极冲突的方式,斯大林在答复肖洛霍夫时有所描述:“你们的区里(而且不仅是你们的区)可敬的农民实行‘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不惜使工人和红军挨饿。尽管这种怠工是无声的、表面上不伤人的 (不流血的),但是它并不改变这一实质,即可敬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无声的战争’。这是把对方搞垮的疲劳战,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14]
这些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思想。
(三)以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方式消灭富裕农民与党内不同意见者
第一,消灭富农。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新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农村普遍走向富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因善于经营而变得富裕的农民。应该说,这一阶层的农民与十月革命前的富农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俄国农民发展的方向。但是,出于集体化的需要以及其他需要,斯大林却对其采取了强制剥夺的冲突方式。
斯大林论述了剥夺的原因,资本主义的老根“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农业“还是一个便于富农分子进行剥削的场所”[15]。斯大林还号召向“集体农庄的死敌”富农进攻。1929年 12月,斯大林说:“现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侈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摧毁富农的反抗,把他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富农的生产。”[16]
于是,在 1930年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大规模群体冲突运动。在此后的两年里,“共有 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有 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村’,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集中营”[17]。对富农的阶级斗争,导致了大量富农及无辜群众的死亡,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据斯大林透露,1942年在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 1000万[18]。
消灭富农的政策,是以有组织的群体冲突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造成了人权可以随便被侵犯、越穷越光荣的恶劣社会风气。
第二,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将肃反扩大化。斯大林错误地解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成就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斯大林还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人民敌人”,以支持他自己的主张,主动发动群体冲突。
斯大林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发动了 20世纪 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1934年 12月 l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遭暗杀。这本来是一起刑事案件,诉诸司法解决即可。但是,斯大林却借此在全国开展肃反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的阶级斗争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 1938年秋,“先后牵连的人在 500万以上,其中 40多万人被处决”[19]。而与斯大林意见有分歧的中央领导人布哈林等都被当作“阴谋集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则以“组织恐怖集团”等罪名被处决。
对于社会矛盾和问题,通过发动大规模的群体冲突等方式加以解决,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教训是惨痛的。
三、苏共两代领导人处理群体冲突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苏联共产党两代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和群体冲突的理论与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学习和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指导我们当前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群体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党的政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建应当以调动和发挥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创造力为根据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能使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要求党在制定政策、建立具体的经济运行体制时,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根本要求。“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引导而不是强迫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情走向,就会使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热情。列宁在处理工农两大阶级矛盾时,当发现政策与群众的利益相抵触时,就适时地采取了农民所喜欢的实物税制和市场交易方式,从而解决了城乡两大联盟的冲突和矛盾,并且迅速解决了粮食危机问题,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二)对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利益冲突应当通过经济手段予以和平化解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个人秉赋、机遇、自然条件等的不同,必然会有一定的贫富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此导致的小范围群体利益冲突也在所难免。对此,如果采取革命时期直接剥夺的强制方式,不仅有失公平,而且还会使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挫伤,使社会生产力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有深刻教训的。社会主义不应当否认人的先天和后天差距这一客观事实,而应当正确引导和调节。既然个人除了劳动所得外,其他财富均来自社会,党和政府就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经济、税收杠杆来调节收入,从而使社会走向公平。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对富裕人群执行的税率最高可达 70%以上,使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这点值得我们加以借鉴。当然,这并不是要完全抹杀差距,而是为了鼓励社会成员更加努力地工作。
(三)正确理解群体冲突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民主正义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当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群体冲突对于改进生产关系,即具体的体制是有一定作用的。社会的运行正常与否,党的政策执行效果如何,总会通过社会的反馈机制表现出来。群体冲突正是此反馈机制的一个表现,它表明社会运行出现了某些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调节和利用规则进行改进。不管是何种体制,总会出现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总会出现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弹性的社会是允许一定范围的群体冲突的,因为它表明社会体制中有一些不合理的关系,使一定的群体受到压抑,而适当地调整社会关系,有利于社会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这种整合在化解矛盾时,也会使社会更加民主化、更加公平。从这个角度讲,适度的、和平式的群体冲突是改革的一个推动力。刘易斯·A科塞认为:“一个弹性的社会在冲突中受益,因为这种行为通过创新的改进规范保证了它在新条件下继续生存。”如果压制冲突,就会“消除了一个有用的警报,因此把灾难性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20]。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群体冲突都是有正功能的。非和平的、破坏性的群体冲突,政治性的反社会组织会使社会走向崩溃,这是必须予以打击的。列宁的做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20]刘易斯·A科赛.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42,137.
[2][6][8][9]列宁全集 (第 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08,51,53,63.
[3][11][13][17][19]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7,68,287,297,321.
[4][7][10]列宁全集(第 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0, 280,364.
[5]列宁文稿(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7-389.
[14][15]斯大林全集 (第 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18, 36.
[12]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49.
[16]斯大林全集(第 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8.
[18]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 4卷下部,第 3分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733-734.
责任编辑:张秀红
D012
A
1002-0519(2010)03-0094-05
2010-03-17
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 2007年度资助课题(07H07)
贺佃奎(1964-),男,陕西榆林人,广东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