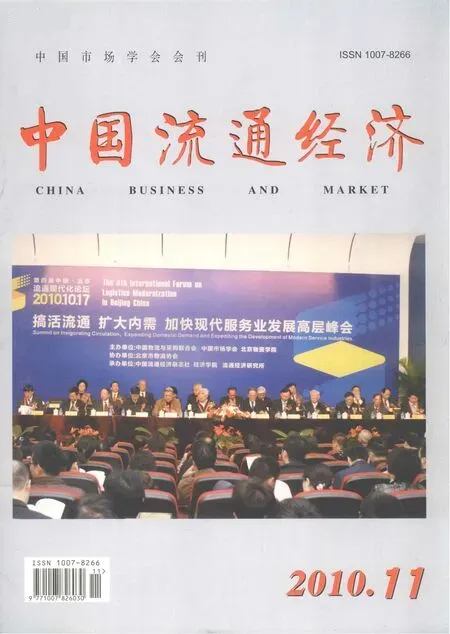论城乡一体化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市 100871)
论城乡一体化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市 100871)
今后30年,我国改革的重点将是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应该是双向的,即农村居民可以迁往城市,在城市工作或经营企业,城市居民也可以迁往农村,在农村工作或经营企业。我国目前的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是单向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关键不仅在于城乡居民户籍分列,更重要的在于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双向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应该尽快消除这种体制障碍,赋予农村居民财产权,发放房屋产权证,将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双向的城乡一体化,有利于中国经济走向以居民消费拉动为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城乡一体化;农民财产权;财产性收入;就业渠道;
一、为什么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
在农村调查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提出为什么不发房产证的问题。有的农民说:城里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在那里,无论是祖传的房屋还是新购的商品房,都有房产证;而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祖传的房屋也好,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的住宅也好,为什么不发房产证呢?农民们想不通。看来这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
农民还反映,由于自家的房屋没有房产证,既不能抵押,又不能转让,要进城经商、开店或打工,如果把家属也带到城里去住,只好门上一把锁,让老鼠在房屋里做窝。那么,为什么不出租呢?有熟人愿意租房,当然是件好事,但正因为出租者没有房产证,只能廉价租给熟人,等于请人代为照看住宅,而不敢租给陌生人。怕自己没有房产证,人家拒不支付租金怎么办?或赖着不走又怎么办?村干部说,还有更糟的呢。比如,农民一家人都进城了,门上锁了,有的却被撬开,在空房子里堆炸药,于是变成了地下爆竹作坊;有的变成炼地沟油的黑店,还有的成了聚赌嫖娼的窝点,给村里带来不少麻烦。
至于那些为住房上锁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则是两手空空,什么资本也没有,因为房屋不能抵押,不能转让,不能合法租出,还有什么资本可以带走?即使进了城,没有房子可住,只得搭个窝棚聊以栖身、安置家属,或者租间地下室住,又潜入地下,过着极其简陋的生活。这就是所谓“两只老鼠”的故事(农村里的自家房屋成了老鼠窝,进城后又过着同老鼠一样的地下室生活)。
这里不妨以19世纪中期以后法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民进城的情况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不少贵族地主逃亡国外,法国革命派把他们的土地没收之后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拿破仑当权后,用法律确认了新的土地关系。波旁王朝复辟后,不敢把农民分得的土地重新归还贵族和地主,因为担心社会动荡。这样,法国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巩固了下来。19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进行,农民纷纷进城。法国成立了不动产抵押银行,容许农民用自己的田产房产作为抵押,带资进城。于是,准备进城的农民不是空手进城,而是带资进城,或开店,或做工,且有房子可住,并且隔一段时间之后把家属也带到城里,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有序进行。农民的田产房产虽被抵押,但等到进城的农民收入增加了,借银行的钱还清了,田产房产依然是农民的。如果农民感到在城里有更大的发展前景,这时还可把田产房产卖掉。
然而,在我国农村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农民没有房产证,他们想开店创业,或在农村扩大经营规模,但靠什么作为抵押品取得贷款呢?农民的房屋不能抵押,这意味着房屋在农民手中并未被确定为个人财产。不仅农民的房屋未被确定为个人财产,连宅基地、承包土地也都如此。农民没有财产权,怎么可能有财产性收入呢?农民没有财产权,想转让自己的承包土地、宅基地和房屋也就不可能如愿。
假定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那么在当前条件下,能不能把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处理?即房屋可以转让,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也可以转让。这是一种变通的做法,而这种变通是必要的。既然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那么它们用于抵押,也就无可争议了。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实行这一制度创新刻不容缓。实践将会证明,它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农民有了财产权以后中国农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让我们仍从农民的住房开始分析。
怎样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给农民各种补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通过农业产业化来增加农产品加工值……等等,这些都是有效的措施。但最重要的是让农民拥有财产权。首先是给农民发房产证,容许农民用房产证作为抵押,取得贷款;出租房屋,取得房租;转让房屋,把实物资产转化为货币资产,再转化为资本。具体的做法可以先从农民迁入新农村的住宅开始,因为散居的农民和他们的房屋由于宅基地面积大小不一,农民之间矛盾很多,一时不易处理。加之,发房产证从农民迁入新农村的住宅开始,还可以鼓励散居的农民向新农村迁移。
据2010年6月5日上海《文汇报》第一版所载,上海市嘉定区在农民迁居之后,每户农民可以分到三套住房,面积分别是 60m2、80m2和 110m2,每户任选两套自住,余下的一套供出租之用。三年之后,房屋可以自由买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2010年7月初在山东省威海市调查时,在其近郊的“小城故事”社区看到了类似的情况。这个社区是由几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的。在那里,每户分得两套住房,都是90m2左右的,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如果农民认为自己住一套就够了,也可用另一套换得几十万元现金。
这样,农民有了可供出租的房屋,或者像威海市“小城故事”社区那样,把可出租的那一套房屋变成现金,农民的收入立马就上升了,日常生活没有问题,而且还有创业的资本金,开店、做生意、外出务工都行。我们在威海市看到,只要农民有房屋可以出租、抵押或转让,他们的经济便活起来了,他们的内需就扩大了,他们的创业活动也就开展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由于在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限制的条件下,即使地方政府想给农民住房发放房产证,也难以真正落实。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的调查,在山东省大体上有三种发放房产证的方式:
一是把土地收归国有后,由房地产主管机构发放正式的房产证。威海市“小城故事”社区就是如此。合并为“小城故事”社区之前,这里原来是几个行政村,属于“城中村”改造的范围,所以行政村一合并,社区一建立,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农民也就相应地成为市民,发房产证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其他省市,凡属于“城中村”改造的地带,也都采取相应的做法。
二是在保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建成新农村,在农民搬进新居后(如莱阳市的一些农村)由城乡建设部门发给房产证。有了这种房产权证,农民不仅可以出租自己的房屋,而且还可以用于农村信用社的抵押贷款。对农民来说,因为农村信用社离自己家很近,贷款是很方便的。
三是行政村同龙头企业融为一体。在龙口市南山集团公司所建的新农村,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入股,公司经营园艺、果树、酿酒、旅游、养殖、其他工业品制造等,农民成为公司职工,公司兴办各种福利事业,并建设新农村住房。农民作为股东每年有红利可得,作为职工每月有工资可领,同时享受各种福利待遇,还分到新农村中的住房,并由集团公司发给房产证(在集团公司内部是承认的)。
农民有了房产证以后,不仅如前所述有了创业的资本(抵押、转让),有了经常性的财产收入(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住房紧张的压力。城市房价高,一般城市居民不一定能买得起商品房,而城市可供出租的房屋通常供不应求,因此农民有多余的房屋可供租赁,对市民是有好处的。离市中心较近的“城中村”改造后,新建的农民住宅中有不少已经租给城市居民,他们上班近,附近又有学校、医院或卫生站,生活很方便。即使离市中心较远的农村,只要公共交通通畅,或者租房子的人家有私人小汽车,也可租赁农民的住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离城市并不太远的农民家庭都有空余房屋出租时,对城市居民方便,对作为房东的农民也有利,因为他们会增加收入。
给农民发房产证的好处已如上述。那么,宅基地与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和转让,又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以下让我们接着分析。
三、双向的城乡一体化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城乡一体化都是双向的。而迄今为止,我国正在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则是单向的。双向的城乡一体化是指农民可以迁往城市居住,可以在城市工作或经营企业,而城市居民也可以迁往农村居住,可以在农村工作或经营企业。中国目前的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是单向的(即只有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不存在城市居民向农村的迁移),关键不仅在于城乡居民的户籍是分列的,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土地制度是二元结构的,即城市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农村实行的则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双向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
能否绕过这个制度障碍,把土地所有权同土地使用权分别对待?根据龙口市南山集团公司和当地一些行政村融合为一体的经验,是可以走出一条新路的。这就是农民可以把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入股于南山集团公司,把宅基地的使用权交给南山集团公司,换取新农村的住房并取得房产证。当然,龙口市的经验只是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若干经验中的一种,但这已经可以说明,如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入股、置换、抵押或转让,符合这一标准的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于是,双向的城乡一体化就具有试行并逐步推广的制度条件。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一方面可使农民“带资进城”,加快了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城里愿意迁到农村的个人和企业也可以如愿以偿,“带资带技术下乡”,在乡下生活、工作、投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将随之取消,代之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制度。随着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传统的服务业会进一步发展,而且现代服务业也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中的比重也将不断上升,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趋于合理,新的岗位将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涌现出来。到了那个时候,城乡社会保障也将一体化。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将逐渐淡化,追求生活质量成为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内需将会有大的突破,中国经济也会转入以居民消费拉动为主的良性发展。
双向城乡一体化之后,中国农业将会有大的发展。限制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体制、资本、技术和物流。其中,体制因素最为重要。
第一,体制。关于体制因素,前面已经提到。农业规模效益之所以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农业产业化之所以难以有更大的突破,充裕的民间资本之所以不愿投向农业和农村,以及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进展得相对迟缓,全都同承包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有关。而农村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和专业人才,同样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因此,如果在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方面寻找突破口,绕开现存的体制障碍,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第二,资本。一旦体制障碍减弱了、消失了,农村不愁没有资本可用,农民也不愁没有融资渠道。特别是在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条件下,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总会相伴而行。其中,资本下乡最为关键,而且资本下乡是先行的。过去被认为没有投资价值的重大项目,如低产田的改造、沙漠化和石漠化的治理、农村公用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等,都会因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第三,技术。技术下乡要同资本下乡结合在一起,都应当给投资人带来收益,否则就是技术下了乡,也不会持久,更不能使技术的采用范围大面积地推广。这个问题也只有在双向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解决。要知道,在单向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的青壮年和专业人才都进城了,谁还会专心致志地使新技术在农村开花结果呢?
可以设想,在双向城乡一体化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除了仍有一部分农业中的散户而外,大体上有三类农业生产者:一是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他们是种植能手、养殖能手,通过转包、租赁、转让等方式,集中了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二是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专业合作社的骨干,一定是懂得经营、善于管理,并且在农业方面懂行的人才。他们同样从事规模经营,会使农业进一步发展。三是“龙头企业+农户”。这里所说的农户,可能是承包土地入股之后仍然留在龙头企业工作的人,也可能是承包土地入股后进城另谋出路的人。这一类农业生产者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使农产品产业链有较大的延伸,并且在营销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
四、让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农村
到了工业化后期,尤其是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来,为什么西欧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农民不再涌入城市去寻求工作?对这个问题需要从工业化的历史进行分析。
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业化,从18世纪70年代算起,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补充了各行各业的工人队伍。到现在,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已经释放完毕。现在西欧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只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百分之几,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在这些国家,农民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拥有自己的住宅,城乡的生活条件一样,甚至农村空气更清新,比城市更能吸引人居住。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社会,城乡没有差别,现在的农民为什么还要舍弃自己的家庭农场和住宅,跑到城里去打工呢?进城打工,那是他们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的事情,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西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农村和农民的现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西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城乡一体化是在工业化后期实现的。而在这之前,即在工业化中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已经消失或基本消失,这就有利于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由于体制上的某些障碍仍然存在,所以有一个先实现单向的城乡一体化,再实现双向的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消除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之一。
第二,城乡生活条件一样,这也是西欧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实现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基础设施较差,公用事业的发展程度较低。但仅仅依靠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以加快缩小城乡生活条件之间的差距。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国并使城乡没有差别,是一个渐进的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根据中国的国情,有必要有序地逐步推进。但最终必须闯过这一关。归根到底,这是国家和地方是否有足够财力的问题。因此,经济发展不可停滞,财政收入应当与经济同步增长,甚至需要略快增长。
第四,也许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居民观念的更新。这里所说的居民观念更新主要是指:无论住在城市还是住在农村,居民都应当有公民意识,有权利和义务的意识,有社会责任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不是什么人的恩赐,也不允许任何人对它进行破坏。有了这种观念更新,社会保障体系才能长久存在。
阿东说:“蛮好。我姆妈原先每天七点半叫阿里起来,现在叫他提前起。把录音机带着,到东湖边去放哀乐。那里没有什么人,放多大声音都不怕。”
这样,我们对于全国许多地方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有新的认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岂止是一排排新盖的住宅楼。应当进一步询问的是:搬进来居住的住户们是不是领到了房产证?住户们有没有权利出租、抵押、转让?也就是说,有没有产权?此外,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落实到人?
新农村是一个社区。这里的公共设施如何?孩子们要进幼儿园、小学,有没有这样的设施?病人要住医院,附近有没有?平时有没有卫生站可以看病?有没有救护车可以运送急症或重病患者?有没有敬老院之类的设施?水、电、气、暖的供应状况如何?方便不方便?这些都是建设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新农村可能位于远郊,甚至位于距市中心很远的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交通和居民生活设施建设。既然要逐步缩小城乡在生活条件方面的差距,那就不能仅仅以让农民搬进新房居住为满足。
新农村作为一个社区,住户的业主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受到保护。社区应设置公共活动的场馆和聚会的会所,使业主有条件行使自己的权利。民主和自治作为社区管理的原则,要始终坚持不懈。
最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居民,都应当有迁移的权利,也就是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城市的规模应有较严格的控制,县城和镇应该是放开的,容许居民迁入迁出。愿意住在城市还是愿意住在农村,居民可以自行选择和调整。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两边都有家。这样城乡的差距在居民的观念和心理上自然而然就缩小了。
总之,建设新农村的住房并让农民搬进去住,这只不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步。要让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农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而且决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曾指出,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前30年,我们着重于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在30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尽管国企体制改革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但大势已定,改革已不可逆转。从2009年算起,改革开放后的后30年,即到2039年为止,改革的重点将是城乡二元体制,以及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由于前面所说的城乡一体化任务艰巨,所以用30年的时间能否实现城乡一体化,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程度。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政企不分和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及城乡生产要素分割和农民没有明确产权的城乡二元体系。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的后30年,改革重点是城乡二元体制;那么,在改革开放60年左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体制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IYi-ning
(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promote the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which means that the rural citizens can resettle in the city and the urban citizens can also resettle in the rural areas.At present,causes for the existing one 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o not only include the separated rural and urban residence registration system;the dual structural land system is the more important one.And the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rural areas i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We should eliminate this institutional barrier,give the rural citizens more right on property,and make the rural citizens to expand income resources by becoming a shareholder,mortgaging or transferring the ownership of housing,land for contract operation and private housing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and expand consumption.The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ll make China's economy to be citizen consumption-oriented,benefit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benefit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property right of rural citizen;income from property;socialist countryside
F120.4
A
1007-8266(2010)11-0007-04
厉以宁(1930-),男,江苏省仪征市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等职,曾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主要代表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等。
林英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