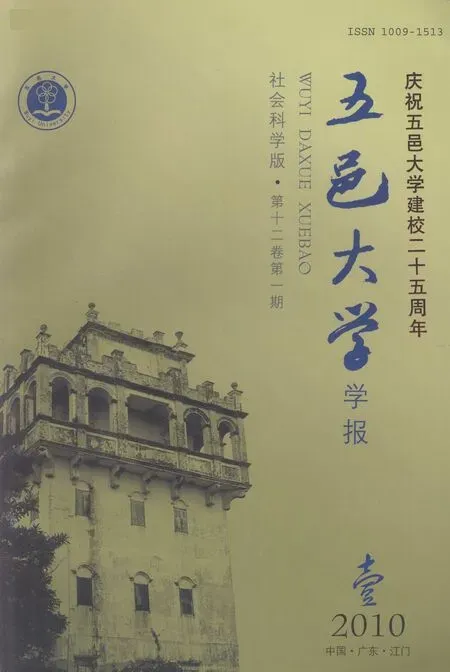主体的召唤与实现
——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新探
郑焕钊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主体的召唤与实现
——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新探
郑焕钊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梁启超认为,传统文化对小说的歧视导致其创作主体沦为华士商贾,整体品位不高。而要实现“新民”,就必须吸引新兴知识分子投身政治小说创作,利用小说的通俗性、感染力来传播启蒙思想。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与科举制的废除为此提供了现实条件,促成文学格局从以诗文为主向以小说为主的演变。
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主体;
中国近代启蒙小说理论的兴起,并非在小说创作繁荣基础上的概括。当时民间通俗小说确实受众很广,但晚清小说理论的兴起却着力于改变民间通俗文学“诲淫诲盗”的芜杂局面,从而利用小说的通俗性、感染力来传递启蒙思想,实现国民政治觉悟、道德品质的改造。因此,它体现出一种提倡创作的特点。问题是,这一特点如何促使晚清近代小说理论冲破传统诗文理论的限制,独立发展并成为20世纪的文论主潮?这显然是思考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作为典型个案,对思考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精英对大众、知识分子对平民的启蒙,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两个阶层的利益、关注、语言判然有别,难以有效地进行思想沟通。因此,启蒙的前提在于精英对大众思想的渗透。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看来,小说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认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敎,当以小说敎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34这就在于小说能够广泛地被阅读,并且还有国外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譬如日本变法的成功就是“赖俚歌与小说之力”[2]。当时,此一看法相当普遍。商务印书馆主人就同样认为:“欧美化民,多由小说。”[3]严复、夏曾佑在其著名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也持有相同的看法,称“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4]12。因此,在梁氏看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5]小说成为启蒙的利器。
小说能够实现这一功能,首先在其语言的通俗,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写作的的弊端,集中体现在语言过于艰涩,下层百姓难以通晓,因而他们的思想受到那些以商业利益为目的、出版诲淫诲盗小说的书商的限制,阻隔了启蒙思想的传递。其次,小说的感染力是小说能够实现启蒙目的的第二个条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对“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进行发问。他认为,小说具有“写实”与“理想”的功能。同时,小说拥有“熏”“浸”“刺”“提”四种力,能够从里向外激发读者的想象、情感,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5]小说感染力如此之强,则其内容的好坏就直接影响着读者的精神、思想乃至行动。因此对新小说的思想要求,就成为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主要的关注点。
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5]旧中国的封建迷信、官僚主义乃至无视公序等一系列违背现代社会的现象,正在于小说的浸染。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5]腐败之总根源在小说,那么旧有小说的思想内涵在梁启超看来就是需要改造的。而旧小说之所以腐败,根源在于创作主体,这又跟中国传统文化对小说的轻视有关。《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家的定义,即是这一腐败的总根源:“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段话指出,小说被视为“小道”、“小知”,与治国平天下相对,是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东西。邱炜爰在《菽园赘谈》中也指出:“诗文虽小道,小说盖小之又小者也。”[4]15所以,深受正统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士人阶层不愿从事小说创作,“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君子,吐弃不肯从事”,这便导致“儇薄无行者,从而篡其统,于是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6]形成恶性循环。这一思想形成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的基本逻辑。早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梁启超就已指出这一困窘:“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7]因此,“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5]文化领导权丧落到华士坊贾手中,“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这是传统士人君子主动抛弃的结果,华士坊贾利用小说的通俗性和感染力,遂使小说“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最终他们“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5]
因此除了从根本上斩断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别无他法。这就要求知识分子阶层取代华士坊贾的位置成为创作主体,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小说“诲淫诲盗”的内容,置入启蒙思想。正如平子后来在《新小说》中所说:“夫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其小说不可以不高尚。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则求高尚之小说亦难矣。”[8]但是,如何让传统士人投身于小说创作,克服传统对小说家职业、身份的鄙视,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梁启超主要是从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改造入手来实现这一转变的。[9]
二
在当时,较普遍的做法就是借介绍西方小说家的“政治家”、“名流”的身份来改变传统观念对小说家的偏见。林纾就借助口译者“晓斋主人”告诉读者:“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4]24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1901年),林纾在《译林序》提到:“昔巴黎有汪勒谛者,在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至今巴黎言正学者,宗汪勒谛也。”[4]26这更证明小说是正统之学。在当时知识分子明显意识到西方文明的进步和力量之际,这一方法显然是有效的,像李伯元等人即专门投身于小说创作。梁启超对此深为认同,也认为西方小说的作者往往是“魁儒硕学,仁人志士”[1]34。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900年),在其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署名为“衡南劫火仙”的文章,明确指出欧美小说家真实、确切的身份:“已故英国内阁皮根之《燕代鸣翁》一集,其原稿之值,获一万磅。法国《朝露楼报》,发行之数,殆及百万册,然其发行之流滞,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为如何。此亦足以验泰西诵读小说之风盛于时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邱炜爰《挥尘拾遗》出版,其中《小说与民智之关系》一文也提到:“英国有皮根氏者(旧任内阁),小说名家也,尝著某帙(今日本人有译之,题以汉文,即名为《燕代鸣翁》者是也),纸贵一时……其他名家类此者,亦时而有。寻常新著小说,每国年以数千种计云。观此而外国民智之益,已可想见。”[4]31政治名流投身创作小说与西方民智提高的关系,似乎显得非常正当、自然。梁启超在宣扬日本政治小说时,也同样宣扬作者的水准和身份:“著者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10]42,“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10]42。因此,面对当时衰弱的国势、蒙昧的民众,目睹西方欧美日本的成功经验,对于承载新民救国使命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从事小说创作呢?至此,梁启超理论的重心得到显现,这就是对创作主体的呼唤——拥有一批“鸿儒硕博”,由他们创作新小说——政治小说,从而实现改造国民的目的,这才是理论的最终归宿。
同时,从传统士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向近代知识分子小说家身份的转化,必须从心理上完成过渡,“政治”与“小说”的结盟便成为最好的方式。因为一方面“政治”是当时知识分子强烈关注的对象,涉及安身立命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政治小说具有崇高的目的,能够使得创作主体倾注政治热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梁启超便畅眀其旨:“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6]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基于日本政治小说的成功经验。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蓄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於是彼中缀学之子,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巿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34-35既然政治小说功能如此之伟,而小说又仅仅是一种手段,因而知识分子的心理包袱可以完全地放下。
由此,梁启超拓实其“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根基,解决了知识分子向小说家身份转变以及“写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中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康有为发现:“传统士子们大都‘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11]徐念慈在1908年的一则统计中也发现,当时购买新小说的“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只有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12]钱基博指出:“迄今六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之士夫,论证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13]
三
晚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促成传统士阶层投身小说创作的重要外部条件。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进行变革,其结果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全军覆没。于是传统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层面上落后于外国,在一直引以为豪的制度、文化层面上,也落后于西方。文化思想变革促成了晚清近代思想启蒙,清末戊戌变法就在这种形势下展开。戊戌变法撼动了传统士人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科举制度,促成近代教育的兴起,形成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而戊戌变法的败局,又使梁启超等人通达政治的路径受到阻碍。无论是传统士人还是新兴知识分子,必然要重新寻求通达公共空间的途径。①另一方面,1900年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群众的愚昧,又促使有识之士不仅要从思想上学习西方,而且开始反思国民性。梁启超的“新民说”正是此一时局的产物。而近代报刊传媒的兴起,使知识分子获得了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的机会,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由此诞生。他们以报刊为媒介,宣传启蒙思想,扩大政治影响,“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14]
思想启蒙的要求与报刊形式的结合,以及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小说的优势得以彰显:小说既有利于吸引读者,又有利于传播启蒙思想,而稿酬制度的建立以及稿酬待遇的差异,更从根本上使小说创作成为文人的首选。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15]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登的《新小说社征文启》宣明稿费标准:“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自著本乙等,每千字酬金三元;自著本丙等,每千字酬金二元;自著本丁等,每千字酬金一元五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译本乙等,每千字酬金一元六角;译本丙等,每千字酬金一元二角。”同时申明稿酬只付十回以上的小说或传奇,一般诗文不付酬。[16]据包天笑回忆,当时他为《教育杂志》写教育小说,每千字三元,而他家庭开支及零用每月至多不过五六十元。另在《钏影楼回忆录》“译小说一节”,包称得一百元版税,除到上海旅费外尚可供几个月家用。可见当时小说稿费相当优厚。失去传统仕途的知识分子,通过创作小说也能过丰厚的生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这些都为梁启超所召唤的创作主体的实现奠定了现实基础。
伴随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大量小说报刊兴起。从1902年至民国建立的1911年不到10年间创刊的以“小说”命名的杂志(报纸)就有21家,更不用说没有直接以“小说”命名的。其中,1905年至1910年5年间所办的刊物有18家,可见废除科举的影响。作为读评互动的举措,报刊小说评论栏目开始形成,像《新小说》的“小说丛话”、《小说林》的“小说小话”等。评论栏目的设置,有利于引导读者进行按照作者“启蒙”思路的阅读,不过,在对传统小说(如《红楼梦》等)进行新的解读时多有牵强附会之处。随着小说探讨辩论过程的深入,最初带有强烈启蒙目的的偏颇,逐渐转为对小说艺术较为客观的评判。如“小说丛话”展开对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等的重新评估,由社会功能性逐步向文学审美性回归。《小说林》的发刊词,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创作主体的实现、小说报刊的兴起、读者群的形成、评论栏目的设置等,构成一个巨大的小说“生产场”,促成小说生产、传播、接受、批评、理论形态的整体转型。
注释:
①陈平原在《新小说的诞生》中指出:“戊戌变法的失败,截断了梁启超等人直接掌握国家政权从事社会变革的道路,使其不能不把主要精力从政治斗争转为理论宣传;同时,也使其意识到启发民众觉悟,提高民德、民智、民力的重要性。既然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而小说又有关于世道人心,于是转而大力提倡新小说——表面上梁启超等人的理论主张戊戌后有转变,可在强调文学必须‘有用’这一点上,却是一以贯之。”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一书第6页。
[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M]//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J].时务报,1897(44).
[3]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J].绣像小说,1903(1).
[4]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1).
[6]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J].新民丛报.1902(14).
[7]梁启超.变法通议[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54.
[8]平子.小说丛话[J].新小说.1903(7).
[9]蒋述卓,郑焕钊.群体心理与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的形态[J].文艺研究,2009(8):52-62.
[10]梁启超.自由书[M]//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889.
[11]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J].中外小说林,1907,1(6).
[12]觉我.余之小说观[J].小说林,1908(10).
[1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世界书局,1933:320.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2.
[1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 1971:349.
[16]梁启超.新小说社征文启[J].新民丛报,1902(19).
The Beckoning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ubject——A new exploration of Liang Qichao’s enlightenment theo ry of fiction
ZHENG Huan-zhao
(College of Liberal A rt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In Liang Qi-chao’s view,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ovels resulted inmerchants becoming the subjectsof fiction creation and its relative poor quality.To create new citizens,refo rm-minded intellectualsmust be attracted to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novelsw hose popularity and infectiousness should be used to sp read enlightenment ideas.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 rovided conditions fo r the change and p romot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oetry-and-p rose-dominated literary creation to that dominated by novels.
Liang Qi-chao;Enlightenment;the theo ry of fiction;subject
I206.5
A
1009-1513(2010)01-0011-04
[责任编辑文 俊]
2009-09-13
郑焕钊(1984-),男,广东潮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近代文学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