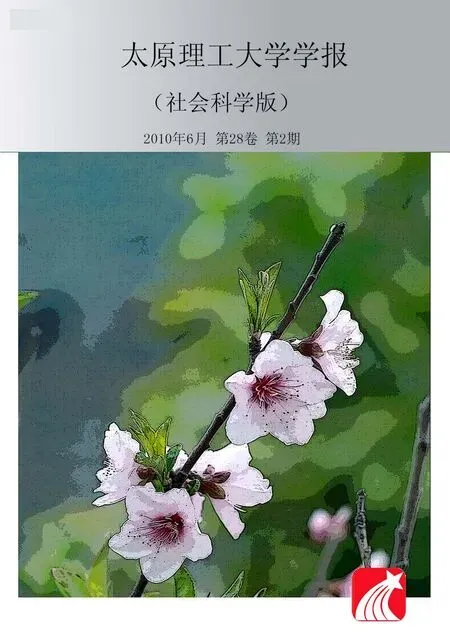庄子与柏拉图的真实观比较
——庄子诗性真实的现代意义
肖云恩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先秦时期的中国和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刚好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轴心时代,此时期盛行的诸多思想流派以其深刻性而具有开启人类文明之光的启蒙意义,其中尤以庄子的道家真实思想和柏拉图的理念真实思想为甚。本文通过仔细比较他们的真实观异同,深层次地指出以柏拉图对理性思维的注重尽管有助于科技发展,但却为后世西方文明的种种问题埋下隐患;而庄子关于真实的思想虽然有忽视人类理性认知的倾向,但却以其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诗性气质发人深省。此种东方哲学特有的诗性气质对处于科技至上、地球日益濒危,以及心灵空虚的当今时代的人们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
在西方,思想家们对存在真实性问题的解答历来都是以理性认知的角度为出发点的。无论是以认知对象来确立存在真实性的思想,如柏拉图的“理念”说;抑或是以认知主体来证明知识可靠的思想,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确立了理性认知在探讨真实性问题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而庄子则放弃了对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对象性执著追求,将存在的真实落在了审美当下的忘我体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他以中国古典哲学特有的诗性思维,将形而上的抽象思索转化为诗意的感性形象,把对“真实”问题的反思性追问具象化为审美的体验过程,使得对终极问题的拷问落实到当下的感性存在。他以人生在世的当下审美体验替代了理性认知对存在真实性的执著苛求,正是此种东方特色的思维方式赋予其真实思想以独有的诗性气质。
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很精到的将现代社会的特征归结为两大类:提倡科学、尊崇民主。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的话,现代化带给人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科学角度讲,比起此前的封建社会,现代社会实现了如较低的婴儿死亡率及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根除等诸多进步;从政治角度讲,现代社会注重更加平等地对待不同背景与收入的人。但是,隐藏在这些表面化好处的背后则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诸如:(1)推崇科技至上,将自然视为被人类征服的对象来加以无穷尽地索取,从而导致了环境恶化;(2)强调工具,一切追求最高效率和流水线式作业,使人盲目服从缺乏反思而至单向度化;(3)过于注重“完美理性”[1]的绝对真实而忽视感性感官存在的合理意义,使得个体心灵内部异化分裂只能求助于宗教信仰等。本文主张,西方现代文明的这些弊端是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们过于注重理性的传统分不开的,而庄子真实观思想中那些推崇自然、返璞归真的诗性气质则有助于当前人们处理好现代社会的那些弊端。下面我们先从分析他们各自的真实观出发,来详细说明柏拉图真实观与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端的关系,以及庄子真实观对于处理那些现代问题的理论意义。
一、 柏拉图的理性真实观及潜在弊端
尽管柏拉图本人强调只有“理念”才是绝对真实。但是通过对柏拉图一些经典著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柏拉图关于真实的思想概括为三个层面:感性真实、理性真实、神性真实。而这三种真实都暗含了一些现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的那些问题的可能性。
首先,本文所说的感性真实指感官对现实事物感知时所形成的意见,它是区别于绝对虚无的感性实在性。这是一种感受论,指在日常生活领域,感官对现实事物感知时所形成的具体可感的感性实在。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完全有的东西是完全可知的;完全不能有的东西是完全不可知的。而意见则指那种包括视、听之类感官功能获得的印象,处于可知和不可知之间的模糊地带。所以,一方面它不如永远不变的美本身或美的理式那样真实;但另一方面,却比 “无”或绝对的不可知要来的实在,它可以驱赶绝对“虚无”的恐惧。关于这个问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这样论述的:“苏[注]苏:苏格拉底;格:格劳孔。:那么一个人具有意见就既不是对于有的也不是对于无的了。格:的确,都不是的。苏:所以意见既非无知,亦非知识。 格:看来是这样。苏:那么是不是超出它们,是不是比知识更明朗,比无知更阴暗?格:都不是。……苏:因此,意见就是知识和无知两者之间的东西了。格:绝对是的”[2]。这种以感官获得的感性实在性是人们日常生活得以成立的前提,虽然这种感性层面上的真实在理性认知层面显得缺乏确定性和恒久不变性,以致被视为不真实。但它却有助于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肯定生命体存在的真实性而不至陷入绝对的虚无之中[3]。柏拉图这种过于否定感性现象且割裂感性现象与抽象本质的主客二分式的做法,尽管对近代西方科技高度的发达具有理论导向上的潜在推动作用,但也容易导致对自然界采取一味的无尽索取,致使自然环境恶化,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处于濒危的状态。
其次,理性真实则指理性思维对“理式”进行观照时所获得的真理,它指不同于感性事物的理式世界的绝对真实。这是一种符合说,指理性认知能力和理性认知对象的符合,从这个层面上说的真实是理性思维对理式世界观照时所获得的真理,这是一种以理性思维方式所构建起来的真实。在柏拉图看来,相对于现象界变动不居的感性实在,只有理式才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指出了理式的绝对真实性的几点特征。首先,理式是绝对不变的,而具体事物是经常变化的。“我们在讨论中界定的绝对实体是否总是永久的、单一的?绝对的理式、绝对的美,或其他任何真正存在的独立实体会接受任何种类的变化吗?”[4]在他看来只有符合理性认知的那种绝对不变的理式才是真正的真实。其次,理式是看不见的,不能感觉到而只能由思想掌握的,而具体事物是看得见的,“但那些永久的实体,你们无法感觉到,而只能靠思维去把握;对我们的视觉来说,它们是不可见的”[4](p82)。相对于感官所关注的对象而言,只有理式才是理性思维所关注的对象,也只有这种能符合理性认知规律的理式才是普遍适用的真实。最后,理式是永恒的、不朽的,具体事物不是永恒的、是要毁灭的。“灵魂与神圣的、不朽的、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4](p84)。总而言之,柏拉图认为只有这种绝对不变的、为思维所把握的、自我圆满的理式才是他所推崇的真实,同时它是现象界感性真实的源头,没有它也就没有现象界的感性真实。但是这种过于突出理性思维的主客二分式做法,易于导致对工具理性过分强调。在现代社会中就表现为,一切都采取流水线式作业只为追求最高效率,使人盲目服从、安于现状,从而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而至单向度化。
最后,本文所说的神性真实指的是存在于个体审美的瞬间体验所获得的生命真实,它区别于抽象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尽管它只能通过宗教迷狂的方式而获得的。这是一种体验论,柏拉图认为既然感性事物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感性世界通过理式世界才具有相当的真实性。那么灵魂也可以通过以宗教迷狂的方式去体验绝对真实的理式世界,来获得有生命的真实。而此时绝对真实的理式同时也是真善美的最高统一体,只要观照到这种最高统一体,不但能获得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同时也能让个体获得最高的审美体验。在《斐德若》中,对美少年的爱恋的迷狂就是因为少年对象的美形体是理式世界里美本身的摹本。“这些少数人每逢见到上界事物在下界的摹本,就惊喜不能自制,他们也不知其所以然,因为没有足够的审美能力”[5]。通过这种摹本,灵魂能回忆起自己还未坠入身体时在理式世界所见到的情景,呈现出一种迷狂的状态。“如果他见到一个面孔有神明相,或是美本身的一个成功的仿影,他就先打一个寒战,仿佛从前在上界挣扎时的惶恐再来侵袭他;他凝视这美形体,于是心里起一种虔诚,敬它如敬神”[5](p127)。而这种迷狂状态便是一种获得生命真实的审美体验状态,只不过他们自己不能以理性认知的形式察觉到而已。然而这种强调宗教神秘体验的做法,为后来基督教神学盲目肯定彼岸世界预留了理论前提。[6]尽管进入现代化后的西方社会并没有像中世纪那样推崇上帝的绝对权威和对神秘天堂的无上向往,但当前西方社会的大多数民众仍然乐意在宗教信仰里寻求内心的安宁。
二、 庄子的诗性真实观及其价值
本文主张庄子的真实观是一种诗性复归说,因为在庄子看来个体心灵只有去除感性欲情和生死痴迷,才能顺应“真情”,即原初的性命之情;通过摒除人为思虑对万物自然情状做理性认知上的刻意区别,才能获得忘知之知的“真知”;感性个体只有以审美体验复归于作为万物根源的“道”,才能成就如“藐姑射神人”那样,以感性的形式获得超感性无限自由之“真人”,实现个体心灵与“道”之心物交融的最真实境界。故此种诗性真实观有三个维度:真情、真知、真人。而这三个维度的真实,也可以理解为对前文所提到的诸多现代社会问题开出了三剂处方。
第一,真情。指真性情,即庄子经常提到的性命之情。是相对于个体欲求而言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万物自有其真实的本性,而个体欲求则会扭曲扼制其自然情性。只有人的真实自然情感才能彰显个体精诚的本性,也正是基于此精诚的本性,个体才能复归于终极的存在。在《庄子集释》中,郭庆藩是这样解释这段话的前几句:“夫真者不伪,精者不杂,诚者不矫也。故矫情伪性者,不能动人也。”[7]说明此处的“真”含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指:精,即不杂、纯粹、单一;其次是指:诚,即不矫、忠于、顺应。这说明,庄子认为“真”便是对事物的原初纯粹状态的忠贞和顺应。他以“真”来形容人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一方面,表明了这些源于自然的性情最能体现人那种纯粹的原初状态;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只有对这些自然性情的顺应,不以人自我的欲求出发去任意割裂和伤害它们,才能彰显它们纯粹的原初状态。由此可见,真情便是指个体心灵安其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这种崇尚自然的思想,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地球日益濒危的当今世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真知。哲学上关于“真”或真实问题的讨论,一般都归属于知识论的范畴。它指真的判断,与假相对,即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性判断。人的理性思维将自然万物作为对象进行抽象思索,从而获取了这种理性知识。而在庄子看来,这种知识论范畴的知识会因为个体欲求而妨碍了自然的性命之情,故应该被摒除掉。此种知识不但有各自有限的偏见,而且以主客二分的理性认知方式易于将原本同人相合一的自然万物当成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来进行刻意的区别,从而引起是非纷争。故他认为只有从“道”的角度来对对象世界进行观照,即“以道观之”,辅之以“心斋”、“坐忘”的修炼,才能取消那种反映人智机心的认知论意义上的“知”,从而实现对万物本根之“道”的复归与顺应,才能获得无知之知的“真知”[8]。只有成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那种“真人”,才能观照到无知之知的“真知”。这样一种“真知”便不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而是以一种虚空心灵将它摒除掉的“忘知之知”的“真知”。这种反对片面推崇人类智力、科技至上的思想,有利于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诸多利益的同时,反思工具理性的作用和意义,甚至采取审美的态度来超越物质对个体心灵的异化,从而达到心灵独立和人格完整。
第三,真人。“真人”则是从体验论的角度来探讨其真实观。在《大宗师篇》中,庄子是这样描写“真人”的: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9]
说明“真人”顺应本真之“道”,超越了死生存亡。他摒除了个体的各种感性欲求和理性思虑,个体心灵以审美体验的方式获得心灵的自由,最终落成了真人或神人形象。这种“真人”境界的获得,必须将对诸如:有无、死生、自由等终极问题的抽象追问,转化落成为具体的感性体验过程。可见“真人”形象的获得是通过个体心灵复归于本真之“道”,又顺应了万物本根之“道”的生生不易之理,从而达到物我两相忘之最寂静处。从而真人得以审美体验的方式,来重新获得的鲜活感性形象“藐姑射神人”——一种具有超感性的无限自由之审美感性形象。这种强调人与自然内在和谐统一的思想在这个人心日益浮躁的世界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宗教信仰的方式来实现心灵的和谐,因为根据庄子的思想,外在世界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与个体心灵相互沟通的。只要个体心灵顺应自然,超越了对生死存亡等终极问题的对象性追问,便能以审美体验来实现个体心灵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
三. 从两者比较看庄子真实观的现代意义
两者真实观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三点:求知性与体验性、对象性与融通性、灵魂不朽与心灵自由。庄子真实观的此三种独具东方诗性气质的特性(体验性、融通性、心灵自由),与其三个维度的真实(真情、真知、真人)一样,都有助于深层次消解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科技至上、工具理性以及心灵空虚等。而这也正是庄子诗性真实观的现代意义所在。
首先,求知性与体验性。柏拉图的真实观是一种从追求知识角度出发的关于对象的真实观,它是相对于存在的虚无而言的。庄子的真实观是一种个体心灵复归于“道”后,体验到与“道”相契合为一的存在状态。不同于柏拉图将事物的共性通过理性思维方式抽象出来的本质属性,并将其推到终极本体的地位[10],庄子不但不注重人的理性思维,反而将其视为有损人的性命之情的人智机心。他认为这种人智机心妨碍了个体心灵以超功利态度,复归于万物根源之“道”的审美体验,所以要毫不犹豫的将其摒弃掉。庄子与柏拉图在对理性认知上的不同态度,显示出了东方哲学家更加关注感性现实的实在性,更加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至于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无止境的开发自然,使后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其次,对象性与融通性。柏拉图的真实观,无论所获得的认识是真理还是意见都不是指向绝对的“无”,都是有所指涉的对象,包括感性事物和绝对理式。同时在柏拉图看来,个体灵魂只有回忆起其未坠入凡尘前对理式的观照,才能获得真善美相统一的最高体验。由于个体灵魂对外在绝对实体的体验是通过一种活动而获得的,所以个体灵魂同理式的关系是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庄子认为无论是对事物真性情的人为束缚,还是对引起俗事纷争的假知识,都是人心违背自然情性的欲求。个体在面对强大的外在世界显得异常无助的情况下,都需要向自我内心的回归。“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同时又是万物之间可以相通的禀性,而人作为天地万物的一种当然也禀有自“道”的“性命之情”即 “道性”,通过这种“道性”,心灵可直接同那个万物本源之“道”相通。心灵与“道”两者之间,并非如柏拉图那灵魂同“理式”那样一种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体心灵在自身中感悟万物的共性。如庄子所主张的那种天人合一,有助于人们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以使个体不至于在追逐最高效率的流水线体制中丧失个性。
最后,灵魂不朽与心灵自由。柏拉图否定了现实事物的生灭变化,而肯定了理式世界的永恒自动,从而确立理式的绝对真实,从侧面成就了灵魂的不朽。那种不朽的灵魂虽坠入凡尘,但却可通过努力修炼来摆脱肉身对灵魂的纠缠,从而进入永恒真实的理式世界。不朽灵魂在面对可朽的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尽如人意时,就会表现出异常的焦灼不安,尤其是在地球濒危各种天灾人祸不约而至的当今世界。而庄子以诗意物化的方式来表现心灵的自由,只需要个体心灵通过审美移情,还原事物的真性情——性命之情,便实现个体心灵与大自然“道”的复归。正是基于万物皆有的“性命之情”,个体心灵可以复归于万物根源之“道”,将只存在于个体内心的自由通过诗性的审美活动体验,使个体心灵落成为具有感性实在的无限自由的“真人”。庄子对个体心灵审美体验的注重,有助于避免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因内心缺乏精神世界归属感,而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进而痴迷于宗教迷狂而无法自拔。
结语
通过比较柏拉图和庄子的真实观可见,庄子所提倡的真实是一种真实的心灵体验,而这种真实体验是由个体心灵向 “道”的复归来落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的真实观就完全是种不符合逻辑、没有任何理论价值的思想。实际上庄子的真实观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即它有别于西方柏拉图式仅用理性逻辑的标准来考查终极真实问题的做法。在著名的“庄生梦蝶”寓言里,在庄子指出人生就像是个环环相套的梦,从一个梦中醒来,却发现原来可能又处于另一个梦之中。从中我们会发现庄子试图通过环环相套之梦的方式来告诉世人,并没有那种可供理性思考来探求的绝对真实,无论是庄生还是蝴蝶都无法自我确立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既然连追问真实问题的主体都是可怀疑的,那么所谓的真实问题就只是个虚假的命题,最好将之放置一边存而不论。既然连真实性问题都是不成立的,显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终极性的存在,而唯一要做的就是放弃对真实问题的质问和追求。而一旦放弃了对真实问题的刻意追问反而能获得一种审美的诗性体验,在庄子看来这样一种真实的审美体验正是对于“道”的复归。
这样一种关于存在的终极真实,即便不再是符合柏拉图式理性认知意义上的真实,但却是个体心灵体验到的诗性审美真实。尽管庄子生活在离现代社会上千年远的先秦时代,但人类对存在真实性问题的探索,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而庄子此种有别于西方柏拉图式理性认知意义上的那种对待存在真实性问题的方式,恰恰对于当前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庄子的真实观不但以其独特的视角昭示着东方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诗性魅力,同时其崇尚自然、反对科技至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在当今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具有发人深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钱伟量.维特根斯坦与技术的后现代策略[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0):68.
[2]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24.
[3] 韩 艳.从生存论角度看柏拉图的“ 理念论”[J].江汉论坛,2002,(3):35.
[4]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81.
[5]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1963.126.
[6] 李秀云,姜婷婷.柏拉图理念世界之“神”与宗教世界之“神”的辨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12):55.
[7] 郭庆藩,撰.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1032.
[8] 杨国荣.《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J].文史哲,2006,(5):131-132.
[9] 陈鼓应,注.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9.
[10] 吴根友.《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命题的现代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6,(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