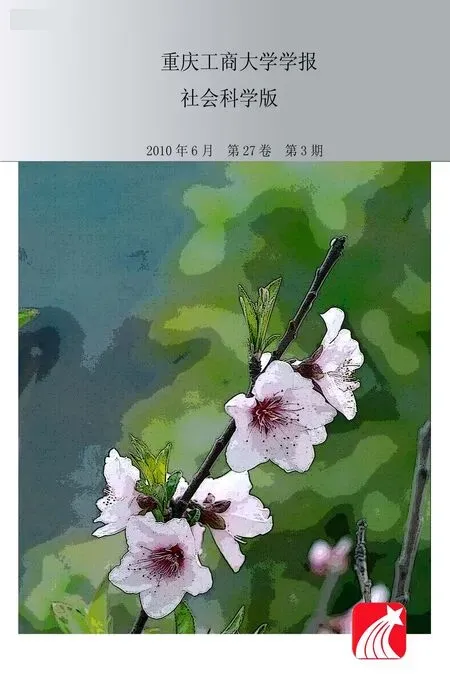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
阳 清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汉魏六朝辞赋[注]本文中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参阅吴广平编注《宋玉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汉魏辞赋文本,参照费振刚主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六朝辞赋文本,参照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与同时代志怪的关联,缘于二者都具有叙事和虚构的特质。志怪亦即记录怪异,其文本无疑是叙事与虚构的结合体。它虽然与小说题材或类型性质的“志怪小说”略有不同,但作为一种描述或记载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佛教灵验、仙境传说、精怪妖异、凶祥卜梦,以及殊方异物之类,乃至社会上和自然界的一切反常现象,包括非常之事、非常之物和非常之人,都应该是其反映和演绎的对象。而与此相关的是,叙事学研究者极力强调,辞赋更应当成为中国叙事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注]详参傅修延《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胡大雷《论赋的叙事功能与中古赋家对事件的参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刘湘兰《论赋的叙事性》,《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不仅如此,辞赋的虚构性亦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专家的共识。郭绍虞先生即指出:“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1]日本学者清水茂亦认为,赋体文学的人事、景物都带有些虚构部分,“在中国戏剧、小说还没发达以前,虚构文学是由辞赋担任的。”[2]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的这种共通性,致使两种文本在融汇和互渗中,最终形成较为特殊的关系。这种关联是主要以意象、情节和题材为典型,表现为辞赋作品描绘神祇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等,以及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表达模式的文学嬗变。
一
先看辞赋作品描绘神祇鬼怪。两汉散体大赋诞生于政治稳定、文化昌隆的历史时期,它与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歌功颂德的时代心理直接关联。如此,与皇室贵族生活融为一体的宫苑台阁、京都阙下以及祭典、羽猎之事,通常成为辞赋创作的重要题材,御用赋家所描绘和渲染的神祇鬼物,亦往往被点缀于此类文本之中。以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为代表,赋者对离宫别馆进行夸饰,或曰“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僤于西清”(司马相如《上林赋》),或曰“神仙岳岳于栋间,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髣佛”,“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雎盱”(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赋者描绘帝王出行时的舆仪声势,或谓“蚩尤并毂,蒙公先驱”,“飞廉云师,吸嚊潚率。鳞罗布烈,攒以龙翰”(扬雄《羽猎赋》),或谓“羲和司日,颜伦奉舆。风发飙拂,神腾鬼趡”,“秦神下讋,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衰”(扬雄《河东赋》),或谓“凤凰献历,太仆驾具,蚩尤先驱,雨师清路,山灵护陈,方神跸御。羲和奉辔,弭节西征,翠盖葳蕤,鸾鸣珑玲。”(张衡《羽猎赋》)如此种种,作者任意驱使神祇鬼怪为我所用,虚幻人神娱游之景来铺采攡文。
刘勰《文心雕龙》曰:“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馀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魍魉,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剌也”[3];左思亦曰:“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两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4]可见这种对神祇鬼怪的描绘,虽根源于《楚辞》却不等同于《楚辞》以及尔后的“游仙诗”,而是体现出“劝百讽一”的特色,它不仅为辞赋创作进一步渲染和夸饰所赋咏的对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影响着六朝以来以京都、宫殿等为题材的辞赋形态。
再看辞赋作品虚构人神同游。与汉大赋有所不同,骚体赋习惯于体物抒怀中追慕人神同游般的超脱,由此展示出颇具志怪色彩的意象或情节,实际上存在着感时伤怀和消解人生的重要意义。这种创作模式,不失为对《庄》、《骚》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汉初贾谊有《鵩鸟赋》曰:“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廖廓忽荒兮,与道翱翔。”这种对至人、真人的钦慕,既吸收了《庄子》的文学成就,又是赋者郁郁不得志时的消极之语。道家经典对真人、至人、神人的逍遥境界多有描绘,《离骚》则幻想人神娱游,集中表现出文人抒发牢愁的主体意识。至汉魏六朝时代,两种文化元素融汇于一体并被掺入了神仙因子,骚体赋借助人神之遇、人神同游以感志抒怀,遂成一种惯用的文学表达模式。譬如杨雄《太玄赋》曰:“纳鄢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役青要以承戈兮,舞冯夷以作乐。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载羡门与俪游兮,永览周乎八极。”又如冯衍《显志赋》曰:“驷素而驰聘兮,乘翠云而相佯”,“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又有张衡《思玄赋》曰:“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于句芒”,“冯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乎稽山。嘉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慭其既欢兮,又诮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挚虞《思游赋》曰:“召陵阳于游溪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尘”,“轶望舒以陵厉兮,羌神漂而气浮”,“讥沦阴于危山兮,问王母于椒丘。观玄乌之参趾兮,会根壹之神筹。扰毚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其共同点,在于对人神之遇、人神同游境界的文学演绎。
《太玄》诸赋所虚构的人神同游,自然不同于散体大赋对“人神娱游”之景的夸饰和渲染,尽管二者模仿《楚辞》“远游”之意至为明显。程千帆先生指出:“《楚辞》郁起,即杂仙心”[5],而《楚辞》之后的两汉,“重鬼信巫、天地祖先信仰、鬼神祠祀、谶纬神学、神仙方术都在这个时期成熟兴旺起来”,“是中国历史上造神运动的第一个高潮。”[6]神仙思潮和道教造神运动方兴未艾,使得辞赋叙事在情节和主题上蒙其寝润并日趋繁富。结合《汉书·扬雄传》,《后汉书》“冯衍传”、“张衡传”,《晋书·挚虞传》等,可见赋者以政治黑暗和仕途挫折为直接动因,以神仙思潮的蓬勃发展为时代背景,通过幻想人仙之遇、人神同游,一是直接继承了《楚辞》以“人神同游”为文学主题的表达模式;二是可与同时代乐府诗、游仙诗对神仙娱游之境的描绘相互参照;三是使得文学创作多呈抑郁不平之气,从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辞赋叙事的人文内涵。要之,魏晋南北朝辞赋通过虚设“人神同游”的幻境,延续了《楚辞》因“不遇”而“远游”的创作传统,并且成为六朝文人感志抒怀的重要表达方式。
二
再看辞赋作品幻想神仙意趣。道教和神仙思潮对中古辞赋的影响,不仅表现为赋者在述志抒怀中假想、追慕神仙般的超脱和逍遥,而且集中表现在赋家想象神仙之趣并融入写景,甚至直接对神仙世界进行歌颂和赞美。某些情况下,诸种创作倾向甚至杂糅交错。早在东汉时期,班彪《览海赋》就借助想象,让神仙之趣与写景抒怀结合起来,客观反映出神仙思潮对汉人辞赋创作的重要影响。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在描绘天台山胜景时,则通过联想“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驰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的仙境,为辞赋文学增添了不少仙道氛围。又,木华《海赋》幻构海景曰:“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泛阳侯,乘蹻绝往,觌安期于蓬莱,见乔山之帝像,群仙缥眇,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以长生。”郭璞《江赋》描绘云梦雷池云:“海童之所巡游,琴高之所灵矫。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抚淩波而凫跃,吸翠霞而夭矫。”两赋虚饰水光丽景,多种神灵意象被融汇其中,遂成吟咏江海的臻品。
赋家对神仙世界进行歌颂和赞美,最初有张衡模仿《七发》而作的《七辩》,文中假托无为先生的描述来颂美神仙,由此深深感染着作者,体现其内心去留的矛盾。西晋陆机《列仙赋》则曰:“夫何列仙之玄妙,超摄生乎世表。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尔其嘉会之仇,息宴游栖,则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观百化於神区,觐天皇於紫微,过太华以息驾,越流沙而来归。”其《凌宵赋》亦曰:“判烟云之腾跃,半天步而无旅。咏凌霄之飘飘,永终焉而弗悔,昊苍焕而运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晨而复举。陟瑶台以投辔,步玉除而容与。”在赋者的笔下,神仙不仅摆脱了世间种种苦恼和疾病缠绕,能够长生不老永葆青春,而且可以神游太虚之境,饱览河山胜景。与陆赋类似的,还有胡综的《凌仙赋》、陶弘景的《云上之仙风赋》,二赋的宗教意味更甚于前者。赋者对神仙世界的歌颂和赞美,充分表达出道教神仙观念对辞赋创作的重要影响。
至于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桓谭的《仙赋》,更是甚而有之,它们以辞赋为文学形态,通过描绘和颂美神仙世界,“赋家常将人间与天上融为一体,人们可升入仙境,神仙亦可光临人间,人们与神仙交流并役使神”[7],故而更为典型地表现了人仙遇合的文学主题。具体而言,《大人赋》虽然对象征武帝的“大人”示有警告、箴戒之意,但实际上对神仙世界和人仙遇合的精彩描绘,从手法上吸取了散体大赋对神祇鬼物的铺陈和渲染:“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蜓”,“使五帝先导兮,反大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长离而后矞皇。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跸御兮,清雾气而后行”,“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泛滥水娭兮,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与《大人赋》相比,《仙赋》所展示出来的神仙元素胜于其象征意义,所谓“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擢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氾氾乎,滥滥乎,随天转琁。容容无为,寿极乾坤”,文章对王乔、赤松成仙高举的纯文学描写,“虽然还不够生动形象,但基本上把神仙的修行方式和自由生活描写清楚了。”[8]要之,《大人赋》、《仙赋》明显呈现出颂美神仙的创作主旨,这与《楚辞》“人神同游”以及散体大赋中的人神娱游,实际存在着本质差异。两赋对神仙超尘脱俗风姿的歌咏,对神仙怡逸逍遥境界的描绘,表达出主体对神仙生活的羡慕和无限向往之情。
再看辞赋作品伪托人鬼交通。东汉以人鬼遇合为情节的辞赋,主要有杜笃的《首阳山赋》、张衡的《骷髅赋》以及王延寿的《梦赋》。杜赋和张赋均采用问答体的形式来展开行文。据《后汉书·文苑传》载:“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时为御史大夫,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高自标持的个性致使作者崇尚高古德操,故而伪托自己在首阳山偶遇伯夷、叔齐之鬼魂来颂扬贤者节义。相比之下,张衡活动于杜氏之后。据孙文青《张衡著述年表》,《骷髅赋》大致与《四愁诗》同作于晚年,平子作此赋,“盖亦因世乱生愁,因愁生厌;因厌而思归;因思归而上书乞骸骨之意也”,如此,作者“乃假庄周,‘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之念,以表现其消极思想”[9],其郁郁不得志之意于此可见。可以说,“《庄子·至乐》为《骷髅赋》提供了基本的骨骼,而张衡则是用自己的心情与才情铺衍出文章的血脉。”[10]魏晋南北朝类似张赋的作品,还有魏明帝曹睿的《游魂赋》,高贵乡公的《伤魂赋》,沈炯的《归魂赋》、吕安的《骷髅赋》等,其中以吕安所作最具代表性。文章借鉴《庄》、《列》“骷髅”寓言和张衡《骷髅赋》甚为明显,通过叙述赋者偶遇骷髅并与其精魂展开对话,意在暗示生活之苦酸。
文学史上最早以梦名篇且叙述“人鬼遇合”的辞赋,首见于王延寿的《梦赋》。作者在噩梦中“悉睹鬼神之变怪”:“蛇头而四角,鱼首而鸟身,三足而六眼,龙形而似人。群行而奋摇,忽来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牵。”更为难得的是,赋者以一连串的行动奋起搏斗鬼怪,用义正辞严地呵斥来回应群鬼的加害,展示出无所畏惧的激越情怀:“于是梦中惊怒,腷臆纷纭”,“乃挥手振拳,雷发电舒,戢游光,轩猛跣,批狒豛,斫鬼魑,捎魍魉,荆诸渠,撞纵目,打三头,扑苕荛, 抶夔魋,博睥睨,蹴睢盱。尔乃三三四四,相随踉 而历僻。陇陇磕磕,精气充布。輷輷,鬼惊魅怖。或盘跚而欲走,或拘挛而不能步。或中创而婉转,或捧痛而号呼。”据学者研究,《梦赋》亦为委托之作[11],这种开文学史上“以梦名篇诗赋”之先河的作品,离不开先秦梦文化的积累和两汉神秘文化的作用。就其影响而论,“后世小说中鬼畏鸡鸣之说,始著于此”[12],后世小说托梦境言鬼神之事亦多受其影响。
三
汉魏六朝辞赋描绘神祇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等,实际上是辞赋这一文学形态在不同时代的主题拓展。
以司马相如《上林赋》、杨雄《羽猎赋》和《河东赋》为代表,西汉散体大赋影响到张衡的《羽猎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以杨雄《太玄赋》、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为代表,两汉骚体赋则影响到西晋挚虞的《思游赋》。而无论是对神祇鬼怪的描绘,抑或是对人神同游的虚构,汉晋辞赋都是《楚辞》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至于赋家想象神仙之趣并融入写景,先有东汉班彪的《览海赋》,后有两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木华的《海赋》以及郭璞的《江赋》;赋家对神仙世界进行歌颂和赞美,初有两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张衡的《七辩》、桓谭的《仙赋》,后有三国胡综的《凌仙赋》,两晋陆机的《列仙赋》和《凌宵赋》、陶弘景的《云上之仙风赋》;赋家对人鬼交通的伪托,东汉有杜笃的《首阳山赋》、张衡的《骷髅赋》、王延寿的《梦赋》,魏晋南北朝有曹睿的《游魂赋》、高贵乡公的《伤魂赋》、吕安的《骷髅赋》、沈炯的《归魂赋》等;其共同点,亦在于新的时代背景下辞赋创作对前代作品的借鉴、模仿抑或开拓。要之,作为两汉文学的典型形态,汉赋对人事、景物的叙述和描写,确实充满了虚构的成分,汉赋中的神仙鬼怪及其文学演绎,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不同程度地再现和延展,从而表现出辞赋作为文学形态的时代传承。
又,以神女为典型意象和文学主题的辞赋,最先出自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据《高唐赋》叙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与《高唐赋》描述女神主动与陌生男子发生性爱关系迥然不同,《神女赋》中的女神可谓内外兼修:她不仅美丽如画,动人心魄,而且在道德礼仪方面有着更为高尚的追求。《神女赋》记载,“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神女虽有丽姿妙质,且有佚荡之心并为之犹豫不决,所谓“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蹰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但是终能矜持庄重,止乎礼仪。如此,神女与襄王“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虽有精神之爱慕,却无淫乱之实质。自战国以来,魏晋南北朝辞赋继承《高唐》、《神女》风格且有所发扬,最终形成大量的“神女赋”系列文本。在以曹植为中心的建安文学集团之中,以“神女”为主题的辞赋创作曾蔚然成风,王粲、陈琳、应瑒、杨修等不少文人均积极参与其中。
当此之时,曹植有《洛神赋》,王粲、陈琳、应瑒、杨修等人均有《神女赋》。汉魏之际的“神女赋”创作,一方面包括刻画神女美貌、表达赋者与神女相好之意、抒发赋者个人情怀等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形成了普遍的叙述模式:赋者首先对神女的出现作背景介绍或言语铺垫,然后重点描述神女的花容月貌,紧接着表达对神女的沟通和爱慕之意,最后是神女欣然应允或微言拒绝,作者亦借此暗示愉悦或惆怅之感。曹植《洛神赋》尽管存在着多种寓意,其说法不一,但是其他建安才子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辞赋创作,实际上是受其影响所致。不仅如此,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结尾模式,对汉魏六朝的“神女赋”系列文本影响颇大。郭建勋先生即认为,“高唐神女”在汉魏六朝“神女—美女”系列辞赋中分化成两个象征体系:一个象征恶的情欲,一个象征至善至美的、带有终极意义的理想和“道”,或者说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如果说前者是“女神”在文明社会伦理化与世俗化的产物,那么后者则是人们渴望摆脱现实苦难,向“女神”寻求精神庇护的结果,两者都不是作者某种客观生活的记载。[13]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继曹氏文学集团之后,六朝张敏、谢灵运、江淹、陶弘景等,亦分别创作了《神女赋》、《江妃赋》、《水上神女赋》、《水仙赋》。这些以“神女”为中心意象,以咏颂神女抑或以“人神相恋”为主题的辞赋作品,既是汉魏“神女赋”系列文本的历史延续,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譬如南朝江淹的《水上神女赋》,其基本结构模式跟前代《神女赋》类似:赋者首先借江上丈人游宦荆吴之事作为巧遇神女的背景铺垫,继而所谓“忽而精飞视乱,意徙心移,绮靡菱盖,怅望蕙枝。一丽女兮,碧渚之崖”,描摹出水上神女的姗姗来迟,接着以优美华丽的辞藻极力描绘神女的美貌、配饰、举止等,最后以“顾御仆而情饶,巡左右而怨多。吊石渚而一欷,怅沙洲而少歌。苟悬天兮有命,永离决兮若何。妙声无形,奇色非质。丽於嫔嫱,精於琴瑟。寻汉女而空佩,观清角而无匹。嫔杨不足闻知,夔牙焉能委悉。何如明月之忌玄云,秋露之惭白日。愁知形有之留滞,非英灵之所要术也”等卒尾,借此表达人神之殊的遗恨和惆怅。与此不同的是,谢灵运的《江妃赋》与陶弘景的《水仙赋》,并非借用传统的“人神相恋”模式来抒己之志。前者敷演史上流传的诸多神女故事组合成文,后者则以“水仙”为中心来渲染和铺叙。结合景物的描写,二赋对神女意象的构设和整合,其造语用典意婉而尽,藻丽而富,充分表现了六朝骈文的美学特征。
可见,借助“人神相恋”的叙述模式,“神女赋”系列文本亦为汉魏六朝辞赋创作增添不少神幻色彩,而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其表达模式的时代嬗变,最能体现出辞赋这种艺术形态在中古之际的文学拓展。
四
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叙事的交互关系,首先表现为辞赋文学对志怪叙事某些信息的吸收。作为一种描述或记载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文言志怪通常在题材上形成仙道记录、神佛灵验、民间神怪鬼魅故事三种,在体制上则大致构成恢宏壮观的“博物”世界、简淡雅饰的“搜神”一脉以及与诗韵相通的“拾遗”情调三类。[14]汉魏六朝辞赋描绘神祇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以及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其表达模式的时代嬗变,实际上证明了志怪对辞赋创作的重要影响。
从题材上看,譬如六朝吴均作《八公山赋》,赋者首先刻画八公山胜景,然后以“维英王兮好仙。会八公兮小山。驾飞龙兮翩翩,高驰翔兮冲天”卒尾,借助淮南王遇合八公的神仙传说,意蕴遂以深远。又如陆机《列仙赋》、郭璞《江赋》、谢灵运《江妃赋》等营造的“江妃”意象,实际上源自《韩诗外传》和《列仙传》中的神异叙事。而马相如《大人赋》、张衡《七辩》、桓谭《仙赋》,胡综《凌仙赋》,陆机《凌宵赋》、陶弘景《云上之仙风赋》等,以及受《高唐赋》、《神女赋》影响的《洛神赋》,建安诸才人的《神女赋》,六朝张敏《神女赋》、江淹《水上神女赋》、陶弘景《水仙赋》等,无疑亦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早期神话传说,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化以及仙道类志怪文本中的相关叙述。又如,汉武帝曾为早逝的李夫人造歌作赋,赋即为《李夫人赋》。此赋描述了武帝与李夫人鬼魂的遇合,一方面是以同时代志怪所载方士李少翁招亡魂事为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亦可与《史记》、《汉武帝禁中起居注》、《汉武故事》等文献中的志怪叙事相互印证。而杜笃《首阳山赋》、张衡《骷髅赋》、王延寿《梦赋》、曹睿《游魂赋》、高贵乡公《伤魂赋》、吕安《骷髅赋》、沈炯《归魂赋》等,不仅借鉴了《左传》、《庄子》的志怪叙事,而且吸收了两汉造神运动的时代成果。
从体制上看,譬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杨雄《羽猎赋》和《河东赋》、张衡《羽猎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以及以杨雄《太玄赋》、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为代表的两汉骚体赋,实际上亦吸收了上古以来的神秘文化和志怪叙事,它们不仅在体制上可与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相提并论,而且因其叙事性、虚构性、寄托性而影响到志怪小说的建构。又如西晋张敏的《神女赋》,文本首先叙述了神女来游的背景,接着假设主人与神女的对话,意在消除人神之间的隔膜和疑惑,继而是人神之间以“房中至燕”、“长夜欢情”为特色的性爱话语,最后是惆怅而别。而与其他“神女赋”系列文本不同的是,原文是以《搜神记》所载弦超与成公智琼的人神相恋故事为叙事背景,故而在素材和体制上借鉴了搜神体志怪中的神女故事。又如作为叙事赋的代表,《高唐赋》、《神女赋》等,“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张衡《骷髅赋》,可谓“故事新编式的小说”,曹植的《骷髅说》,“也是一篇辞赋体的小说”[15],而杜笃的《首阳山赋》,全文脉络条贯,文采斐然,钱钟书谓:“情事亦堪入《搜神记》、《异苑》等书”,又曰:“玩索斯篇,可想象汉人小说之仿佛焉。”[16]汉魏六朝辞赋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实际上可分别与搜神体、拾遗体当中的志怪叙事相互参照。
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叙事的交互关系,还表现为辞赋文学对志怪创作产生影响。董乃斌先生指出:“汉魏以来的赋作者们,在赋这一文体之内,已经努力尝试过发展它的叙事功能,并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然而实践证明,赋体文章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叙事艺术,局限很大,前途不广。它的优长还是在于像诗那样言志抒情,宣泄怀抱。古代文人渐渐懂得,赋并不是充分发挥文学叙事性特征的合适文体,他们必须探索新路。这路无疑是存在的,那就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17]这种说法,无疑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汉魏六朝辞赋的地位和价值。辞赋文学虽然呈现出某种叙事特性,但相比之下,其抒情性更强、更为突出,在这种有关文体本质特征的先天性因素的制约下,传统叙事模式必然要在史传文学基础上寻求突破,最终走向以“虚构”为主,以审美和人文为追求的“小说事体”。
尽管如此,在这种寻求突破的过程当中,作为叙事文学的承担者,汉魏六朝辞赋的叙事元素及其实际功能,特别汉大赋以主客问答为特色的体制和模式,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壮大并影响着叙事本身。与此相关的是,辞赋文学的叙事性、虚构性及其综合功能,必然会影响作为早期叙事的另一承担者,亦即志怪文本;而另一方面,汉魏六朝辞赋的叙事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包括志怪文本在内的早期叙事传统的时代嬗变。以骚体赋和抒情小赋为代表,赋体文学述志抒怀的创作机制,引导着早期叙事的正确方向,亦即逐渐走向审美性和人文性。与此相关的是,辞赋创作的艺术特质和人文旨归,实际上影响着志怪文本在较为深层的文化意趣、文学功能层面产生时代转变:如果说汉晋之际从神学到玄学的转变,曾一度使原先的神异叙事“在传承中逐渐风化变质”,表现为“政治价值逐渐地跌落”,人们开始关注“怪异之事本身所具有的怪异色彩”[18],以满足其游心寓目的需要;那么随着时代的演进,包括志怪叙事在内的神异叙事,正逐渐从传统的史传叙事中分离出来,继而被作家演绎成为满足人类某种精神需要的文学形态。如此,以志怪文本为载体的“‘若隐实显’的陈说模式与概念”,成为“时人在困顿的时局中,抒发胸臆的一种策略”,毕竟,“长期被压抑的人们或因外在压力而不敢恣意直言”,但可以“改以某种另类方式表达心中不满与抗议”,对神性世界的相信“则是一种身处横逆然却有所不屈的曲折表现。”[19]六朝志怪最终从正面展示多重而又杂糅的宗教信仰,从侧面映射出唐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从微观呈露出芸芸众生的人情世态。
汉魏六朝辞赋影响着志怪叙事文化意趣和文学功能的改变,六朝志怪叙事的时代嬗变,其前途则指向唐代传奇。由此可以说,在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的双重作用下,在其他诸种文化因素的积极推动下,文言小说最终走向“文备众体”的传奇时代。对此,李剑国先生指出:“唐初传奇小说是在志怪小说基础上融合史传、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及佛教叙事文学而形成的,是多种作用力综合作用下的结果。”[20]这种说法无疑客观、周详而又全面。具体而言,六朝志怪在发展过程中,情节上渐趋繁复,内容上渐涉人事,结构上日益完整,抒情气氛越来越浓厚,创作方法上更加呈现出浪漫主义色彩[21],所谓“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燥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2],科学地诠释了传奇与志怪之间既继承而又变化的关系。不仅如此,汉魏六朝志怪向传奇的转化,还离不开辞赋文学的时代影响[23]。赋家“所创造的亦真亦幻、花非花雾非雾的迷离奇谲的氛围,却很接近传奇作家重‘意想’、‘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的审美趣味和风流情怀”,“唐传奇在语言的简练、精确以及富有音律美诸方面都得益于赋体不少”[24],辞赋文学由此促成文言志怪在内的叙事文学走向人文和审美,走向小说事体以及这种文学体裁的真正独立。这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毋宁说,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叙事的交互关系,表现为两者在融汇和互渗中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7.
[2] 清水茂.辞赋的虚构[A].清水茂汉学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3:245.
[3]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33.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5.
[5] 程千帆.古诗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05.
[6] 马晓宏.天·神·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造神运动[M].台北:云龙出版社,1991:117.
[7] 王焕然.试论汉赋的小说意味[J].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2003(5).
[8] 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78.
[9] 孙文青.张衡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108.
[10] 蒋文燕.张衡和他的《骷髅赋》[J].名作欣赏,2004,(12).
[11] 郭维森.王延寿及其《梦赋》[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1).
[12] 钱钟书.管锥编(三)[M].上海:三联书店,2001:266.
[13] 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2.
[14]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331.
[15] 程毅中.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J].中国文化,(24).
[16] 钱钟书.管锥编(三)[M].上海:三联书店,2001:225.
[17] 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38.
[18] 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19.
[19] 谢明勳.六朝志怪小说“寻迹觅踪”故事研究[C]//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五辑).台北:里仁书局,2004:387.
[20]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1] 张莉.六朝志怪小说审美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1):33.
[2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9.
[23] 童苏婧.论白饭如霜作品中的六朝志怪文化积淀[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2):26.
[24] 陈节.论赋与唐传奇的关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