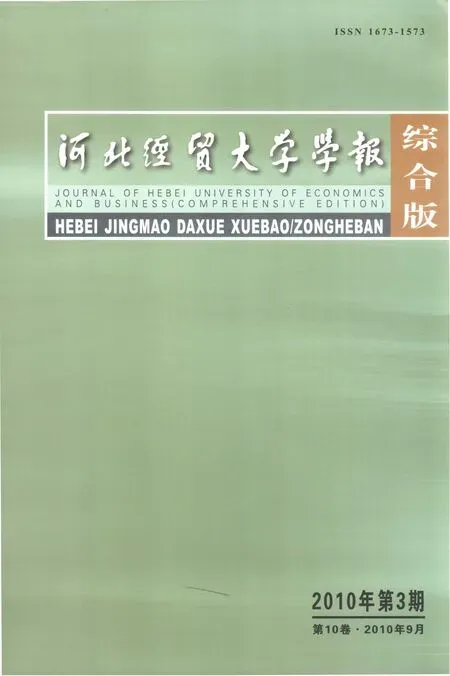水成岩——浅谈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
张高峰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文学研究
水成岩
——浅谈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
张高峰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通过细察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深入发掘出方方作品文体中独有的“生命质感”内在地隐含着“诗性温度”,兼与卞之琳《水成岩》一诗相比照,进行互文解读,并追溯方方之前的创作经验,体悟小说中奇巧地运用两类技巧:错位模式与平行模式,如何促生了小说的诗性锋芒。在归纳方方“诗性写作”的基本特质的同时,理解方方创作中一贯保有的“生命温度”和“诗性关怀”,追问《水在时间之下》超验般诗性姿态之上,作者所寄予的历史情境中人类个体生命意识蕴藏的普遍情感与反察生命存在本身的精神向度。
方方;水成岩;诗性写作;生命温度
作家心绪的“浮躁”与时代商业竞卖氛围的“狂欢化”成为当下文学症候。“诗性语质”一再溃散、被消解,骨子里留有诗性的作家不多了,而诗性中构成对生命意识诘问的作家微乎其微。方方无疑对于女性写作中日益鄙俗化、低劣趣味化创作形成挑战与反驳,是少数保有诗性的作家,弥足珍贵。
2008年底,方方终于贡献出了继《乌泥湖年谱》后的又一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诗性与哲思洋溢的书名是作家别出心裁的寓言方式。方方在新写实创作阶段中是个独异的存在,保有着烛照般的诗性语态,或隐或现,自始至终。“善于在小说中营构诗性氛围,是方方一贯坚持的写作方式。即便是像《风景》、《落日》、《定数》这些写实作品,也呈现或隐含某种诗意的色彩。”[1](P393)读方方的小说有着自然般真切的生命质感,而又因了诗性的温度,又不致使作品缺少艺术性审美含量而显得粗糙。是这“生命质感”,逼近现实,又是“诗性温度”将距离拉开,心灵获得超升,又不致于窒息。方方许多有才情的作品,开头或文中常引用诗歌,而作为喜欢一头“扎猛子”入水式的读者来说,故事情节性成为他们关注的关键,又常忽略了这些诗与小说的内在联系。诗的内涵可以把握作者小说中许多关键的情绪,“这是种氛围上的需要”,“再就是这首诗的氛围与这部小说的氛围特别吻合,还有就是引入这种可以沟通感觉的诗,可以把读者一下子带入这种氛围中”[2](P396)。的确如方方说的那样,“诗歌本身也不明确。它呈现一种想法,一种空间”[2](P397)。诗的引用方面,没有仅局限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方方同样也“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一种非常优雅的气质”[2](P399)正是她创作的底色,对传统情愫的衷爱,也正是方方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初发源。
一、“生命质感”的“诗性写作”
《水在时间之下》引领我们重温了凡人传奇故事,曲折动人的情节及诱人性自不在话下,而紧紧攥住内心的却是一股被时间所埋的悲凉的水流。笔者想到了中国现代杰出诗人卞之琳的《水成岩》,这首诗与这部长篇小说,笔者始终认为:它们本质上流淌的是同一条水脉。“卞之琳也许更多地是受到瓦雷里、爱略特等后期象征派的影响”[3](P367),“卞之琳是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人们说他的诗常‘于平淡中出奇’,就是因为善于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与开掘’。”[3](P367)而我们知道,方方“很多作品都引用了爱略特的诗”[2](P397),爱略特是她喜爱的诗人之一。这一点上卞之琳和方方在艺术审美取向上是相通的,笔者始终愿意将方方的小说当做一首首长诗来读,她的小说局部或细节上是写实的,整体情愫丝丝入扣地连起来却又是诗,非用诗性感悟不可。诗歌及情感对现实的突入与理解,到了自身无法包容的程度,她便自然而然地通过小说这样的文体来表达。作家只能听从情感的召唤。“说到底,写作是个人与话语发生的特殊交锋,文体的界线该冲破就得冲破”,“关心的是‘写’,而不仅是写诗”[4](P278)。方方的创作较于其他作家显得通达,多了一份“灵气”,多了一份“才情”。《水在时间之下》没有滞重感,这样一部“大诗”(整体的情脉把握)将目光投向了永不变化,却又永动不息的时间,被时间开凿又被时间穿透的“岩石”,凄美悲凉的人生这场戏,流水般从我们心头缓缓淌过。方方一贯的“诗性写作”在此有了高度凝结,这样的小说文质构成上又不同于沈从文、汪曾祺、萧红等的“诗化小说”,“诗化小说”文体上的创新与突破是分外明显的,而方方式的“诗性写作”也不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策略。“诗性语态”如盐融水,化为无痕的整体流动的“诗与思”的情感。因此它表层仍在小说文体的情节性层面,连贯性强中“穿梭织锦”,仅就这“劳动的局部”而言,小说仍是现实的。而一旦曲终锦成,再回头细细看来,除了“诗”的赞叹,还有什么,如若说“诗化小说”在文体上使小说“中正”的面貌多了些修饰,他们的大胆创新,散文化不免冲淡了故事性、情节性,那么“诗性写作”恰如诗歌创作中的“主智”类型诗歌,开始抬脚迈进“小说文体层面上的审美超越”这道门槛。它们本质上都是抒情的,都属于“诗性言说”的范畴。以此类喻,“主智”诗歌却在策略上多了一份“用心”,相比“主情”诗歌却是更自觉的,不再是“文体侵入”,倒有几分“文体内置”的味道。而就方方创作的一路走来来看,多为无名的诗性所牵,多少有一些不自知的状态(自写诗跨入创作小说,自然难免)。《水在时间之下》在故事性与诗性的双层把握上,有了深入的开掘,而这种努力是一贯的,是自觉应受的最好的“诗神缪斯的馈赠”。也许理念的侵入会使我们忧心于削弱作家艺术审美的程度,对于这部作品,笔者看到甚为高妙的地方,正是方方“诗性语态”插上一双哲理寻思的翅膀,意外地获得了喜人的超验般的引人遥想的姿态,有着丰盈的生命追求意识,而此时理念浸入整体小说过程当中,也如盐融水一般化为无痕。值此,笔者想强调的是,方方的创作没有蛊惑于“浮躁”的商业化写作和“狂欢化”的时代氛围当中,失去方向,正是为内心写作,是她保持着当代文坛少有的审慎,持守。而这些虽不免又有一些寂寞,而这些正是一名真正的欲有为于当代文坛的作家所必须的,又是一份责任的考验。方方在后记中写到,“这是一本尖锐的书”,“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汉剧艺人的人生经历不断地闪现在我眼前,让我难以忘怀,他们的命运,唤起了我写这部小说的欲望。这个欲望,存放在心许多年”[5](P465),这样的努力,大抵是可以想见的。
对于作品内在的诗性寄托,不妨通过细读卞之琳《水成岩》一诗,来达到互文的认识效果。
水成岩
水边人想在岩上刻几行字迹;
大孩子见小孩子可爱,
问母亲“我从前也是这样子?”
母亲想起了自己发黄的照片
堆在尘封的旧桌子抽屉里,
想起一架的瑰艳
藏在窗前干瘪的扁豆荚里,
叹一声“悲哀的种子!”
“水哉,水哉!”沉思人的叹息
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
当代诗歌评论家陈超将《水成岩》看做诗人“生命的现身和领悟”,他说“水边之岩/岩下之水/水成之岩,种种关系交叠融合,完成了对生命流逝的痛惜和奇异赞叹”[4](P168)。我们倒不妨将方方看做那个若有所悟,想在岩上刻字的“水边人”,《水在时间之下》,乃及水上灯(杨水滴)都是这样一块岩石,方方想在自己的创作中镌刻下那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意识。水上灯凄美悲冽的一生,生命行水终致凝结。楔子中我们看到水上灯对于自己生命流向的体认,有着这样的喻象。“但她却说她叫杨水滴。一滴水很容易干掉,被太阳晒,被风吹,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她说,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埋在时间下面,就是不干。”我想,这样的一滴水被“宇宙锋”似的时间之流裹挟,历经起伏于动荡不安的世事变化大潮当中,终于被打磨成了一块既有“时间记忆”又被“时间埋下”的“水成岩”,这样的生命意识透过篇章题目也可感知。从第一章:生与死,第二章:风雨无情,第四章:人生如梦到第十七章:人生的层叠,终至第十九章:喧哗中的冷寂及尾声:活在时间之下。而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水成岩》一诗,两者便发生了交合、相生的启示指向。第十七章:人生的层叠,诗中有着通感式的表达“层层叠叠旧照片和层层干豆荚,豆为比拟,记载了生命由瑰艳到衰退的流程。而这层叠的生命记忆之喻象,又被和谐地纳入同样层叠的水成岩这一整体隐喻之中,三个意象发生了交溶、叠加、共生”[4](P169)。在书中肖锦富被施计害死,张晋生同样死于非命及玫瑰红的疯掉,在水上灯这滴水的生命记忆中渐已沉积成一层层沉重的生命灰岩,人生是层层叠加的,水文的无辜被害累及水家家破人亡,生身母亲李翠沦落街头,水武陷入傻症,一层层叠加,种种世间苦难,就如被太阳晒,被风吹的一滴水在时间大流的冲击下,磨生出层层沉淀的灰岩,最终化为“水成岩”。“水边人还用在岩上刻些什么字吗?噢,不必了,水成岩已是最好的无字诗碑”[4](P169)。喧哗中的冷寂,被时间撕裂的情感,水上灯含泪演完《宇宙锋》一出汉剧后,宣布了终身退出舞台,“她从炫目的舞台走下来,就仿佛从海上风暴中挣扎而出”[5](P460),繁华尽处的落寞,使人有股贴骨的悲凉,凄美而不施脂粉,“日子就这样变成了静静的。两个曾经生活在戏里的女人,现在生活在庸常的日子中。她们洗净脂粉,脱下绸缎,换下高跟的鞋子,剪短了头发,着一身蓝布褂出没在陋巷中,一天一天,竟没人知道她们曾经是谁”[5](P461)。后来林上花三年自然灾害中因患败血症死亡,傻瓜哥哥水武的出现,使她又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已成水婆婆的水上灯,在水武死后,平静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处。“她果然被时间掩埋在了深处,连一点光亮都没有露出来”[5](P463),无言的沉痛,触及的是历史长河中人类个体生命颤动中凝结的普遍情感。“人之所以被叹为‘悲凉的种子’是由于在广阔的世界,只有人这唯一的物种才能体会到时间的流动,生命的不可重复性,死亡乃是最根本的必然。人的‘此在’感,是建立于有限的时间境域内的。‘水哉,水哉’,这古老又常新的叹息,既是对生命的痛惜,又不妨看做是奇异的赞叹——毕竟也只有人能将自身对象化,像水成岩那样,使诗意的栖居过的“瑰艳”生命,在回忆中现身并领悟”[4](P169)。
借《水成岩》诗韵所呈现的想象与空间,去理解和体会《水在时间之下》,会有助于思想和审美取向上的深一步思考。读完小说,《水成岩》一诗隐隐浮于眼前,读小说读出一首诗来,这“神秘的传达”,应不是“误读”,而恰恰是“正解”,两者相通的隐秘的经验与情感,是潜在的。方方以往作品开头或文中都有引诗,如《风景》便引用了波特莱尔的诗,“……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水在时间之下》开头是一篇形成悬念回溯式的楔子,没有引诗,笔者认为,《水成岩》或可补缺。打捞旧有岁月年华,出水的是一幕幕湿漉漉的身影,是一场风暴,一江汉水;还有一场戏,一座深宅大院的记忆,诉说着繁华落尽的悲凉与凄美。生命有时可以寻找,但有时又不免苍凉,而水上灯的苍凉却是最终归寂于平淡的苍老,褪去喧哗纷纭的传奇故事表象后,流来了悲冽的诗思。水流过了,留成石头,曝晒或者埋入时间之下。当人们面对时间这沧桑的手,谁又能再说什么?曾有的记忆见证了一切。读这样的凡人传奇,称得上“灵魂的奇遇”,生命中沉淀良久而又难言的情感与经验,凭想象方式再次激活。有人说,泪流了两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心灵超越贫乏现代生活的美好感动,是直抵心灵岸涯的残缺木筏,带来了“生命关怀的温度”。在一个喧嚣着“拼贴复制”与“炒作勾兑”的年代,这样的作品应该称为:有着“生命质感”的“诗性写作”,而它的特质是有着“诗性投入”和“生命温度”的文学作品。
方方正是少有的保留了“生命质感”的“诗性写作”。方方以往作品没有仅囿于方式上的“零度写作”,其实深处潜隐着一条更本质的抒情与哲思追求的线索,直至《水在时间之下》,涌动的潜水突破表层寒流,浅浅地浮出岩边。笔法上她保留着一贯的节制性,沉下来的没有郁结。对主人公形象的投入也绝非“道德批判式”塑造,而是尽量凸现水上灯的形象复杂性,力避类型化、平面化,寄寓了无限的苍凉与无奈的生命诉求。
二、经验的回溯
方方的创作大致经历了这么一条线:浮——潜——升。20世纪80年代早期作品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1](P444),写作中呈现出“浮”于生活之上的状态,也是自然的,作家难免受制于现实人生阅历,再加上作家骨子里的抒情气质。由写诗转向小说创作优势与局限都是明显的。方方曾谈到,“写诗总有一个年龄病,它需要一种激情去战胜理性,而人到了一定年龄便受到语言和思考的各方面限制。我现在偶尔也写写,但不去发表”[2](P396),如《大篷车上》、《啊,朋友》等作品,难掩的诗性激情,虽然我们读到的是小说体式。这股诗脉“随着作家人生阅历的增长和对底层生活体察的深入,其创作中理想色彩也逐渐减弱”[1](P444),这是必然的诗性隐退,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哪一个作家可轻松跨过现实的种种羁绊,砥砺中诗性抒情转潜为表层寒水下的股股内含“生命温度”的潜流。方方永远是“新写实创作”中的个例,诗性的抒情本质与哲思氛围,使她难以割舍。“‘零度写作’实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新写实小说极力消解理想主义激情的倾向却是明显的”[1](P438),现实理性使方方选择了小说创作,诗的现实包融性使她感到有些难以尽显,而小说叙事的方式必然一定程度上会压抑诗性的表达。新写实阶段的方方,似乎给我们创作了一些颇具现代主义味道的左拉自然主义式作品。但作者的方向是明确的,“左拉的作品当然可以,但是我的《风景》绝对不是受左拉影响”[2](P397)。
如果将《风景》中的引诗说成是作家策略上的兼顾,诗性的徘徊,到不如看成一种自然的进取。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说道:“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度的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方方写作策略上的取弃,小说穿行人生种种,才有成熟后的饱满,才有写实般的生命质感,设若没有“生命过程关注的投入”,诗的内质也都是不真切的,在此意义上小说未必不是一首“长诗”,这其中有着复杂的人生。《水在时间之下》,作家以往那种“零度写作”式的对书中人物平视及俯视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久经“潜”式写作之后,在既关注现实,又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的基础上,形成了向上提“升”的张力。“生命质感”的“诗性写作”缪斯翩然莅临,对书中人物的视角转变为了“平视及仰视”,而这“仰视”穿透人物生命本身,直抵彼岸的意象界,升腾起形而上的超验姿态。而这种写作的特质便是“生命温度”和“诗性关怀”。
三、小说的两类技巧:错位模式与平行模式
《语言中的方方》一文中,林白面对方方家的旧影集,遥想方方家族先人的曾有辉煌,感慨道,“社会的变故改变了这一切,为了生存,‘王熙凤’曾一度居破庙而沿街乞讨,最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下婆子。影集中那些风光倜傥的人物,一个个在人生的落差中飘零四散,那些大起大落由繁华到苍凉的故事让人无限感慨”[2](P392)。“这一部‘红楼’方方什么时候才写出来呢?”,想必这样的发问,而今有了回答:《水在时间之下》。“红楼”式作品,这是情感上更本质的认同与无答的追问,而绝非情节方面类同性。“艺术之梦的确可以使人沉入过去的岁月,唤醒和复活昔日记忆,更重要的在于,它们是对生命灵性和真血性,真情怀的呼唤,是实现人格发展这一最终目标的蓝图”[6](P154)。
从小说技巧上来看,“错位模式”和“平行模式”成为《水在时间之下》比较突出的特点。方方此前的作品便显现出这样的取向,“在《船的沉没》、《随意表白》、《桃花灿烂》等爱情小说里,见得更多的是一种错位模式,寄寓着“真正的爱情的失败”[1](P445),“而这种错位模式寄寓着‘真正的爱情是很难得到的”[2](P402)。《水在时间之下》中,玫瑰红和万江亭的错位爱情模式与水上灯和陈人厚的错位爱情模式,形成平衡的人生困境模式。“错位模式”与“平行模式”形成有效地“形式”,使悲剧精神内涵得以最大程度彰显。
玫瑰红和万江亭在余天啸的帮助下订婚后,遭遇了肖锦富不断制造的威胁迫害。他们俩人相爱相知多年,出逃芜湖的计划隐秘也是完全可行的,但始终犹豫的玫瑰红不愿离开舞台上那光彩照人的一面,贪图过上舒服的日子,稍后李翠的一番话,玫瑰红犹豫的心,打定了主意,她放弃了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灰色的幻影,美丽而忧伤。玫瑰红的选择是在灵魂挣扎于物质界的现实考量中悲剧性决定的,正是寄寓着作家对女性性格复杂内涵的严肃“拷问”。她的选择,有着生命遭际的估衡,虽然是违心的。爱情的择取,因人物的心理及社会现实左右终致失败,酿成悲剧,万江亭吐血而死。后来不久,玫瑰红失了灵魂,抽吸大烟,深院常锁,陷入困境。错位模式和平行模式同步展开。社会动荡,兼及个人爱恨情仇,一切在水上灯这里有些“走形”,也更为复杂。日据汉口时期,抗日小组成员的陈仁厚实施了乐园爆炸行动后,希望水上灯同他离开汉口,水上灯踌躇了“她蓦然想起玫瑰红的逃避”,玫瑰红始终还是没有走,“而她水上灯呢?难道会吗?离开汉口,她能做什么?它的戏台呢?她的戏迷呢?她的汉剧呢?这一切,哪里能有?没有这些了,她又是什么?这是当那个苦到骨头里的水滴吗?瞬间她就理解了当年的玫瑰红”[5](P328)。我们从这里,已然看到情深意合的水上灯与陈仁厚的爱情发生了错位,而这源于置身其中的人物个体的悲剧性体验。女性选择流露出的“动摇性”却又真实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这样的昭示类似于平行模式的展开中,越发触目惊心。“玫瑰红说,我知道你像极了我”[5](P258),当玫瑰红放弃出走,欲从水上灯那里打探出万江亭的情况,玫瑰红谈论的一番话,使水上灯感觉到“玫瑰红说的这些,其实正是她曾经想过的,直到现在依然在想的。她和玫瑰红的心思一模一样,她们是同样的人。”[5](P206)当然个体生命的差异性,亦不能忽略,“玫瑰红说她,水上灯想,不,我不能理解你一样哩。我将来一定会有自己满足的日子。”[5](P258)生命困惑的类似性和生命体验的不一性有着区分度。爱情的错位,在水文的胁迫压力下,陈仁厚的出走,水上灯轮回般的悲剧性的投入张晋生的怀抱,初步成形。而后当张晋生被贾屠夫设计害死后,水上灯再次陷入了寂寞无助的生活,戏演不成,丈夫又死。女性强烈的依附性不是天生的,世事纷乱的社会造就的苦难,使置身其中的女性不得不设法面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和同情水上灯这个女性形象,而不是武断地否定与苛责。陈仁厚再次出现,水上灯方才知道了水文以“告密”为要挟的内情,我们看到深情人几乎可能重结旧缘。怎奈命运垂下的手又将残酷制造,两难选择中为救陈仁厚,水上灯仇恨式的谎言,矢口否认了水文当夜到过她这里,宿命般地终致自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意义方位”全乱了。这一条“解气而又无心置谁于死地”的“谎言”导火索,引发了“爱”(和陈仁厚生命的患难真情)与“恨”(对水家的复仇式情绪)的全部灰飞烟灭,物是人非。水文入狱被害,刘金荣跳江自杀,水武疯掉了,生母李翠沦落街头……水家彻底败落了。陈仁厚看到水文的死,水家的败亡,深感因己而累及的悲剧,罪责于心。再加上同去刺杀叛徒的两个弟兄,也同水文一起被砍了头,陈仁厚感到自身有罪,无法面对自己,削发为僧,入寺出家了。当身为戏子的水上灯与身为和尚的陈仁厚,在两岸分别写有“放下着”和“莫错过”的桥上相见,命运的无情捉弄已分外刺人眼目了。历经苦痛,而负有鲜血的爱情,已然不再可能。流水积淀成的岩石,有着退潮后远离喧嚣的冷寂。此时的落泪,悲进骨头。
四、结语
对方方作品的解读不应限于女性写作视角,其实她写的女性形象,“做足‘女’字只是她的手段,做足‘人’字才是她的目的”[2](P404)。当然她的创作亦非限于此,她写作中力促趋于诗性锋芒,文本有着顽韧的生命力和超拔力,引人向上思考。
拉康提出过主体的三层结构理论: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拉康认为主体“不过是各种心理功能之统一,是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组成的系统”[6](P58),而“主体的存在取决于象征层功能正常发挥。”[6](P58)并且“想象界与象征界却包含在实在界之内。这三个层次具有使主体与他者和世界发生联系的功能”[6](P58),这样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创作主体与文本的内在关系。“这三者是从现实到想象,从想象到象征的梯次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较窄视野到更广阔的视域推进。”[6](P59)笔者想确认的是体现主体心理结构层次的虚构性小说,审美构成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体验力(感性)、想象力(灵性)与超验力(思性)。
若我们细细地去分析《水在时间之下》,笔者认为构成上正是三者的力量驱动了本书的“生命厚度”。作者说,“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5](P465)对于这样的作品,笔者分析也实不过只是部分上的探询。
《水在时间之下》以小水滴(即水上灯)喧哗的哭闹为悲剧的始端,水家视小水滴为灾星,迫使李翠将她抛弃,菊妈出于善心转送给了“下河”的表第杨二堂,生命流变其间又遭受种种人生变故,如慧如私通琴师吉宝,汉口发水慧如出走生死不明,小水滴陷入被世界抛弃的孤独境遇。她知道了自己被亲生父母抛弃,杨二堂被水武毒打致死……才有了“昨夜一场大雨,打落一枝玫瑰红,却开出一盏灯”,小水滴已成为舞台名角水上灯,“一盏明灯,随水而来,飘在水上,光芒四射”。苦难将生命之流一再波折,而“最是时间残酷无情”穿透了一切,动荡纷纭的社会变革,爱情与仇恨的撕裂,水上灯最终选择了“从炫目的舞台走下来”,“从海上风暴中挣扎而出”。她“通过她的血肉生命”、“有了她对这个世界的透彻了解”、“喧哗中的冷寂”,时间改变了一切,喧哗的流水打磨成沉寂的岩石,层叠的人生,望着时间之水缓缓生命中淌过,默然伫立。生命最终静静地归于冷寂成为悲剧的终结。
水上灯有着复仇女神般的烈焰,也有着弥足珍贵的正念守持,如随离开上字班仍不改“水上灯”艺名,守信绝不为占据汉口的日本人演出,气骨顿出。没有一般戏子随浊自沉的惰性,虽身上难脱女性的依附性。作者内心里珍爱着这一角色,没有将其单一化、平面化,她有着复杂的个性内涵,自然地流露出作者有意识地考量女性命运,“拷问”女性自身的倾向。水上灯面对的困境,看似是有权去选择的,实则选择却是两难的。水上灯内心始终有着执着的坚守,不同于铁凝《玫瑰门》中司漪文的形象,到有些似于《长恨歌》中王琦瑶,繁华梦灭后的寂然时间,将一切超度,终致“人生的无常与苍凉的喟叹”[1](P423)。笔者倒不认为她是“恶之花”的形象,却倒似“水成岩”般被时光岁月打磨雕刻的对象,而在时间的穿越中,有着人类自身命运与乱世幻灭情感的普遍忧伤。在时间这把“宇宙锋”下,人事纷离、灰飞烟灭、刻骨铭心般“水成岩”的时间意识,表象世界将意志世界淹没。
“现代艺术不仅成为一种生存的抗争,也不仅是人生的表达和呼求,而且直接成为生存的一种方式,艺术成为生存本身”[6](P50),《水在时间之下》阐释着一种人生,尽着自己最大的可能性,本身也成了人生的表征。“悲剧作为最高的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灵魂不在于故事情节,而在于表现诗人的灵魂,在于抒情”[7](P304),这自然寄寓了方方的“审美超越和艺术之梦”。一首“长诗”,有着来自人类普遍的生命关怀的自我意识渗入,看这凄美悲冽不变的风景,凝结着“水成岩”的泪,让我们重听哪拥有“生命温度”的咏叹:
“一滴水很容易干掉,被太阳晒,被风吹,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她说,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埋在时间下面,就是不干……”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方方.奔跑的火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陈超.游荡者说[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5]方方.水在时间之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6]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艺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7]马新国.西方文艺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Water and Rock
Zhang Gaofeng
This paper examines Fang Fang's novel,Water Under the Time,to discover the unique"life experience"and" poetic temperature"in her works.By comparing with Bian Zhilin's poem Water and Rock,it tracks Fang Fang's previous writing experience and the two skills in the novel,the displacement and horizontal modes,which help to add poetic glamour to the novel.While summarizing her poetic writing style,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life temperature"and"poetic care"to seek the common emotions in the life of individuals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beings.
Fang Fang;water and rock;poetic writing;life temperature
I206
A
1673-1573(2010)03-0069-06
2010-04-21
张高峰(1984-),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新时
关 华
责任校对:世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