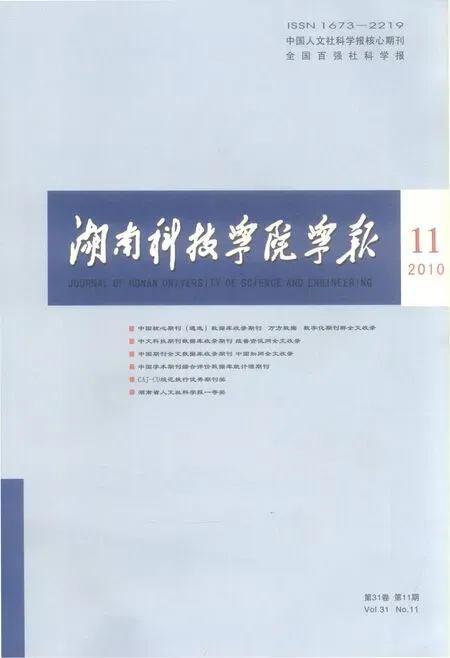论翻译中“境”的析解与“意”的传达
戴建春
(温州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8)
翻译是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翻译活动产生2000多年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和探讨从未中止。对于何为翻译,至今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如我国《辞海》和《汉语大词典》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中国大百科全书 · 语言卷》认为翻译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认为:“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语义上,其次是文体上(2003:12)。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昌盛的目的(孙致礼,2003:6)。审视这些翻译定义可以看出,尽管它们措词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翻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传达“意义”。可以说,“翻译的本质是释义,是意义的转换”(陈宏薇等,2010:1)。然而语言离不开语境,总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确定的意义。因此,翻译时,译者对语境的正确解读对于意义的正确传达至关重要。本文试从翻译的本质出发,阐述翻译中“意”和“境”的关系,以及“境”的解读对于“意”的传达的重要作用。
一 翻译中 的“意”与“境”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人们进行交际的手段。但是人们在交流的时候,传递的信息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表面意思,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要透过语言表面,深入进去,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图,达到交际的目的。所以,在翻译中,译者要理解的不仅是原文的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而且是原文作者的真正意图 (intention)。由于语篇生成于一定的交际情境、特定的文化中,译者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的意义,还要注意文化层面以及语用层面的意义。在此,笔者将其称为“意”。然而,交际者的“意”,即意思、意图的传递是借助一定的载体得以实现的。这个载体笔者称之为“境”(context),这个“境”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上下文语境,即语言语境,还包括文化语境。虽然由于生活的地域、环境条件、生活方式、思维、文化的差异,人们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别,但这一切都会在使用语言的“境”中得到反映或体现。所以,翻译时,译者必须根据原文(source text)产生的“境”中分析和理解“意”,然后在译文(target text)的“境”中传达“意”。
二“境”的析解与“意”的传达
(一)通过析解“境”确定词语意思
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弗斯(Firth)说:“每个词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就是一个新词”(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new word)(1957),“没有语境,词就没有意义”(Malinowski, 1923) 。正因为词义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因此,在翻译实践中,传“意”决不能不顾“境”而仅仅死搬词典释义。否则容易出错,造成上下文脱节、文句不通。
例如,在我国十分流行的教材《新概念英语》一书的第四册 (Fluency in English) 的第五篇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The gorilla is something of a paradox in the African scene。可是国内几个版本的译文对paradox一词的翻译大都难以让人理解。有的译为“自相矛盾”,有的译为“难以捉摸”,有的译为“怪物”,有的甚至译为“隽语”。其中只有“难以捉摸”还是个可以接受的译文,其余的几乎都是错的,甚至是笑话(如“隽语”便是)。其实,要确定这一词的特指意义,除了要了解它的基本意义“自相矛盾”外,还需联系上下文。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文章共分为两段,第一段讲述人们对“大猩猩”这种动物是很了解的,几百年来人们捕捉它,饲养它,观赏它等等。但第二段又讲述人们对野生状态下的大猩猩的生活习性等方面仍很不了解,仍有许多谜。所以,根据该词的基本意义“自相矛盾”和文章上下文语境(既了解又不甚了解)可以译为“在非洲的自然界中,大猩猩是一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动物。”这样,这句统领全文和总括性的句子就得到了很完满的传达,对全文的翻译也起到了定位作用。
再如,《水浒》上有一段写到,武松到酒店喝酒,店小二说有酒无肉,武松只好吃寡酒。正喝着,进来一帮人,小二一见,马上端出大盘肉来。武松大怒,质问小二。小二说是客人自备的肉。武松不信,一拍桌子,喝道:“放屁!”
美国驰名世界的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却把最后两个字译成了“pass your wind”,回译成中文,是一个命令:“放屁!”如果不放在语境中,“放屁”是有“pass your wind”这个意思,但根据上下文,明明有肉,却要看人分别对待,岂不可恼!所以武松是在申斥店小二,带有不相信他的话,责骂的意思。因此,译为“nonsense”(胡说)较为贴切。
另外,交际是在一定的“境”中进行的。句与句的意思相互连贯,每一句的意思都受“境”的制约,许多句子只有结合“境”才能准确把握。若离开了“境”,解“意”就会有困难,达“意”就失去了前提。比如:“他来了,我走。”这句话可能作下面几种理解:
如果他来,我就走。If he comes, I will go.
既然他来,我可以走了。Since he comes, I will go.
当他来时,我就走。When he comes, I will go.
因为他来,所以我走。As he has come, I must go now.
(二)通过析解“境”识别风格意义
从奈达给翻译所下的定义中,翻译时,译者不仅要传达原文的意义(meaning),而且要传达原文的风格(style)。原文风格主要体现在其使用的文体和语体上。而语言交际的目的、传达内容信息、表达思想感情的不同,采用的文体,语体也会不同。如,文体有应用文体,科技文体,法律文体,论述文体,文艺文体等等,语体有正式,一般性,非正式语体。因此,选词、造句、修辞、结构都会存在某些差异,而文体和语体都体现在原文的“境”中。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对原文所在的“境”作透彻的分析,弄清其文体和语体,在译文中采用相应的文体和语体。使译文在风格上与原文相一致。
比如,在The Celestial Omnibus这篇小说中有一个广告如下:
As an extra inducement, the Company will, for the first time, issue Return Tickets!
某人把它译为:
作为额外优待,本公司首次发售来回车票!
虽然,该译文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但根据英语原文“境”可知,这则广告显然语句简短,但不失其正式性,如,用第三人称而不用第一人称,状语部分(for the first time) 放在谓语助动词与动词之间,并以逗号隔开,并没有像口语体那样放在句末。用语也十分正式,如 inducement, issue等词的使用。从交际内容,方式和关系来看,它是用庄重的正式语体,这样可以体现其严肃性和给人以可信性,原文的语体十分庄重,而将Return Tickets这个十分关键的词译成“来回票”就太过口语化了。因此,译文应表现出原文的正式性文体特征。宜译为:作为额外优待,本公司首次发售双程车票!
另外,翻译时要使译文保持原文的味,即使是那些通过语法或语音变异所表现的不规范语或者俚语。这种表达法可以用来渲染人物的个性,体现人物的文化层次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等。比如:
“I kept it from her after I heard on it ,” said Mr. Peggotty,“going on nigh a year. We was living then in a solitary place,but among the beautifullest trees,…”
“起那时俺听了消息后,”辟果提说:“瞒着她快一年了。俺们那时呆的地方挺背,前后八方的树林子说不出的最漂亮,……”
根据整个“境”,读者可知辟果提先生的话错误百出,说明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不是上流阶层的人物。译文尽可能地把表层结构的这一特点做了如实传达。假如把译文中划线部分改为“我听到那消息后”,“我当时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周围有十分美丽的树……”,译文虽然通顺,但有悖于原文,原有的“土气”已丧失,不利于再现辟果提说话的口吻与神态。
再如,在Charles Dickens的小说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伯菲尔》)一书中,描写了一个总是期待好运的乐天派人物Wilkins Micawber,他说起话来总是文绉绉的,爱用大词,古语,以显示自己的学问,例如在第十一章有这样的一段话:
“Under the impression,” said Mr. Micawber, “that your peregrinations in this metropolis have not as yet been extensive,and that you might have some difficulty in penetrating the arcana of the Modern Babyl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ity Road—in short,” said Mr. Micawber in another burst of confidence, “that you might lose yourself—I shall be happy to call this evening, and install you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nearest way.”
翻译之前,译者应先对“境”作分析,这段话中之类的词都是文绉绉的古体词和句式,但又在之类的句子中露出了现代语言的白话痕迹,这说明这个说话者在有意卖弄学识,又缺乏足够的知识,这对人物刻画非常重要。所以在翻译时应忠实地再现出来。可以译为:
“我觉得于此大都会之中,你的游历尚欠广泛,你在探索向城市路那一方面这个近代巴比伦的奥秘时,或许仍有困难,简言之——”,麦考伯先生说,“你可能会走丢了的——我今晚来拜访以指示你一条捷径。”
上面译文特意采用古体汉语来译,但其中“你可能会走丢了“却用大白话,以示语体的不同,而不译为“恐你迷路”。
还有,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篇散文Of Studies,其作者是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都处在现代英语的初级阶段,语言中还有不少古英语的痕迹,与现代英语有较大差异。因此,王佐良先生把握了这个“境”,译文用了较为浅近的古汉语,十分得体,是译中精品。比如文中的第一句话“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若译成“读书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得愉快的感觉,可以增添光彩及增长才干”, 虽然其意思同王佐良的译文“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大致相同,但风格上与原文相比,神韵味道尽失,且还破坏了原文表层结构的三项式排比特点。
(三)通过析解“境”传递文化意义
语言和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早就指出:语言是自我的表达,也是文化的反映。(陈德鸿等,2000:157)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1989:18-19)。各个民族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我们在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为了使交际成功,在翻译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文化之间的差异。比如: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般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但在下面句子中,却不能不作改变。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红楼梦》)第六回)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and something may come of it for all you know.(杨宪益,戴乃迭译)
话中提到菩萨(Buddha)是佛教词语,God disposes 却是基督教词语,译文如不改,不但会造成矛盾,又会使外国人认为刘姥姥信基督教呢,所以只好把“God”改成“Heaven”。
再如,在甘地遇刺身亡后,美联社一篇题为Gandhi’s Assassination: “Bapu (Father) Is Finished” 的报道,该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 A panic-stricken Moslem woman echoed the thoughts of thousands with a cry: “God help us all!” 此处能否译为“上帝保佑!”呢?如果没有语境,这样译无可非议。但是根据这句话所在的“境”,即上下文和故事发生的地方,这样译就显得不妥。因为,穆斯林教徒信的不是上帝,而是真主安拉。因此,宜译为“真主保佑!”或“安拉保佑!”
英汉两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英语中出现的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在我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文化。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象和含义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故翻译时特别要引起注意。例如英国翻译家霍克斯把《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译成 “God bless my soul!”,把上帝拿来代替佛教的无量寿佛,这很可能让西方人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译文大大地削减了中国文化内涵。
(四)通过析解“境”领会作者意图
由于中西方思维文化的差异,在翻译时信息不能或很难进行“等值转换”时,我们应根据“境”来分析作者的“意图”,辨别信息的主次,采用合适的翻译方法,使信息量尽量少“打折”。如:
钱歌川先生在译矛盾的小说《动摇》时,遇到这样一段对话:
胡太太叹了口气,看见胡国光还是一肚子心事似的踱方步。
“张铁嘴怎么说的?”胡太太惴惴地问。
“很好,不用瞎担心了。我还有委员的福分呢!”
“么事的桂圆!”
“是委员!从前行的是大人老爷,现在行委员了!你还不明白?”
这段对话中“桂圆”与“委员”是谐音词,显示了胡太太的愚昧与对新事物的无知,如果将“桂圆”直译成的话,是表现不出胡太太的无知和愚昧的,而这正是文章要表达的重点。钱歌川先生仔细推敲后,考虑到“委员”的英语对应词Committee与Common tea(普通茶)是谐音的,于是用Common tea (普通茶)来代替Longan(桂圆),因为虽然字面意思不一样,但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显示胡太太的为人无知与愚昧。
又如一些一问一答类似我们常见的“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考虑整个“境”,问与答孤立开来按字面翻译,就会失去作者的“意”。如:
——Why flower does everybody have?
——Tulips.(Tulips=two lips)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郁金香。(郁金香的英文与双唇的英文发音相似)
(《英汉翻译概要》,第244页)
分析原文的“境”后,我们知道,作者的主要意图并不是要表达文字的表面意思,而是想借助文字的语音双关来传达幽默诙谐的智慧。而《英汉翻译概要》中用了“注释法”,译文在理解上是正确的,但由于加上了“注释”,即使读者能够看明白,原文的幽默诙谐已不复存在。诚然,“注释”法虽不失为一种可用之法,但实在是因“无可奈何”而采取的下下策。退一步说,读者能完全理解这一“加括号”译文,可这一问一答若出现在电影对白中又当如何呢?难道也给听众“加括号”解释?我们不妨根据“境”中信息因素的次重,译为: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泪花。
三结语
翻译即翻“意”,但“意”须在“境”中去把握、去传达。通过“境”,译者可以准确地把握原文的表面意思和深层含义,可以把握原文的文体和语体,可以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译者可以根据“境”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使原文的“意”得到最大限度的传达。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3]靳梅琳.英汉翻译概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6]Firth,J.R.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7]Malinowski,B.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Rutledge &Kegan Paul,1923.
[8]Nida.E.A.&Taber.C.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