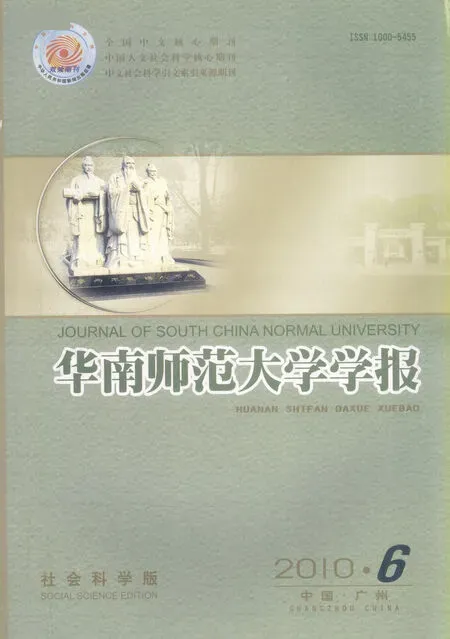归纳的非概率式辩护及其难题
荣立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替换为 250100)
归纳的非概率式辩护及其难题
荣立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替换为 250100)
归纳的辩护可以划分为概率式辩护和非概率式辩护两种不同的形态。概率式辩护由于得到数理统计理论支撑而得以成立,然而概率式辩护并不足以承担整个为归纳辩护的职责。作为补充,归纳的非概率式辩护并不成功,不论是皮尔士所说的“归纳具有自我修正性”还是刘易斯的“先验分析式”辩护最终都没有说明归纳推理的有效性。
归纳;概率式辩护;非概率式辩护
休谟指出:“说到过去的经验则我不能不承认,它所给我们的直接的确定的报告,只限于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物象和认识发生的那个时期,但是这个经验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将来,扩展到仅在貌相上相似的别的物象,这正是我欲坚持的一个问题。”[1]25休谟问题所关注的正是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归纳推理是指基于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单个事实做出一些概括性的陈述。但是,如果一个概括性陈述为真,那么它不仅断言了过去的经验,同时也断言了将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归纳推理是一个从部分到达整体的扩充性推理[2]1;从科学知识内容的增长来看,归纳推理使得“从已知事物特性的描述过渡到未知事物特性的描述”[2]2。然而,如何从部分到达整体、从已知到达未知、从过去到达将来,休谟问题不仅质疑了扩充性推理的逻辑根据,也提出了科学知识内容的合理性问题[2]2。如此看来,除非我们甘愿对科学的内容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否则我们不能回避归纳推理的逻辑辩护。然而,休谟和波普尔先后指出:“在逻辑学的范围内休谟问题的正面解决是不可能的。”[2]3这迫使着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还能不能对归纳推理进行辩护;如果可以,应该怎样来对归纳推理进行辩护。通过皮尔士和刘易斯的归纳理论,我们试图回答上面的问题。
一、皮尔士的概率式辩护
如何为归纳推理做辩护呢?皮尔士认为可以对归纳进行概率式辩护,即把归纳推理表述为统计推理的一个反证法转换,并通过辩护统计推理而使归纳推理得到辩护。为此,皮尔士首先给出了统计推理和归纳推理的基本形式:[3]第二卷,347
统计推理的基本形式
(1)S是从 M(总体)中随机抽取出的系列样本,
(2)有比率为 r的 M是 P,
(3)因此,很可能有比率大致为 r的 S是 P。
归纳推理的基本形式
(4)S是从M中随机抽取出的系列样本,
(5)有比率为 p的 S是 P,
(6)因此,很可能有比率大致为 p的M是 P。
观察两组患者检查结果(股骨头坏死情况)。总共分为3个等级:若患者两种方法检查均显示正常,则判定为0期;患者行走受到限制,髋关节会出现疼痛感,CT检查未显示异常,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异常,则判定为Ⅰ期;患者疼痛感觉为针刺或钝痛,活动时感觉明显,休息时好转,CT检查结果显示存在硬化或囊变情况,核磁共振显示有异常,髋臼变化不明显;则为Ⅱ期;患者休息或活动时,均疼痛严重,CT检查显示,患者骨性关节出现硬化,有明显增生,核磁共振显示为新月征,为Ⅲ期;患者疼痛难忍,两种检查方法结果均显示股骨头变形、变平、塌陷,则为Ⅳ期。
在皮尔士看来,如果 r是 p的逻辑否定,即“比率 p在 0到 1这个取值空间内容许 r所排斥的所有取值而排斥比率 r容许的所有取值”[3]第二卷,347,那么 (5)就是 (3)的否定,(6)就是 (2)的否定。很显然 ,“如果 (1),(2)/(3),那么“(1), (3)/(2)”这种反证法变形是逻辑上有效的。因此,如果概率推理“(1),(2)/(3)”是有效的,那么归纳推理“(4)[=(1)],(5)[= (3)]/(6)[= (2)]”也是有效的。
统计推理当然是有效的,成中英的工作表明,(1)当把一个样本从总体中取出时,样本的构成比率和总体的构成比率相等的概率是最大的。(2)给定一个差值域,样本的构成比率和总体的构成比率相等的概率要大于在同样的差值域下样本有其他构成比率的概率。(3)通过设定一个合适的差值域,我们可以使“样本的构成比率与总体的构成比率相等”这个假设成立的概率尽可能地高,并且这个概率要比同一差值域下样本有其他构成比率的概率都要高。[4]172在这个意义上,统计推理是一种演绎性的推理,其指导原则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是否可以把归纳推理作为统计演绎的反证法转换,从而为归纳原则提供一种演绎的辩护呢?
然而,这一辩护途径面临着一个根本的困难:统计抽样必须是无偏好的随机抽样,否则无法让样本的特征逼近总体的特征。根据现代统计理论,我们需要根据总体的大小估计样本的大小,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期让样本的特征在设定的差值域下逼近总体的特征。然而,在归纳推理中,总体是未知的,因此人们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判断所抽取的样本相对于总体是随机的。正是这个重要的区别使得为归纳推理寻求一种演绎的辩护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随机抽样的方法并不能保证归纳推理中的归纳前提是适当的,当然也没有任何因素保证总体的特征总是受限于它的某种样本的特征而进行变化。皮尔士显然也看到了概率式辩护的这一局限,于是他转向了归纳的非概率式辩护。
二、皮尔士的非概率式辩护
对于归纳推理来说,怎样的样本才算是随机的样本?样本的大小又怎样才算是合适的?怎样预先设计样本之于整体的误差范围?这些问题都因为总体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而得不到回答。那么,在归纳推理中,到底有没有理由确认一个样本是适当的,并使得适当样本的特征能够限定未来事件或未知总体的特征呢?皮尔士的非概率式辩护正是从这一个问题出发的。皮尔士认为这一限定是通过归纳的自我修正实现的,“归纳作为一种推理方法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在一个很长的试验序列中通过归纳方法总是可以不断地修正现有的结论并引导我们获得真理 ”[3]第二卷,375。但是 ,说归纳是“自我修正 ”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说这样的归纳结论总是“引导我们获得真理”又是什么意思呢?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归纳的自我修正。I.莱维在介绍皮尔士的这个概念之前,先阐释了统计演绎中的自我修正:[5]137在统计演绎中,已知总体具有性质 P的概率为 p,我们采用有放回的抽样方式 (有放回的抽样,指的是从总体中抽取出样本之后,所抽出的样本放回总体之中,并进行下一次抽样),经过 n次随机抽样得到一个样本,进而人们可以根据样本具有性质 P的相对频率对总体的特征作出预测。重复地进行以上步骤,人们可以不断地得到新的样本和新的预测……经过一个很长的实验序列,这些正确的预测所确定的相对频率将收敛于一个值。……在作这样的预测时人们难免有犯错,但是只要他们重新运用上述的规则从总体中抽取出样本,那么由此所确定的具有压倒性的概率还是得到了证实。
比照莱维的解释,我们接着来看看皮尔士对归纳之自我修正的说明:[3]第二卷,339我们说样本中的个体具有性质 P的比率为 p,因此很可能总体中的个体具有性质 P的比率也是 p。假如不是这样的话,这个推理的结论也会通过持续不断的抽样而得到修正,进而成为真的。在类似的情况中,我们称统计演绎的结论在持续不断的抽样中得到了证实。即使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下统计演绎推出的结论有可能被否证,但是大多数统计演绎所得出的结论和总体特征是一样的,这一事实证明了统计演绎所推出的结论是近似地为真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称统计演绎推理是或然的。归纳推理也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被称做是或然的:尽管通过归纳可能会产生假的结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按照这种规则来进行推理,那么我们在一般情况下都将得到一个近似为真的结论。
很显然,比照统计演绎的自我修正,皮尔士解释了归纳的自我修正——假如人们在做出一个归纳结论时犯错的话,他们仍然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不断地抽样以修正原来的归纳结论。但是,这样的比较出现了一个困难。统计演绎之有效的前提是假定抽取的样本相对于总体是适当的、随机的,进而人们通过可靠的经验程序判定样本相对于总体是否是适当的。辩护归纳推理也必须假定抽取样本之于总体的适当性。但是由于归纳推理所涉及的总体是未知的,人们不可能找到一套经验程序来判定样本对于这个未知的总体而言是适当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选择出来的样本特征可以限定未知总体的特征,除非是一种心理习惯。在概率式辩护中出现的难题——面对未知的整体,人们无法确定所选择的样本是否是适当的,在皮尔士的非概率式辩护中又改头换面地出现了。对皮尔士而言,一个样本是适当的仅仅在于它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出来的。因此,莱维说:“对皮尔士而言,归纳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从总体中抽取样本才称得上是随机的抽取,如何在各种情况下确定我们‘获得事实’的方式是随机的。……皮尔士没有像莱辛巴赫那样试图去先验地证明存在有一些随机的抽样方式,而是像康德一样直接根据假定‘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推出存在有一些合法的归纳。”[5]139
很显然,皮尔士的概念——归纳之自我修正,并没有合理地建立起来。因此,归纳的自我修正性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真理。如果皮尔士坚持认为归纳的自我修正性能够告诉我们以“真理”,那么这一定是因为皮尔士有一个不同的真理观。于是,我们的讨论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确如此,皮尔士开始抛出他那个著名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和实在论:“我们所谓的真是指某个最终必定被所有的研究者赞成的主张。同时,在这个主张中所表征的对象就是实在。……恺撒跨过了卢比肯河这个命题是真的就在于,随着我们的考古学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展开,这个结论将在我们心中得到不断地加强;或者说,我们始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话,情况也终将是如此。”[3]第五卷,565
是的,我们的确看到了皮尔士的坚韧。当真概念发生了上述的改变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归纳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这种归纳问题的解决已经与我们当初所想不同了:我们的实在只是科学理论中所表征的对象;我们的真理也不再与客观世界相符合,而变成了研究者所赞成的主张。然而,同意皮尔士的解决方案的后果是“休谟问题”或“归纳问题”的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皮尔士所讨论的问题不再是如何把过去的经验扩展到未来,而是如何通过过去的经验获得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获得“研究者赞成的主张”。
三、刘易斯的先验分析式辩护
与皮尔士一样,刘易斯也坚持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人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那只能是通过归纳。换言之,存在有效的归纳是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的必要条件。故而,只要承认存在关于实在的知识,归纳结论的可靠性和归纳推理的有效性自然就得到了辩护。如墨菲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刘易斯所描述的经验知识是可能的,那么从过去到达未来的论证存在就必定是可能的。”[6]164一般来说,要断言概念可应用于直接的经验、要断言存在从过去到达未来的论证 (即断言有效的经验概括存在),人们需要断言某种自然齐一性或秩序的存在。但是,后者一再地被证明是难以得到辩护的。为了达成为归纳辩护的目的,刘易斯不是从形而上学去论证自然齐一性的存在,而是把归纳的辩护问题转化为经验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这种转化的合理性在于:假如经验知识是可能的,那么它不仅适用于过去的经验,而且也必须适用于未来的经验,据此归纳推理就得到了辩护。因此,墨菲说:“刘易斯认为,只要我们意识到需要辩护的仅仅是或然的知识,那么归纳辩护问题的本质就发生了改变,进而它的解决也成为可能。”[6]165
然而,是否存在关于实在的知识呢?刘易斯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关于实在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为了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有两类基本要素是不可或缺的:直接的感观呈现和用以表达思想活动和意识反应的所需要的先验形式(先验概念)。他认为,经验知识就是将这些先验形式应用到经验之上而产生的结果。经验知识并不是对感观呈现的直接反映。人们只能将已经把握的先验形式 (心智中的某种标准,用以帮助人们确定某个概念是否适合于特定的感观呈现)应用到直接的感观呈现上才能形成对经验的解释,进而也才能形成经验知识。事实上,不仅获得经验知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先验形式,就连确认实在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先验形式。在刘易斯看来,任何能被看做是实在的事物也都是通过先验概念加以解释、加以确定了的某种经验序列。因而,用先验的概念去确定和解释某一给定的经验就成为了我们探求关于实在的知识的起点。从这个角度看,先验的形式首先使得实在本身成为可能,进而也使得经验知识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刘易斯指出:“实在比经验更加规整,因为实在是经过分类后的经验。”[7]365“所有的概括都是基于实在,而不是基于没有经过分类的经验。”[7]366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及实在或者是作出关于实在的陈述时,我们就已经预设了某种先验结构。其中我们的“实在”概念和我们关于“实在”的陈述都相应地被给定了意义。为了从纯粹的经验中得到实在,刘易斯着重强调:我们必须把经验划分为不同的范畴,以便不同类型的经验彼此间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于是,只有借助于先验的概念,我们才能清楚地阐述“预先确定的用于解释的原则,用于解释我们做识别、关联和分类的标准”[7]230-231。
不过,先验的形式只是让经验知识和实在成为可能,而不是现实。那么是否存在有关于实在的知识呢?刘易斯认为,让经验知识和实在成为现实还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感观呈现的经验的确是秩序的,因而是可以用先验形式加以识别、关联和分类的。为了论证世界是有秩序的并且经验中存在有秩序性 (齐一性),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原则 A,其内容是:“认为经验片段彼此结合的机会是均等的,这一观点必定是错误的。”[7]368为了论证原则 A,我们不妨先从原则 A的反面来加以考虑。一般情况下,当一个可辩识的经验片段被给定时,例如一个独特的“似狗”的经验片段被给定时,我们可以基于这个经验片段作出预测说存在有一只狗并且期待它发出汪汪的叫声。现在,假设经验中每一个可辩识的经验片段都可以彼此间均等地结合起来,那么设想接下来会听到汪汪的叫声和听到喵喵、咕咕等叫声的机率就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断言这个经验片段中出现的不是狗就显得更为可信,因为接下来的经验片段证实“非狗”的几率要大大地高于证实“似狗”的几率。因此,由于设想原则 A的反面是不可能的,所以原则 A就是成立的。
到目前为止,刘易斯的理论确实需要经验中存在有秩序性,但是刘易斯强调说这里所要求的秩序性不是严格的。正如墨菲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刘易斯的理论确实需要经验中存在有秩序性,但是刘易斯强调说这里所要求的秩序性不是严格的。经验中确实必须有秩序,但是这只是说经验中有秩序,而不是说经验完全是秩序的。有些经验不满足实在或事实所应有的秩序要求,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它们重新归类为不同于实在或事实的其他什么东西,比如说梦想或幻觉。”[6]165正是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指出:“为了让经验是可理解的,为了让经验知识是可能的,我们必须要求经验中有秩序。但是,这种要求仅仅只是说存在有可被理解的事物或客观事实。我们不能设想经验中没有任何秩序,除非我们愿意承认无物存在。”[7]367
前面的讨论都集中在刘易斯的实在—知识论,可是他的实在—知识论是怎样被利用起来为归纳辩护的呢?人们对归纳和经验概括的常识理解是这样的:由于之前所发现的所有天鹅 a,b,c都是白色的,通过经验概括人们得出结论说“凡天鹅皆白”。刘易斯显然不赞同这种常识的理解,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经验概括之前就已然获知了一些关于实在的知识——“天鹅 a,b,c是白的”。然而,在刘易斯看来,“实在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我们通过把概念应用于经验所能获知的东西,实在就是以某种特定的秩序排列起来的可能经验的序列”[4]108。仅仅依靠我的感观经验是不能发现天鹅 a的。只有当 a当下呈现在我面前并在我的经验中显示出一定的秩序性,这个时候我才能把概念“天鹅”应用于当下的经验片段并作出断言“a是一只天鹅”。先验概念“天鹅”是心智中的某种标准,它是以假言条件句的形式出现的:假如 a是一只天鹅,那么它向我呈现出如此这般的形状、颜色、声音、行动方式等等。因此,当我们断言“a是一只天鹅”时,在刘易斯看来这实际上是作出了一次经验概括。因为我们是用“天鹅”所标识的某种心智标准整理了 a呈现给我们的感观经验。在刘易斯看来,经验概括不是简单地讨论如何从单称陈述过渡到全称陈述,而是“经验概括是可能的,如果概念可以应用于经验并用以区分不同类型的经验,如果经验概括中的概念连接在实在的领域中是可应用的”[7]345。正是因为这种对经验概括的理解转变,归纳辩护的内容在刘易斯这里也发生了转变——归纳辩护变成了讨论心智中的先验概念是否可应用于经验中的秩序性。
如上所述,刘易斯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和他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进行了捆绑。刘易斯的归纳辩护可以概括成一个三段论:
(7)如果有实在或关于实在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够作出概括,并且它们是真的;
(8)确实有实在或关于实在的知识;
(9)因此,我们就能够作出概括,并且它们是真的。
在刘易斯看来,(7)显然是真的。因为经验概括就是将心智中的标准应用于经验以获得实在和关于实在的知识的过程。(8)也是真的,因为原则 A保证了不能设想经验中没有某种秩序性,因此人们总是可以找到合适的先验概念应用于经验中的秩序性,从而得到实在和关于实在的知识。谈到 (8)时,刘易斯说,“尝试着去设想某一经验或事态使得人们揭示其秩序性的每一次努力都必然会遭受失败,这相当于尝试着去设想一个不可能设想的东西,去设想一个不能将其称为事物或客观事实的东西,去设想一个不屈从于任何经验概括的东西。由于经验概括所指涉的东西,即经验概括的主题,总是与某些概念一致,因此,去设想一个不屈从于任何经验概括的东西就是去设想一个不屈从于任何概念的东西。进而,设想与任何概念都不一致的经验或实在,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设想的。”
四、非概率式辩护的难题
对刘易斯的先验式归纳辩护的批评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一些概率论者如莱欣巴赫,不会认可刘易斯的先验辩护。他们不会认为诸如“a是一只天鹅”这类命题也是一个经验概括,他们追求的辩护是从确定的单称命题过渡到全称命题的逻辑理由。由于此类批评涉及研究进路不同,本文在此不作重点介绍。我们更关心来自刘易斯理论体系内部的批评。在考察了刘易斯的先验式辩护之后,成中英提出了三个批评意见[4]130-135。首先,即使人们可以简单地认为一个为真的经验概括就意味着某种关于实在的知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说成是对归纳和经验概括的一个辩护,因为这时说一个为真的经验概括就是某种关于实在的知识只是在说一个重言式。事实上,真正的辩护需要我们指出某个的独立理由以使得我们发现归纳确实有益于我们的关于实在的知识。其次,即使我们假设刘易斯可以用上述方式来为归纳辩护,我们还是会提出下面的疑问——我们为何要相信隐藏于这个论证背后的实在理论?这也就说,我们为何要相信事物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即它们是通过归纳所得到的某种可能经验的序列?刘易斯意义上的“无物存在”并非是不可设想的。成中英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有这么两类人:一类人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和归纳规则不断地修正他们的归纳结论,而另一类人并不会采用这种方式来修正他们的经验概括。可以想象的一点是,第一类人犯错误的机会和第二类人犯错误的机会是一样的,甚至是更大。如果一个魔鬼创造出一些既不同于第一类人的预测也不同于第二类人的预测的经验序列,那么第一类人犯错误的机会和第二类人犯错误的机会是一样的。如果一个魔鬼,抑或是太坏的运气使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第一类人的预测、但是却和第二类人的预测相差不多的经验序列,那么第一类人犯错误的机会就比第二类人犯错误的机会要大。果真有这样的一个魔鬼存在的话,无论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概念框架,基于已知经验而得到的实在理论总是不可靠的。这也就是说,不存在有为真的经验概括。最后,即使我们承认“归纳和经验概括具有一般的有效性”这个论证是有效的,但是它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一个具体的经验概括是可信的。既然,归纳的有效性只是大体上的,因此对具体的归纳来说它总是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的。然而,刘易斯并没有说明一个具体的经验概括有效或无效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综观之,归纳辩护的真正难题在于: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总体时,人们如何作出归纳结论并辩护说这个结论是或然为真的。在皮尔士那里,这个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归纳前提的适当性,进而把一个归纳推理合乎逻辑地转化成一个概率推理。正因为如此,皮尔士所说的“自我修正性”最终把归纳的非概率式辩护转化成为知识论和真理观的讨论。然而,采用这一策略的皮尔士显然改变了休谟问题的实质内容,因而也就没有真正地为归纳作出辩护。刘易斯似乎面对着理论上的困难,因为我们要说明的不是经验概括使得过去的经验得到了解释,进而使关于实在的知识成为可能的;而是经验概括也可以在我们的关于实在的知识论下面使得未来的经验得到解释,使得关于实在的知识也是适用于未来的。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刘易斯抛出了他的递加过程理论(cumulative theorem):“如果一个关于某物的未来经验的预测是有效的,这意味着我们就通过一个陈述把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经验联系起来。而这恰恰就证实了把一个特定的概念应用于关于某物的当下经验是恰当的。”[6]166进一步,如果关于未来经验的预测不断得到证实,那么概念应用于直接经验的恰当性 (或者说经验概括的可靠性)就不断地得到了证实。为了充实递加过程理论,刘易斯还指出:“从过去获得的一个关于未来的统计性预测不可能总是无效的,因为相对某个给定过去的一个未来而言,它终究会成为另一个未来的过去。”[7]386
不论是皮尔士还是刘易斯,他们的立足点都是根据他们的实在—知识论来辩护归纳前提的适当性。在皮尔士那里,归纳前提的适当性是相对于他的真理观所预设的,因此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只是相对于已被掌握的经验而成立,因为他的真理只是科学家根据已有证据而一致赞同的理论。在刘易斯那里,归纳前提的适当性来自于存在有先验概念用以标识感观经验中的秩序性。但是,先验概念标识感官经验中的秩序仅仅是对过去的经验成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可以扩展到未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刘易斯的论证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刘易斯之所以认为原则 A成立,乃是因为人们设想它的反题是不可能的,即设想“经验知识中设定的实体彼此之间可以均等地结合”这一观点成立是不可能的。但是“经验知识中设定的实体彼此之间可以均等地结合”只是在过去的经验中被证实为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命题在未来的经验中也始终被证实为假。因此,这个命题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恒假 (即矛盾),据此我们不能推出在未来一定存在可理解的事物或客观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刘易斯的论证链条断裂了,作为结果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先验论证辩护了通过归纳可以得到或然性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成中英才会设想出那个恼人的魔鬼。面对未来不确定的经验原则 A也不是必然成立的,这成为刘易斯整个先验论证的梦靥。也许,刘易斯仍然会争辩说,即使未来不确定的经验可能会与当下我们承认的实在或关于实在的知识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经验概括获知其他的实在和知识以便把过去和未来的经验都合理地加以解释。举例来说,假如在今天以前的经验中,太阳总是辐射能量,但是今天它却没有辐射能量。刘易斯的理论一定是建议我们应该把“太阳”和“辐射能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抑或改变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以便把今天这个异常的经验包容进来。但是,这并不是在为归纳辩护。归纳的辩护是要我们回答“归纳结论的或然有效性”,归纳的辩护不是要把归纳结论中的实在进行改变。刘易斯只是在为关于实在的知识论作辩护,而不是在为归纳推理辩护,尽管在他眼里这两者是同一的。面对着未来不确定的经验,人类纵有理性又奈其何?这也许就是真正的归纳难题。
[1] D.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 鞠实儿.论休谟问题与科学研究活动启发式程序重建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5).
[3] CHARLES S P.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Edit by Charles Hartshorne et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
[4] CHENG Zhong-ying.Peirce's and Lewis's Theories of Induction.The Hague:MartinusNijhoff,1969.
[5] ISAAC L. Induction as Self Correcting according to Peirce∥MELLOR D H.Science,belief,and behaviour:essays in honour of R.B.Braithwait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6] MURRAY GM,LEW IS C I.The Last Great Pragmatis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New York Press,2005.
[7] LEW IS C I.Mind and the World Order.New York:C.Scribner's Sons,1956.
【责任编辑:赵小华】
B81-06
A
1000-5455(2010)06-0088-06
2010-05-2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内涵语义的辩护途径”(09DZXJ0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内涵逻辑及其当代发展趋势”(IFW09043)
荣立武 (1979—),湖南岳阳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