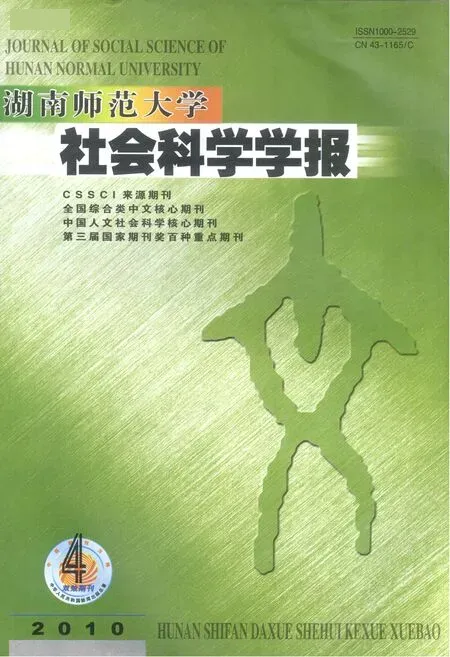论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分析
马俊领
(广东医学院 社科部,广东 东莞 523808)
论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分析
马俊领
(广东医学院 社科部,广东 东莞 523808)
埃尔斯特以解释的清晰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为标准,借鉴现代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某些结论和方法,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分析和重构。他认为国家政权具有概念自主性和解释自主性并对自主性生成的机制进行了系统勾勒。埃尔斯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他忽略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潜力以及人类在道德、制度和社会规范领域的进化能力,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滥用也使他的分析和重构部分地表现为物化意识的产物。
埃尔斯特;国家理论;概念自主性;解释自主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自述,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他的研究就得出了以下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P32)叶汝贤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历程中的第一个发现,其意义就在于它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说明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现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萌芽”,“为进一步发现唯物史观开辟了新的途径”。[2](P57-63)
寻求对国家、革命和人的解放等政治现象的解释是马克思研究物质生活现象的主要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为政治理论服务的,后者才是他关切的焦点。在埃尔斯特的分析语境中,国家自主性或者政权自主性是指国家政权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的独立性,蕴含二者相对分离的关系,并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相对于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独立性的意味。国家政权属于上层建筑的子范畴,阶级经济利益属于经济基础的子范畴。基于这种理解,埃尔斯特有时把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一般化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于经济基础来说的独立性吗?
国家政权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看起来比较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表现为这样的历史事实:当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时候,它就产生和发展,当其不适合于经济基础的时候,就要发生程度不同的变革;具体到国家政权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的关系来说,当地主、资本家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以后,他们就力求推翻或变革旧的国家政权并掌握国家政权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西方诸多学者也这样来解读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想。威廉姆斯认为,“透过历史,政治思想家试图提供开启政治世界秘密的钥匙,并且使支撑政治现象的实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当苏格拉底强调灵魂的牵挂、霍布斯强调人的利己主义、边沁强调快乐和幸福的实质、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时,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探求表面混乱背后的明晰性”。[3](P1)在他看来,经济因素在马克思那里是决定政治现象的东西,或者说经济是政治现象的本质。克劳浦西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经济是社会的活生生的内核,因而把握了现代经济的真相就理解了现代社会绝大部分的重要事实”。[4](P402)他们所代表的观点是对马克思通行的理解。一方面,他们把握了马克思论断的实证性特征,即在马克思作为范例来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经济因素的确取代了人的主观谋划而成为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并未理解马克思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从而忽略了马克思不是要把资本主义物化特性绝对化,而正是要在批判这种特性的基础上诉求超越性目标。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偏离了唯物史观深刻的批判意蕴,停留在以历史事实校对理论诉求的水平上,也缺少对唯物史观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认真探究。与之相反,埃尔斯特力图对经济基础解释上的优先性作更为细致的分析。
埃尔斯特首先要解决国家政权的概念自主性问题,即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能否与经济基础特别是与所有制在概念上区别开来;第二个问题是,在国家政权具有概念自主性的前提下,它具有解释自主性吗?即国家政权结构和政策是否能够不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所解释。埃尔斯特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一、国家政权的概念自主性
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所有制形式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法律规制而不能与上层建筑相分离的。在此,所有权被国家政权所支撑并由此而前置了政治体制。国家政权如果能够被经济基础所解释,则政权和经济结构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分离的实体,这样才能从逻辑上建立起二者之间因果性联系。那么,一种不能与上层建筑相分离并且由上层建筑来配置的现象(所有权)如何能够作为独立的变量来解释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及相应的法律体制)呢?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上层建筑通过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来获得解释的命题所受到的第一个质疑。
柯亨的解决办法是在权利和权力、法定状况和实际状况以及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作出区分。特别地,他在财产法定所有权和有效控制之间作出了区分。[5](P226-230)按照柯亨的理解,法定权利、所有权和财产关系概念是对现实权力、财产实际有效控制状况和生产关系的反映和适应;因此,经济结构可以被财产实际有效控制关系所界定,而财产实际有效控制关系则功能性地进入到对所有权法律关系的解释中去了。
那么,柯亨的解释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我们看不同时期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有这样的论述:“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6](P134)“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体系迫使议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这种认可”。[6](P191)这表明法的关系是对既在财产关系的确认,并且这种确认表现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种迫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到:“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7](P831)这描述一个历史事实:占有财产的人直接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来进一步扩充自己的财产。就土地所有者正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立法主动权的事实来说,这是法的关系对财产关系的被动适应;就法律使进一步的掠夺合法化来说,这是法的关系对财产关系的主动配置。但是,由于前一个事实决定了后一个事实,所以财产关系对法的关系仍然具有解释的优先性。可见,柯亨的解释基本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是,就以上所引文本,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二者的重大区别:马克思主要以占据统治地位的财产动态流转方式解释法的关系的形成;柯亨则着重从既定的所有制状况来解释法的关系的形成。在柯亨的静态理论视角内,从一种法的关系向另一种法的关系转变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唯物史观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柯亨把财产实际有效控制与法律上的所有权静态对应的解决思路受到埃尔斯特的质疑。在后者看来,存在着不必甚至不能被法律关系所巩固的独立的对生产力实际控制。比如,作为生产力的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并不能通过被法律公示的方式获得独占权,否则只能导致自我挫败,因为从法律上确认独占权就要公示这一信息,而这一行为无异于使他人免费获得了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经济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并非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静态对应,尽管在专利制度中专利权必须通过法律确认的方式才能获得。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埃尔斯特认为,柯亨以法的所有权关系反映和确认实际财产控制关系来论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是有缺陷的。再者,国家政权的完整概念既包括政治系统的结构,也包括这种结构实际上做出的决策,而“在后者当中,一些采取了制定法律的形式,而另外一些却没有;在被制定的法律中,一些牵涉到所有权形式而另外一些则没有”。[8](P404)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把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在逻辑上分离开来。可以看出,柯亨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来解释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并进而扩充为通过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解释上层建筑的性质。但是,埃尔斯特却通过指出财产实际控制状况与法定财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的脱节,指认了柯亨论证中的缺陷。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写到:“同直接生产者直接相对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亚洲那样,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国家,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任何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9](P894)在此,马克思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家政权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引出了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的第二个质疑: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下,租金和税款是直接一致的,政权和经济结构是直接一致的,亦即政权和经济结构是无法分离的,那么政权如何被经济结构所解释呢?既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不构成独立变量,它也因此满足不了作为解释项的条件。
埃尔斯特认为,上述困境并不构成两个概念分离的障碍,因为仍然存在二者相分离的三种途径。第一,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被完全不同的人群所支撑。比如在古希腊,生产活动大体上由奴隶来进行;贸易活动由自由的非公民来进行;政治活动由公民来进行。第二,这两个领域可以被看作由不同的角色系列所承担,比如马克思曾经论述说:“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10](P149)在此存在如下可能性:一个人在有关领域如何行事解释了他在另外领域如何行事。比如,控制的政治关系可以被剥削的经济关系所解释,即使同一个人参加了这两种性质的活动。第三,既定行为可以既具备经济方面又具备政治方面,比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政体。埃尔斯特借助于柯亨的研究成果认为,一个政策的经济方面或经济后果的确可以进入到对同一个政策的政治方面的解释中去;同一个行为的经济方面或经济后果可以进入到对这一行为的政治方面的解释中去。[8](P404-405)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存在着把经济结构与国家政权从概念上划分开来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政权和市场经济行为的分离,从概念上把国家政权和阶级利益混淆起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埃尔斯特对国家政权概念自主性的确认为他对国家政权解释自主性的确认提供了逻辑前提。
二、国家政权的解释自主性
埃尔斯特认为:“当(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国家上层建筑和政策不能够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所解释的时候,政权具有解释自主性”。[8](P405)在唯物史观视域内人们通常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它为统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服务;在阶级社会,即使国家承担某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它也从属于阶级统治特别是经济剥削职能。很明显,埃尔斯特试图通过对国家政权解释自主性的确证来反思这样一种“常识”。
让我们首先考察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权的相关论述。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谈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时认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11](P356)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此的确把资产阶级国家定义为阶级统治工具。但是,这并非是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权性质的唯一论断;相反,考虑到这是马克思在法国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所作的观察,我们还应该考察马克思对国家政权常态运行时所表现出的性质和职能的探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社会化劳动过程时认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9](P431-432)这里实质上把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在经济过程中发挥的职能分成了两类。其一是具有公共事务管理性质的职能,这种职能在任何一种社会化劳动过程中都会产生,一般也使经济活动参与者整体受益;其二是建立在社会对抗基础上的具有阶级统治性质的职能,这种职能为阶级社会所特有,是为阶级统治服务的。可见,马克思并未单纯地把国家政权看成是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的,它还包括社会公益的重要一面。但是,马克思无疑强调的是其从属的一面。这是因为在其语境中,阶级社会国家政权公益性的一面有利于巩固阶级统治;另外,即使国家政权对某个统治阶级来说具有自主性,它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也不具有自主性,就像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贵族建立的联合政权服从于他们的共同利益一样。
埃尔斯特则试图把马克思对国家政权公益性职能的论述扩展、深化和细化。他想证明的是,国家政权结构及其政策有时不能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所解释,亦即国家政权具有“解释自主性”。从埃尔斯特对国家政权“解释自主性”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他并非要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权阶级属性的论断,而是尝试证明,(a)国家政权结构和政策有时可以在其他利益序列中得到解释,比如统治集团的利益或者作为整体的社会利益。需要指出的是,统治集团不同于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它仅仅指参与统治决策的人的集合。比如,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家有时采取代理人统治的形式,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或者代理集团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引导国家政权的结构和政策。(b)国家政权的行为有时可以作为官僚体制内部决策机器的输出结果得到解释。[8](P404-405)比如,官僚体制通过日常运作流程和商谈程序制定政策,而这些流程和程序具有重要的形式特征,它们本身并不预定要实现任何被恰当界定的利益,包括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从埃尔斯特整个论说语境来看,他试图把个体理性选择理论引入马克思政治理论。比如,当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代理人统治形式的时候,作为代理人的官僚机构的决策者和作为被代理人的资本家之间便存在着博弈行为:资本家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代理人则根据资本家为了满足不直接统治的意愿所能够付出的代价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种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可能影响政权结构和政策走向。另外,在埃尔斯特的语境中,商谈行为也是一种博弈行为。因此,商谈参与者在法定框架和程序内也通过种种策略的采取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同样可以影响政权结构和政策走向。
三、生成国家政权自主性的机制
从以上分析看出,国家政权和阶级利益可以在范畴上相互分离,这就形成了它的概念自主性;国家政权能够不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经济利益得到解释,这就形成了它的解释自主性。问题在于,埃尔斯特如何在不否定马克思关于群体利益(包括阶级利益)对国家政权具有重要影响论断的前提下主张国家政权自主性呢?
我们首先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代议制的有关论述。最为简要地反映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是马克思关于选举的论述:“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12](P289)这在经济基础和政权性质之间建立起了最为直接的因果关联。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谈到法国工人革命的性质时认为,“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谓的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12](P94)在此,马克思把代议机构看成是进行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力的工具;它没有独立存在的资质,也就谈不上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抗衡。在这个意义上,议会只不过是行政权的延伸而已,二者都是为阶级统治服务的。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马克思则提供了政府和议会尖锐斗争的实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12](P117)这里蕴含的判断是,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或个人之间也有博弈行为,而这种博弈行为也会影响国家政权结构和政策选择。埃尔斯特并未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发现这一判断,但他的分析工作无疑使之显性化和充实化了。
埃尔斯特认为,群体利益塑造政策具有两种途径。第一,特定群体把自身利益作为政策选择的最大化目标;第二,特定群体把自身利益作为政策选择的限制性条件。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权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换句话说,国家政权选择行为的可行性目标范围都受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是掌握权力的,这种权力的表现就是约束国家政权政策选择的范围。但是,埃尔斯特认为,“权力也包括界定可选择政策的序列和把限制施加到可行序列上去的能力”。[8](P406)埃尔斯特的意思是说,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国家政权提供了可选择政策的模糊集合{a,b,c,d,e……},这是它的权力表现。随后,在资本主义代议制下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就要进一步从这个集合中界定出可行的政策集合,比如{a,b,c};直到最后,挑出最为可行的政策,比如a,这是国家政权相对于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来说的自主性权力表现。
那么资本为何不想拥有权力呢?埃尔斯特认为,如果以A代表资本,以B代表政权,以C代表工人阶级,则三者可以处于下面的意向性网络中:第一,由于存在发生劳资矛盾的普遍理由,A和C卷入了相互斗争之中。结果是,C倾向于反对拥有决定性形式权力的任何人,A则力图把工人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A来说,B拥有形式权力是较好选择,因为C的部分注意力和能量会部分地指向B。第二,A认识到,假如他掌握权力,他将被自己的短期获利所驱动去做出决定。他还认识到,如果让这种权力处在自己不能触及的安全地方,就有可能避免这种结果发生。从A追求长期利益的角度来看,让B根据B的利益来做出决定是较好选择。虽然B未必根据A的长期利益来做出决定,但是在A的牵制下,这样的结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接近。第三,假如A不得不投入时间去制定政治策略,那么留给他追求私人利益的时间就会减少。也许,A的利益会被其他行使形式权力的人所破坏,但是这种破坏并没有他自己直接承担权力所带来的损失那么多。第四,B认识到,对于A来说,参与到政治中去就像是一笔昂贵的投资,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获得收益,却要求当下的支付;假如A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利益在当下是获得充分尊重的,他便可能不会为了将来更大的预期收益去付出掌权所需要的成本。于是,B便会一方面恰到好处地尊重A的利益,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使掌权的成本高昂,使之成为对A有效的遏制力量。[8](P407-408)
可见,埃尔斯特反对只把金钱和强力甚至暴力作为政治权力仅有源泉的狭隘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或者说资本是政权的操纵者。他认为,个体或群体在战略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也可以成为政治行为者权力的基础。比如,在历史上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曾经把贵族推上政权舞台,而这与后者实际支配的积极资源几乎没有联系,因为当时贵族既不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也不掌握暴力机器。再比如,一个政党也可能由于碰巧处于两个主要政治集团斗争的枢纽地带而获得执政权。在这些情况之下,权力产生于政治系统本身而非前政治性的资源,比如金钱和强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埃尔斯特把政权所拥有的权力和金钱、强力等前政治资源分开,从而认为政治系统本身可以自主性地衍生权力。
针对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即使在埃尔斯特所列举的情况之下,国家政权仍然是以金钱和权力为主要基础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另外,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没有实际地掌握权力有时是它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并非由于它们没有获取政权的能力。简单地来说,政权的自主性仍然是通过阶级利益得到解释的。对此,埃尔斯特提醒我们分清政权自主性的获得和政权决策这两个范畴:即使政权的自主性可以通过阶级利益来得到解释,或者说政权的自主性正是来自于阶级利益,这种事实也不会改变政权自主性的性质;因为政权本身所做出的决定并不一定可以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利益来得到解释。在事实上,政权的绝对优势和资本的绝对优势都是极端的情况,经验的历史状况往往是处在这两个端点的中间状况,而政权自主性的大小则取决于情势和上述博弈状况使天平倾向于哪个端点。
从埃尔斯特的理性博弈立场分析,具体到资本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资本可以通过包括投票、商谈、游说等机制把自己的利益作为政权政策选择的最大化目标或者限定政权政策选择的范围;国家政权则具有在可行的政策序列之间进行正式选择的权力以及把来自资本的限制施加到可行的政策序列上去的能力;而后,资本又具有在这些可行的政策序列中排除其中的一些选项的权力。从传统的资本主义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过程中,政府或者说政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它们的在形式上所行使的权力只不过是资本意志的执行。在此,埃尔斯特在什么理由上把政权所行使的权力和资本所拥有的权力在性质上等同起来呢?在埃尔斯特看来,政权固然要避免刺激资本去自己行使权力,固然要避免杀死资本这只可以产下金蛋的鹅,因而固然要避免越过一定的界限。但是资本又何尝不是被自己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亲自掌权的理性考量所限制呢?因而,资本和政权都拥有受到对方限制的权力,这两种权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政权和资本所拥有的权力在数量上则不必相同,这是因为,资本和政权对权力的塑造结果的分配取决于资本厌恶行使权力的力量,也取决于政权避免伤害资本的必要性。因此,资本和政权谁拥有的权力较多这应当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验前的问题。换句话说,资本并不必然地支配政权,政权并不必然地匍匐在资本的脚下,反之亦然。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二者所处的社会情势和二者的博弈过程。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这也应当是一个商谈的结果,固然其中有着策略行为。埃尔斯特对国家政权解释自主性的确认,以理性选择理论把马克思在政治著作中偶有涉及的意向性分析规范化了。
由于不同的理论和社会背景,埃尔斯特和马克思对国家考察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基础具有重大差别。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他对异化与剥削的憎恨以及对一个更好社会的渴望所导引。然而,埃尔斯特的理论分析是没有关于未来社会价值负载的,理性选择理论契合于当代市场社会,在其中工具性价值几乎是所有人的最佳选项。也许,埃尔斯特忽略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潜力以及人类在道德、制度和社会规范领域的学习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尔斯特的理论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物化意识的产物。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叶汝贤.唯物史观发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3]Geraint Williams.Political theory in retrospect:from the ancient Greeks to the 20th century[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1.
[4]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Jon Elster.Making Sense of Mar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On Elter’s Analysis of Marx’s Theory of State
MA Jun-ling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Dongguan,Guangzhou,Guangdong 523808,China)
As the standard of clari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rigor of argument, Elster employs some conclusions and methodologies of modern psychology,sociology and economics to analyze and reconstruct Marx’s theory of state.Elster holds that state has conceptual and explanatory autonomy and undertakes systematic explication of autonomous mechanisms.Elster’s views are instructive for us,but perhaps he has disregarded potential rationality of the life-world an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ability to learn in the realm of morality,regulations and social norms.The abuse of rational-choice theory makes his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partly the product of reified consciousness.
Elster;theory of state;conceptual autonomy;explanatory autonomy
A81
A
1000-2529(2010)04-0022-05
2010-04-07
马俊领(1972-),男,河南上蔡人,广东医学院社科部讲师,博士。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