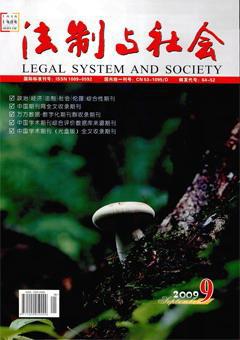开设赌场罪的司法适用释疑
施志刚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其中第18条规定将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修改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①
2007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开始施行。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新增了“开设赌场罪”罪名,从而将“开设赌场罪”从“赌博罪”中剥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新罪名。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修正,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持续超常规增长,但精神文明建设并未实现同步跨越,相反,物质生活的富裕,伴随的却是近年来赌博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危害日见严重,尤其是开设赌场的犯罪分子,往往能通过赌博犯罪活动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有的从形式上已转化为巨大的合法财产,甚至有的涉黑、涉恶犯罪集团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完成资金上的原始积累。而原有的刑罚设置和执法司法的打击乏力,使得刑法的修订成为必然。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采用修正案的方式对赌博罪予以修改,将其单独成罪,并加重刑罚力度。
自开设赌场罪罪名确立并用于司法实践以来,该罪名的司法适用与日俱增。有资料显示,实践中的涉赌犯罪7件就有6件属于涉嫌开设赌场犯罪,而只有1件是涉嫌聚众赌博的赌博犯罪,由此可见一斑。②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开设赌场罪、如何区分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以及如何认定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仍然是三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亟待厘清。
一、如何认定开设赌场罪
依据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开设赌场罪脱胎于赌博罪,其犯罪构成与赌博罪的犯罪构成在主体、客体以及主观故意方面一致,但在主观目的、客观事实方面存在一定的争议,甚至是显著差异。
司法实践中,认定开设赌场罪的第一个争议是开设赌场是否需要以“营利为目的”。有人主张,修正案已经把开设赌场行为单独列出,且前面并没有附加目的,因此开设赌场行为应不局限于“以营利为目的”,对以非营利为目的而开设赌场的行为也应追究刑事责任。对此笔者不敢认同。姑且不论在现实中是否有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开设赌场的“公益”行为,③仅从语义上看,修正案虽然把开设赌场行为单独列出,是为了增加刑档和方便表述刑档,其表述结构“开设赌场的”仍然与“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的表述结构一致,属秉承同一语境下的省略表述,如此表述方能与修正前关于开设赌场的表述一致,即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的开设赌场行为方能予以刑事处罚。
另外在两高《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如此也可以看出开设赌场罪必须以营利为目的方能构成。
认定开设赌场罪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于开设赌场罪是属于实行犯还是营业犯?现实中,开设赌场是为了经营营利,一般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持续性的行为。开设赌场的行为人主观上就预订要反复实施经营赌场的营业活动以获得利润。因此,开设赌场罪与刑法理论中的营业犯,即以营利为目的意图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有形式上的共同点。但是两者有根本的区别,营业犯是集合犯的一种,其本质是行为人具有实施不定次数的同种犯罪行为营利的犯意倾向,虽然实施了数个同种犯罪行为,刑法规定仍作为一罪论处,即是法定的一罪。而开设赌场罪的营业活动虽具有反复性、持续性,但是是作为经营赌场行为的整体来看待的,无论经营一个赌场多长时间,也只是一个经营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应当评判为单纯的一罪;而开设、经营数个赌场,也仍然是一个经营行为,并不构成开设赌赌场罪的同种数罪。
因此开设赌场罪应属于实行犯,只要犯罪嫌疑人开设了赌场,并实施了聚众赌博,坐庄抽头营利等行为,哪怕只有一次(一天、一晚)就被抓获,也已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当然在实际办案侦查中,此时要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内容就至关重要,必须准确认定其主观故意是为了开设赌场,而不是临时性的聚众赌博等或其他故意内容。
开设赌场罪的第三个争议焦点在于如何从中区分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行为,还是以博采为目的娱乐行为。对于一些赌具兼具赌博和娱乐两种模式的时候,如一些具有赌博机色彩的游戏机,以及日常人们熟悉的打麻将、斗地主等方式,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让人不是能很清晰的分辨开来。总体而言,这可以从赌场开设的地点、时间、赌博方式、赌资数额、营利数额、开赌人员构成以及参赌人员构成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
现实中的赌场一般都设立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最多是半公开,④时常伴有一层合法或娱乐的外衣,如在批准营业的游戏机室内“挂羊头卖狗肉”,或假装是一般的博采娱乐等。赌场开设的时间一般都集中在下午或晚上,甚至是深夜时分,一般具有准时性、连续性。赌博方式一般都会选用当地人所共知的方式,如广州地区最常见的赌博方式就是以纸牌“打三公大吃小”,当然也有基本全国通用的方式,如玩骰子、打麻将、斗地主等等。最能将赌博和娱乐区分开来的属于赌资数额和营利数额。赌场中的赌资数额、营利数额一般都远远超出了开赌、参赌人员正常的合法收入,这一点,结合开赌、参赌人员构成以及当地同身份地位人的合法收入进行对比就一目了然。另外从开赌、参赌人员的构成也可以管中窥豹,一般开设赌场的人员都有明确组织、管理等分工,属于团伙共同作案。单个自然人开设赌场的极端案例虽不是没有,但在现实中由于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一般都只能局限于提供场所,仅抽头渔利的情形。而赌场参赌人员往往是得知有赌场可以参赌,自动或被邀请而来,相互之间一般并不熟悉,仅仅是认识开赌或参赌人员中的某一人或某些人,甚至一个人都不认识。这点与以博采为目的的一般群众娱乐决然不同。
二、如何区分开设赌场罪和赌博罪(聚众赌博)
聚众赌博的赌博罪,根据司法解释,其应该属于情节犯,而非实行犯,即聚众赌博的赌博罪必须达到起刑点规定的追诉情节,才能定罪处罚,而达不到相应情节,只能作一般违法活动进行治安处罚。这与开设赌场罪属于实行犯的规定大不一样。因此,聚众赌博的赌博罪没有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等犯罪停止形态,但开设赌场罪有上述犯罪停止形态。
现实中开设赌场的形式纷繁复杂,结合司法实践,可以依据开设赌场的行为人是否为参赌者简单地划分为两种情况去把握。一是目前多数开设赌场行为人自己为庄家,接受参赌者财物投注,通过获胜几率上的差异而赢取多数参赌人员的财物,实现其营利的犯罪目的。如赌博游戏机、网络赌球、“六合彩”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二是行为人只提供场所与服务,通过抽头、收取佣金或收取高额的场地费、设备使用费来实现其营利目的。如有些赌博性质的麻将馆、棋牌馆就属于此类。
因此笔者认为,开设赌场,不仅仅指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更是指开设者(及其帮助犯)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组织,该组织的目的在于通过开设赌博场所(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分散的数个),实现非法营利。因此,开设赌场罪与聚众赌博的赌博罪最大的区别在于开设赌场罪具有更加明显的组织犯罪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区分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看赌场由谁所有、受谁控制;二看赌博场所是否相对固定;三看赌场存续时间是否相对稳定;四看参赌人员是否相对固定。五看赌博方式由谁设定;六看赌具由谁提供。⑤
但笔者认为,“开设赌场”主要看行为人是否对赌博活动、场所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聚众赌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召集、招揽他人参赌的行为。至于场所、存续时间、赌博方式、赌具、坐庄等因素是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参考因素,不是决定因素。刑法修正案另设开设赌场罪是因为开设赌场的社会危害性大,有加大打击力度的必要。如果将这么多的因素设定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条件,必然会出现许多“疑似开设赌场”,给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带来困难,也违背了立法的初衷。笔者在司法实务中就有遇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为逃避打击,基本将赌场开设在偏僻的农舍或旅店,且经常更换地点,但他们有比较严密的组织,“老板”下面有专门负责发展赌徒的,有专门负责接送赌徒的,有专门负责赌场餐饮的,有专门“望风”的,有专门“放数、收数”(放高利贷)的,有专门“抽水、派牌”的,有专门“护场子”的(负责赌场秩序和安全)等等人员。像这种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牢牢掌控赌场的行为人显然应该构成开设赌场罪。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上述案例中,开设赌场的“老板”等人极有可能既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也涉嫌构成聚众赌博的赌博罪,那究竟是应该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处罚?笔者认为,在上述案例中,既不能适用数罪并罚,也不是一般的吸收犯关系,而应该是想象竞合犯关系,原因如前所述,开设赌场必然包含“聚众赌博”,行为人开设赌场是一个行为,不是营业犯、连续犯,而是实行犯。
当然,如果有证据显示,行为人一边开设赌场,另一边又在不同的场所临时性的聚众赌博,这时的行为人将其开设赌场的行为和聚众赌博行为已经分开,就应该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按照开设赌场罪和赌博罪并罚。
三、如何认定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共同犯罪问题)
如前所述,开设赌场罪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开设行为人的组织性。有组织就会有共同犯罪,因此共同犯罪也是开设赌场罪的一般特征。⑥在此有必要对开设赌场罪中的共犯问题进行探讨。
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一般按照角色分类,有“老板”(组织者)、“庄家”、“抽水”、“派牌”、“放数”、“收数”、“望风”、“看场”等人员,如果是以赌博机开设的赌场,一般除了“老板”,还有专门的“收银上分”、“兑分”、“放机”、“查分记帐”等人员,除此以外,赌场甚至会有负责提供饮食以及打扫卫生,保养机器的工作人员等。⑦
对上述人员按照共同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大致进行分类,“老板”一类的人肯定属于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是主犯。但对其他人员的共同犯罪认定确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依据司法解释,只有“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因为开设赌场也是以营利为目的,只有“只有当行为人个人的获利与赌场的经营利润实际挂钩或密切相关,以至于行为人热切盼望并积极推动赌场营运获得利润时,行为人的行为才可被评价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行为”。而“对于受人雇佣,在赌场内从事特定工作的人,如端茶送水、操牌、兑换筹码、接送赌徒、望风的行为人,虽然在客观上,其亦为赌场的经营营运提供了帮助,但是主观上其更直接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固定的报酬,对于赌场的营利,其通常没有明确追求的态度,因而不应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⑧
笔者认为上述认定过于狭隘,有放纵犯罪的嫌疑。诚然上述坐庄派牌、兑换筹码、接送赌徒、望风看场、放数收数的行为人在现实中往往仅接受的是赌场组织者的雇佣,“薪水”一般都是固定的,其主观上对于赌场的营利,通常没有明确追求的态度,但上述人员的存在,从实际情况看,往往赌场组织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是由上述人员各自负责洗、发牌以及抽水等工作,实际上维持了整个赌场赌博活动的正常运行,对开设赌场者起的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帮助的作用,又明知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应按开设赌场罪共犯论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侦查机关能抓到的就是这些维持了赌场正常经营的“帮助犯”,正是这些人的存在,导致赌场组织者往往逍遥法外,如果对这些人都不加以惩处,那么在司法上要认定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就更加困难。
当然,对一些在赌场中起的是非决定性的帮助作用的人,如打扫卫生、端茶送水等工作人员,其地位和作用基本上与赌博活动不相关,对这些人如无特殊的分红等与赌场营利直接相关的证据,应不宜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以免打击面过大。
另外在现实中,还有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的行为值得探讨。一个就是提供赌博场所的“房东”,如“房东”直接就是赌场的组织者,那涉嫌犯罪勿庸置疑,但如“房东”仅仅为了场地费而提供赌场场所,是否一定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呢?笔者认为,如有证据证实,“房东”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提供场地,收取场地费,应涉嫌构成共犯;反之,则不构成共犯,除非场地费高得出奇,远远超出了正常值,可以推定“房东”知情并参与共同犯罪。其次在现实中,有些赌场组织者并没有组织“放数”人员在赌场放高利贷,而是有“放数”人员不请自来,此时该“放数”人员并不从赌场组织者那里领取报酬,而是以自有赌资通过放高利贷给赌徒营利,此行为是否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呢?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放数”人员并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宜认定为“以赌博为业”的行为,涉嫌构成赌博罪,而非开设赌场罪。最后在现实案例中,还有执法、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对管辖范围内的赌场“查而不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此类人员应按照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对甚至定期接受赌场组织者的分红,在查赌过程中为赌场通风报信,使其逃避打击的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应按照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和开设赌场罪共犯的规定数罪并罚。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赌博犯罪仍是一个相对高发的犯罪。自开设赌场罪独立于赌博罪以来,开设赌场罪的司法适用与日俱增,但相关争议也持续不断,严重影响了该罪名的认定与适用。本文结合办案实际,通过对开设赌场罪司法适用上的三个相关疑难进行剖析,期许统一认识,并在办案实践中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