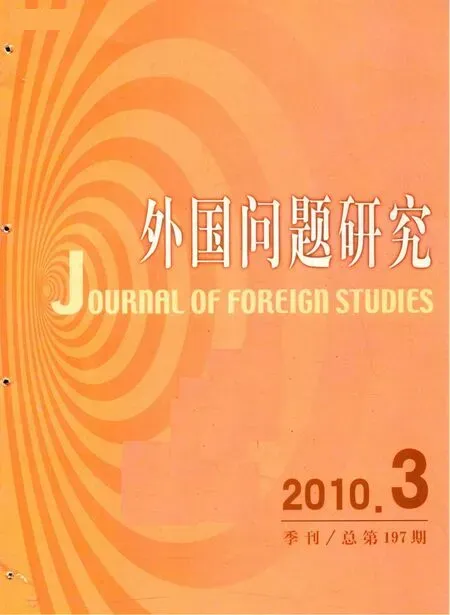日本汉字的近代演变、动因及启示
赵守辉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新加坡637616)
日本汉字的近代演变、动因及启示
赵守辉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新加坡637616)
本文在参考现有国内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日本汉字存废和限制用字的历史过程及最新进展。日本历史上的文字改革始于明治维新,二战以来限制汉字使用,普通常用汉字被严格限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并且在数量上长期保持稳定。近年来则由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日本汉字规范化过程的特点和困难,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以期为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汉字现代化和标准化工作提供参照。
日本;(汉)字表;明治维新;二战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出现多篇文章探讨日本汉字的规划和使用。这些研究对汉字政策具体方面的论述已经相当细致透彻,如姓氏用字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1][2][3]。但这些学者的工作多具有针对性,对其影响和意义的社会历史动因鲜有深入讨论和全面的考察。中国在经历50年代的简化和整理完成后,汉字问题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引人注目者如80年代的汉字文化之争程度之激烈,参与者涉及之广泛与复杂,颇为罕见,影响深远。此后表面上偃旗息鼓,但风云变幻,争论从未停止,比如呼吁恢复繁体(或“识繁写简”)的声音时有所闻。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日益呈现宽松与容忍,汉字问题近年来再次受到学者和社会的关注。一方面是在国内,国家新的语言文字政策的出台不时成为媒体热点,另一方面在海外,随着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经济影响力及软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全球及地区一体化过程的加速,汉字文化圈地区的有关汉字的使用(如字量的增减及字形的标准化)的研究和争论的报导与日俱增。东邻日本是汉字在境外的主要发展地区,其汉字使用和改革政策一直为中国学者和民众所关注。我国汉字重大基础建设工程《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2009年8月发布后,引起热议。日本的汉字改革经验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从历史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日本汉字政治化的发展过程,无疑具有史鉴价值。
二、日本文字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现状
日本的近现代文字改革运动大体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始于标志日本现代化开始的明治维新时期,到1946年《当用汉字表》的公布与实施,才宣告了80年来关于汉字存废之争从讨论进入落实阶段;二是文字现代化运动发起后,汉字的命运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呈现了一个S型发展轨迹。先是19世纪末甚嚣尘上的汉字废除论,进入二战,一部分保守派将汉字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和大和精神相联系使其得以保存,进入短暂的存废相持阶段。战争结束后,由于对战败的反思使存废之争再起,最后是限制汉字派占了上风,减少汉字的路线得到落实,日本的书面语生活进入以汉字定量为特色的假名汉字混同期;第三个特点是人名用字规范的重要性。1946年日本政府颁布《常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用法》后,进入定量使用汉字的平稳发展阶段,此后的文字改革运动多是受人名用字宽严之争的讨论所驱动。
(一)汉字在日本的命运变迁
汉字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惠赐进入日本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日本在汉字未传入之前本无文字,这一观点早在公元9世纪时便存在。但文化界国粹主义鼓吹“固有文字存在说”,沉迷“神代文字”①神代文字是指日本史前时代的文字(“神代”即日本史前时代),散见于一些神社典藏书籍以及碑文、宝镜之上,鲜有正式文献。从字形看,神代文字多数是仿照出现于15世纪朝鲜语的谚文。二次大战时曾被部分右翼学者宣传为日本最早的文字,意在表明日本早于史前已拥有独立文化,但现代日本学者一般对神代文字均持否定意见,甚至视为虚构。,以此证明日本文化并非在汉文化中孕育,但反汉学的思潮从来未能广泛蔓延。多数严肃的日本学者视其为虚构历史,而承认日本有文字是约在公元3世纪末叶,即284年王仁从百济渡日,献《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此后中国古籍十之七八都传入日本。自汉字输入日本后,至8世纪中叶,日人始用汉字楷书和草书偏旁,创造片假名与平假名,以为标注汉字及日本语音之用。假名即假的文字,同朝鲜世宗大王创造谚文后的情形一样,多为妇女所用,故当时称汉字为男文字,而称假名为女文字。汉字不仅方便了一般学者著书作文,官方记录史实也必须使用汉字。虽然自公元9世纪初叶以后,有书籍开始采用假名记述,直至明治初年,汉字一直作为日本正式文字,假名难登大雅之堂。这是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在日本发展的大致脉络。对日本汉字的发难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江户时代,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的杰出政治家新井白石提出西方的表音文字优于中国的表意文字。但直至明治维新时期,这种零星个人批判才发酵为大规模的反汉字运动并达到高潮。决定了与汉字乃至中国文化的决裂。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化惯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动因可简括为如下两点。
一是同汉字在本土的存在方式一样,作为交际工具的汉字同时兼具标识社会地位的价值。汉字的这种阶级标志属性在日本表现尤其明显,它的精英性质在明治维新反思传统时首当其冲,使其从引进的文化精华变成了国家现代化的负担与障碍。此外,维新运动也催生了反思本土的“国学派”思想主张与国家主义的文化立场;但更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第二个动因,即中华帝国自身衰落的因素。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日本文化界开始鄙视和疏离汉字文明。然而,汉字深植日本文化,文化界和政府对废除汉字的条件和程序缺乏共识。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叩关”,“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以大举引进西学,崇尚欧美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运动加速了汉字在日本的衰落。甲午战争更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国语论达到高潮②据统计,在甲午战争取得胜利的1895年,日本文化界讨论“国语国字论”的文章量一下子猛增到32篇,明显高于其前后的年份。[4]。发生现代派与历史派之争。在改革思潮中,一部分精英认为在语言中找到了西方发达的真谛,有主张以西洋语言(如法语、英语)代替日语者,新造文字代替汉字就更不在话下了,需要争论的就是以哪套文字取而代之。
走向崇洋思想的极端是放弃国语说,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驻美外交大臣森有礼。1872年他发表公开信,希望以简化英语变成日本的语言,并批评日语是“无法通用于日本列岛之外的贫乏言语”,理应废除。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被誉为“日本现代小说之神”的志贺直哉在1946年4月发表《语言问题》时论断,明治时代因没有采用英语,妨碍了国民吸纳文化,他当时进一步建议,日本应采用世上最漂亮的语言——法语作为官方语言。转用外语说看似匪夷所思,在当时也少有支持者,但至今仍有市场。直到上世纪末,时任总理的小渕惠三(在中国媒体上一直被误写作“小渊惠三”)曾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制定日本21世纪发展远景规划,目标之一便是将英文作为第二国语。
改革大潮涌动之时,新旧文化交替,对立思想激烈交锋。另一方面,在对汉字的一片挞伐中,汉字的坚定维护者也不乏其人,并且是最掌握话语权的一大批贵族支持者。正如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在前岛密提出改用假名时所批评,这些人掌握汉字知识,朝廷上下以至士农工商都要听命于他们,若废除汉字,无异于打倒贵族。汉字维护者的理论根据是,他们质疑假名派或罗马字派忽视日语同音字多的事实,从汉字消减歧义的贡献看,日本根本就是汉字之国。汉字不但没有阻碍日本现代化,当时正是汉学带领日本走向维新①明治维新时期海量的西方观念是依靠汉字词汇进入日语的,所以当时的调查证明,与此前的江户时代相比,此时在对汉字危害一片情绪高涨的声讨中,汉字的使用反倒大幅度增加了。[5]77,支持明治维新的几乎全都是汉学出身就是证明。即使是伊藤博文,在办理洋务时也是以汉学为根。特别是他们把天皇权威、忠君仁孝与汉学连成一线,指否定汉学等同动摇天皇权威。这种论说触动了日本社会的神经。当时日本天皇的诏书仍是以汉字书写,废汉字派力陈平、片假名或罗马字好处不遗余力,但对于昭敕上的汉字一直避免,这成为日本在20世纪前汉字改革方面少有实质性举措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脱亚入欧的首倡者福泽谕吉②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在其所著的《脱亚论》中,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提出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吸收西洋文明。被批评为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也认为需要3000个汉字以应付日常之需,他1873年编写的小学教科书《文字之教》里仅用了802个汉字。
(二)二战后汉字改革的新起点
总括前文,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日本民族意识抬头,伴随着儒学转衰的是和学兴起及西学的传入,日本人开始思考汉学的优劣和危害,汉字命途由是多舛。汉字由“正政之始”和“经艺之本”,变成了“学生的地狱”③视力检验表和色盲表的发明者石原忍(1879-1953)语,他甚至将日本的近视多发归罪于汉字。和“人民的公敌”。自前岛密于明治初年上书请求废除汉字后,日本社会虽然普遍认同文字必须改革,废除汉字的论调层出不穷,但汉字毕竟已深植于日本文化之中。为考察究竟选择怎样的一条文字路径,日本政府于1902年成立以废除汉字为宗旨的日语调查委员会,这一般被视作近现代日本汉字改革的开端。该调查委员会1934年重组为“国语审议会”,作为国家常设语言规划机构一直有效地运转到本世纪初。
(1)政策的确立——政治的参与
毕生关注中国文字现代化的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DeFrancis,1911-2009),在其名著《汉语:事实与虚幻》(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Fantasy)的整个第一章中,简述了他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份东京图书馆绝密手抄文件:日本在二战初期,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并进一步在文化上统一帝国领地,东条英机特组织了一个由日、中、越、韩学者秘密组成的四人语文委员会,研究决定未来世界的统一文字系统,特别是如何创造出以汉字为基础的书写体系,用以代替腐朽的拉丁文字。德范克的原意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虚构的历史,使关于汉字音意关系的枯燥讲解变得引人入胜,但实际上问题极端政治化并非完全虚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日本二战前后的汉字政治中,一直可以看到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影子。1931年6月,日语调查委员会曾与新闻界商定使用其编制的《常用汉字表》,尚未执行,“九一八”事件爆发,每天的战况报道需要使用大量的汉字人名地名,使计划流产[6]145。到1942年再次制定《标准汉字表》,限定常用汉字1134个,准常用汉字为1320。但计划被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以爱国的名义加以阻止。右派精英为了以忠君爱国鼓舞士气,在文化中寻找民族主义的基础,反而推动民间复古热。例如日本军方曾经为维护汉字反对用西语(英语时称“敌性语言”)或假名对译武器及部件名称。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军人集团又以一切为战争服务为由,转而支持汉字的简化和定量④主要是因为兵源的紧张,征召的青年教育程度下降到平均小学四年级,以至连续出现严重的武器零件错订事件。日军当时使用2000多种武器,兵器部件说明涉及四五千汉字,但士兵平均识四五百字。[6]7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便召集包括人类学者在内的专家制定对日本的统治方式,结束二战的《波茨坦宣言》要求必须清除所有妨碍民主发展的障碍[7]。1946年3月,肩负改造日本文化精神使命的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一次考察日本,由这27名专家撰写的《教育使节团报告书》一个主要内容便是陈述使用汉字的弊害,建议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指出[8]142-148,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考虑到采用西文字母为书写系统,对美国监视日语的书信文件更为方便,并且,作为思想控制手段,可以使日本新一代免受以汉字为载体的战前宣传熏染。所以有人揭露美国人的汉字有害论目的在于“使日本人失去战前那样的阅读能力,整个民族的传统被切断,全体人民变得愚昧无知”[9],这种阴谋论也并非空穴来风。更极端言论还有“如今日本既没了关东军,也没了联合舰队,如果再弄到将来连古籍也读不懂了,我们还剩下什么呢?”[6]107。所以,有一些原来主张废除汉字的人被驱赶进了汉字保留派的阵营,这些人的共识是将天皇和日语包括汉字作为国体加以维持与保护。
针对美国占领者废除汉字的“指示”,日本采取以文化事业需考虑民众意愿为借口的拖延策略,以美国式的民主理念顶住了美国一再催促实现日语罗马化的压力。为应付美国关于罗马化要求,而专门成立了国语调查研究所。调查的结果是日本的书面语能力不比拼音国家低,而且罗马字的教学效果也不理想。当时84.3%的小学和48.1%的中学进行了罗马字教学实验。一份1948年的对21008人(15~64岁之间)的调查显示,完全不认识汉字的2.1%(称不完全文盲),不认识假名的1.6%(称完全文盲),明显低于当时的美国和波兰等拼音文字国家[10]。另一个保留汉字的策略也是将语言问题国家化政治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来要走汉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日本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唯一使用汉字的国家[8]146。
可以说日本是以限制和简化的手段使汉字又一次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内阁于1946年公布的《当用汉字表》(包含1850个汉字)就是在这样复杂微妙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了增加其权威性,字表特意由内阁而非文部省公布。但当时对字表性质的认识仍有分歧,很多人把它看作是在废除汉字前一个过渡措施①为了说明与后来的《常用汉字表》相比,《当用汉字表》更具有硬性,国内一些学者通常将“当用”二字解释成具有强制性的“应当、必须”,根据何群雄的研究,“当用”实际为“临时用”之意。[6]102,认为它失之于匆忙和粗糙(从提交到正式公布只用了11天时间),这成为其后饱受诟病和要求反思的原因之一。但无论怎样,这个规范字表与同时公布的《现代假名使用规则》一起,构成了对汉字改革产生最大影响的重大政策之一。此表明确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其中的881个汉字,被当做小学教育期间所应习得的汉字,即所谓的“教育汉字”。这一字表的意义还在于,对其中一部分比较复杂或存在多种写法(即异体字)的汉字进行了简化和整理。其中除了有131个是简体字以外(这些民间流行的常用简化字日本称为略字),其余为传统繁体汉字。这131个略字与中文简体字相同的有53个(如“灯”),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由此可见,日本的汉字简化工作并非如中国那样,对汉字的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化的变更,而仅仅将个别已经流行的简笔字在公布字表时加以整理认可。这种做法此后一直被作为日语简化汉字的一个主要手段[11]。
(2)政策的实施——在争议中跋涉
《当用汉字表》自公布后一直到1981的正式调整,日本的书面语生活虽然保持了相当长的稳定,期间也并非一帆风顺。反对声来自两方面,一是因为限制给语言文字生活带来了不便,还有是对改革本身的不满。后者抱怨说文字改革是由听命于美国大兵的软弱政府搞的,改革有美国势力的背景在里面,是非正常情形下的产物。语言和经济外交不同,它需要全体国民的赞同和执行,使用禁止、限制等手段强制推行绝非上乘的政策。字表在执行初期也曾遇到阻力:出版部门有把不符合限制的稿件退给作者,搞得写作的人很紧张。由于需要死记1850的限制,要严格执行的话,就要背下来,或者经常对照字表,反而造成记忆上的困难,还不如一下子只记住3000字更省事。后来写文章的人就采取全权委托出版社或专业校对员处理的办法。《当用汉字表》规定:“本表没有的字用其他词或假名改写”,这就等于不仅限制了汉字,也限制了词汇。而排斥汉语词,实际上就等于排斥汉语自身。为了具体指出《当用汉字表》的可笑之处,日语问题协会曾编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当用汉字表》:有犬无猫,有鸡无兔,有马无鹿。有松无杉,有桃无栗子,……只准喜欢,不准厌恶,纵有才,亦无智……[6]115。
此外,汉字存废之争在学者中和民间依然在继续。表音派(假名派,罗马字派)把字表看做是正式放弃汉字的准备,而汉字派认为字表的推行意味着对废除汉字主张的正式否定。有时两派争吵相当激烈,曾发生“五委员大闹国语审议会”事件。在1961年的大会上,舟桥圣一等汉字派因为反对审议会长期由文字改革的激进派(包括其同情者及没有主见随大流的人士)所占据,在辩论中途愤然退场。这次事件导致审议会大改组,使汉字改革发展向利于汉字派转轨的分水岭[12][2]39-42。
这次事件影响深远。1962年,国语审议会委员吉田富三表示“国语(日语)是以汉字假名混合表记作为正式规则的。国语审议会在此前提下对国语的改善进行审议”;1965年,国语审议会会长森户辰男于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汉字假名混合表记①《当用汉字表》公布后的“混同书写”主要有假名替换和同音别字替换两种情形,比如:妨碍→妨害。这种以简代繁的方针在中国1977年所实施半年的“二简”方案中也曾大量采用。但这种方式有时也遭遇阻碍。如对这个“碍”字的处理,目前正在讨论《新常用字表》时,日本残疾人团体(目前称“障害者团体”)要求追加“碍”,使“障害者”改回“障碍者”。这与中国“二简”的情形有些相似。人们可以接受“刁刻”和“发”,但不接受“刁像”和“览”。是审议的前提。汉字全废不予考虑。”[2]39-42这样,《当用汉字表》正式公布近20年后,汉字政策才正式稳定下来。此后虽然如前所言,由于字表本身的仓促确实带来一些技术问题,从1946年实施后一直到1981年,在近35年的漫长时间里,字表应民众要求进行过三次微调,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加。1965字表扩充至1866字②在《当用汉字表》中增47字,删31字。该表的第一次修正是在1954年,因为那一次是增28字,删28字,总数仍为1850字,所以有人认为1965年是第一次修订。,然后是1977年颁布《新汉字表试行草案》又增加到1900字(增83字,删33字)。1981年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再次颁布,更名为《常用汉字表》,同时宣布以前有关汉字改革的各字表自动作废,汉字量长期固定在1945个。此时加上《人名用汉字别表》,合法汉字总和为2229字[5]78。
(3)最新的进展——技术成为推力
作为最重要的文字改革文件,《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保证了汉字使用的规范、稳定和高效,历史性地改变了全体国民的书面语生活(graphiclife)。《当用汉字表》的效力当时虽然规定了明确的适用范围和对象(主要为公文和教育领域),实际上受到了社会各界团体和机构的大力支持,这可以看做是日本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从社会学视角看,通过文件公布字表将书写标准官方化为政府提供了社会控制的手段,说明国家对书面语的控制在日本基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值得强调的是,技术和经济因素对政府干预语言生活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书写工具的革命推动书面语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常用汉字表》是随着新的信息技术的降临而出台的,虽然这一用字标准公布后,认可的字量长期基本稳定,但由于技术带来的冲击,使字量的限制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进入90年代,软件公司在处理汉字时并不太理会政府的标准,日本工业标准协会(J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收录的汉字远远超出《常用汉字表》。日本标准协会(JIS)也针对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中所使用的汉字,不断独立制定字符集和数值表达方式(字符编码),称JIS汉字,最初的JIS汉字是于1978年所制定的6355个汉字(包括各种符号为6802字)。第一水准为常用的2965字,第二水准为次常用字3390个。包括此后数次修订的第三和第四水准,现在JIS汉字的数目总数已达12156字。另一方面,“教育汉字”经过1968年、1977年、1989年的追加与改订,现在共计1006字。这样一来,日本现行的汉字定量实际上就形成了三个层次或范畴,JIS工业标准(信息交换用)用字、民众常用字和教育用字(分中小学)。三者之间形成如下关系[3]141:
汉字电脑化带来了书写文化的深刻变革,官方对汉字的限制在新兴通讯技术的冲击下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有意思的是,汉字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声誉在信息时代获得了新的表现,成为突破限制汉字的催化剂。普通民众具有视汉字为高雅身份象征的强烈心理倾向,这鼓励了文字处理软件以大字符集为卖点。罕用字被赋予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性价值,购买者以是否具有处理罕见字能力为评价产品性能的标准之一,导致商家争相展开大字符集开发的竞争。电子传媒技术一方面使速写能力快速退化,另一方面由于可以方便地打印繁难字体,使汉字的使用量突然增加,大量死字复活,人们甚至担心技术将使汉字使用再次陷入战前的无节制状态。正是在电脑和手机高度普及的背景下,为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文部省于2005年就修改字表进行了咨询,讨论再次修订《常用汉字表》。收到反馈意见约220条,共有302个汉字被认为应该收录到新字表,其中要求收录“鹰”字的呼声最高,以22条列首位;最希望从试行方案中删除的汉字中则是“鬱”字。据中国语言文字网2009年1月报道,日本文化审议会国语组1月27日审议通过了《新常用汉字表》(暂定名)试行方案,新增“虎”、“熊”、“鹿”等191个常用汉字,并删除了5个不常用的汉字。修订后的新字表共收录2131个常用汉字。据报道,遵循地名不列入常用汉字的规则,用于都、道、府、县名称的“埼”、“阪”、“阜”、“栃”、“茨”等字也将被删除。该字表可望于年内(2010年)正式批准生效。
人们把文字处理机对语言文字生活的影响比作汽车之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如澳大利亚的日本汉字问题权威Gottlieb女士指出[13]128,技术终于使民众在官方严格的汉字政策下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并有可能成为推动下一轮文字政策变化的动力。鉴于原来的要求限制在汉字的支柱产业如新闻印刷、办公自动化等部门,科技的进步使其对文字数量的关心成为多余,有人建议字表最终将扩展到3000字,但多数只要求认读,而不是书写。未来汉字政策的中心将聚焦在字形字音的规范化而非字量的限制。

三、结语:经验与趋势
本文首先追溯日本汉字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原点出发以发展角度考察汉字存废之争的兴起,旨在为深入讨论后续的发展建构社会政治背景。接下来的分析集中在二战及其前后的发展过程,讨论的重点是围绕几个社会语言学变量(战争的需要、视汉字为国体的一部分等)对汉字改革方向的影响,从而使读者看到战后汉字是如何成为政治和外交较力工具的。美国占领当局废除汉字作为根绝军国主义并操纵日本政府实行有限民主改革的措施之一,而在战败国日本方面,汉字问题被提升到国体高度使其得以保存并受到限制,终使明治维新以来的“废除汉字论”偃旗息鼓。此后直至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展汉字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周有光先生曾论述汉字具有技术和艺术的双重属性,作为书写系统,后者是汉字在世界上特有的属性。50年代在批判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语言具有阶级性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是,汉字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汉字的使用和改革无疑是有阶级性并充满斗争的。汉字在日本近代史上的发展命运更加说明了这一点。本文中我们一直试图把语言文字问题置入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强调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对日本汉字规划的制约作用。展望未来发展趋势,在政治和生活文化因素仍然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来自经济技术的冲击将更加直接和明显。以往的汉字政策是建立在手写汉字的基础上,日本由于率先解决了方块字编码,也反证了汉字其实是世界上最为实用、最有效力和方便的一种文字。针对汉字的不便已被机器带走,支撑战后文字政策的一些前提已经失去意义,Gottlieb[13]132-133对是否还有必要遵循一份固定汉字表提出了疑问。
另一方面,就中日两国就汉字改革问题的沟通与互动而言,语文现代化事业与政治社会发展相平行,从过程上看,日本文字改革的讨论和实施过程都早于中国,1923年就曾发布过《常用汉字表》(1962字)和《简体字表》(154字)(为当年的关东大地震打断)。两国在各自的汉字规范化道路上,还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鉴的不同点或合作的领域,今天仍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总体而言,中日两国汉字规范化的总体方向相异,日本是以限定字数为主,简化为辅,边限定边简化。中国从上世纪30年代起民间已有固定汉字总量的倡议和实验,此后学术的努力也一直未断,官方的规划直到本世纪初《(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正式立项才得以实施。当然这与汉字在两个不同语言体系中作为视觉交际工具的作用和价值不同有关,这也正是日本学者所强调的。但两国在个体和细节方面又是同远大于异:如汉字简化的具体方法,如两国学者都把专用字和特殊用字作为限制汉字数量的核心问题。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对待汉字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废除到减少简化再到增加的转变过程,从一直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书面文字问题,到最后逐渐放弃完全拼音化。这也与中国的文字现代化的过程大体相平行。今天,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微妙变化,中国的汉字繁简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出现新进展和新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来回顾日本汉字规范化的进程和政策转变,也许别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鸣谢: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郑梦娟教授对本文初稿所提的宝贵意见。
[1]赵守辉.日本的人名姓氏用字及相关问题[A].周庆生,郭熙,周洪波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 [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洪仁善.战后日本人姓名中的汉字使用政策评析[J].外国问题研究,2009(1).
[3]刘元满.日本人名用汉字数量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2007(4).
[4]陈月娥.从原敬的“减少汉字论”看近代日本东西方文明的撞击[J].日本研究,2008(3):89-92.
[5]崔崟.评日语汉字的改革之路[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1).
[6]何群雄.汉字在日本[M].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
[7][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6-218.
[8]洪仁善,尚侠.战后日本汉字的平民化问题[J].日本学刊,2005(5).
[9]Carroll,T.LanguagePlanningandLanguageChangein Japan[M].Richmond,Surrey,UK:Curzon,2001: 155.
[10]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83.
[11]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321.
[12]Gottlieb,N.KanjiPolitics:LanguagePoliciesandJap2 aneseScript[M].London:KeganPaulInternational, 1995:166.
[13]Gottlieb,N.LanguageandsocietyinJapan[M].Cam2 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责任编辑:冯 雅]
M odern Evolution , Causes and Revela tion s of Japanese Kan ji
ZHAO Shou2hui(National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7616)
Drawing upon the research work done so far by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 ts toexamine the historical p rocess of Kanji abandonment and Kanji restriction, als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Japan. Reform of a writ2ing system in Japan began inMeiji Period. After the SecondWorldWar, Japanese government imposed a rigid restriction on thenumber of Kanji for common use, and such a polic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a long time. The state quo has been challenged in re2cent year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rough discussion the features and difficulties in Japanese Kanjistandardization p rocess, this dissertation endeavors to reveal deeper socio2cultural reasons. It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mod2er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na.
Japan; table of Kanji; Meiji Reform; the SecondWorldWar
H36
A
1674-6201(2010)03-0050-07
2010-08-01
赵守辉(1963-),男,吉林双阳人,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