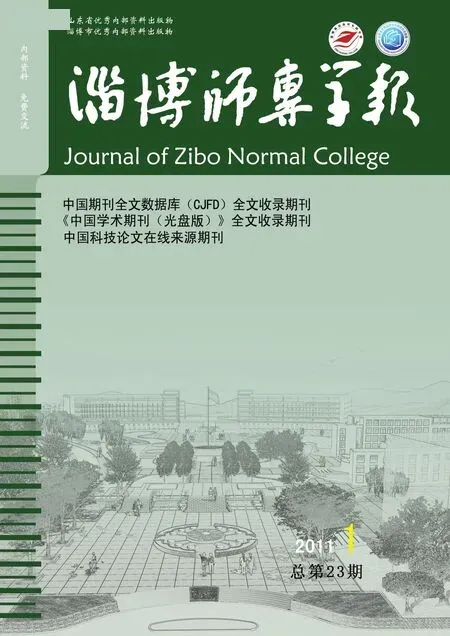文本向剧本的转变
——作为表演艺术的戏曲文学的新变化
李瑞瑞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中国古典文学一路走来,是在直到以杂剧、南戏为代表的俗文学正式登上舞台之后,才彻底与之前的正统文学区分开来,开创了新一代的文学样式与文学理念。文学由文人墨客的案头走下神坛,逐渐成为娱乐民众的消遣之物,由孤芳自赏的高傲姿态向在生存中求发展的转变,这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而奇妙的意义。通过分析以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的传承与发展的脉络,我们也可以窥测到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一些新的特点,这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剧本由于表演而变化
戏曲舞台艺术建立在“虚拟化”的美学理论基础上,综合地按程式构成的审美因素来“写意”地概括生活,表现生活。在此时,戏曲的曲词本身,就只能作为表演的一部分而存在,而远非全部。况且,此时戏曲演出所要达到的美学效果就不仅是形式美的声色之娱,而是以所能达到的意境撩动观众的心灵,让观众获得戏曲艺术特有的审美享受。因而,作为舞台艺术的戏曲的创作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对于价值追求的转变作为内在转变则只是其一。
如果考虑到演出效果,那么剧本中过长的独白、唱段、心情表达等必然会造成演出时的冷场,或者使舞台上的其他人变成木偶式的哑角。所以,在唱词处理上,剧作者往往会采用折中的方式进行处理,对此缺憾进行弥补。试看《牡丹亭·游园》的一折:
(贴)早茶时了,请行。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绣襦,异花疼煞小金铃。(旦)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旦)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
……(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
……(旦)春香呵,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贴)成对儿莺燕呵。
……(旦)去罢。(贴)这园子委是观之不足也。(旦)提他怎的!
在游园中,就本质而言,旦几乎占据了全部的戏分。事实上,设想如果没有贴的“捣乱”,由女主角一人独游花园所起到的艺术效果也许会更好,她也可以更自由地进行心理的独白和展现。但是,出于演出的考虑,随机插入了贴的言行。这样设计,一是活跃了情节,使整个故事的发展更显摇曳多姿;二是贴的天真烂漫与“闺门旦”的温雅娴静形成了对比,也更暗示了身为公侯之女伤春身亡的可能性;三是极大地弥补了偌大戏台上孤单一人的单调和尴尬。戏者,戏也。所以,作者必须要考虑舞台搬演时的效果。此时,戏词相对于舞台的屈就,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可以想见,在中古时期的戏园中,一出同样的戏可以由不同的歌妓,不同的场景安排、道具布置和扮相设计轮回搬演。一部《西厢记》历经千百年,已经被搬演出无数个相似或不相似的版本。甚至前去观看的听众本身已对戏曲本身烂熟于心,“看戏”中“看”的本身几乎成为全部,戏词俨然只是一个载体,“听众”已变化为了“观众”,“演出”也变为了一种程式。“戏由人传”的说法也包含此意。一出戏往往可以因一个歌妓而走红,反之一折好戏又可以成就一个歌妓,这是一个奇妙的现象,也是俗文学相对于雅的正统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并且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二、剧本由于演唱而变化
在古典的中国,歌唱的技巧是古而有之的,中古时代对音律平仄、音韵和谐、开口音闭口音等的讲究远胜于现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在当时就常常以“奇曲拗口、不和音律”而横遭指责。事实上,宋词作为一种歌词艺术,如果不易被演唱,或者说演唱时不易听懂,时人的指责也有确处。
在戏曲创作中,剧本的最终形成也是经由演唱的反复实践、反复润色修改而成的,这在剧本这一特殊文学样式的创作中实为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毕竟作者在创作的初期不可能完全预见到演出时的现实境况。例如,某些韵脚的和谐、某些闭口音在剧场演出时是否足够清晰,某些唱词是否会因为演员的较大幅度的动作而发生颤动进而产生误听。即使作者对于演戏本身十分熟稔,恐怕也是不能够完全做到的。况且,剧本的最后定稿往往还是经过演员们的试演,才完成了最后的修正。
另外,流传民间的各种戏文都有诸多版本,这些差异或大或小的版本除了印刷或传抄的讹误之外,完全不能排除人们有意地增删改动。在这些改动中,包括原作者不同时期对作品的不同领悟而进行的二度创作,包括流传过程中文人雅客的善意匡正,这些修改无疑也是在观看了演出之后的“有感而作”,当然修改者应包括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戏曲演员。他们根据亲身的体验对剧本进行实际的修改,这纯粹是为了演出的方便和效果。
三、剧本由于听众理解而变化
对于剧本这一特殊文学体裁,作者的完稿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完成,作品则是需要借助听众的接受而最终达成作者、作品与读者的创作循环。听众的接受是戏曲艺术不可分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历代戏曲观众,从来都把审美理想放在首要的地位,他们欣赏戏曲,除了把它作为娱乐性活动,还对戏曲寄托褒贬善恶、分辨忠奸、抑扬美丑的希望。为此,历来有成就的戏曲艺人都很懂得情节本身不是他们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情节反映出角色的思想感情,使观者悟出天地万物之间的运动规律,领悟做人的道理。”[1]
当剧作者的原稿被搬演舞台,原稿被当作一件本真未琢的璞玉被抛至听众。在听众那里,它需要无奈而坦然地接受它被填充改写的命运。戏曲在其本身仅为文本之时的意义远远没有在传承之后的意义更加丰富。文本,即戏词,在不断地被接受传播、被口耳相授的过程中也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而显得更加圆滑。戏曲的听众数量是远远多于文学作为案头文字时的阅读者数量的,理解的循环并非一个随意认知斡旋其中的圆圈,领悟也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实,或者说是所谓的不变的真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广大听众在戏中人物的身上寻找着自我与救赎,在上演的故事中去理解和亲近人自身存在的各种潜在性和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开放性也是戏曲作为一种演出艺术的最大的特点。听众对它的所有的理解、升华、顿悟、迷惑、混沌甚至是歪曲和误读,都将无一遗漏,成为剧作本身的一部分。继而,剧本携带观众所有的感受继续走上流传之路,渐行渐远,不可遏止地不断生发着不可预料的变化。
四、剧本由于表演者传承而变化
中国历来有“戏由人传”的说法。戏,无疑要不时地被不同的表演者演唱、表演、传承,而在此过程中,剧本也在不断地生发变化。
“当一位拥有了程式、主题的积累,拥有创作技法的故事歌手,站在听众面前讲述故事时,他会遵守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程序以及其他的职业要素。我们将这种歌视为一种特定的文本,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吟诵过程的变异。”[2](P142)而作为剧本表演者的歌妓,事实上,他们是最了解戏曲的人。即便是文化水平不高,歌妓们多年的演出经验和耳濡目染的熏陶使他们完全具备修改戏本的能力,而演出实际和迎合听众又使他们修改剧本具备了极大的可能性。即使若非如此,他们在演出时会潜意识地根据自身体验通过强化、弱化、夸大等手段使戏的本身产生微妙的变化,“当一个人被视为某一特定角色时,他会被这一角色所吞噬,这既不是戏剧化的表演,也不是‘真实’的,而是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模糊和消失。”[3](P274)一个认真而多情的歌妓,往往会把自己融入他(她)的角色里面去,牺牲自己的情感给角色输血,使角色更加立体丰满。
当歌妓们拿到前辈们传下的戏曲,或是通过口耳相授的方式得到戏词,这种方式也决定了剧本在代代相传中被不断增删,或是由于时代变迁为了市场口味而有意为之,或是由于时代心理的变化而无意间使剧本衍生出了新的意义。
来看《桃花扇》中的一节——女主角李香君在老师苏崐生的指导下练唱《牡丹亭》中游园的一折:
良辰美景奈何天……
(净)错了,错了,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连下去。另来另来!
……(净)又不是了,“丝”字是务头,要在嗓子内唱。
……(净)妙!妙!是的狠了,往下来。
……(净)这句略生些,再来一遍。
……(净)好!好!又完一折了。
“在这里,中国戏剧传统中最艳丽、最热烈的唱段之一,被作为技术性的表演练习而呈现出来。……这个少女是一片空白,被她的角色填充起来,没有怀疑,没有其他的视角,也没有微妙而丰富的多重层次。……而在这出戏结尾,她独自留在舞台上,感叹自己被锁在深宫不得自由的命运。镶嵌在全剧开始时作为无名少女的空白和全剧结束时悟道之空白的框架之中,她既不变化,也不突破自己的角色。……有那么短短的一会儿功夫,旦真地变成了一个‘旦’; ……她如此完全地投入角色,……在重复的边缘,她几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旦,一个身为女演员的女演员。”[4](P278-291)我们不得不说,李香君在牡丹亭的长梦中游走了一生,她口下的杜丽娘既是当年的女主人公,又浸渗着自己的全部情感,自然又是另一番沧海桑田不堪回味的杜丽娘了。戏由人传,此时的《牡丹亭》,不再是汤显祖的个人作品,而成为戏中的李香君的专属了。
当文本向剧本转变,当雅文学向俗文学渗透,一些文学上的新变化就无可避免。在俗与雅的变奏中,以杂剧、南戏为代表的俗文学正式登上表演艺术的舞台之后,彻底地与之前的正统文学区分开来,这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必然的历史现象。毕竟,时代心理和大众期待是文学发展趋势的必然指向。
[1] 胡芝风.谈戏曲剧本创作技巧要素[J].艺术百家,2004,(5).
[2]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4][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桃花扇》中求真[M].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