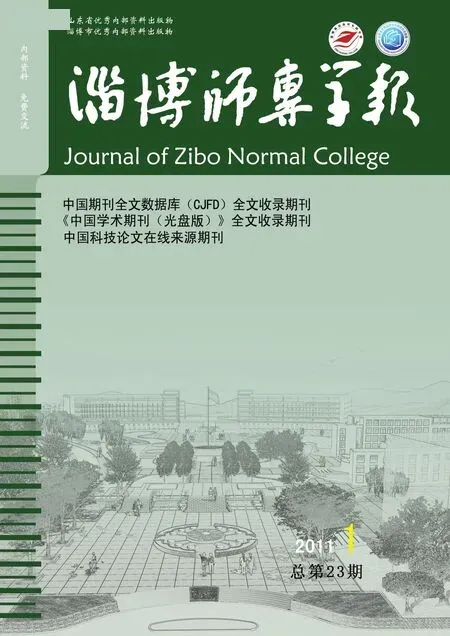大家族与战国秦汉间人口的关系
尹建强, 陆祖吉
(1.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科学部,广西河池 547000;2.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工程系,广西河池 547000)
春秋末战国初,铁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的相对发达,使家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存在成为可能。而且,此时期列国间争霸不断,战争频起。各国政府出于对兵赋和战争动员的考虑,大家族制的存在与现实的冲突日益显见。
春秋以来,大族制不只是社会的细胞和经济的集团,并且也是政治的机体。各国虽有统一国家的形态,但每一个大族可以说是国家内的小国家。晋、齐两国的世卿最后得以篡位,根本原因也在此。
战国时代最有系统的家族生活是秦国。商鞅变法中明确规定: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1]
商鞅的政策主要有两点。第一,废大家族。二男以上必须分异,否则每人都要加倍纳赋。第二,公民训练。在大家族制度下,家族观念太重,国家观念太轻,因为每个家族本身几乎就是一个小国家。当时列国纷争,战事频起,而战争又是最要集权的。国君要使每个人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就必须打破大家族,提倡小家庭生活,使得全国每个壮丁都完全独立,不再有大家族把他与国家隔离。家族意识削弱,国家意识强化,兵员的动员和补充就会变得迅速而及时。
事实证明,商鞅的政策完全成功: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
以上是秦国对家族制度改革的片断。其他各国的情况虽无明文,却也可有一大概推测。商鞅变法,以李悝的《法经》为根据。《晋书·刑法志》:“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李悝前曾相魏文侯,变法魏国,魏因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楚悼王用吴起变法,也在商鞅之前,“秦在七国中似乎变法最晚,并非战国时唯一变法的国家。”[3]此时各国大都在变法,秦变法又最晚,况且同一文化区域内,一切的变化都是先后发生的,且各国变法内容大致相同。
各国变法后,家族制度没落,相随而来的便是子孙繁衍观念的淡薄。大家族制度下,子孙众多当然是必要的。西周、春秋时代的铭刻中,就充分地表现了这种心理。
“其永宝!”
“子孙其永宝!”
“其万年宝用!”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但是在变法的冲击下,大家族破裂,子孙繁衍的观念趋于微弱。那时,公民观念代替家族观念后,一般人认为,一人无子国家并不见得没有人民。而且,小家庭中,儿女太多的确是累赘。此时,人类的私心也便彰显。对个人太不便利时,团体的利益往往会被牺牲。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有过人口过少的恐慌,也都设法增加过自己国内的人口。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越国,勾践为雪国耻,极力鼓励国内人口的繁殖:
(1)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
(2)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3)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4)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4]
魏国居中原,也患人少,梁惠王向孟子诉苦: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5]
梁惠王以后,秦国也患人少,《商君书》有《来民篇》以招徕三晋人民。此时战争激烈,杀人过多,坑卒和战争造成的死伤不绝于史,数目宏大。据《史记·秦本纪》和《始皇本记》所载,前后共十五次:
(1)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2)惠文王七年,与魏战,斩首八万;
(3)惠文王后元七年,秦败五国兵,斩首八万二千;
(4)惠文王后元十一年,败韩岸门,斩首万;
(5)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击楚于丹阳,斩首八万;
(6)武王四年,拔韩宜阳,斩首六万;
(7)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
(8)昭襄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9)昭襄王三十三年,破魏,斩首十五万;
(10)昭襄王四十四年,白起攻韩,斩首五万;
(11)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余万;
(12)昭襄王五十年,攻三晋,斩首六千,晋军走死河中二万;
(13)昭襄王五十一年,攻韩,斩首四万;攻赵,首虏九万;
(14)王政二年,攻卷,斩首三万;
(15)王政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
战争造成的杀伤,是人口稀少原因的一方面。另外,小家庭制度盛行多子观念薄弱之后,杀婴的风气势所难免。此时虽无直接的证据,但是,汉代杀婴的事却十分注目。风气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汉之前必有端倪可寻。
战国时代,中国已盛行节制生育的方法,即房中术。《汉书·艺文志》中,此种书籍甚多。战国、西汉间,最重要的有八种:
(1)《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2)《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3)《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4)《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5)《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6)《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7)《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8)《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这些书现已失传,内容不可考。但都是专讲如何禁内情之法,最后一种虽承认“有子”,也是有条件的。
汉时,人口稀少仍是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房中术仍然流行。王莽相信黄帝御一百二十女而致神仙,于是遣人分行天下,博采淑女,一直到新朝将亡时候,王莽仍“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6]王充谓“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7]
此外,汉时有些地方盛行杀婴的风气。东汉末,贾彪为新息县长,还有这样的表述:
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千数。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为贾子,生女名为贾女。[8]
新县数年间可杀而未杀的婴儿有千数。可见杀婴不完全因为贫困,贫困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已。汉代房中术盛行,不明其法的人就难免采用野蛮的杀婴方法,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原因。
人口的缺失使得汉代政府极力提倡人口的增加。高帝七年,“命民产子,复勿事二岁”。[9]宣帝之时,人口增加的多少作为地方官考察的重要标准,黄霸为颖川太守,“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10]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其化大行……百姓归之,户口增倍”。[11]
东汉诸帝极力奖励生育,章帝元和二年将下有名得胎养令:
(1)产子者,复勿算三岁;
(2)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12]
生育的前后共免四年的算赋,外给胎养粮。“产子者,复勿算三岁”,未分男女,大概是夫妇皆免,两人前后免算八次,共九百六十钱。可见,政府对鼓励生育的优厚。并且,此法作为以后的常法。
虽条件优厚,但效果未有显见。两汉四百年间,人口总数始终徘徊在六千万,未逾此数。
汉代诸帝只能采取恢复大家族制度来增加人口了。因为小家庭制与人口的减少几乎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故而,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豪族强宗在地方拥有极大势力,有众多依附民。
汉代天下一统,过去那种列国纷争的紧张局势一去不复返,皇帝只求社会的安定。而小家庭制度下,个人流动较大,况且小家庭经济单薄,农业生产受自然影响较大,破产的机率极大,社会因而不安。大家族则可使多数人安于其位,生计的问题即使面临困难,亦可以在家族内部得以解决,不会危及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能促使人口的增加。
汉代在大家族的制度下,人口虽然没有过多增加,也并未过度减少,所以帝国仍能维持,不至于像罗马帝国在日耳曼狂风暴雨般的冲击下灭亡。所以,之后的中国虽有五胡的入侵,但最后能把他们消化、同化,再创造出新文化的盛世。由此可见,大家族对于人口的保存之功是不言而喻的。
[1]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9][10][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王充.论衡[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