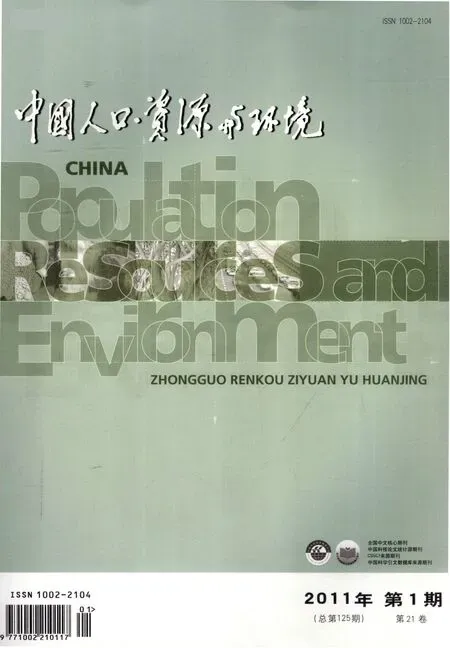环境安全问题的工业设计观
刘桂艳 肖立峰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北京100191;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北京100191)
环境安全问题的工业设计观
刘桂艳1肖立峰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北京100191;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北京100191)
从历史观和哲学观探讨环境安全问题的成因,将环境安全问题与工具的发明创造联系在一起,论述了环境安全问题就是工具的缺陷恶化了环境与人以及人类之间的和谐关系。环境安全问题不再是简单地针对环境的治理或对人的管理问题,而应该从工具的产生过程中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工具的功能和性能设计,仅仅是完成工具设计的初步阶段。在投入社会之前,必须完成工具的人机环境设计与评估,用于平衡或消除工具所蕴含的潜在危险因素。因此,要解决环境安全问题,必须突破狭隘理念,以环境安全作为核心价值进行工业设计,创造与使用符合人机环境因素的优质工具。
环境;安全;工具;工业设计
安全本是个体现象,但随着社会的形成,个体的安全问题就会变成社会的安全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学术界所阐述的安全多指有一定规模效应的群体安全问题。由于人类个体与社会的高度关联,个体安全可以是社会安全的引发者,也可以是社会安全的受害者。安全问题可归结为“环境对人的伤害”和“人对人的伤害”。前者俗称天灾,后者就是人祸。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在环境和安全问题的导火索上存在着“人→工具→环境/人”的行为模式,其中工具是人类影响环境和人类社会的主要手段,环境状况和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工具的创造与发展失衡。
1 从历史观和哲学观探讨环境安全问题的成因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产业之间的交叉渗透使得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纵观世界历史,和平时期因为环境安全问题而死亡的人数已远远超过几次重大战争的死亡人数。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类的生存状况处于完全依附于自然与环境,人类安全问题主要是环境对人的影响。随着劳动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始尝试改变自然环境,以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这种改变一旦破坏了环境,反过来人类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
改变环境的重要手段就是工具。科学技术促使了工具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削弱了人的个体性,在极端层面造就了杀人的工具[1]。“是科学而不是罪孽,让我们失去了乐园”[2]。爱因斯坦曾这样说:“痛苦的经验使我们懂得,理智的思考对于解答我们社会生活的问题是不够的。透彻的研究和锐利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往往具有悲剧的含意。一方面,它们所产生的发明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活更加舒适而富裕;另一方面,给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而最大的灾难是为自己创造了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令人心碎的悲剧”[3]。凭借各种先进的工具,人类的行为实际上已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灾害不断涌现。
回顾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演变历史,人类不断繁衍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创造或发明工具的过程,也是自然环境不断遭受破坏的过程。“火”是人类使用的第一个重要工具。远古时代,火的产生主要源自雷电,但人类学会钻木取火后,火灾就开始成为人类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安全问题。如今,随着电、火药、煤气和油等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火灾的规模和数量也远远超过远古社会。由于一系列不良工具的存在,人类的任何错误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灾害。烟花、建筑材料和消防设施的缺陷构成了央视大火的主要工具因素。汶川地震给人的震撼是天灾,更因劣质房屋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相比之下,饱受地震之苦的日本,其优质建筑设计可以确保在地震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保护国民安全。近年来国内矿难事件频发,最大的原因也是煤矿作业场所缺乏足够的安全设施。而智利矿难则由于提供了人性化的避难所,给井下人员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可见,工具的优劣决定了环境安全问题的程度。
当前,环境安全问题多以人为治理对象,通过控制人的行为模式,来减少对社会和环境的伤害。尽管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法规限制人的行为方式,但实际效果收效甚微。从历史观和哲学观来说,人是最靠不住的因素。因此,通过控制工具的运用应成为环境安全治理的主要因素。
2 环境安全治理必须改变人类创造工具的模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具有一种动态平衡。人类利用工具,在满足人类自身利益的同时,往往会改变这种平衡关系。但宇宙演进的过程是一种平衡过程,于是自然界会透过某种灾害形式释放被强制改变所带来的能量,从而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伤害人类。因此,针对工具的破坏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消灭工具;控制工具的使用;提供某种对立工具。工具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消灭工具只能使人类社会倒退。控制工具的使用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利益面前,国家、企业不愿增加更多的投入,工具对环境安全的影响最终因为人的因素而得不到控制。提供某种对立的工具,是当前许多制衡工具对环境安全的负面影响的匹配工具,如一系列消防安保或环境治理工具的出现,可以缓解工具的破坏力,但远未达到平衡工具的程度。人类不断创造发明新的工具,只享受工具所带来的“功能性”力量和权利,却没有履行与工具收益相匹配的环境安全义务。这种义务是一种成本,在小概率的环境安全事件方面,就会被人类有意无意的忽视。因此,新工具的潜在危害就不会得到节制。
人类创造工具的模式存在一种严重的失衡行为。工具的创造模式只注重功能和性能的设计,却忽视了工具的环境和安全设计。工程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只培养工程师学习功能型学科知识,对环境和安全有关的知识往往被淡化或忽略,导致工具的创造者们严重缺乏环境安全意识。工具一旦被投入使用,直到看到产生环境安全问题后,才会以亡羊补牢的形态进行工具的完善和环境的治理。当前许多国家标准、政策和法规对工具的准入限制,也多从功能和性能上考虑,现有的环境和安全标准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下门槛不仅低而且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现在借助计算机工具,人类越来越能够创造自己难以控制的新工具,相比人类花在工具功能和性能的精力来说,环境安全方面的设计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3 工业设计可以促使“工具的物化”向“工具的人化”的有效迁移
马克思指出任何工具都是劳动耗费后的“物化”[4]。从使用价值来说,工具是人类劳动手段上的帮助与延伸,借以更大地发挥人类能力,同时节约自己的手段。在哲学上,“工具”具有双重属性:“工具的物化”和“工具的人化”。“工具的物化”是指工具存在的客体化,“工具的人化”是指工具适合人的需求。“工具的物化”就是人的工具构想如何实现,主要涉及到工具作为物的制造技术与工艺。工具在物化过程中,人们关注物化的方法和途径,而不关心物化后,工具与人的关系。“工具的人化”的本质是工具必须体现出人的特性与需求,使其成为人这一主体向外延伸的对象,必须反映出人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物质功能需求及审美需求等特征[5]。
工业设计的对象是“物”,是通过物的创造满足人类自身对物的各种需求,“物”本质上就是人类的工具,无论大小、技术含量高低,都是人的肢体、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延伸。工业设计的基本理念:必须使得工具与人之间取得最佳的匹配[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研制成的高速喷气式战斗机在试飞过程中屡屡失事。为了弥补高水平驾驶员的不足,展开了由工程技术人员、医学和心理学家的共同协作,从实验心理学的立场出发用工程手段来分析基于人类知觉的判断及动作的特点,并在事故预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现代工业设计的研究领域,战后从军事扩展到一般工业领域。现代工具的规划设计,不仅要审定并实现“工具的物化”,并且最终还要根据与人的关系实现“工具的人化”。
在工具的设计过程中,“工具的物化”和“工具的人化”应成为设计过程同等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工具的物化”一直是设计的主要关注点,而忽视了“工具的人化”这一重要问题。因此,许多工具与人的需求距离相差甚远,不能作为“人的生命外化”而存在。“工具的人化”表明了工具从自然物向人性化的发展,使得工具成为人的一部分。人类通过“人化”的工具完成向目的过渡。这样,工具对于人来说,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人的工具,也是人的组成一部分。工业设计因此建立了“人化”的设计思想:任何物的设计都是人的构成的一部分的设计,都是人这一生命体的生命外化的设计。
工业设计的出现使得人类生活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但现在大多只注重视觉和易用性等方面,工业设计教育也还停留在人机接口或产品的外观造型上。实际上,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工业设计理念。工业设计应针对“人机环境”要求实现“工具的物化”到“工具的人化”的迁移,从环境和安全的高度引领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设计。因此,工业设计应突破狭隘的成本意识和价值观,加强与环境安全工程的融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政策也应抛弃盲目的经济效益,而应大力促进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从环境和安全的角度全面扩大工业设计在工具设计制造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解决工具对环境安全所带来的危害。
4 促进环境安全和工业设计学科融合,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学科
由于专业知识和学科门类不断分化和细化,许多专业领域相继出现了针对环境安全的研究,但仍是从工具的“物化”层面解决环境安全问题,依旧不能改变工具创造过程的失衡状况。因此,环境安全学科应与传统工业设计结合在一起,形成面向工具使用品质和环境安全的广义的工业设计学科,以“人-工具-环境”为对象进行研究,辐射各个功能型专业学科,确保工具符合人机环境要求。“人-工具-环境”包含三个主体:“人”指主体工作的人,“工具”指人所控制的一切对象,“环境”是指人与工具共处的特殊条件,包括物理、化学因素的效应,也包括社会因素的影响。
许多行业制定了市场准入政策和相应标准与规范,也出现一些专门针对环境和安全的评估部门,但这些都是因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安全形势而被迫出现的措施,这种被动策略只是工具物化过程的监管形态。实际上,这种监管更像为事故进行法律背书,而不是从源头上扭转工具对环境安全的负面影响。工业设计则不同,首先它是整个工具设计过程中应该具备的环节,是从工具的概念设计阶段就介入工具的创造,通过培养工程师的“人-工具-环境”意识,可以有效地规范设计行为,在工具在进入社会前就完善了环境安全设计,提高了工具服务于人的品质,这正是现代工业设计的全部内涵。
工业设计学科涉及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领域的知识。科学技术是工业设计必须涉及的领域,包括物理学、数学、材料学、力学、机械学等。工业设计结果必须严格符合科学技术的“客体尺度”。社会科学反映工业设计对象的应用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社会群体行为,必须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群体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使产品为社会所接受。工业设计的实质是设计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方式,正确的设计思想应是通过物的设计体现出人的力量、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方式[7]。
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指出,工业设计师是在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利益、尊重现实环境和遵守职业道德的角度,在责任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8]。工业设计是为了给特定功能寻求最佳形式,而形式又受到功能条件的制约,则形式和使用功能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就是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可以有效改进工具的设计过程,在兼顾生产者和使用者对产品外观、结构、功能及安全性等方面要求条件下,始终站在生产者与使用者(消费者)之间,用适宜的形态将工具的使用要求有效地传递给使用者。
5 从工业设计视角审视高层建筑火灾成因与防治
在“人-工具-环境”系统中,人是系统的主体,是系统的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在系统中人的位置特别重要[8]。任何系统始于人、终于人。工具与环境则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功能因素,两者构成的系统又对人施加影响。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伤害人类。一个系统可以因人的完善运作而起到超常的效益。一个系统也可以因人的不良或错误运作造成毁灭性的效果,甚至将系统本身破坏。高层建筑是一个典型的“人-工具-环境”系统,建筑物或建筑群就是工具所依赖的环境,而与建筑相关的设施就是工具。所以,在建筑这个具体条件下,就是人、设备和设备系统建筑和建筑群的系统关系。只有在这三者经过精心地优化组合之后,才能使系统达到最佳的运作条件,最大程度地防治灾害的发生,或在灾害来临时,协助人做出正确的逃生决策。
以2010年发生的上海高层居民楼的火灾问题为例,我们将“人因”纳入建筑工程来进行环境安全评估,不难发现建筑设计及后续工程更多考虑的是成本因素,同时也缺乏环境安全的整体设计。整个大楼外墙面完全被脚手架、尼龙防护网和聚氨酯泡沫材料包裹,形成火灾隐患,由于施工过程产生的电火花,加之大风天气因素,火灾是工程缺乏技术评估与设计的必然结果。根据消防要求,高层建筑应提供足够的消防停车面及消防通道,但实际工程中却被脚手架占据,凸现施工方安全意识薄弱,消防监管严重缺失;巨大的伤亡也表明居民缺乏安全逃生指导,甚至出现了二层居民的死亡现象。这起安全事故再次表明,人是最靠不住的因素,依托人的本能,根本无法有效完成设计施工决策,受害者也无法做出正确的逃生决策。
通过工业设计的视觉传达方法,使不同人群之间能够形成环境安全意识的视觉传递,相互制约以形成潜意识群体监管。在建筑楼外面应有系统全面的安全警示标识,传统的安全措施仅仅是进行所谓的专业配置,但是缺乏一种让任何人都能够采取预警行为的视觉设计。按照工业设计人机环境设计理念,从“人因”逆向给出建筑设计必须实现的安全功能[9]。施工现场的设备和材料如果在外包装或材质表面颜色采取不同灾害类型的警示颜色,让任何人都知晓施工现场给自己带来的危害程度,就可以及时制约施工方的鲁莽无知的行为。视觉上确保楼内有明显的安全逃生路线图和安全警示标识;听觉上设置铺设到户的小区应急广播系统;嗅觉上让人闻到有毒气体或烟雾时,能够启动楼内的强力吸排风扇,将进入室内的有毒气体通过建筑通风管道排放出去。楼内的安全设施具有良好的人机接口,易于操作使用。户与户之间,室与室之间强制采用阻燃材料进行设计,可以确保火灾发生时,可以将灾害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因此,现代建筑应该向模块化设计转变。2010年湖南某建筑公司采取模块化设计理念在六天时间内完成了一座高层建筑的主体建设,代表了未来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更容易实现符合人机环境要求的建筑。
6 总结
人类的文明不是靠征服自然获得的,而应该是在人类不断发展过程中在不同领域追求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存的境界。工具不应该成为放纵人类野蛮行为的帮手,而应该成为促进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粘合剂。因此,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可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为新工具的投入使用提供全面可靠的评估,消除工具的各种破坏环境安全的危险因素和隐患。否则,随着工具的日益强大,其对环境安全的威胁也变得越来越大,在不受约束的状况下,宗教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在技术和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就不再是危言耸听的谣言了。
(编辑:温武军)
[1]王丽,从工具理性到信仰的理性[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65(6):29 -33.
[2]考夫曼,宇宙之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1.
[3]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程能林,工业设计概论[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6]张宪荣,陈麦,季华妹.工业设计理念与方法[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7]龚克,赵江洪,西方产品设计新趋势[J].产品与设计,2003,(1):78-81.
[8]林贤光,建筑是一个人机环境大系统工程-论建筑师在智能建筑中的作用[J].建筑,2001,(12):37 -40.
[9]Carlo Vezzoli,Ezio Manzini,刘新,杨洪君,覃京燕译.环境可持续设计[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
Industrial Design View from Environment and Safety Problem
LIU Gui-yan1XIAO Li-feng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2.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The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safety problems is discussed from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and the problems are associated with invention and creation of tools.The paper elaborates that environmental safety problems,due to the defects of tools,are worsen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man.They are no longer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that are not simply directed at environment governance or the management of man,and their fundamental solutions should be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tools.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design of tools are only the initial step in the completion of tool design.Before new tools are used in society,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man-tool environment should be completed so as to be used to balance or eliminate potential danger factors.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safety problems,we must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take environmental safety as the core value in industrial design,create and use high-quality tools suitable for the factor of man-too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safety;tools;industrial design
X24;X913.3
A
1002-2104(2011)03专-0058-04
2010-12-12
刘桂艳,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安全、环保、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