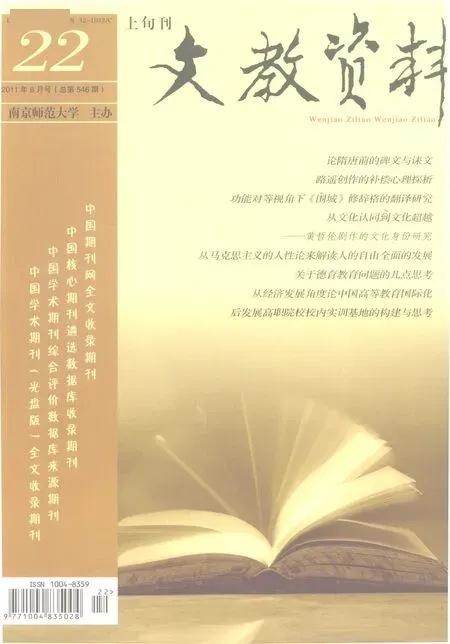诗可以群和而不同止于至善——关于古代儒家群育思想的美学审视
谭志伟
(华南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群育,即“群体适应性教育”,旨在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合群、合作、共处等内容的教育,促进其个体的群化和社会化过程。群育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孔孟为代表的古代儒家思想体系包含大量的“群育思想”,有博大而厚重的关于“群育思想”的智慧。它以“仁”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秩序这一问题来展开自身的群育观念及理论。 “仁”通“人”,字形从“人”、从“二”,既表明人必定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又表明“仁”是作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关系的基础和纽带正是“仁”与“爱”。“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有“爱”方成“仁”,不“仁”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儒家“仁爱”思想由亲及疏,由近而远,以家庭为出发点,将孝悌观念不断扩大,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则视人若己、推己及人,恪行“忠恕”之道。一方面,从自身出发,视人若己,尽其在我谓之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另一方面,推己及人谓之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把“克己复礼”和“推己及人”相统一,凸显教化的作用,强调个体的人格完善和人生责任,强调群体的人伦仪轨和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各安其位、各膺其德的和谐群体关系和社会秩序,以最终实现“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理想。
在此教化施行及其强调个体实践的过程中,儒家群育思想始终坚持“凡先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记·文王世子》)这一塑造和实现理想人格的“双途径”施教道路,对艺术—审美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注重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强调:“乐者,通伦理者也。 ”(《乐记·乐论》)强调以美导善的方向和理念,强调美育对人格培养和人际关系秩序构建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其群育思想之玉与美育思想之泉相互涤荡,闪烁出情理相融、美善双辉的审美意趣。
一、诗可以群,彰显礼乐相运的艺术功能美
“《诗》可以群”一语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著名的关于《诗经》社会功用的“兴观群怨”观其中的一个命题。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之名”。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孔安国注释为“群居相切磋”,是指诗歌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和关系认同,促进个体与人群的和谐相处。一方面,《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基本内容与儒家“礼”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相一致。学习《诗》,其中所渗透的宗法伦理道德必然会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训导作用。同时,《诗》是礼仪活动所奏的乐歌,包括礼与乐的精神,当《诗》被配上合于雅正之义的音乐后,便与礼仪进一步相结合,使“礼”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发挥出和谐上下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成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群体关系和谐的一种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诗可以群”这一命题积极肯定了诗乐对个体道德情感培养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群体的精神培育和人文化成功能。以诗的优美意境和音乐的独特魅力娱乐人的心志,净化人的灵魂,通过对生命主体的普遍关怀和精神慰藉,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从而使原本气息相关、生命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致生命契合,形成人人友爱相处的融洽氛围,将社会维系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这里,诗乐,并不单指诗歌和音乐,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音乐、诗歌、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段也被包含其中,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教育或美育。事实上,儒家正是把这种综合性的艺术教育视为其君子培养的必然途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一个人主观意识的修养,要从诗开始,用乐来完成。在孔子看来,理想人格固然需要规范的“礼”和行动的“践”来实现,但是作为人生境界之美的体验必须通过心灵来完成。艺术、艺术教育或美育恰恰是直接指向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苏霍姆林斯基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良心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艺术教育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又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说教与规劝。它通过运用语言、动作、线条、色彩、音响等各种手段塑造出立体、多彩、直观的艺术形象去影响受教育者的感官和心理,以其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感染性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从而使受教育者在美的享受中得到熏陶。情感性和愉悦性,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艺术的渗透将人的审美情感内化为道德情感,并作用于人的道德行为,从而使受教育者不仅从理智上认同教育者的道理和观念,而且激发起两者之间的情感认同,并使审美情趣与道德情感相互交融,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同时,艺术教育注重营造和谐、宽松和快乐的教育氛围,充分利用各种生动有趣的艺术素材和使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手段和组织形式,让受教育者在愉快轻松的状态下投入教育活动之中,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能体验到其中的快感和乐趣。艺术教育,正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教学,使人学有所乐、乐有所得,真正收到使受教育者“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教育效果。
可见,艺术教育在实现以“乐”求“礼”、以“乐”成“礼”的过程中,一方面,始终以情感培养为目的,以情感交流为桥梁,具有强烈的“动情性”,能引发受教育者的情感运动,激发他们的审美情趣,达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和理性认同。另一方面,“礼”与“乐”在功能上又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审美需要正确的审美观和高尚的思想情操为基础,艺术教育需要把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只有当受教育者对事物的美丑评价与善恶评价相一致时,随之而来的道德情感才能有助于他们的审美情感得到进一步增强,才能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真正以情感人、以美趋善乃至美善合一,从而实现提升受教育者道德情感、深化受教育者道德认识、改善受教育者精神风貌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孔子之所以重视诗乐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君子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 ”(《论语·阳货》)对于孔子来说,礼乐都不过是手段,是一种以礼乐方式和谐群体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手段,“和群体、正天下”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二、和而不同,追寻平等性共存的人际和谐美
“和而不同”的命题是孔子在继承春秋以前“和”、“同”观念,以及史伯、宴婴“和同之辩”基础上,着重从社会和人伦的角度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其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儒家群伦思想。“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句意为,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和”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字义为口声相应、声乐调和,并以此引申出和谐、和睦之义。“同”者,则强调仪轨、外在行为的绝对一致,而不管内心如何。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之一,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正如朱熹所言:“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从哲学角度看,“和而不同”揭示了社会事物的多样性统一。“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平衡或统一;“同”则指事物的绝对一致、等同。“和而不同”这一命题揭示出:差异,使万物品类丰富,相辅相成;和谐,则使万物处之有道,共生共长。自孔子后,“和而不同”思想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它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求个体自身的立己、处世法则,探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共处之道。儒家把一种上下内外的高度和谐作为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生活的最佳状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儒家和谐观是一种具有辩证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普遍的和谐观。
和谐,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对“和而不同”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和谐,不仅是一种圆融的状态,而且是一种美的境界。和谐美之所以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事物间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在古代中国,《易经》通过阴爻(--)与阳爻(—)这两种不同性质卦象的交互变化,阐述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对立统一、生生不息的内在规律。《乐记》指出:“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将“中和”与音乐艺术相结合,这既是对儒家中和之道的发扬,又是对音乐艺术和谐论的美学创造。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首先提出了“美即和谐”的命题,赫拉克利特也指出:“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古希腊美学家普遍认为:和谐起源于差异的同一,对立的统一,不协调的协调,不一致的一致。这种看法一直被西方美学家奉为美的圭臬。事物间的和谐美如此,人与人的和谐美也如此。人,不仅作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而且是社会学上的社会人。人之美,既属自然美,又属社会美。而社会美的中心恰恰是人之美,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之美。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所理解的儒家“仁爱”说应同时也是一种美学原则,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学原则。正是儒家“仁爱”说赋予了“和而不同”命题更深刻的内涵。它使我们认识到,群体的融洽和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社会个体差异性,并促进和造就差异性个体平等共存的文化心理、信仰和价值观念基础上。“不同”者,社会个体和角色的多样性也“和谐”者,统一于“仁爱”之美也。把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视为具有道德自觉的平等主体,并具备可以进行平等沟通和交流基础的平等主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努力通过对人与人之间角色、身份差异性的肯定,促进其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尊重、理解和关爱,使平等成为一种价值追求,乐群、爱群、协群成为一种道德素养,这样,才能真正把社会维系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人之美,应是一种群体和谐之美,一种建立在平等性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和而不同”不仅成为一种处世法则,而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和人性美的境界。
三、止于至善,涵养文质彬彬的人格精神美
对于和谐的追求,无论是中国古代儒家立足于社会伦理的阐释,还是近现代美学理论立足于心理观照的论述,我们都不难发现,强调通过对个体自身美(即人的自身和谐)的修炼与加持来达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的和谐,是实现自身道德超越和自他、物我、天人和谐共处、无间契合的一条必修之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开篇明示儒家君子道德修养的三种途径和境界。“明明德”,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释:“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朱熹将第一个“明”释为“使之明”,即将人天性中就存在的高尚德行重新显现。“亲民”则与“明明德”相互呼应,指在道德的养成过程中,以“明明德”为道德理想,以“亲民”为道德实践,通过为民、利民、服务于民来实现入世利人的理想,而且,只有将“明德”与“亲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人、自利利人,从而使个体的精神境界升华到“至善”之境。所谓“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已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止”是锁定目标不动摇,“至善”是道德修行到达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这种境界的实现,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纯道德的恭行与实践,而是一种将美善合于一身的身心统一之境,是身体、气质、德性、意志和精神的有机统一,是生命的感性具体和美学超越。它是一种伦理道德而又超越伦理道德的审美境界,具有令人欣赏、景仰和不懈追求的审美状态,是一种“浩然之气”的人格美。
人格修养,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美学课题。人格修养既关涉到个体的安身立命,又与社会道德风尚和精神追求紧密相连,其理想状态将达于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美学境界。在儒家看来,这种美学境界与“君子”人格是合而为一的。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物境,而是一种通过修炼达成的自由心境。君子,是孔子思想体系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中国古代儒家对实现或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个体的尊称与肯定。孔子赞美“文质彬彬”的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文”与“质”都是就人品道德的修为而论的,其中,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行为、语言和文饰之美;质,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灵、精神和道德修养之美。二者的结合与相济相成,才能谓之“彬彬”。可见“文质彬彬”是孔子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他的培养目标——君子所提出的道德诉求和审美要求。孟子也认为,人性是善而先验地存在的,人格美所内含的善不是一般的善,而是由仁义所充实的善性:“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但人格美不是天生的,这些天赋的道德秉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它需要社会个体通过主观的努力,通过意识的修养,在善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扩张、磨炼修养而成。因此,一方面,人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另一方面,要寡欲清心,“善养浩然之气”,积极追求“万物皆备于我”、“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必须从自身出发,从自身和谐美的建设着手,通过自身道德涵养和审美升华来实现人身心、人格的和谐发展。其中,身心和谐是自身和谐的起点,只有身体健康、心理正常才具备成为一个自身和谐美的人的基础;人格和谐是自身和谐建设的关键,只有思想与时俱进、人格健全完善才能超越小我,担当起社会建设的责任,从而努力达致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更好地体现及处理自身与外部的各种和谐关系。在此基础上,自觉、主动地接受美的熏陶。无论是自然美、艺术美,还是社会美,都蕴藏着精神理想和思想境界,都能使人在美的观照中心灵受到震撼,情感得到陶冶,精神得到净化,气质获得升华,进而达致高尚的人格和审美超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天与地、人与人,何其美也,何其和谐。
[1]杜卫.美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02-103.
[2]王朝闻.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王旭晓.美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赵伶俐.百年中国美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陈小鸿.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冉祥华.美育的当代发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7]向春.中国传统群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08,8.
[8]刘金荣.试论孔子诗可以群的命题含义及文化意蕴[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1.
[9]李广龙.孔子诗可以群的历史成因及内涵管窥[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0,9.
[10]孙光贵.和而不同疏证[J].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2.
[11]王敬华.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与和谐世界[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4.
[12]顾勤.孔子的乐教观及其对当代艺术教育的启示[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6,6.
[13]黎红雷.孔子君子学发微[J].中山大学学报,2011,1.
[14]伍永忠.儒家君子人格的美学内涵与和谐社会[J].长沙大学学报,2007,11.
[15]于民雄.孔子的君子人格[J].贵州社会科学,2009,12.
[16]王明居.美与和谐[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