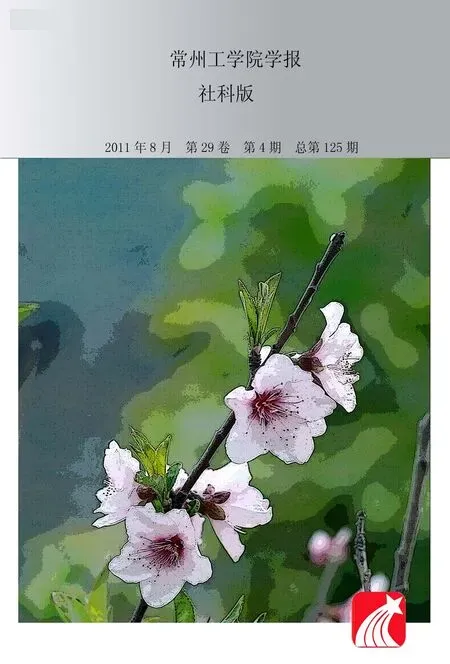契诃夫静态美学特征对曹禺戏剧的影响
刘晓蕾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说是一个西学东渐的历程。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从西方作家那里汲取了不少养料。提到中国现代戏剧之父曹禺,有一个人是无法绕开的,那就是契诃夫。契诃夫戏剧创作中较为突出的当属其静态化艺术手法,这种戏剧手法对曹禺后期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曹禺经过《日出》、《原野》、《蜕变》等剧本的实践,及至《北京人》,成功地领会到了契诃夫戏剧平淡悠远的静态化艺术特色,并且在平淡中保持了自身的特长——内在的紧张感,完成了自身艺术风格的转型。中国戏剧在曹禺、夏衍等作家的努力下,走上了“非戏剧化倾向”的道路,他们也开创了中国戏剧史的新篇章。
一、契诃夫戏剧的静态美
通读契诃夫各种体裁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能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愁,在美学特征上较接近中国古典文学审美理念之“哀而不伤”。与这种风格相统一的便是作品的静态化美学特征。尤其是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更是突破了传统戏剧强调戏剧冲突、舞台动作、戏剧语言等创作手法,呈现出一种静态美:戏剧之中充满了停顿,交流不断被隔阂打断;戏剧中的冲突倾向于内在化、隐秘化;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抒情性气氛进行烘托。
“停顿”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标志之一。人物语言上的不断停顿实际上是人物内心戏剧动作的隐形展现,是一种无声的台词,是作者抒发情感、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特殊手段。这就好似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大片的空白不仅没有带来单调和乏味,反而给予观众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回味、思考的余地。这些“停顿”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充满了悲伤、欢乐、绝望和期待。著名导演、艺术家焦菊隐曾深刻阐释道:“‘停顿’是现实生活本身的节奏。越能接近生活的,便越能理解现实生活中最深沉有力的东西……它既表现一种内心纷扰的完结,同时又表现一种正要降临的情绪的爆发,或者某种内心的期待。它表现出内心活动的最澎湃、最热烈、最紧张的刹那。……这是一种最响亮的无声台词。”[1]如《樱桃园》中第三幕,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得知樱桃园被罗巴辛买得后的“停顿”正表现了二人此时此刻的复杂心理。契诃夫戏剧的静态美跟他对戏剧冲突的处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再强调紧张激烈的外在事件冲突,而是重点描写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戏剧化戏剧开始转变成生活化戏剧,视线转入到人物内心世界的细微冲突。外部世界变得平淡,甚至乏味,但是观众却能在这种平静中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微澜。戏剧冲突不再局限于具体的事件,而变成更具有抒情哲理意味的人与环境、人与时间的冲突,这也是契诃夫戏剧静态性特征更为本质的意义所在[2]。契诃夫戏剧的静态化特征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即舞台抒情气氛的营造。飘散着淡淡哀愁的抒情气氛与人物语言的不断停滞、戏剧冲突的内在化相得益彰,更烘托出戏剧的忧郁情调。
契诃夫的这种创作理念不仅对曹禺等中国作家影响甚大,而且对20世纪戏剧创作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自19世纪以来,静态化成为戏剧发展的一个趋势。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作家创造性地借鉴了契诃夫静态化戏剧的表现手法。
二、曹禺对契诃夫静态美学特征的借鉴
曹禺的早期创作主要是以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形式为主,冲突激烈,结构严谨。《雷雨》就是这样一部广受好评的代表作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禺开始厌倦这部作品,认为《雷雨》“太像戏了”[3]388,不够自然朴实,故事情节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缺乏平淡日常的生活气息。强调现实写作的契诃夫影响了曹禺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在阅读了契诃夫的《三姐妹》后,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的曹禺谈到:“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伸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灵魂……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3]389曹禺从创作伊始学习易卜生与奥尼尔到走向契诃夫,开始了对自己戏剧观念的反思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北京人》最终成为他转型成功的杰出作品。
(一)人物言行的迟缓
曹禺学习模仿契诃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戏剧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停顿”的手法。比较他的早期代表作《雷雨》和完成自我风格转换的标志《北京人》两部作品,可以明显发现曹禺的作品风格越来越靠近契诃夫的戏剧静态化特点。《雷雨》严格按照“三一律”来创作,整体上情节紧张激烈,从一开篇就围绕着蘩漪和周萍之间的爱恨纠葛来发展,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矛盾、周朴园和鲁大海的冲突……几乎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人物语言上也少有平和的对谈。各种人物之间似乎都处于一种对立冲突的状态,尤其是到蘩漪雷雨般爆发时,全剧达到了高潮。在第四幕,蘩漪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积怨发泄出来,揭发了真相,既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另外三条无辜的生命。
周蘩漪(失去了母性,喊着) 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3]170
周蘩漪(惊愕地) 侍萍?什么,她是侍萍?
周朴园 嗯(烦厌地)蘩漪,你不必再故意地问我,她就是萍儿的母亲,三十年前死了的。
周蘩漪 天哪![3]171
《雷雨》全剧节奏紧张,戏剧冲突尖锐,故事情节峰转浪急,仿佛滔滔江水一泻千里,让读者和观众感觉酣畅淋漓。但其缺点如作家自我反思时所言,这种结构和情节矫揉造作,缺乏给观众思考和回味的空间,忽视了一定的时空所蕴含的深刻内容。曹禺反思之后,借鉴了契诃夫剧中“停顿”的处理方式,旨在用生活本身的最深沉的“停顿”来暗示一种力量,表现一种情绪,让观众参与到戏剧的演出中来,体验人物的所思所想所感。在之后的创作中,曹禺明显放慢了剧情的节奏,契诃夫的“停顿”在曹禺这里被处理成了人物的言行的迟缓。对话不再是“雷雨”般地爆发,变成了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甚至无言以对。如《北京人》第二幕:
曾思懿(狞笑) 这是愫妹妹给文清的信吧?文清说当不起,请你收回。
愫方(颤抖地伸出手,把文清手中的信接下)
曾文清(低头)
[静寂。
[愫方默默地由书斋小门走出。
曾文清(回头望愫方走出门,忍不住倒坐在沙发上哽咽。)[3]518
曾思懿刁钻刻薄,言语毒辣,三番五次欺辱逆来顺受的愫方,对丈夫也总是恶语相对。《北京人》完全可以像《雷雨》一般充斥着爆炸似的冲突,饱含戏剧之张力,然而《北京人》中,剑拔弩张被不断的停顿所代替。曹禺的高明之处正是在处理戏剧冲突时,虽然表面平静,不动声色,实则人物内心活动之澎湃和紧张却是暗潮汹涌。那些看似平常、漫不经心的言行里,是曾思懿的狠毒,愫方的痛苦,曾文清的无奈和无能。往往在最无声的一刻,冲突矛盾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展现。观众于静默中体验和思考着人物精神世界的内在律动。如《北京人》第四幕:
愫方(回头望见文清,文清正停顿着,仿佛看不大清似的向她们这边望) 啊!
[文清当时低下头,默默走进了自己的屋里。……
[愫方呆呆地愣在那里。
[远远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3]561
软弱的曾文清在外闯荡未果后灰溜溜地回到家中,愫方看到心爱的男人如此无能,她惊讶地“啊!”了一声。这声“啊!”包含了丰富复杂的情感。她对文清爱得最深,希望也最大,看到他无功而返时失望自然也最大。曹禺没有再使用过多的言语动作描写,只是轻轻的一声“啊!”就把愫方的失望、心酸、后悔以及痛苦完全包含在内,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曹禺创造性地借鉴契诃夫的“停顿”手法,让沉默像火花似的放射出丰富异常的色彩,戏剧作品内涵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悠远,艺术水准大大提升。
(二)戏剧冲突生活化、内在化
契诃夫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勇敢地对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革。其戏剧观念的核心是淡化外在情节和戏剧冲突,追求一种“非戏剧化”倾向。“所谓‘非戏剧化’倾向,是指将显在的紧张的事件冲突放在暗处,而将人物间心理的、情感的冲突放置于明处;台前显示出的是片断性的,并不很连贯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抒情展示,其间没有一个构成全剧情节始末的戏剧冲突,而某个贯穿始终的行动或事件却被放在了幕后。”[4]契诃夫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并非像传统戏剧演绎的那样激烈紧凑,也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及奇遇,平常事件也并不总是突然和迅速地发生。舞台上的一切事情既有生活中复杂的一面,也有平凡简单的生活剪影。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被毁掉了[5]。
曹禺的《雷雨》是欧洲传统模式戏剧,情节与冲突在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每一幕的若干场面都是紧紧围绕着周、鲁两家三十年的纠葛展开,通过一个接一个场面的展开来推动中心情节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雷雨》紧张激荡的风格。曹禺在经过对契诃夫的学习后,《日出》、《北京人》中均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从《日出》中男男女女们的日夜颠倒、荒淫混乱的生活,吆五喝六的谈话,此起彼伏的麻将声,到《北京人》里琐碎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曹禺已经转向了对平常生活事件的描述,开始通过平凡普遍的生活现象探寻背后丰富深刻的本质。潜在于曾家的各种矛盾冲突,在似乎没有什么大的起伏甚至近乎琐碎的生活化场面中表现出来。剧中一会儿仆人告诉太太有人来讨账,这时老仆人陈奶妈又从乡下来拜节;一会儿妻子叫丈夫起床,闲扯起来;一会儿曾思懿又与曾文清为一幅画发生口角,忽而曾思懿又指桑骂槐,训斥儿媳瑞贞。姑老爷江泰三番五次在屋内大吵大闹,老爷子曾皓的棺材又被暴发户杜家看上了用来抵债,哭闹声中被强行抬走……许许多多小小的场面引出一场场风波,拜节、吃饭、三句闲谈、两声唏嘘、一场口角都可以构成戏剧场面,成为戏剧表现的主要内容,而这些也都是一个封建家庭内经常发生的事件。生活不再如“雷雨”般爆发,而是如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激不起汹涌的波浪,情节平稳而自然地前进着,完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发生发展。但戏剧这种艺术体裁所要求的戏剧冲突并未因此消失殆尽,而是转向了人物的心理内部。陈白露面对日出时的内心独白,展现了交际花在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上流社会中的痛苦、心酸和无奈。她心灵深处对过往淳朴真诚生活的怀念从另一个侧面深刻批判了金钱社会的无耻与堕落。
曹禺过去的“戏剧化戏剧”真正走向了“生活化戏剧”、“非戏剧化戏剧”,平凡琐碎的生活取代了过去戏剧中的非常性紧急事变,那些“太像戏”的因素消失了,张牙舞爪的穿插不见了,出现了以描写日常生活琐事为主的叙事性特点。在这些平凡的生活之中,作家的笔触更多地放在人物的内心活动之上,戏剧内涵愈见深厚。在这一点上曹禺显然与契诃夫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三)诗性美——舞台抒情气氛的营造
契诃夫戏剧艺术的基本风格是抒情性,这也是他所追求的“非戏剧化”演出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契诃夫总是力求在戏剧舞台上营造出一种淡淡的抒情氛围,这也是他与其他欧洲传统戏剧家的不同。舞台上的这种抒情气氛在契诃夫戏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已不再仅仅表示故事发生的环境或烘托剧情的进展,而直接是剧中人心灵的对应物,是剧中人心灵的音乐化。它与‘契诃夫情调’共同构成契诃夫戏剧抒情性与诗意品格的重要因素。契诃夫戏剧的独特的审美魅力在于,不是首先借助情节与冲突来引导观众理解戏剧人物,而是首先让观众掉入通过强调的戏剧气氛与情调的特殊感染中,从而让观众审美心灵径直进入剧中人心灵世界。”[6]契诃夫戏剧中这种带有一丝淡淡哀愁和忧郁的美,十分富有东方情味。如《海鸥》第四幕的场景描写:“晚上。只点着一盏带罩子的油灯。半明半暗。风在树枝间和烟囱里呼啸。巡夜的更夫敲着梆子。”[7]如此诗情画意的描写,烘托出诗一般的舞台气氛。
曹禺明显地借鉴了契诃夫的这种抒情形式,他摆脱了“雷雨时期”的焦躁、郁愤与闷热,在场景的描写上更加注重抒情氛围的营造。如《雷雨》第一幕的场景描写:“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3]15全剧整体风格上显得十分令人焦灼。而到了曹禺的尝试之作《日出》,这种风格就在逐渐发生变化。作家通过日常生活的片断,拼成了一幅都市生活的图景。戏剧中间插入了工人们打夯时唱的《小海号》,使整部作品充满了音乐之美。命运不幸的陈白露不断地吟唱、背诵着诗句“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身后。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更增添了一丝伤感。在契诃夫的《三姊妹》中,同样爱情不幸的玛莎也喜欢背诵诗句“海岸上,生长着一棵橡树,绿叶丛丛,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亮铮铮”,并反复出现过多次。两部作品在不经意的叙事中都蕴含着深情的诗意,读来让人动容。《北京人》里,景物描写完全变了个样,如第一幕:“白鸽成群地在云霄里盘旋,时而随着秋风吹下一片冷冷的鸽哨响。异常嘹亮悦耳……从后面大花厅一排明净的敞窗望过去,正有三两朵白云悠然浮过蔚蓝的天空。”[3]407此时曹禺笔下的秋天,萧索凄冷,空中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鸽哨声,深夜,斜风细雨,一声悠长的叫卖音从远处传来。屋内一盏孤灯,半枝残烛,诵读《秋声赋》的声音伴随着凄凉的更锣。到最后曾家彻底败落,西风呼啸,凄风苦雨,渲染出一片凄苦情调。那忧郁的、富有诗意的审美境界,与中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意境极其吻合。剧作将形式与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
三、结语
曹禺经过自身的学习实践,对艺术风格加以改进,转向契诃夫式的平淡而又意味深长,自然而又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格,形成了后期作品自然平和、诗性美等特征,为读者营造出一幅幅极富诗性美的动人画面,增加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但他在追求静态美时也没有忽视戏剧本身的特点,仍保持了必要的情节和冲突。即使是在《北京人》这样一部最“契诃夫”的戏剧中,仍然有着符合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冲突矛盾。曹禺既能“舶来”西方先进的戏剧创作方法,又保持了中国本土戏剧的特征,不愧为一代戏剧大师。
[参考文献]
[1]徐祖武.契诃夫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273.
[2]董晓.契诃夫戏剧在20世纪的影响[J].国外文学,2010(2):40-47.
[3]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董晓.舞台的诗化与冲突的淡化[J].俄罗斯文艺,2008(2):51-56.
[5](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6]朱栋霖.论中国话剧艺术对契诃夫的选择[J].戏剧艺术,1988(1):26-35.
[7](俄)契诃夫.契诃夫精选集[M].李辉凡,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