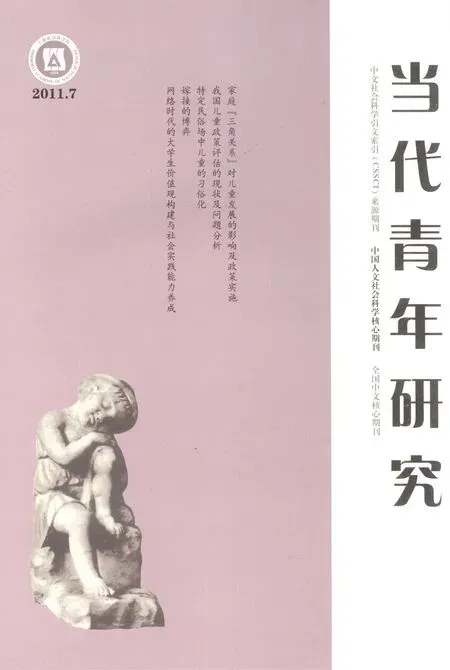特定民俗场中儿童的习俗化——以洋县正月耍社火为例
◎邓 苗
“社”,古指土地神,《白虎通义·社稷》记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一一敬也,故封土立社。”郑玄作注:“后土,社也。”以后为便于祭祀土地神,又称谓社为地域区划中一个比较小的单位。“火”,主要是指节日期间张灯结彩所形成的一个喜庆空间及其所营造的红火、热闹气氛。①社火是中国民间一种传统庆典狂欢活动,也是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和秧歌等等的通称,具体形式随地域而有较大差异。社火在我国西北地区是指正祭祀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表演。具体到洋县社火,它是一种民间综合性文化活动,包括舞蹈、杂技、杂耍、武术和鼓乐等,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年节庆典、庙会上自娱自乐的、表演性极强的民间歌舞技艺活动的总称,有的地区也称之为“社伙”、“社户”和“射虎”等。本文论及的洋县社火,早年间主要包括抬社火、地社火利骡马社火三种类型。随着时代的发展,洋县社火已经演变为主要由抬阁、早船、秧歌、彩旗队和舞龙队等组成的集歌舞、游乐、迎春和祈福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节庆活动。本文的关注对象是这诸种活动中的一种——抬阁——的表演者和观察者:儿童。我们知道,儿童(15岁以下)正处在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其性格、气质和能力诸因素正处在塑造阶段,其生活环境和接触到的事物都会对其以后的成长产生极大的影响。社火,作为一种规模较大的民俗活动,无疑会对接触到它的儿童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作为表演者和观察者两个向度的儿童——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能否藉此得出一些对儿童成长产生积极作用的经验和认识?这正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一、洋县社火概况
洋县社火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不固定),为时三天。男女幼重化好妆,穿上戏装,拿着各种木制的刀、枪,被人们绑在车上固定的铁架子上。他们在车子行进的过程中要模仿戏剧中演员的动作,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车厢里还坐着七八个成年人,其中五六个敲锣打鼓,另有一两个专门负责在社火演员的帽饰等物件掉落后帮他们重新弄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芯子”社火。对此,王杰文在《民间社火》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芯子’是表演难度最高的一种社火节目,最引人入胜,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欢迎。其基本的形式是:在一个专用的桌子上固定一根直径约3公分、高约2—3米的钢筋,然后,用彩纸在上面做出诸如花草树木、烟雾云朵、飞禽走曾种种造型:然后,按照所要表演的故事内容,将4—7岁的男女儿童装扮成戏剧人物,站立在钢筋棍的顶端,少则一人,多则十余人。孩子们有的并排站立,有的错落悬置,有的横卧,有的倒立,千奇百怪,十分惹人注目。”负载社火的车辆被装饰一新,外边只能看见司机和社火演员。锣鼓手和后勤人员被用布蒙在车厢里边。幼童们的造型、服装和脸谱是根据所设计的这一台社火的内容而装扮的。他们所扮演的内容多是一组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人们根据其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模仿出一个个社火场面,文臣武将、生旦净丑应有尽有。例如,一男一女两个幼童分别穿上男装女服,男童扮作许仙,女童一身素服手持利剑扮作白素贞,这就是一出完美的“白蛇传”。其他的还有“梁山伯利祝英台”、“牛郎织女”、“桃园三结义”、“西游记”和“沉香救母”等。早晨,各村的社火陆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县城一角,沿着县城的主要街道徐徐行进。在社火队伍行进的过程中,演员们一般都是一个姿势坚持到底,只有在休息时才会活动一下,而车厢内的锣鼓声也是响彻天地、此起彼伏。在这期间,四乡八镇来看社火的人们挤在路边,看着一车车社火缓缓前进。在这些看社火的人中间,当然也包括儿童,儿童是最热衷于看这些场面的。每年正月十五六日来县城看社火几乎成了儿童春节期间的一件大事。他们同家长到县城看社火、逛“交流会”,不但玩得高兴,而且看见了许多平时不曾见到的东西,这带给他们相当大的乐趣和刺激。在看社火这个时空场景之下,儿童演员、儿童观众和大人们共同构建了社火这个民俗场。
二、“民俗场”与作为表演者和观众的儿童
(一)习俗化
在社火这样一个民俗的时空场景中,社火的展示和表演对儿童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儿童的习俗化过程中。习俗化既指个体通过对习俗体系的学习,增长习俗知识、培养习俗意识和能力,并逐渐对习俗惯制适应的过程;也指社会群体对其成员进行习俗体系的灌输和教育,使其逐步适应习俗惯制的过程。在个体习俗化的过程中,习俗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使用工具获得产品的习惯、社会生活的习惯,以及语言交流习惯的形成。个体习俗化的内容既包括习俗知识的积累,也包括习俗技能的养成。个体的习俗化是在人的自然成长过程中进行的。人的童年行为习惯对于人的一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民俗养成的最为重要的过程,也是任何人终生必不可少的习俗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发生的时空场景即下文所说的“民俗场”。
(二)“民俗场”
在社火的表演过程中,大人、儿童和社火情节等要素共同建构了社火这一欢庆的场面。其地点在县城的大街上,参加者主要是当地的民众,时间是在春节期间。在这一系列要素的共同组合和相互作用作用之下,形成了社火这一特殊的“民俗场”。场,本是物理学中所使用的一个术语,是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对处于其能量范围内的物质产生某种影响,例如:电场、磁场和引力场。在社会学中,布迪厄借鉴了这一概念,提出了“场域”的概念,指:“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布迪厄运用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指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要求共同建立的充满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其目的是生产有价值的符号商品。这个词强调的是场域之内人们的竞争和处事策略。李稚田在1987年《民俗研究》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民俗场论》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民俗场”,并且他对民俗场的发生、传播轨迹与特征进行了理论化的研究。在此,我们认为:物理学中的“场”的概念适用于我们所研究的社火这一民俗事象,而社会学中的“场域”概念同样对我们有借鉴作用。但我们明白:物理学中的“场”有一个十分明显的、重要的中心;“场域”中的人们则没有明显的中心。虽然在李稚田《民俗场论》中对“民俗场”的表述显示山明显地向外发散“能”的中心,但我们认为在“民俗场”中,没有明显的其作用凌驾于其他要素之上的中心存在②。
在社火这个特定的时空内,人们互相吸引,共同建构了一个充满引力的“民俗场”。这一“民俗场”的形成,是由作为表演者的民众和作为观众的民众共同努力建构起来的。虽然,看起来表演者更像是一个中心,但是,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他们和观众处于同等的地位,他们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道具的作用,他们在这个“民俗场”中,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特的性格特征,他们只是代表自己所扮演的哪一个角色,与其他同伴共同营造了一种节日的民俗场面。他们的本质在于凝聚起人们的视线,增强彼此的吸引力,整合起社火场面。他们在被别人注视(包括观众的注视、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注视和所扮演的角色对自己的虚拟的注视)的同时,也在注视别人。从观众的角度而言,表演者所看到的东西,应该和观众自己所看到的一样多,甚至比观众还少。但是,从表演者的角度而言,他们所看到的绝不仅仅如观众所看到的,因为绝大多数观众所看到的只是新鲜、有趣和好玩的节日喜庆场面;而表演者在看到这些的同时,还会看到自己的表演在观众中的反应,观众中所展现的人生世态以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他们由这一切而想到的东西。表演者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相当复杂的角色,第一个是所扮演的角色,第二个是自己(作为表演者的自己),第三个是观众(作为观众的自己)。
在这一民俗场之内,具有三种人(角色):观众、表演者和被表演者。而这三种人之间是相互吸引的。观众吸引力在于观众的情况是复杂的。首先,规模庞大的人群形成了一种轰动的效应:其次,观众成分的复杂导致了同龄、同性的吸引和异性的炫耀;再次,观众活动的不一(观看的、嬉笑怒骂的和吃东西的等)导致了场面的热闹。被表演者,也即表演者所扮演的戏剧角色,他们的吸引力更多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造型、着装和脸谱的丰富多彩③。而表演者的吸引力则在其姿势和行为上。因此,各类人之间的相互吸引是这一民俗场存在的基本构成要素。
其他的民俗场要素还有社火举行的地点和时间。县城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和生活的中心,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县城的街道上进行表演,无形中就有了一种炫耀的意味。而传统春节期间的这一特殊时间则会因为节日本身特有的娱乐性而使其产生吸引力。节日时间的特殊性在于其与平时的不同,这种不同具体表现在节日期间的轻松、喜庆等因素上。由这一时间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而产生了民俗场中的吸引力。
民俗场的特殊性在于其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在民间,是一种无形的、轻松的氛围。民俗场的“场”不同于“语境”,或者说“上下文”。语境也就是背景,它是静止的、死的、无生命的;而民俗场则是生动的、活泼的、有生命的,是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进行建构的。
(三)作为表演者和观众两个面向的儿童
在这个“民俗场”中,有一类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那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儿童。儿童时期作为每个个体人生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为人生打基础的早期阶段,对于个体的一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儿童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儿童、妇女、老人和病残者一起处于一个被保护、被照管的境地,日常的生活空间总是大人、强壮者的乐土。但是在社火这一民俗场中,儿童的境地却由以往的被动、弱势地位变为主动、强势地位。因此,它对于儿童的影响就必然是巨大的、复杂的。如上文所述,在社火这一浑然一体的民俗场中,表演者当中有青壮年,也有儿童,同样,在观众中也是如此。那么,儿童(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就具有两个向度:表演者和观众。而且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其他人一道共同构建着这一民俗场。不论是作为观众的儿童,还是作为表演者的儿童,他们的处境、留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印象以及他们自身所受到的民俗影响,都是与成年人有所不同的。
作为表演者的儿童,从他们的处境上看,他们之所以选择进行这种表演,是主观希望和客观环境(主要指家长的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愿意,或者说希望,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爱玩好动的年龄段。而春节正是一个喜庆、玩乐的时空。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处于一种被家长管制的地位,而在社火这一民俗场中,他们则处在一个强势的,或者说众人注目的中心的位置。再者,在儿童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模仿的天性,一种对于表演的热衷的天性。而在社火场中,恰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表演欲。戈夫曼提出“拟剧论”,认为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是在演戏,台前的戏和台后的戏不一样,台前是做给人看的,而台后才是自我的本色。在社火这一民俗场中,儿童们则是把表演当成了生活,他们通过表演所展现的恰好是他们所期望的、所乐意的。而在平时,这种欲望却被大人们所禁锢这当然并不一定是大人们主动有意为之,而是因为缺少这样的机会。通过去扮演社火角色,儿童的本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伸张,自己内心所真正渴望表达的东西借助所扮演的角色充分地得以表达,虽然他们的这种表达不一定被大人们所觉察、所认可。他们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事迹并没有十分完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儿童可能会通过其他渠道(如大人们的闲谈、书本和电视等)对这些角色有些许的了解,而有些则一无所知。那么,对于那些有一些了解的儿童而言,在扮演的同时,这一过程则会激活他们记忆中早已储存的这部分知识,从而使之得到强化。而那些对此没有任何了解的儿童,这一过程则会增加他们的感性认识,会在他们的记忆中积淀下来、储存下来。当再次遇到这样的知识(如看戏时看到、大人们闲谈时听到和看书时看到),这部分知识就会或快或慢地被激活,这自然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增加他们的人生经验与生活阅历,成为日后生活的参考和借鉴。他们所看到的,从表面上看来,增加了生活的乐趣,满足了自己玩耍的愿望、表演的欲望。实际上,也为他们传达了——并且会潜移默化地进入他们的生活经验——这样一种信息:在如同节日这种特定的时空中,人们的行为是与平时不同的;或者更具体地说,在节日期间,人们更多的是以一种轻松、愉快、欢乐和戏谑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这不仅可以从社火所表演的各种游乐活动中看出来,也可以从观众的神情、行为中看出来。
作为观众的儿童,从他们的处境上看,大多数也是兴高采烈地同家长一起来县城看社火的。同作为表演者的儿童一样,他们感受到的也是一种喜庆和欢乐。在这个时间段内,家长除了对他们的安全操心之外,其他的一律不管,对之放任自流。在这样的民俗时空中,他们获得了自由,从而可以任情地玩耍,并且也可以向家长要各种零食吃。他们的心中充斥的是欢乐、兴奋、刺激、新鲜和有趣的情愫。他们所看到的除了同样身为观众的其他人的嬉笑怒骂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火场面了。他们当然明白:那些表演者是他们的同龄人,有的还是他们平日里的玩伴。对于他们所表演的角色(如“包拯”、“孙悟空”和“沉香”)有的或许知道,有的或许不知道。假如他们知道,或者有人告诉他们,不论他们注意与否,都注定会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难以忘记的痕迹。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关注的内容。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和同伴一块玩耍的乐趣和好吃的零食。而对于那些表演者,他们具有的则是向往的感情(当然会有不向往,或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的,但这应该是少数人的态度)。他们与这些表演者之间是一种向往和被向往的关系,因为当这些表演者高高地站在车上,穿着戏服、画着脸谱招摇过市寸,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相当有吸引力的活动。其实这也就是他们身心当中表演(模仿)本性的表现,这种情愫虽然在此时没有显露出来,但当机会成熟时就会表露出来,例如我们经常看见小孩学电视中的武打场面、学大人们的神态动作等。因此,这一方面会增加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则会强化他们这方面的本性的发展。总之,在社火这一特定的民俗场中,虽然作为表演者和观众的儿童处于不同的地位(角色),但他们对于民俗知识的接受的模式在某些方面却是一致的,而这也正反映了他们的本性。
三、社火这一“民俗场”中的儿童的习俗化对我们的启示
从表演者和观众两个面向对儿童在社火这一特殊民俗场中的习俗化过程中儿童主要接受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儿童的所观、所行和所思。所观包括社火场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欢庆氛围和成人并非有意设计的欲图使人们接受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及节日期间人们穿新衣、吃美食和进行欢庆的活动等;所行则主要是表演者进行的表演和观众对社火的参与、建构:所思具体是指他们在社火活动进行期间及以后所产生的联想和思考。
这一个过程是由当地民众主动进行的,参加者也完全是当地人。他们在进行这一当地的习俗活动时,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从成人的角度出发,却至少有两层意思希望儿童接受:其一是希望儿童习得当地人们约定俗成的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其二则是希望儿童明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具有不同寻常性。这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即是儿童所表演的社火内容的爱憎戏谑以及遵守表演秩序等内容。这一系列民俗在经过人们的表演之后,对于儿童而言,却并非会产生立竽见影的影响,其影响实际上是潜移默化式的。这个过程,同时也强化了整个社会的民俗认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要比那种有意识的社会化效果奸。因为这种影响是自愿的、无意的,因此并不会激起儿童的反感和反抗。这一过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第一,儿童的习俗化过程要与其天性相吻合,而不能采取一种先入为主的模式。我们不能在“为你好、为你的前途着想”的名义之下,将儿童的本性予以压制,或视而不见。如果这样,我们的努力如果不是失败,至少也要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了解儿童思维和行为的特点,要顺应儿童性格发展的特点而采取合适的策略,要清楚儿童行为的模仿性和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可以指导甚至帮助他们参与成人的生活,但不要轻易地否定其模仿和参与的愿望。因为这种模仿和参与对其以后的人生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早一些参与和理解就会早一些自立自强,否则就会晚熟晚知。
第二,我们要充分发挥当地社区习俗的作用,使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民俗力量能成为儿童成长的一种助长剂。儿童的天性并不适合接受那些宏观的、抽象的教化,而通过习俗这种深深融入当地社会的经验和知识,必定会使他们对社会试图加于他们的知识的接受更有成效。我们在欲图给儿童施加影响的时候,一定要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采取符合儿童好玩的天性的模式,这样我们的努力才会事半功倍而非事倍功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向儿童传达的东西虽然不一定在当时就被他们接受,但却可以储存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激活。如在社火所表现的内容中不乏“沉香救母”、“包公怒斩陈世美”、“桃园结义”等充满道德意蕴的戏剧情节,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对儿童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机会。借助社火这种生动活泼的民俗形式,不用我们挖空心思地在课堂上对儿童进行一遍又一遍的道德说教,那些我们希望儿童接受的精神品质就很自然地被儿童习得。
注:
①田荣军.社火文化研究:以宝鸡县天王镇社火为个案[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2008:9.
②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种表面上的中心地位,因为这种地位不论对于表演者自己还是对于观众而言,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③被表演者,即儿童所扮演的戏剧人物。它们在被展演的过程中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性格特点、道德品性已经内在于人们对于戏剧和历史内容的知识当中。儿童在扮演的过程中,不时做出各种动作,这更加显示出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生命力.
1.班固.白虎通义[C]//永瑢,纪昀.四库全书:子部:八零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1.
2.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94.
3.余永红.菲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民间社火现状及保护问题[J].社火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02):140-144.
4.王杰文.民间社火[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5.惠中.人类与社会[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205-206.
6.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72.
7.汤银英.物流场理论及其应用[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2007:1-2.
8.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146-150.
9.李稚田.民俗场论[J].民俗研究,1987(04):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