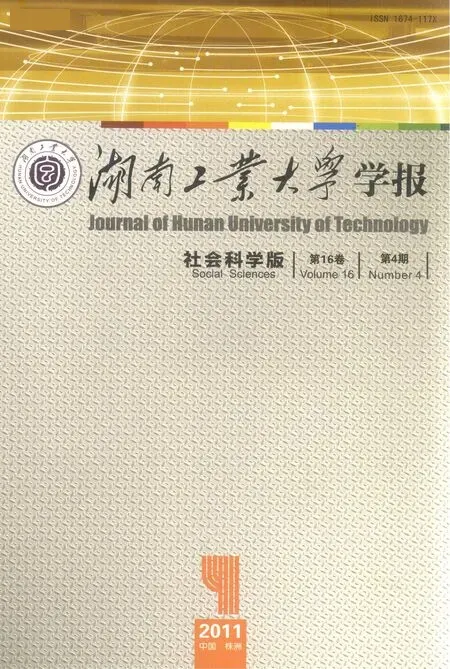论陶渊明“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段幼平
(湘南学院中文系,湖南郴州423000)
论陶渊明“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段幼平
(湘南学院中文系,湖南郴州423000)
“雅”和“俗”,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审美特质却在东晋诗人陶渊明身上得到了最和谐的统一。他儒道调和的价值取向,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吟诗、品酒、弹琴、读书的生活艺术,以及关注田园,追求冲和自然的诗文创作风格,无不在质朴中透显高雅,在超远中浸润平俗,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陶渊明;“雅”;“俗”;审美人生
陶渊明可谓晋宋之际最为独标一帜之人,他既是品质高尚的雅士,又是躬耕畎亩的俗客;他也曾未能免俗地投身于仕途洪流,却又难耐身心拘役,辞官归隐;他饮酒作诗,辞无诠次,却“词采精拔,跌宕昭章”[1]。陶渊明无论是其精神追求、生命选择,还是人生情趣、诗文创作,无不在寻常质朴中透显高雅韵致,在飘逸超远中浸润平俗冲和。“雅”和“俗”看似矛盾的审美特质,却和谐地统一于陶渊明一生,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审美人生境界。
一 退仕归隐,儒道调和:高拔凡俗的价值取向
传统儒家和道家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判定是大相径庭的。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2],“朝闻道,夕死可以”(《里仁》)。儒家认为“道”是个体生命价值所在,强调个体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功名事业的追求。儒家在重视个体“志于道”外在实现的同时,也强调对内在道德修养的把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3]。道家也强调“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03只不过这里的“道”指的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为、超越时空的无限实体,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物我相融,进而达到自我超越的最高境界。所以,道家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衡量更多的是强调个体生命与宇宙精神的契合、对真诚淳朴人生的向往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朝廷偏安江左,没有将收复中原作为奋斗目标,而是在“王与马,共天下”[5]的政治格局中,寻求宽和、偏安,这使得士人们淡忘了乱亡的心理威胁,丧失了奋发进取精神。再加之东晋玄风煽炽,士人重虚诞,轻实务,对国家民生毫无责任感,只求自全。士人个体意识的崛起带来了人性觉醒,对生命的崇拜使得士人更在乎当下的生命感受,尤其是对肉体感官快乐的把握。这种极端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让士人在奢靡的生活状态中虚耗人生。
面对俗世纷扰和精神领域中的此消彼长,陶渊明的人生价值取向则体现出儒道调和的人性光辉。他曾说:“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他渴望像曾祖父陶侃那样有所作为,鼓励自己即便功名未就,也要“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直至晚年,还慨叹“有志不获骋”。但那个时代并没有为他提供一个实现理想的舞台,偏偏他又深契于老庄哲学,质性自然,追求精神的超越和自由,因此,在世人奔波竟逐仕宦名利之时,他却选择了“击壤以自欢”的隐逸生活。晋宋之际,有许多人打着隐逸旗号,标榜着高雅脱俗的风致,却难守内心的一方净土。只有陶渊明真正放弃了俗世的种种利诱,恪守坚贞不屈的独立人格。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6]
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仕”到“隐”的人生选择,是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规范的循规蹈矩到道家人格的心灵追求的一次精神飞跃,是他“兼济”受挫,失去了外在肯定之后转向对“独善”内省的自我认可。陶渊明在归隐之后,没有像许多士大夫那样神情沮丧,意志消沉,而是用“羁鸟归旧林”的喜悦面对躬耕生活的清贫和辛劳,这都是因为他巧妙地将儒家的现实精神与庄子“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人生摆脱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纯理性和对人性的冷漠,而饱含着对质朴人生的眷念与热爱。陶渊明把寻常人生提炼为高雅脱俗的生活艺术,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代表。
二 躬耕自资,安贫乐道:平俗随顺的生活方式
儒家一直鄙视农业生产,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道”是第一要义,经世致用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两晋士人谈论玄理,游山玩水,吟月赏花,视农耕稼穑为俗务,以不染事务为高雅。但陶渊明偏偏要步入这“俗”流,不但身归田园,还亲自耕种,这无疑与当时所谓的心怀尘外高韵,不谙粗作之士形成鲜明反差。陶渊明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中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他对独立于物质之外去追求纯粹的礼乐道德的行为表示了怀疑,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个体生命只有立足于踏实、勤奋的春耕秋收才能变得切实而充盈。这些认识在“耻涉农商”的魏晋时期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陶渊明不是圣人,对生活的认识也和普通人一样经历了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例如对农耕,在归园之初,陶渊明认为:“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劳动是陶渊明内在精神返归自然的一种外在行为体现,是他保持完整人格,坚守自然人生态度的一种方式。因此,此时的亲耕垄亩更多带有一种审美趣味。但是,随着田园成为他劳动的主要场所,农耕成为维系家计的唯一手段时,他对劳动的认识就有了转变。“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陶渊明亲眼目睹了田园的凋敝,经历了从小康之家到家徒四壁的人生变故。如果他被生活的困苦、平庸和琐碎磨蚀了志向而变得怨天尤人的话,那么他与那些满口玄理,貌似超然俗尘,实则向往富贵利禄的假名士又有何区别?如何才能身处俗世又不溺于俗?陶渊明的方法就是用审美观照让世俗生活“脱俗”,努力从世俗生活中品尝出超尘脱俗的韵味,获得高雅享受。
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陶渊明从孔子的遗训中汲取了生活的智慧,当人面对生活困苦时,就应该像颜回那样用内心“道”的充盈消除现实中穷困和欲望的羁绊,这样就可以具有包容万物的博大心胸和广摄深远的眼光,捕捉到凡人忽略的生活之美和人生情致。在陶渊明的笔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耕生活虽然艰辛,但他从中获得了“但使愿无违”的精神满足,领略到了“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的人生乐趣,同时也获得了“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的人间至情。山光水色、方宅茅舍、鸡鸣犬吠、风土人情让陶渊明心境冲和闲淡,任性自得,忘怀得失。他用返归人性真淳的心态消弭了世俗中的一切丑恶和困顿,“用审美的态度对待衣食住行,以艺术家的眼光打量着身边细事,将其‘诗化’、艺术化,从俗世中辟出一片清幽淡雅的意境,体悟出一点玄澹高远的意趣。”[7]
三 吟诗、品酒、弹琴、读书:玄澹高雅的生活艺术
陶渊明在肯定了衣食住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之后,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需要,又不像两晋某些名士为一味攀附风雅过着所谓闲云野鹤的生活,他不是强作风雅的人,但他无论是饮酒吟诗、赏菊观云、弹琴读书、都有别于时人,而足见他的古风高韵。
魏晋士人大多嗜酒,张季鹰认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也说如能“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8]。饮酒行为从最初人的简单饮食之欲逐渐成为名士标榜脱俗,展现个性,对抗名教的工具,直至最后又陷于单纯生命享乐的庸俗泥泽。陶渊明却不同,颜延之说他“性乐酒德”,他的饮酒并不为满足单纯口腹之欲,而是具有高洁出俗的特质。陶渊明曾在九月九日诗中写到:“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重阳饮菊花酒,这种传统的民间风俗,通过陶渊明的诗作被赋予了一种酒关人生忧患,菊显人格品质的丰富文化内涵。他喝醉了,在自家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别人家便“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饮酒时绝弃伪饰,张显真率之情的人格风神,又岂是世俗那些用酒精麻醉人生之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陶渊明“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也。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1]2463在萧统看来,陶渊明的饮酒志趣是不同于一般人的,而是将酒与人生思考、与诗联系起来,酒已成为他人生艺术化的媒介,饮酒行为本身也就有了一种诗性的超越。
《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一张没有弦徽的素琴,又如何能弹出美妙的乐声呢?琴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因为其取材制作清雅,加之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话知音的优美故事,常常被视为文士抒发个人情思的最佳工具。伴随着魏晋以来人性的自觉,琴的社会功用也从早期儒家推崇的“皆反中和,以美风格”(马融《长笛赋》)的道德教化逐渐显示其“宣和情志”(嵇康《琴赋》)陶冶情性的娱乐作用。陶渊明说自己“少学琴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归隐之后“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琴书成为他娱情悦性,寄托情志的一种高雅方式。甚至到了晚年,他还“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与琴书相伴的生活让陶渊明平息了内心波澜,忘怀世事功名,体会到田园生活的悠闲和欢娱。至于陶渊明是否“解音”,琴上是否有弦,倒不必过于追究。《礼记·乐记》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9]从本质上看,音乐是直接从心生发出来的,而无需客观外物的介入。老子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171。所以陶渊明的“无弦琴”追求的是在弹拨琴弦的过程中获取的人生至理,是一种超越了具体声音形迹的更为深广的审美追求。
四 关注田园,追求冲和自然:清新脱俗的诗文创作
在东晋南北朝,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刘勰《文心雕龙》对陶渊明无一字涉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论札》历评自古而今的五言诗人,惟独没有陶渊明,甚至沈约在《宋书·陶渊明传》中也没有论及他的诗文创作,原因何在呢?
《文心雕龙·时序》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0]、“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10]49(《明诗》)。在这样的文学风气影响下,许多诗人热中阐释玄虚哲理,刻意雕琢藻饰,形式重于内容。颜延之是当时文坛巨擘,其诗“尚巧似,题材绮密,情喻渊深”[11],如“错彩镂金”,且能“垂范后昆”。可见,陶渊明诗文在当时被忽视就是因为诗文的美学特征与当时的文学风气和时人审美期待视野难以契合。但在遭遇短暂的冷遇后,陶渊明诗文1 500多年来一直受到后世诗家的顶礼膜拜。宋代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一引范正敏语云:“渊明趋向不群,诗采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明代何孟春认为陶渊明是“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12]王国维更是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后世仿陶诗更是数不胜数。陶诗从被冷落到被推崇,这说明陶渊明诗文的生命力,也证实了在晋宋绮密华靡的模式化创作中,“陶诗开辟的是一条与俗迥异的道路。”[13]
(一)田园题材的开拓。尽管在陶渊明之前已存在田园诗的滥殇,但田园和农耕仅是作为农业生产生活的背景出现,是衬托主体活动,表达主旨的媒介,不具有独立审美作用。随着魏晋诗人自然思想的逐渐成熟,山水和田园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也逐渐走入他们的诗文创作。但由于政治权势、门第出身、经济基础和审美风尚等因素的影响,上层贵族文人多写名山大川、亭台池苑,而鄙写稼穑,“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身心不可能进入乡村田园,不可能发现平凡的景物之美。”[14]而陶渊明却写田园竹篱茅舍、狗吠鸡鸣、炊烟山岚、春种秋收等普通农家生活,打破了以往写田园只言农家苦的陈旧模式,尽情讴歌了田园宁静、和谐、清新、朴野的审美特质,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
(二)开创了冲淡自然的诗歌风格。建安时期,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是以三曹等人为代表的慷慨苍凉之美,西晋是是以潘岳、陆机等人为代表的绮丽之美,而陶渊明却开创了冲淡自然的美学新天地。
陶渊明心念丘山,厌鄙官场,向往真纯人性的自然生活,因此身归田园,平居澹素。再加之以默为守,涵养既深,委运顺化,与自然冥和,自然就看淡了人间悲喜,他的诗正如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概括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15]这种冲淡之美在《和郭主簿》(其一)中体现得最为鲜明,诗人不用典故,不施藻饰,既无比兴对偶,也不渲染铺排,只是真情流露,就营造了一种“冲淡”的艺术境界。
自陶渊明之后,“冲淡”作为一种诗歌美学风格受到了诗家大力推崇。例如,苏轼在《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明代李东阳也说:“诗贵立意,意贵远而不贵近,贵淡而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可与知者道,那与俗人言。”(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从诗人创作角度看,一切诗文创作皆因“质性自然”的真情流露,不是刻意追求,理、事、情、物等人的生活中一切物质的与精神的都真实存在,诗人将这些真实存在如实地呈现出来;从读者的角度看,“自然”风格下的诗文给人的感觉是泯灭了人为雕琢而以本色呈现,就“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给人以至美享受。
(三)朴实无华“田家语”的运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到“诗缘情至于绮靡”。诗歌语言的“丽”与“情志”相配合,已经成为魏晋时期诗人们对文学创作的一个认识,以至于后来过于追求藻采、骈俪、用典,“铺采摛文”以达到“丽”的效果,导致了“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的后果。陶渊明诗歌大多描写的是田园朴实生活,平淡的景色不宜浓抹雕饰,所以他开创性地运用了朴素无华的“田家语”来再现生活的本色,这也是陶渊明在身心回归到“自然”后,语言也回归到一种毫无人为雕饰、去除铺金叠绣、典丽新声的语言自然状态。如: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其一)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
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给人以朴素自然之美,仿佛是从珠光宝气的贵妇堆中走出的一位荆钗布裙的村姑,让人不禁为她清新脱俗的风致所折服。
在传统的审美心理中,“雅”是以突出个性,不以追随时尚俗好为特征的,因此“雅”是阳春白雪,难免曲高和寡;“俗”是以当时的大众审美心理为目标,强调通俗、平易,所以“俗”是下里巴人,难免粗野简陋。可是在东晋,士人却将追随玄思、沉溺玄理,纵乐服药,绮丽浮华诗风等所谓“雅致”当作士林风范加以推崇,反而遗失了自我,落入庸俗的窠臼;陶渊明却能坚守躬耕田亩的“俗行”,固穷守节,老死丘园,以脱落世故,纵浪大化、委运随顺的态度洞悉生命本质,体味人生百态;用平淡冲和的田园诗风,彰显其傲岸拔俗的精神气韵、平俗随顺的生活态度,以及不同流俗的审美视野。他用艺术审美的心态观照生活,从而使他的人生平俗不失高雅,诗歌清淡,高远又平易,通俗,较好地做到了“雅”“俗”的调和和平衡,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1]萧统.陶渊明集序[M]//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出版地不详].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
[2]孔子.论语[M].程昌明,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81.
[3]杨伯峻,杨逢彬.十三经今注今译:下[M].长沙:岳麓书社,1994:2149.
[4]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54.
[6]朱熹.论陶三则[M]//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75.
[7]韦凤娟.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中国闲情[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100.
[8]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730.
[9]钱玄,等.十三经今注今译:上[M].长沙:岳麓书社,1994:887.
[10]刘勰.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79.
[11]钟嵘,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67.
[12]何孟春.陶靖节集跋[M].[出版地不详].明嘉靖癸未重刻本.
[13]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39.
[14]杜景华.陶渊明传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75.
[15]司空图,袁枚.诗品集解续诗品注[M].郭绍虞,辑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5.
Combination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 in TAO Yuanming's Aesthetic Life Realm
DUAN Youping
(Chinese Department,Xiangnan University,Chenzhou Hunan 423000,China)
The most harmonious unity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esthetic idiosyncrasies,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life of TAO Yuanming,a famous poet in Eastern Jin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TAO Yuanming resigned and returned to his rural life which is composed by his harmonious and Confucius value orientation,feeling of contenting in poverty and devoting to things spiritual,life arts of reading,poem and music,poetic writing of rurality and nature.All of these represent TAO Yuanming's special aesthetic life realm where simplicity implies elegance,vulgarity embodies overpass.
TAO Yuanming;elegance;vulgarity;aesthetic life
I206.2
A
1674-117X(2011)04-0074-04
2010-12-20
湖南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生态思维视境下的东晋诗歌研究”(10c1218)
段幼平(1971-),女,山西太原人,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