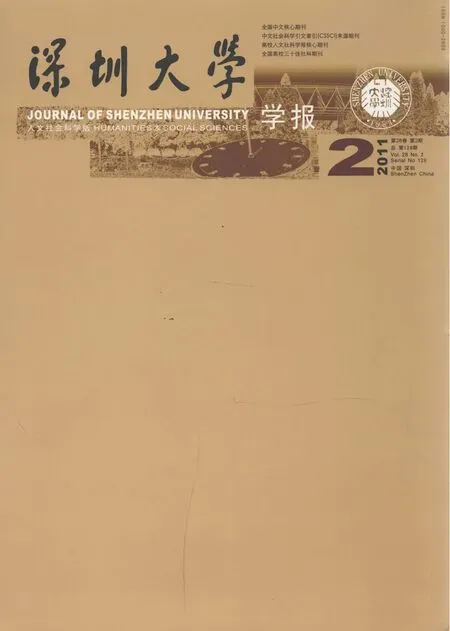分配正义与政府管理价值导向之重塑
崔宏轶,马芝兰
(1.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2.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分配正义与政府管理价值导向之重塑
崔宏轶1,2,马芝兰1
(1.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2.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进行批评借鉴,可以为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理念下政府管理价值导向的重塑提供理论资源。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价值导向应以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为基础,有效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初次分配中追求机会公平、竞争条件公平,在再次分配中追求实质的公平。
分配正义;政府管理;价值导向;和谐社会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管理的两个基本价值导向。党的十七大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在“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目标和方向。可见,社会公平、统筹发展、和谐社会已成为党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政策导向,这意味着政府管理的价值导向亦将随之重塑。本文从罗尔斯《正义论》中汲取理论资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来探讨和谐社会理念下的政府管理价值导向之重塑这个新时期的新问题。
一、分配之正义:重温《正义论》
1971年,罗尔斯出版了名著《正义论》,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P1)。一种制度,无论多么有序和有效,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即使以社会整体的名义,正义也是不可侵犯的。罗尔斯从个人主义出发,以个人利益为基点来建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即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关注的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划分的方式”。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关注,对社会基本权利、义务和利益之分配的关注,充分表明罗尔斯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强烈愿望。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
契约论是罗尔斯提出和论证正义原则的基础。罗尔斯认为,只有在一种理性的处境中进行选择,正义原则才能达成,这就是“原初状态”纯粹假设。在原初状态下,人们所选择的正义原则是“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各种基础等——都应该被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或所有这些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会有利于最少受惠者”[1](P292)。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念具体可表述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1)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2)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用以保证一种平等的分配。
实际上,罗尔斯提出了三条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包括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鉴于这些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性,罗尔斯提出了关于正义原则之间的两个“优先规则”。第一个优先规则规定,第一个正义原则优先于第二个正义原则;第二个优先规则规定,第二个正义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而且,这些优先规则规定正义原则按照一种辞典式序列来排列,只有首先满足了在先的原则,才考虑后面的原则。
罗尔斯把社会基本结构分为两个部分,即政治部门和社会经济部门。平等的自由原则主要适用于政治部门,规定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而且政治过程总体上应该是一个正义的程序。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经济部门,要求社会经济政策必须在平等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均等条件下,最大程度地提高最少受惠者的长远期望。
罗尔斯的经济正义思想带有强烈的要求平等的倾向,但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试图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建立某种平衡:一种保持某种合理效率的、尽最大可能平等的分配正义。罗尔斯认为社会中通常存在的三种分配模式,即“按贡献分配”、“按努力分配”和“按需要分配”都存在缺陷,它们只能作为社会某一部分通性的“准则”,不能作为指导整个社会分配的原则。能够作为分配正义之指导原则的东西只能是差别原则。差别原则是罗尔斯经济正义的核心,其实质是通过再分配,将社会上处境较好者的一部分利益转让给处境较差者。根据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根据差别原则,经济正义必须确定社会的“最低受惠值”,而这种“最低受惠值”必须符合代际正义并与适当的社会储蓄率相一致。在罗尔斯看来,理想的平等是“民主的平等”,即差别原则,一个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最少受惠者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二、形式的抑或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把对人的自由平等问题的关注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之上,考察了这种生产方式下的人的生存处境。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他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由自由自主的活动来界定的人的本质严重冲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处于“异化”状态。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开始思考造成这一对立的根源。他发现现代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的矛盾隐藏着这个根源。由于私有制下的社会分工,即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自发的分工,使得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这种分工的发展造成了个人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矛盾。人们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的调和寄托于国家身上。而实际上,国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仍然是同真正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国家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国家所维护的只是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因此,所谓在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观念,只是“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
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集中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关系,实质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成为商品意味着劳动者已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人”。资本家按照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法则购买劳动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它的自由平等的一面。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且剩余价值为资本家独占。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而这样的社会生产实现了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实质上又不断地再生产出剥削与奴役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不仅存在着私人利益的相互对立,而且这种对立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自由与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为维护财产所有者统治的合法性借口,正义被用来保卫一种非正义的、没有价值的现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社会公正首先是社会制度的公正,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首先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以公正的社会制度代替已经变得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在批判资本主义公正原则的过程中,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了“实质公正”和“形式公正”两个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形式上的,现成的财产所有制在制造着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消灭私有制,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消灭供求关系的统治。马克思的“实质公正”思想体现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描述中: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强制。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即经济分配方面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和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原则。
《正义论》出版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罗尔斯的正义论进行了严厉批判。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可分为3个部分,即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基本理论及理论的运用。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方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尔斯犯了3大错误:一是撇开生产来谈分配正义,二是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三是不加批判地假定社会阶级存在的永恒性,即误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社会特征当作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关于两个正义原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们在理论与实际之间都是难于相容的。明显的矛盾是,当平等的自由原则要求广泛的公民政治权利平等时,差异原则却允许社会经济不平等。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即使人们都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必然会产生严重不平等的实际效果,这种结果恰恰影响着不同的个体行使那些平等的权力,限制着平等的自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与平等观点的延续。
三、和谐社会理念下的政府管理价值导向重塑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借鉴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可以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有一个经典判断,“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2](P22)。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现实出发,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推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紧紧抓住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必须注意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单等同于只要经济增长,不顾社会发展,只要效率、不顾公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走出“GDP政府”的误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重塑政府管理价值导向,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就阶级立场、理论基础、方法论等方面而言都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有益养分,当然这是建立在去除糟粕、取其精华基础之上的。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形式与实质二分来看,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重塑政府管理价值导向有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根本上要求政府管理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某些情形下表现为替代关系,在某些情形下表现为互补关系。这种复杂性容易造成政府管理在价值导向选择上的偏差。将公平等同于结果平等的狭隘理解,使得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替代关系掩盖了公平与效率的互补关系,支配了政府管理对公平与效率价值导向的选择,造成了政府管理实践的盲点误区。要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必须全面地把握公平的丰富内容,理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与互补的复杂关系,防止片面牺牲公平追求效率或者片面牺牲效率追求公平两种错误倾向。和谐社会的建设,必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建立在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基础之上的。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基础,而公平为效率的实现提供保障。
第二,和谐社会的建设有赖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保护。在全能主义社会中,公民丧失其基本权利,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整体利益。改革开放后,公民的基本权利获得了法律的形式上承认与保护,但仍旧缺乏实质性有效保护。和谐社会的建立首先必须对行政权进行有效控制,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必须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合法利益。特别是在利益日趋分化、多元的当今社会,个人利益、集团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利益矛盾十分紧张。要消除或显或隐的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政府管理的首要任务即是公平合理地界定各方的权利与利益,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挟公共利益的名义利用公共权力侵害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与机会公平原则,虽然受形式上平等之诟病,但却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有效保护之后,社会公正才可能实现。
第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赖于在初次分配阶段实现机会的公平、竞争条件的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是和谐社会在经济运行方面的基本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初次分配的主要机制。当前我国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严重失衡问题并不是市场机制造成的,而是行政权力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机会公平、竞争条件公平的基础之上。行政权力对于市场机制运行的介入,破坏了应有的机会公平、竞争条件公平,形成了人为的身份歧视,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以行政权力替代市场机制,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自由竞争的必要条件,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这种分配失衡与健全的市场机制所导致的贫富差距不同,它是权力经济的恶果与市场经济的失灵的混合。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实现机会的公平,维护市场竞争条件的公平,是政府管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只有实现机会公平、竞争条件公平,才能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
第四,和谐社会的建设有赖于在再次分配阶段实现实质的公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25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效率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而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当前,如何从先富走向共富、从小康社会走向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任务。而这有赖于经济正义的实现,或者说,如何运用再分配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有能力行使其基本权利,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实质上的平等。罗尔斯认为,公共政策应以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导向。政府管理应关注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通过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这必然要求政府管理的价值导向进行重大的调整,实现实质性的平等应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价值基点。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张西山】
On the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Readjustment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CUI Hong-yi1,2,MA Zhi-lan1
(1.School of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2.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518060,China)
Making a critical use of the Justice Theory of Rawls by appl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value orien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of society harmony.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tect citizens’basic rights eff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Fairness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chances and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while in the redistribution the essence of justice should be stressed.
distribution justice;government management;value orientation;harmonious society
D 523
A
1000-260X(2011)02-0079-04
2010-08-06
崔宏轶(1974—),男,河南新乡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从事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研究;马芝兰(1982—),女,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从事公共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