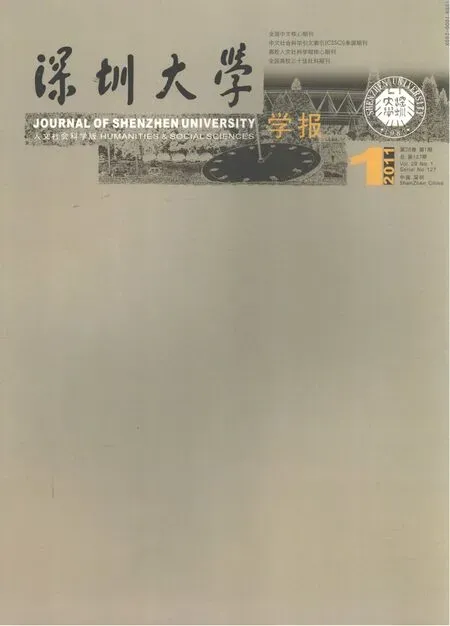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
——答国际知名学者阿莫尔多·沈之问
郁龙余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
——答国际知名学者阿莫尔多·沈之问
郁龙余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阿莫尔多·沈问:为什么1924年被翘首以待的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尽管原因多种多样,当时泰戈尔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打倒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独立解放道路和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当然,我们不应回避,当时的左派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做法是失礼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然又会犯“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同样的错误。
泰戈尔访华;阿莫尔多·沈之问;根本原因
2010年8月22~2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上,出现了三个讨论热点。其中之一就是关于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起争论的问题①。无论是会议论文还是与会者发言,许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极大兴趣。阿莫尔多·沈这位泰戈尔的小同乡,有足够理由关注自己前辈乡贤的国外评价。他为会议提供的论文《泰戈尔与中国》和他1997年写的《泰戈尔与他的印度》形成呼应②。阿莫尔多·沈认为,1924年泰戈尔访华,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反对和斥责。而现在也正是合适的时机来探究:“为什么1924年被翘首以待的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1]。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场悲剧(当然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效)[1](P4)。著名学者谭中不同意他的悲剧说,认为“中国的上层社会通过戴季陶、蒋介石,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到国际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和他在国际大学讲演中对泰戈尔的称赞已经把1924年的不愉快(我认为‘悲剧’是莫须有的)抹掉了”。[2]
阿莫尔多·沈在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是“掺杂了政治因素”,“泰戈尔到达中国之时,中国正处于一场大辩论中,其中有一部分人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部分新生积极分子却深切关注改造当今世界,不再留恋传统历史”。[1](P2)他的分析是深刻细致的,有很大的逻辑说服力。
印度著名的泰戈尔研究专家沙潘·摩炯达认为,是因为受到了西方人的影响。他说:“最早抗议与发生不和谐声音的不是中国的年轻左派,而是英国报刊。1924年4月24日的《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刊载了有关的社论与署名‘西方人’(Westerner)的读者来信。”“那封读者来信说:‘有足够的理由质问哲学家和诗人泰戈尔,他访华的目的何在?是提倡精神理想吗?如果这样的话,他夸大民族的骄傲、激起民族偏见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难道亚洲没有犯下够他关注的罪恶?难道他找不到足够的事情去鼓励中国人有高尚的思想而不是对欧洲指手画脚呀?!’有意思的是,泰戈尔在中国呆得越久,这种情绪就越膨胀以至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中发酵。”[3]
中国学者则较多地认为,是当时国内外的信息局限造成对泰戈尔访华的种种误解甚至歪曲。例如,青年学者侯传文为会议提交了一篇名为《认同、误读与化用》的论文,讨论泰戈尔对《老子》的接受。他在新著《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指出:“我国五四时期的文化人对泰戈尔也有许多误读。如在文学方面,突出了他善于幻想和超越现实的一面,忽略了他关心人生、关注实际的一面;在社会政治方面,夸大了他的出世隐退和保守妥协的一面,忽视了他作为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积极入世、斗争进取的一面;在哲学思想方面,强调了他追求梵我同一的无限境界的一面,消解了他执著生活、热爱人生的一面;在文化思想方面,强调了他因袭继承的传统性的一面,隐没了他突破创新的现代性的一面;在东西方问题上,抓住了他关于东方精神文明抵制西方物质文明的宣扬,丢掉了他对‘活生生的西方文化’的赞美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4]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刘建则强调信息的稀缺,认为:鲁迅批评泰戈尔赞美“萨蒂”,“失于偏颇”。原因是“在他那个时代,除了一些诗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译成中文,有关资料亦相当匮乏。因此,鲁迅很难对泰戈尔形成准确而全面的判断和评价。”[5]
谭中引用了尼赫鲁等人的观点,使我们对真正原因的了解又前进了一步。他说:“尼赫鲁和其他人曾经把中印两国的发展的主要分歧聚焦于一个英文字母‘r’之上——中国是‘revolution’(革命),印度是‘evolution’(进化)——,两者之者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3](P153)一个字母的差别,深刻揭示了中印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道路的不同,离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论的真正的原因只隔一道门了。
我们认为,以上学者都在尽力找寻1924年泰戈尔访华发生争议的真正原因,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们又认为,以上各家所述虽然都是重要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原因。
那么,1924年泰戈尔访华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陈独秀这个特殊人物。他是1924年责难泰戈尔访华最力者,又是最早将泰戈尔诗歌介绍来中国的翻译者③。他于1915年10月15日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四首《吉檀迦利》中的译诗。在“注”中他这样介绍:“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除了将“文学奖”误认为“和平奖”之外,陈独秀此时对泰戈尔的评价均属允当。但到1923年10月27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第20期上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尔?》一文。1924年,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集中发表了11篇文章,责难泰戈尔访华。④这些文章有三个特点:“(一)时间集中。几乎全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有时在一个刊物上同时发三篇文章,如1924年5月28日的《向导》第67期。5月30号泰戈尔就在上海乘船去了日本。显然,这些文章都是逐客令。(二)文章短小。陈独秀的文章都非常短小急促,有的只有一百多个字,如《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太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显然,这是一篇心胸狭小的骂人文章。(三)化名发表。也许陈独秀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失身份,所以都署名‘实庵’。以上三点出现在陈独秀身上,实际上反映了深刻的时代烙印、阶级烙印,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陈独秀的个人情绪。”[6]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1915年的陈独秀到1924年竟判若两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极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历史进程、社会形态、文化状况讲,中印两国在近代以前大体相似。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印两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情况。这主要表现为:
独立解放的道路不同。印度走的是非暴力的独立道路,从甘地到尼赫鲁一脉相承,其间虽有阿罗频多和S.C.鲍斯等人主张暴力革命,但始终不能成为主流。中国走的是武装革命的道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脉相承,其间虽有保皇改良的声音,但是十分孱弱。
打倒推翻的对象不同。印度自公元1600年后,渐渐沦为西方殖民地,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则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所以,印度的民族精英要推翻和打倒的,就是英国殖民当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但国家政权还掌握在代表西方列强利益的中国人手中。所以,中国的民族精英们要打倒和推翻的,首当其冲是中国的反动政府。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印度民族精英靠什么打败英国殖民者,靠留英学来的民主政治或现代科技?显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和现代科技,不但不能解放印度人民,而且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他们赶走英国殖民者、拯救民族的唯一有效武器,是印度的传统文化。所以,印度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视传统文化为神圣,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对抗殖民者的武器——非暴力,也取自于民族的传统思想。在反殖独立斗争中,武器越是民族的,就越有杀伤力。除了“非暴力”(Ahimsa)之外,甘地还有意地选用了民族语言的“不合作”(Asahayog)、“坚持真理”(Satyagraha)、“自治”(Svaraj),而决不用英语词汇。我们曾经说过,“印度学者在比较研究中知己知彼,敬祖重道,高声礼赞传统诗学”,“印度比较诗学高屋建瓴,俯视西方学术,不跟风、不失语,充满批判精神”[7]。其实,何止是诗学,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印度学者的这种自尊自爱立场是普遍常态。中国民族精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正好相反,采取的是否定与批判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孔家店”的口号,因传统文化顽固,所以后来口号中又加了一个“倒”字,非要“打倒孔家店”不可。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似乎只能看到“吃人”二字。“全盘西化”的叫声,甚嚣尘上。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有的。不过人数不多,被扣上“保皇党”、“玄学鬼”的帽子后,就几乎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中国精英要如此仇视民族的传统文化呢?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国旧政权的护身符。精英们要弃旧图新,要打倒腐朽、反动的旧政权,自然要将它的护身符一起打倒。
独立解放的道路、打倒推翻的对象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三者的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打倒推翻的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独立解放道路和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无可否认,中国自1840年尤其自1919年以后,批判传统文化的选择,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的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然又会犯“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同样的错误。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混乱、黑暗的年代。所有爱国者都在思考革命救国之道。就连出家僧人,也提出了“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不然不足以救佛教。于是出现“政治家、诗人、佛学家三位一体,造成变法、诗歌、佛学的三位一体”[8]的独特社会景象。在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出现了民族精英“手持《薄伽梵歌》赴汤蹈火”的动人场面;而在中国,很难想像会出现“手拿《四书五经》冲锋陷阵”的情景。国情不同,斗争的对象、目标不同,其策略、手段亦不同。
了解了以上情况,我们对泰戈尔1924年访华引发争议,遭到中国左派精英的嘲讽、责难,就不会吃惊了。当时,泰戈尔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这就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并导致一系列不愉快事件的根本原因。抓住了这个根本原因,其他的问题就都不难回答了。当然,我们不应回避,当时的左派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做法,是失礼的。阿莫尔多·沈一再强调,泰戈尔在印度国内和国外的文化身份是不同的。在国内,泰戈尔倡导民主、科学,甚至认为甘地太过传统而与之争论;在国外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一是因为他受到一战惨祸的刺激,的确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本质性缺陷,二是受到西方崇拜者的赞扬的裹胁。应该说,当时泰戈尔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总体上要比中国的左派精英来得全面和深刻。
随着历史的前进,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对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起的争议,有了新的认识。1956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国际大学对泰戈尔的高度评价,应该引起国际学者的足够重视。他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9]这位老资格的中国共产党人上述的这段讲话意味深长,为30年前的那场争议做了公正的结论。
1961年,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写出长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周年》。他说,泰戈尔“有光风霁月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他能退隐田园,在大自然里冥想,写出那些爱自然、爱人类、爱星空、爱月夜的只给人一点美感的诗歌,但是他也能在群众大会上激昂慷慨地挥泪陈辞,朗诵自己的像火焰一般的爱国诗歌;当他看到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及其他魑魅魍魉横行霸道的时候,他也能横眉怒目、拍案而起,写出刀剑一般尖锐的诗句和文章。”⑤“周恩来以他政治家的睿智和感召力,在政治上为泰戈尔评价确定基调;季羡林则以印度学首席专家的学术说服力,在学术上为泰戈尔评价划出了框架。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基调和季羡林的框架,经住了历史考验。因为它们是与时俱进及实事求是的,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6](P313)
在今天中国人的心目中,泰戈尔是一位道德高尚的爱国者,才华盖世的大诗人,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和中国文缘持久而深厚。这四大美好形象正好吻合中国人交友之道的四大原则:崇德、爱才、急难、惜缘。但是,由于沟通的问题,许多印度学者并不很清楚,中国人对泰戈尔有了非常一致的全新的评价。如果阿莫尔多·沈知道,也许就不会提出这个悲观的问题了。
另外,我们必须考虑泰戈尔本人对那次访华的感受。1925年,泰戈尔在《在中国的谈话》中说:“我从来不曾这样愉快,也从来不曾像与你们这样密切地与任何别的民族接触过。有些人,我觉得我们仿佛从小就已经相识。我在此逗留期间,一切都被安排得十分美好,我感到愉快。”[10]诗人在80岁时,依然对1924年的中国之旅,怀有美好的记忆。他在一首诗中深情地写道: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在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
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11]
我想,泰戈尔的这些美好感受,应在阿莫尔多·沈的“也有许多积极成果”之列吧。我们应尊重泰戈尔本人的感受,不必过多渲染其所谓“悲剧”色彩。何况在今日中国,泰戈尔在外国诗人中享有独尊地位。
今天,我们纪念泰戈尔诞生150周年,除了客观、公正、准确评价这位伟大诗人之外,还应学习他的高贵品格,毫不动摇地支持中国抗战、支持中印文化交流的坚定立场。谭中说,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我们应倍加珍惜、爱护这座金桥。
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过泰戈尔这座金桥虚心主动地向印度学习,是极为重要的。
独立以后,印度人民在自己当家作主的情况下,不拘泥于争取独立时的道路、方法及对传统文化的立场,而是与时俱进,建立世俗政权,全面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对不合时宜的部分作出限制或禁止。如“萨蒂”制度、种姓制度、童婚习俗,等等。对西方文化,凡是有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都加以吸纳利用,反之则坚决排除。凡是与民族文化相冲突的,如酗酒、杀牛、色情等等,则严加管制。印度的这些政策和作为所体现的精神,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
当下中国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五四”时代。我们须应时而进,使我们的思想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热和当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反映了百姓和知识精英回归传统精神家园的热切希望。我们应审时度势,顺应民意,认真回顾、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之路,汲取历史教训,以便制定一条跟上时代步伐、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符的新的文化之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旅途中,印度是一个极佳的参照。
加强中印文化交流,造福中印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对泰戈尔的最好纪念。
注:
①在会议论文集《泰戈尔与中国》、《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及与会学者发言中,形成了“1924年泰戈尔访华”、“泰戈尔和中国学院”、“泰戈尔与中国古典诗词”等三个讨论热点。其中,又以第一个问题讨论最为热烈。
②此文原刊于1997年6月26日《纽约书评》。收于阿马蒂亚·森著,刘建译:《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9-93页。
③陈独秀用“五言”诗形式,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第1、2、25、36首诗。
④这些文章分别是:《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尔?》(《中国青年》第20期,1923年10月27日)、《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4月25日)、《太戈尔与梁启超》(《向导》第63期,1924年4月30日)、《好个友好无争的诗圣》(《向导》第63期,1924年4月30日)、《太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向导》第64期,1924年5月7日)、《太戈尔在北京》(《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诗人却不爱谈诗》(《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太戈尔与金钱主义》(《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反对太戈尔便是过激》(《向导》第69期,1924年6月11日)等文章。
⑤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59页。这篇长文写于1961年2月21日,但当时没有全文发表。其中的一些内容以《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为题,发表于《文艺报》1961年第5期。其余内容以《泰戈尔与中国》、《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和1981年第2期。全文发表于《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之中。1978年12月17日,他在“羡林按”中说:“这是将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纪念泰戈尔的文章。由于一些原因,当时没有发表。”季羡林在这个按语中,对泰戈尔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侵略,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艺的创作,他对中国的感情在印度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响应。”
[1](印)阿莫尔多·沈.泰戈尔与中国[J].深圳大学学报,2011,(1).
[2](印)谭中.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J].深圳大学学报,2011,(1).
[3]王邦维,谭中.泰戈尔与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56.
[4]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15.
[5]刘建.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N].社会科学报,2010-08-05(6).
[6]郁龙余.中国人心中的泰戈尔[A].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2010.311.
[7]郁龙余.中国印度诗学比较[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568.
[8]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149.
[9]新华半月刊,1956,(6).
[10](印)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M].刘建译.印度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出版社,1925.112-113.
[11](印)泰戈尔.泰戈尔诗选[M].谢冰心,石真,郑振铎,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81-182.
【责任编辑:来小乔】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Disputes Caused by Tagore’s Visit to China in 1942——My Answer to Amartya·Sen’s Question
YU Long-yu
(Center for India Research,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518060,China)
Amartya·Sen asked why Tagore’s great visit to China in 1942 expected ardently by our Chinese people then caused a dispute.Though there might be many reasons,the basic one was that he advocated that the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should be upheld,which was in extreme disagreement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the th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The differences of the target of revolution decid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aths of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and the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traditional cultures.We should,of course,not avoid the fact that the leftists of the time were naive and immature and having breach of etiquette in many of their acts.Today we should not negate totally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ithout analysis,or we shall commit the same mistak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which had negated totall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agore’s visit to China;Amartya·Sen’s question;basic reason
G 112
A
1000-260X(2011)01-0014-05
2010-12-20
郁龙余(1946—),男,上海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印度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