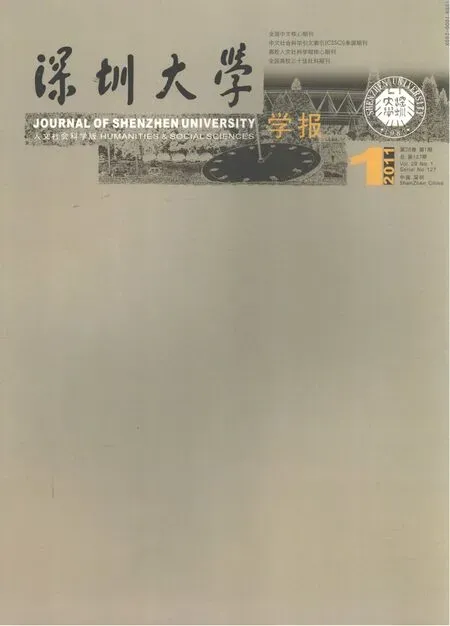唐诗山水自然生态之审美价值
李金坤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江苏镇江212003)
唐诗山水自然生态之审美价值
李金坤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江苏镇江212003)
中国山水诗的发展至唐代可谓已臻登峰造极之胜境。由于唐代诗人对山水自然美的价值所特有的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故而使得唐代山水诗别具“畅神之山水”、“感怀之山水”、“人化之山水”三种自然生态的审美价值。诗人们凭借山水,或体现个性,或感怀身世,或畅神适性,或抨击黑暗,或避世隐居,或陶冶情操;它们既是诗人创作的素材,又是诗人自由往来的精神家园。唐诗自然山水的丰富内涵,实即“天人合一”思想在唐代最为突出的体现,这对于增进当代人们的环保意识、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皆不无启迪与教育意义。
唐诗;人与山水;自然生态;审美价值
中国山水诗的发展至唐代可谓已臻登峰造极之胜境。山水自然对于唐代诗人的作用与意义是全方位、多元化的。它已完全突破了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的比德范畴,拓展了唐人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唐人抒情言志,畅神解忧,托寓感慨,诗人个性,仁心体现等等,无一不可借山水以歌咏之。翻检《全唐诗》中部分诗人集子发现,唐代诗人普遍具有浓厚的山水情结。唐人与山水之间的关系,可谓已臻山水即唐人、唐人即山水的浑然莫辨的融洽境界。由部分唐代诗人所涉“山”、“水”之多的情况可证之。王维:山,258次,水95次;高适:山,147次,水,52次;岑参:山,275次,水,114次;李白:山,770次,水,525次;杜甫:山,614次,水,443次;柳宗元:山,91次,水,52次;李贺:山,97次,水136次;李商隐:山,148次,水,127次。在这8位著名诗人中,李白、杜甫所涉“山”、“水”遥遥领先,而李白则更是独占鳌头。兹就唐代诗人笔下的“畅神之山水”、“感怀之山水”与“人化之山水”三种自然生态作一初探,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畅神之山水
山水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看法,这在《诗经》中已见其端倪。如《卫风·竹竿》末章云:“淇水悠悠,松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人可以驾舟出游,观赏景物,消解忧愁。到了屈原,因遭放逐而行吟泽畔,诗人往往借助于游览山川而发抒幽愤,同时以求得心灵的安栖。如《九章·思美人》:“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等等。到了汉魏六朝,山水美景的娱乐性特征日益为人们所发现。如左思《招隐诗二首》(其一):“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尽管人们已经感觉到山水娱情的重要意义,但还未能形成人们的普遍观念。真正普遍认识到山水娱情进而畅神之审美价值的时代,则在唐代。唐代的山水诗人,似乎人人都发表过对山水畅神消忧的切身体会。王维、孟浩然、高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且不必说,就连以“苦吟”著称的贾岛与孟郊,一旦他们置身于山水美景中亦会情不自禁地抒发欢快愉悦之情。由此可见,山水美景,在唐代诗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一座广袤无垠的天然的娱乐场所。只要进入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的需要出发而得到满意的心灵安顿、精神慰籍。山水娱情、山水畅神的价值与意义,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前文提及,在唐代诗人的抽样统计中,“山”、“水”字样在诗中出现次数最多者为李白。李白具有超乎常人的天然的山水情结。他天生“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他对山水有着一种特有的爱好与兴趣。他一见山水便精神焕发,诗思泉涌。他的山水诗中常常喜欢写到“兴”与“兴趣”,如:“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下浔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幽赏颇自得,兴远与谁豁”(《江上寄元六林宗》)。“兴发登山屐,情催泛海船”(《送杨山人归天台》)。“三山动逸兴”,“佳趣满吴洲”(《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峰隐者》)。“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自巴东舟行经翟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淹留未尽兴,日落群峰西”(《春日游罗敷潭》)。“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等。诗人面对真山真水,兴趣是如此异常的浓厚,而当他见到山水画时也依然兴致勃发,情不能已。如《当涂赵少府粉图山水歌》云:“洞庭潇湘意缠绵,三江七泽情回沿。……心摇目断兴难尽,几时可到三山巅。”诗人已完全忘掉了目前所见乃是一幅山水画了,而他似乎已陶醉于画中之山水矣!诗人对山水兴趣如此之浓,感情如此之深,其根本原因不是在于他切切实实感受了自然山水所带给他畅神解忧之好处。由超过常人的浪漫豪放性格所决定,李白笔下的山水形象多呈现出雄奇壮阔、酣畅淋漓的气势特征。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云: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百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发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云气,石作莲花云作台。
又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云: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爆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上列二诗突出描写华山与庐山的超拔与峥嵘之势,而写黄河,则突出其一泻千里、不受阻隔的冲决力之巨大。如此山水的自由之态与纵逸之势,使得李白豪放恣肆的天性找到了可以释放、可以表现、可以渲泄、可以畅神的对应自然物,这些山水形象是诗人李白心灵的折射与外现。还有诗人那些富有梦幻神活色彩的山水诗,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中势拔五岳而压倒赤诚与天台的天姥,是诗人极力塑造的一个雄奇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仙山形象。很显然,诗人是借梦中天姥超凡脱俗的雄奇形象,来释放他曾经在长安遭到压抑的自由天性,这是他一贯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体现。在李白山水系列的形象中,雄奇壮阔的黄河与长江两大河流在诗中出现频率很高。除上列诗中提及的黄河、长江外,写黄河的还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等等。据《全唐诗》,李白集中写到的“江”字共315次,“河”字出现121次,“江”字作为专名使用的频率要比“河”字高。诗人写长江,其气势雄奇壮阔与黄河相似,除上列诗中有关“长江”描写的诗句外,尚有:“一日三风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六首》其一)。“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横江词六首》其四)等等。诗人不厌其烦,屡屡描写黄河、长江,其宽广浩瀚、充满活力、雄奇豪迈、奔腾不息的特征,适与李白胸襟阔大、精神飞越、不受羈束、追求不止的主体精神特征相吻合。要之,李白笔下的这些雄奇壮阔山水形象的塑造,正是诗人借此而畅神解忧的最佳载体。因为在诗人心目中,这些雄奇超拔、壮阔非凡的山水,已完全成为其化身了。
如果说李白主要是凭借雄奇壮阔之诗境来达到其畅神解忧之效果的话,那么,王维则主要描写空寂之禅境来满足其畅神超俗之欲望的。王维诗中的禅境呈现方式主要有二:
其一,山水寂境。释教以寂灭为至高佛性,王维毕生都在坐禅诵经,体悟寂心,故其诗中“寂”字多达21次。其代表作《辛夷坞》云: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是《辋川集》二十首中的第十八首,主要写木芙蓉花开花落的情景,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从容与宁静。“涧户寂无人”一句,乃全诗之眼。涧户者,涧水之端口也。“寂无人”三字,极写环境之幽寂宁静。“无人”是补足“寂”之内涵。诗人通过幽寂无人的生态环境以及木芙蓉花开花落两由之的自然特性,充分体现出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愉悦美感。著名汉学家、法籍华人程抱一先生曾利用汉字的象形、会意等造字结构来剖析王维此诗,别具幽妙情趣。杜青钢曾转述其分析要义说:“《辛夷坞》的第一句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辛夷不同于桃、梅等树。它的花蕾开在枝的末端,形同毛笔。从其诗意,作者写了花之发。细究,我们会发现,诗中的文字结构和秩序也直观地演现了开花的过程,隐示了物我合一的幽境。‘木’喻树枝,其上多一横为‘末’,一横恍若枝头之蕾。在‘芙’中出现草字头,暗示花之萌发,‘蓉’沿用草头,笔划增多,有如微绽的花瓣。最后成形于‘花’。从象物过渡到意指,诗给人直觉美。而且,从文字结构中,还能窥见花与人的巧妙关系。五个字中均有‘人’迹。‘木末’之下有‘人’,‘芙’下见‘夫’。(蓉)字隐现人的面容,有眼有鼻有口。‘花’由人(‘亻’)、草木(‘艹’)合‘化’而成。芙蓉花乃物我之化,物、人与文字交融的植物,是主观返照于物,物我合一之花。”[1]尽管王维当初下笔时也许未有如许深意的设置,只是很普通的一种花名的称引,然而,程抱一先生却能从中引发出一种新的美学见解,委实是启人良多的。虽然难免牵强附会之嫌,但它的确是紧紧围绕“木末芙蓉花”本身而作的合理的想象,而其想象出来的幽妙之处又完全切合于《辛夷坞》的意境审美内涵,像这样的牵强附会依然是美味诱人的。正如清人谭献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2]可谓言外之意,味外之味也。
其二,山水空境。翻检《全唐诗》中王维诗集,其中“空”字共出现98次,远远超出“寂”字出现的频率。可见,“空”字,是颇能体现王维佛禅思想与境界的一个关键性字眼。王维诗中每每出现诸如空山、空秋、空谷、空林、空碛、空馆等与“空”字组合的名词。这些“空”字,并非仅仅是空间概念中的“空”,而且还是王维那颗禅心之中的“空”,是诗人勘破万物无自性、无实体后的入我空,法我空,此乃高僧大德才能恍悟的至高佛境。如其代表作《鹿柴》云: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另一首代表作《鸟鸣涧》云: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二诗巧妙地运用色空相即之法,通过以动衬静之描写,更突出空山、空林、空涧之空寂之境,而真正之用意则在于诗人以此来体味空觉、空理、空性之禅理佛趣,以达到心融物外、道契玄微而禅悦于山水之胜境。明人胡应麟认为王维的《鸟鸣涧》、《辛夷坞》诸诗已“入禅宗”,令人“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3]像王维此类充满禅意禅境的山水之咏,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诗人难以言表的禅悦之情。
李白的畅神于雄奇壮阔之山水胜境,王维畅神于幽寂宁静之山水胜境,二者取悦之对象虽然有别,但他们山水畅神解忧的效果却是异曲同工的。
二、感怀之山水
林庚先生曾就山水本身对唐诗艺术所起的重要作用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说:
诗歌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主要文学形式,它成熟得较早,又很少凭借故事情节,就更多地利用了自然景物来丰富它的想象力,于是宋元嘉以来突出地出现了大量的山水诗,使得诗歌的表现方式更为多样,这对于唐诗的艺术成就起着促进和丰富的作用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这里“山河”、“草木”、“花”、“鸟”都成了内心世界更深的揭示,如果没有山水诗的基础,是不会出现这样类型的诗句的。至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李白《灞陵行》)这些丰富的想象,也不是脱离了山水诗方面既有的成就能够单独出现的。[4]
唐代诗人借鉴前人山水诗的艺术经验,在山水诗中自觉而自然地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怀,创作了一大批情景交融、思想深厚的优秀诗歌。因此,唐代山水诗中,大部分作品明显蕴含着诗人们身世之慨的内容。阅读此类作品,必须透过山水之表象,去探求诗人的精神世界。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尝云:“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以此来考察唐代诗人的部分山水之作,其身世感慨之内蕴便自有可察。
寓身世感慨于山水的表现手法渊源流长。《诗经·周南·汉广》通过一位青年男子“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反复咏叹,表达求女不得的失望心情,汉江之水仿佛染上了一层悲凉之雾。《秦风·蒹葭》的托寓之情亦与之相似。屈骚中的《离骚》、《哀郢》、《九辩》等作品,诗人借助于大量山水景物之描写,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曹植《赠白马王彪》、王粲《七哀诗》等都是寓身世悲慨于山水景物的抒情名篇。到了唐代,诗人们承继并发展了《风》《骚》以来托寓山水的表现手法,将山水的表情达意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并未满足于以山抒发悲慨的感情层面,而是拓宽到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如张九龄《侯使登石头驿楼作》:“山槛凭南望,川途眇北流。远林天翠合,前浦日华浮。万井缘津渚,千艘咽渡头。渔商多末事,耕家少良畴。”《九月九日登龙山》:“楚国凛秋时,桓公旧台上。清明风日好,历落江山望。极远何萧条,中留坐惆怅。东弥夏首阔,西拒荆门壮。夷险虽移时,古今岂殊忧。”等等,都是将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慨寓于山川形胜之中的传世佳作。因此,“他在感怀山水诗中所显示的极其清拔孤高的气质和深刻的人生思考,使汉魏风骨在山水诗中得以传承”[5]。作为贬谪诗人柳宗元,他的山水诗中又多了一份仕途的困顿与遭贬的哀怨之情,所谓“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是也。如《溪居》诗云:“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乐有所归的诗意颇与陶渊明《归园田居》组诗相似。不过,诗人隐含其中的无可奈何的故作旷达语的哀怨之绪是不难理解的。《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云:“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末二句的“适”、“偶”字眼,表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其诗句的背后难免遭贬的怨恨之情。沈德潜尝评柳氏愚溪诸诗云:“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唐诗别裁》卷四)。这些都是柳宗元借清幽淡泊之山水抒郁愤哀怨之情的例子。他还常常借助于惊险奇异之山水直抒幽愤之情,如:“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等。哀伤幽愤之情,于山山水水之中一一可感可触。杜甫的《秋兴八首》、《登高》等杰作,更是借秋日萧飒山水之景,抒忧国忧民之悲怆情怀的千古绝唱。其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浸染着诗人“孤舟一系故园心”、“白头吟望苦低垂”的深厚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还有寓人生哲理于山水诗的千古名篇,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首二句写所见日暮苍芒之景,黄河东流,又昭示着“逝者如斯”的自然规律,未言理而理已寓其中矣。后二句为设想之辞,昭示着登高才能望远、求索方可获胜的人生哲理。“这正是盛唐山水诗因具有极高概括力而进入哲理境界的最好例证”[5](P281)。又如白居易的《白云泉》云:“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其七)云:“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二诗皆以波浪喻指社会之险恶形势,寄托遥深,象外有意。唐朝人借山水而感怀人生之作甚多,大量感怀山水诗的兴盛,大大促进了《风》《骚》所创立的比兴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和日益成熟,最终哺育了唐代诗歌意境理论这个宁馨儿的诞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人李白的山水诗,在他的全部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些山水诗,无一不是诗人喜怒哀乐情感的最佳载体,感怀气象,扑面而来。诗人“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表白并非虚言,他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这一美好愿望的。名山大川的雄奇壮丽的形象,也都一一因其灵笔所描绘而彪炳千秋,永垂诗史。“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在他的诗酒人生中,又别有一种山水人生。诗酒之豪情,又必然焕发起高歌山水的万丈豪情。每遇诗酒欢会,他必挥毫抒怀:“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同时,他又高唱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他完全把自己融化于自然之中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真因为如此,他才能达到山水即李白,李白即山水的人与自然的化境。
三、人化之山水
《诗经》中《周南·关雎》、《召南·甘棠》、《邶风·燕燕》、《小雅·采薇》等诗中,已有将关雎鸟、甘棠树、于飞燕子、依依杨柳等物象注入人格精神的倾向。到了《楚辞》的香草恶禽以及《九章》中的《橘颂》等诗,人格化的现象已趋于鲜明而突出。至于人化之山水,《楚辞》中始见萌芽现象。如“《九歌·湘君》:“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宋玉《九辩》:“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等等。中国第一首较为完整的山水诗——曹操的《观沧海》,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已烙上了诗人的精神品格。“曹操把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融而为一,通过对大海吞吐日月星辰那种壮丽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他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诗中的山水景物却被人格化了。诗人就是用这种人化了的自然形象,来抒发自我的情趣”[6]。曹操《短歌行》(其一):“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也是山水人格化的典型例子。山水人格化现象,在唐代诗人笔下已甚为普遍。人们与山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完全视其为同类而相处友好。在人与山水关系发展史上,唐人达到了空前亲密友好的程度。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江海母亲之情怀,宽厚无私,温柔体贴,格外感人。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把江海、明月、花林、流水皆人格化了,给人以亲切温和之感,与柔和多情的月光共同构成了温馨和美的艺术境界,由此拉开了唐代山水诗山水人格化的序幕。自此而下,人格化的山水名句便俯拾皆是。诸如,王湾《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宋之问《度大庾岭》:“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王维《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归嵩山作》:“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戏赠张五弟諲》:“云霞成伴侣,虚白持衣巾”;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雍陶《题君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等等。读着这些人情味颇浓的山水名句,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唐人与山水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山山水水在唐人的笔下,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庸,而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它们与人一样有思想、有感情、有人性、有人格,与诗人一起抒情言志,泄愤排忧。它们与唐代诗人一起,共同开创了唐诗的新局面。
在山水人格化的诗歌创作中,成就最著者当推李白。上文曾言及李白多喜用雄奇壮阔的山水形象来抒发其孤高豪迈的情怀。李白笔下的天姥、太白、华山、钟山、蓝山与黄河、长江等顶天立地的雄姿、跨河凌江的豪气、龙盘鲸吞的声势,无一不是他昂首天外、睥睨权贵的傲岸形象的体现。如此山水,则是烙印极深的李氏山水。可谓李白即山水,山水即李白。李白有生以来就有很深的山水情结。他早年离开家乡时曾作有一首《别匡山》,堪称是诗人山水人格化的发韧之作。诗云:
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此乃李白早期的重要作品。历代李白诗文集均未见收录,仅见于四川彰明、江油二县县志。县志录自匡山宋碑《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大明寺,兴建于唐初,葺修于北宋。匡山位于旧彰明县北、今江油县西,李白故里青莲乡在匡山之南50余里。李白青年时期便读书于此。《别匡山》是诗人告别家乡、只身远游前所作之诗。诗题以拟人手法,直把匡山当亲人;著一“别”字,依依惜别之情深寓其中。全诗八句,前六句写匡山景美、人和、情闲的交相融合,组成一幅立体的匡山胜境图,而诗人本身则是画中之一员。后二句写诗人带着歉愧的心情,请求匡山不要责怪他无心留恋欣赏的清幽之境,因为诗人已决计将自己的宏伟抱负与文武双全的本领奉献于清明的大唐时代了。“清境”一词是对前六句的高度概括,而“莫怪无心恋清境”二句,与《别匡山》诗题遥相呼应,体现了李白山水人格化的浓厚的人情意味。其他如:“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登太白峰》);“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等等,都是山水人格化描写极好的例子。而山水人格化描写最为脍炙人口者,则是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诗云: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敬亭山在宣州(今安徽宣城),宣州乃六朝以来江南名都,谢灵运、谢朓等都在此做过太守。谢朓常来敬亭山登临吟咏,因此而为其在山上建了一座“敬亭”,敬亭山由此而得名。李白非常喜欢“二谢”,尤其是小谢。正因为此,诗人对敬亭山亦就格外挚爱。李白一生七次来宣州,此诗是诗人于天宝十二载(753)秋游宣州时所作,其时与他被迫离开长安已整整十年了。期间,诗人飘泊四方,处处遭受白眼冷遇,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使他日益感觉到孤独无友的痛苦。人世间的冷若冰霜,肮脏龌龊,使得一向孤傲的李白不得不投向无私的大自然的怀抱,所谓“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是也。李白的明月之诗、山水之诗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大自然的博爱与无私。诗人每到宣州,他就觉得格外亲切,因为在这里,有他推崇的诗歌偶像谢朓,以及谢朓登临敬亭山的足迹。李白心中的敬亭山,已非一般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敬亭山,而是最可爱的友人、最值得信赖的亲人。李白诗中多次写到敬亭山,如:“敬亭惬素尚,弭棹流清辉。冰谷明且秀,陵峦抱江城。”(《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敬亭白云气,秀色连苍梧。下映双溪水,如天落镜湖。”(《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春日独酌二首》)等等。基本了解了《独坐敬亭山》的作诗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此诗,题旨便一目了然矣。开头两句,说鸟飞云去,此乃诗人仰视所及,其中暗示着一个诗人所见的时间过程。本来敬亭山上空有许多鸟儿在翱翔,结果皆一一飞走了。看见鸟飞走了,唯独一片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的绕山之云(想必起初也是众云绕山的,不知何故,也都纷纷飘离敬亭山而去,但却独有一片云未离开,还想继续陪伴敬亭山),终究经不住飞鸟们的引诱,结果也晃晃悠悠地离去了。此时此刻,敬亭山是孤寂的,诗人也是孤寂的。鸟飞云去的“无情”结局,给敬亭山与诗人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然而诗人与敬亭山的“相看两不厌”的现实情景,又使得诗人与敬亭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相”、“两”二字,同义复指,“不仅诗人看山,山也在看诗人,这是何等的天真!仿佛是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一切都有了生命,一切都富于性灵”[4](P132)。而且,诗人“相看”的感悟,与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情感活动形式有别。陶渊明是此情飞向彼山的单项活动,而李白则是此情飞向彼山、情又对面飞来的同时双向活动,体现出双方感情的一致与融洽。此外,“相看”之“看”,具有一看再看,莫逆于心的持续性,这又与“悠然见南山”之刹那间的感兴不同。李白从自己的静“坐”默察中,已确切体悟到敬亭山与自己那种心心相印、互不厌猜的亲密感情,大有“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快慰感。末句“只有敬亭山”是诗人在与鸟飞云去的冷酷无情的现实比较以及“相看两不厌”的感情体验之后得出的牢不可破的结论。“只有”二字,斩钉截铁,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与敬重。此乃一首极为典型的山水人格化之杰作,其寓意甚明,即以鸟、云喻指那些排挤、打击、疏远自己的奸佞小人;以鸟飞云去的无情比喻世态炎凉的冷酷;以敬亭山喻指理解、关心与支持自己的最亲密友好之知音。要之,此诗通过将敬亭山人格化的表现方式,婉曲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孤愤与为世疏远的孤愁。以山写人,寓意深刻;象外之意,涵咏不尽,真乃“传‘独坐’之神”(《唐诗别裁》卷一九)。李白所建立的“相看两不厌”的“人”“山”相亲的情感模式,又为后来的辛弃疾所承传,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较之李诗,辛词少了一分“两不厌”的坦诚交流,却平添了一分缠绵而浪漫的情思,而以人格化的山来写诗人之孤独情怀,则是一脉相通的。
以上就唐代山水诗中的“畅神之山水”、“感怀之山水”与“人化之山水”三种自然生态作了简要论析,由此可见,自然山水对于唐代诗人的作用是多元化、全方位的。诗人们凭借山水,或体现个性,或感怀身世,或畅神适性,或抨击黑暗,或避世隐居,或陶冶情操;它们既是诗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又是诗人自由往来的精神家园。唐诗离不开山水,山水成就了唐诗。山水由唐诗而妩媚,唐诗因山水而生辉。此乃刘勰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江山之助”。
自然山水诗,是唐诗之大宗。其诗歌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广泛性、丰富性与空前性,实即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唐代最突出的积极反映。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诗歌创作与人文思想资源,对于增进当代人们的环保意识、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皆不无启迪与教育意义。
[1]杜青钢.披褐怀玉,琐物纳幽[J].外国文学评论,1996,(3):86-91.
[2]谭献.复堂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
[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119.
[4]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65.
[5]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178.
[6]蔡厚示.山水即人[J].古典文学知识,1992,(4):8-12.
【责任编辑:来小乔】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Tang Poems of Landscapes
LI Jin-kun
(School of Humanities,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Jiangsu 212003,China)
Chinese landscape poems reached the acme of perfe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As Tang poets harbored deep feelings and profound knowledge and in-depth awareness about the values of landscapes,poems of this type are characterized by 3 sorts of aesthetic values of ecology:landscapes of refreshment,of mental reflections and of personification.The poets,by depicting landscapes,expressed their personal individuality,or reflected upon their lot,or refreshed their mind,or criticized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or enjoyed their reclusive life and refined their sentimen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e.Landscapes provided both rich materials of composition and spiritual homes for the poets.The affluent implication in the Tang landscape poems is in reality the most outstanding embodiment of the idea of“harmony of man with nature”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education in reinforcing contemporary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and secur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man and landscapes;ecology;aesthetical value
I 207.22
A
1000-260X(2011)01-0100-07
2010-03-10
李金坤(1953—),男,江苏金坛人,江苏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