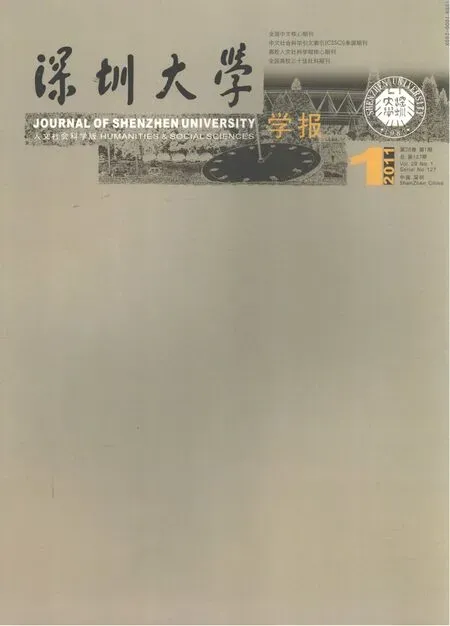《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马珏玶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马珏玶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叶宪祖《鸾鎞记》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
叶宪祖;鸾鎞记;晚明;才女文化
借历史人物写时代风情,是古典戏曲的经典手法之一。明人叶宪祖(1566-1641)创作的传奇《鸾鎞记》,即是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该剧通过赵文姝与杜羔、鱼玄机与温庭筠两条情感线索,讲述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那么,该剧与明代中后期蓬勃发展的女性文学,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的才女文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血脉勾连?剧中女性人物的形象建构及其叙事设计究竟如何受到晚明才女文化的影响?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那么,《鸾鎞记》着意塑造了怎样的女性特质?
第一,对女性优秀品格的褒扬,特别是才情第一的推崇。《鸾鎞记》刻画了赵文姝、鱼玄机、赵母等众多女性形象,并对女性人物言行举止体现出的高尚品德深加赞许。
鱼玄机舍身救友,剧作者不仅特设《仗侠》一出以醒众目,而且借剧中人之口反复予以揄扬。鱼玄机自言此举“比似夜出荥阳解楚围”,因为“自古为朋友者死”,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赵文姝赞美道:“昔卫寿窃旄以代兄,纪信忍烹而诳楚。妹妹的义气,何忝于两人”、“矜义侠,敢捐躯。古有黄屋将军,今属青闺黛眉”、“寻生替死德无伦”(《仗侠》);杜羔则赞其为“女中侠客”(《谐姻》);最后一言以蔽之:“尽将女侠标奇异,凭教打入英豪队”(《圆成》)。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剧第三出《闺咏》中,赵文姝自道:“自小聪明,爱观书史,镇日幽静,好就诗词。除了班家女师,那左贵嫔、鲍令辉也则寻常。”第二十出《春赏》,剧作者借太和公主之口盛赞了鱼玄机的诗才:“那些人间粉黛,怎比仙姿?这还不足为异,鱼炼师的诗词歌赋,当世罕出其右,这才可敬。”明确指出女性的可敬可爱,不在容貌在诗才,对女性才情的推崇溢于言表。
第二,婚恋观念的通达。在《鸾鎞记》中,剧作者一方面首肯传统的婚姻观,即婚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正礼,因此设计女主人公赵文姝面对权贵的逼婚愤然拒绝,甚至不惜以死相抗。危机化解后,又火速安排杜羔入赘赵家,以维护婚约的神圣性和赵文姝的贞洁。另一方面,剧作者也有意识地在《闺咏》一出将赵文姝萌动的春情予以刻画。
人们不仅可以从中体味到闺秀的思春情态,剧作者肯定女性情欲合理性的创作态度也显而易见。
首肯传统婚姻模式的同时,叶宪祖对女性的婚姻观又表现出通达的态度。鱼玄机以女冠身份交接男性文人,实属违滥。然正如后世学者所言:其“男女之欲岂其性与人殊哉!”[1]因此,尽管私订终身不仅于礼有碍,即使结合亦应断离。但剧作者却超越历史真实,以艺术手法虚构了鱼玄机的行为和命运,将其塑造成守身如玉、慷慨任侠的正面女性形象,颠覆了历史评价和传统形象。唯其如此,她与温庭筠之间的感情才显得纯洁真挚,她的再醮之举也因而变得合情合理。郑振铎认为:“(《鸾鎞记》)中间插入温飞卿与鱼玄机之姻缘遇合,牵拢得很可笑。”[2]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公允。
鱼玄机的心路历程在剧本中清晰可见,而又层层递进,她对朋友的慷慨任侠和对情感的执着同样令人感动,而面对赵氏做媒时的羞涩回避之态愈发显出她的纯情和天真。
第三,女性主体意识的鲜明体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鸾鎞记》中的女性们表现出对命运的强烈关注并自主设计人生。
无所畏惧地反抗强权。赵母虽是一介贫寒寡妇,却当场拒绝当朝宰相为其友人李补阙的提亲之请。其女赵文姝也宁死不背叛婚约。逆来顺受的妇德训诫与民不斗官的处世法则在此喑然失声。
赵文姝婚后主动催促丈夫上京应举,在其落第后仍写诗激励其继续参加科考。杜羔中进士的捷报传来,赵文姝不免得意:“不是我昔年相劝勉,今日里缘何得上天?”(《捷贺》)遂题诗相贺:“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杜羔金榜题名的结局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夫贵妻荣的回报证明了她的远见和英明。《唐诗纪事》确有杜羔妻寄诗的记载,然字句有出入。剧中杜羔认为其妻所寄前一首诗语句激切,后一首诗语句秾丽,“这般诗才,不怕杜羔不退避三舍。”(《京晤》)剧作者将杜妻一腔忧思化作卿卿我我的呢喃。吕天成《曲品》“鸾鎞”条则以为:“杜羔妻寄外二绝,甚有致。曲中颇具愤激。唐时进士题名后,可以遍阅诸妓。必作羔醉眠青楼之状。而其妻‘醉眠何处’之句,猜来有情耳。”[3]
自主设计人生。鱼玄机为了友情,舍身相救。到京城李亿已死,拒绝李亿之妻要玄机改嫁其兄弟的建议后,鱼玄机毅然出家为女冠。但她出家后积极参与世俗生活:“连日到施主人家修斋,不曾上殿参礼”(《入道》),且与皇室亦有往来,并一直暗中寻觅乘龙快婿,最后终于与心上人盟定今生。“在鱼玄机身上,交织着家庭生活给予她的压抑着的痛苦和道观生活加给她的隔绝人寰的寂寞,所以她的追求和反抗更加强烈,更带有典型性。这一形象比之晚明传奇中青年女子对爱情的追求和反抗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通过这个形象既表达了作者对于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切,同时也传达出作者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呼声。”[4]
二是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故的深刻体察。古代社会,女性以家庭为生活重心,对男性有人身依附关系,与男性相比,和社会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鸾鎞记》中的女性却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体察。她们对人情世故并不陌生,反而颇有见识。
“做媒为活计,说合是生涯”的媒婆在剧中虽是丑角,但她的职业敏感性和视交往对象的身份地位而采取不同态度的交际手段委实值得注意。《觅赠》一出中,媒婆虽心有所许,但身为官媒婆,面对当朝宰相令狐绹为友娶妾的要求,她却一口推托:“初至京城,这京中女子不曾遍识”,及至宰相表示襄阳女子更好的时候,她才推出赵文姝这一人选。此举不仅是媒婆要表现自己对宰相嘱托的慎重,而且以退为进的手段更容易奏效。当媒婆见到一起前去的官差,立刻判断出此人“路上不好打发”,果然官差提出了娶妾的要求,媒婆巧舌如簧,既拒绝了官差,又未惹恼他。及至到得赵家提亲被拒,又是媒婆出主意造成赵家骑虎难下的局面。媒婆之举虽属可恶,但其察人之明、度人之准、权变之巧可见一斑。
赵文姝不肯连累朋友,鱼玄机说道:“若优游无事,日逐往来。一旦有事,便掉臂不顾,岂是人之所为。”(《仗侠》)虽是有感而发,却似有所指,颇有讽世骂道的意味。当鱼玄机决定舍身救友时,并未与赵氏母女哭做一团,而是叮嘱道:“只有一件,还须厚赂居间,免使临期露机。”其处事冷静、心思缜密的性格特点不言自明,而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也颇见力道。
赵母“苦守未亡年,贫居只自怜”,但当朝宰相为补阙行聘其女时,她却清醒地意识到:“送与恶姻缘,少不得活离死怨”(《仗侠》);当邻女愿冒名顶替时,赵文姝尚不肯移祸诗友,赵母当机立断道:“我儿,鱼家姐姐既有这等高谊,我们拜谢”,既使文姝摆脱了一女二嫁的祸事,保全了自己的家庭,又让事情再无反复的余地,并且避免让女儿产生不义的自责心理。鱼玄机自愿以身相替后,她亦并未乐而忘忧:“鱼家姐姐虽则去了,还怕中途有变。明日黄道吉日,不免迎杜郎过门赘亲,绝了后患,多少是好。正是:早谐男女愿,永断是非门。”其对攀附高门一事的本质认识可谓一针见血,对寒族闺秀无力自保的见地也属的论。
《鸾鎞记》表现出如此鲜明的女性意识,与晚明才女文化的发达密不可分。明代女性文学,特别是明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发展颇为迅速,“从现在的角度看,我们听到了一些女性的声音,看到了明代女性书写的一些特殊风格,和时人藉此修改男性文化的愿望”。[5]而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6]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
根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考录,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女性文人及其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除了传统的诗歌领域,以叙事见长的弹词和戏曲领域也活跃着女性作家的身影,以致于社会上由此出现了女子无才是德的反拨言论和壸德焦虑。另外,正如高彦颐《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所言,嘉兴黄氏、山阴祁氏、桐城方氏等晚明江南女性社团的纷纷涌现及其积极活动,一方面增加了女性群体内部的情谊交结,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女性的文学自信和社会认知与交往能力。再次,黄媛介、王端淑、文俶等职业画家、职业作家以及闺塾师等职业女性的不断涌现既是女性谋生自立的现实途径,也是女性主动关注并参与自我人生发展的明证。此外,女性的帖括造诣也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揄扬,而其由此对家族成员的成才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明人光禄卿文翔凤的姐姐文氏,是祠部文在中女,葛大受妻,据文翔凤《哭姊诗》自注:“大人家庭谈学,惟以姊代子,予亦师父友姊。”(《宫闺氏籍·艺文考略》)“精帖括,断决不爽”[7]的杨文俪,“诸子成进士者四人,钅龙、铤、钅广皆至尚书,钅宗至太仆寺卿,皆文俪教之。”[8]沈德符也特地对女性“娴习时艺,评骘精确”[9]的时文造诣加以揄扬。
那么,《鸾鎞记》与明代中后期蓬勃发展的女性文学,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的才女文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血脉勾连?该剧女性人物的形象建构及其叙事设计究竟如何受到晚明才女文化的影响?叶宪祖本人的境况对其《鸾鎞记》的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科举荣家传统的影响。叶宪祖的祖父叶选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父亲叶逢春嘉靖四十四年(1556)进士。叶宪祖的母亲吴氏,是济南知府吴至之女,封宜人。其父叔仁“夜入室,仍篝灯以读,宜人不为讶,谓:‘男子励志当如此。’谨治食饮,执女红对之。嘉靖戊午,叔仁举于乡,宜人意稍慰,益勤佐读。……子宪祖,幼就塾师,夜入内,宜人必取所授书,口助之诵。比明,辄熟诵。师讶其颖异,然不知宜人训之也。叔仁五十八捐馆,弗跻上寿。宜人痛焉,则益督宪祖学。”[10]叶宪祖所“娶邵氏,赠恭人,佥事梦弼之女。继梁氏,封恭人,参将仲海之女。”[11]出身仕宦;母亲相夫教子,助其成才;嫡妻和继妻也都是官府千金,叶宪祖的承训经历及其女性家庭成员的出身境况决定了科举对他的生活及创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光耀门楣、夫贵妻荣自然就成为叶宪祖的人生追求和屡败屡战的动力源泉。联系剧中赵文姝在丈夫中进士前后的两次赠诗之举,徐朔方先生认为叶宪祖“本人多次落第,妻子出身官府,夫妇之间也可能有近似的经历,虽然方式可能不同。”[12]可见,晚明才女文化的风行与家庭女性成员的关系不仅促进了叶宪祖《鸾鎞记》对女性品德的肯定及才情的推崇,而且使他真切地体会到女性参与人生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科举实况与诗坛品评的影响。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已二十九岁的叶宪祖才在南京乡试中式,之后连考九次,方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因此他对科举落第有切肤之痛,对科考情状也有深切的了解。崇祯十一年(1638),叶宪祖曾写信,为女婿黄宗羲科场之事关托祁彪佳。《鸾鎞记》创作于场屋困顿之时①,因而在《论心》、《觅赠》、《合赞》、《摧落》、《劝仕》、《廷献》等出,剧作者对科举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予以尖锐地批评,揭露了当权者左右科考、漏题、倩人代作等严重问题,而《催试》、《诗激》、《捷贺》等出则对举子及其家人在其科考前后的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细致生动地刻画。另一方面,该剧也以科举成绩为标准来突出其女性人物的才华与自许:
(旦)妹子,我二人如此诗才,若去应举,那女状元怕轮不到锦江拾翠的黄姑。
(小旦)正是。若使天下词坛,姐姐主盟,小妹佐之,那些做歪诗的措大,怕不剥了面皮。[13]
鱼玄机所居之咸宜观,“户外之履常满,笥中之句频投”,尽管乞诗、投诗者尽为京中“王孙公子,骚人墨客”,但从第十五出《品诗》侍女转达鱼玄机的品藻之辞,凸显了来者的文字粗劣,俗不可耐。鱼玄机以女冠身份直言品评众多男性文人的诗作,意味着剧作家将品鉴批评的话语权赋予了被传统文化视为不善诗的“第二性”,其为女性才华张目的用意不容忽视。而绿翘“可人期不来,俗子推不去”之言,或可视为鱼玄机对文坛诗歌创作状况批评的间接传达。明代女性的时文造诣与文学修养由此成为叶宪祖《鸾鎞记》的催化剂,催生了其对女性社会认知能力的真切表达,也再次印证了才女文化的盛况及其在文坛的一席之地。
第三,真情到底的社会风尚的影响。晚明社会,传统婚恋观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继续主导着现实生活中的男婚女嫁。同时,人性的觉醒和情欲的重视又成为晚明思想解放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戏曲创作领域,就是汤显祖为代表的至情论大行其道②。叶宪祖本人即为主情一派,他在《广连珠》中说道:“梦是真而真似梦,煮残一勺黄粱;生可死而死可生,唤起三年红粉。是以仙家破安,先从妄处穷源;词客钟情,且向情场证本”[14],与汤氏宣言一脉相承。
叶宪祖现存戏曲很多都是言情剧:杂剧《四艳记》③的四个短剧《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素梅玉蟾》都抒写了女性咏月嘲风,寻求爱情归宿的故事;改编自《窦娥冤》的传奇《金锁记》、据《剪灯新话·翠翠传》改写的杂剧《金翠寒衣记》都是改死离为生聚,令生、旦当场团圆;杂剧《团花凤》取材《绯衣梦》和《后庭花》,将一场公案化为佳话,等等。“作者用这么多篇幅,费这么多笔墨,又引出这么多人来参与完成,在本剧是独有的,这足以证明作者对玄机身世的关切,也更说明作者此剧对以玄机为代表的女性问题的郑重探讨。”[15]
当然,剧中鱼玄机虽曾为李亿之妾,入道观后又交接男性文人,但她始终保持着处女之身,这种身份的设定体现了剧作者女性意识中保守的一面。联系古代女教对贞节的重视,即使是在开放的晚明,虽然剧作者本人风流放荡,在刻画正面女性形象时,也仍然无法摆脱贞节观的束缚。通过剧本的研读,不难看出,鱼氏的处女之身既是鱼、温爱情的前提,也是能够引发读者体谅其处境、赞叹其结局的基础。
鱼玄机历史上虽确有其人,但其放荡风流为人周知。《三水小牍》、《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都记载了她的生平事迹。她原为李亿妾室,后为李妻不容,托身于咸宜观,后竟以杀女奴绿翘处死。鱼玄机生前确与温庭筠有来往,但温氏只是她众多的交往对象之一。[16]“(鱼玄机)虽与庭筠相识,未必属意庭筠,无所为嫁庭筠事也。……以玄机配合庭筠,盖作者之意,以庭筠有才而沦落,玄机有才色而飘零,以为二人相偶,庶几无憾耳。”[17]对女性情欲的正视和传统婚姻观的影响交互作用,致使叶宪祖大幅度改写了鱼玄机的人生,将一个越界的女性纳入到正统的婚姻体系中,令其初嫁充满侠义色彩,而再醮则完成了才子佳人的神话。
总之,叶宪祖《鸾鎞记》的创作体现出与晚明才女文化的密切关联,因此,才情第一、德行高尚、坚持自我追求等方面成为该剧女性人物的核心特质,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叶宪祖的创作对明末剧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值得我们重视。
注:
①魏奕祉《<鸾鎞记>校点说明》推断《鸾鎞记》“约成于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至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期间”,见﹝明﹞叶宪祖撰,魏奕祉校点:《鸾鎞记》,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页。徐朔方则明确《鸾鎞记》创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后,详见徐朔方:《叶宪祖年谱》,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②按:孙钅广《湖广郧阳知府和斋叶公墓志铭》云:“隆庆戊辰,迁抚州通判,威少霁,喜进诸生如故。今汤礼部显祖在诸生中未有闻也,公独异之,汤生名由此起。辛未会有荐公文似华州者,执政奇之,擢都水主事。”﹝明﹞孙钅广著:《孙月峰先生全集》卷十一,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叶宪祖的父亲叶逢春隆庆戊辰(1568)迁抚州通判,隆庆辛未(1571)升为都水主事;而汤显祖生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隆庆庚午(1570)乡试中举,万历己丑(1589)升南京礼部主事,此处明确指出叶逢春对汤显祖有知遇之恩。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万历四十四年(1616)所作《负负吟序》中回顾了平生于己有赏识、提携之功之人:“予年十三,学古文词于司谏徐公良傅,便为学使者处州何公镗见异。且曰:‘文章名世者,必子也。’为诸生时,太仓张公振之期予以季札之才,婺源余公懋学、仁和沈公楠并承异识。至春秋大主试余、徐两相国、侍御孟津刘公思问、总裁余姚张公岳、房考嘉兴马公千乘、沈公自邠进之荣伍,未有以报也。四明戴公洵、东昌王公汝训至为忘形交,而吾乡李公东明、朱公试、罗公大紘、邹公元标转以大道见属,不欲作文词而止。眷言负之,为志愧焉。”﹝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4页。该序特别提及汤显祖为诸生时对他有深刻影响的诸人,除何镗外,包括时任抚州同知张振之、抚州推官余懋学、南昌推官沈楠,但对叶逢春只字未提。从上述材料来看,汤显祖与叶逢春应该是有过交往的。那么,究竟是汤显祖年高忘事,还是孙钅广过誉叶逢春,或者是叶逢春与汤显祖对二人交往一事的认知出现偏差?真相如何,存疑待考。
③《四艳记》究竟是杂剧还是传奇,明代至今聚讼纷纭,参见谭坤《叶宪祖的杂剧创作》,《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明人胡文焕所编《群音类选》第一次提出南杂剧的概念,叶宪祖也是明代南杂剧作家之一,参见徐子方:《文人剧和南杂剧》,《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1期,2003年1月版。我的同事孙书磊教授向我指出《四艳记》当属南杂剧,特此致谢。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90.
[2]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三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9.
[3]吕天成.曲品[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34.
[4]魏奕祉.叶宪祖及其〈鸾鎞记〉[A].戏曲研究:第十九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5]俞士玲.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A].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6]江庆柏.苏南文化望族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7]朱彝尊著,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23.
[8]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2447.
[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595.
[10]诰封叶配吴宜人墓志铭[A].孙鑛.孙月峰先生全集:卷十一[C].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11]黄宗羲.外舅广西按察使六桐叶公改葬墓志铭[A].黄宗羲全集:第十册[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2]徐朔方.叶宪祖年谱[A].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卷[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494.
[13]叶宪祖撰,魏奕祉校点.鸾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6.4.
[14]叶宪祖.广连珠[M].藜照庐丛书本.19.
[15]叶宪祖著,詹怡萍评注.鸾鎞记评注[A].黄竹三、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第十二册[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61.
[16]梁超然.鱼玄机考略[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17]曲海总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24-625.
【责任编辑:向博】
Luan Bi Jiand Talented Female Culture in Late Ming Dynasty
MA Jue-ping
(School of Art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China)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female literature,the prosperity of talented female culture in particular,in late Ming Dynasty infused vitality into the literary community,and provided more materials and inspiration for male writers in their creation of romantic stories about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YE Xian-zu’s drama Luan Bi Ji not only became the artistic illustration of females’life,especially talented females’life in late Ming Dynasty,but also was rather popular when performed in that period.It had still been performed until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YE Xian-zu;Luan Bi Ji;late Ming Dynasty;talented female
I 207.3
A
1000-260X(2011)01-0113-05
2010-10-18
南京师范大学哲社跨学科重大项目“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研究”(0909023)阶段性成果
马珏玶(1971—),女,甘肃天水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明清小说和古代女性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