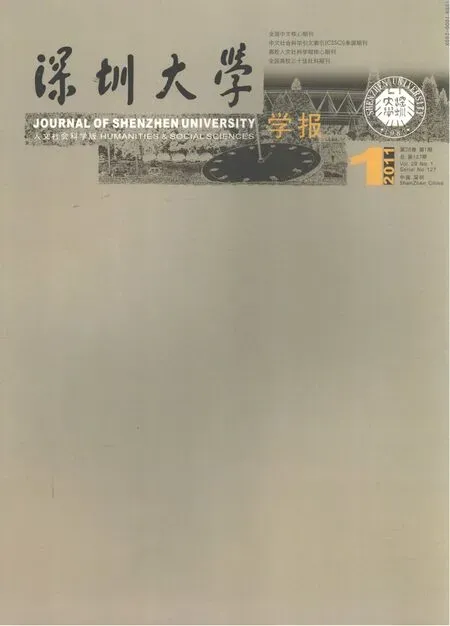近年来我国电视重大报道的若干反思
彭华新,欧阳宏生
(四川大学新闻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近年来我国电视重大报道的若干反思
彭华新,欧阳宏生
(四川大学新闻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近年来的电视重大报道凸显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是当今时代无法破解的悖论,但追根溯源,可以找到悖论的根基;从电视对灾难报道、危机报道和盛会报道三个场域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在灾难报道中诉求人文精神,报道中就没有宏大与细节之争,在危机报道中回归精英主义,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矛盾也迎刃而解,所谓“点名”或“不点名”实为无谓之争;在盛会报道中树立“理性民族观”,平衡“兜售民族”与“融合世界”,二者将在传播活动中并行不悖。
重大报道;灾难报道;危机报道;盛会报道
站在2010年的历史终结点,综观2010和2008重大题材的报道容貌,不得不惊叹历史近乎重合。2010发生的大喜大悲,际遇的所有“红”与“黑”,都能在2008找到对应项:旱灾与冰灾、玉树地震与汶川地震、江西境内铁路出轨与胶济线车厢脱轨、王家岭矿难与陶寺乡矿难、世博会与奥运会、“三鹿”与“圣元”、嫦娥二号“奔月”与神七飞天、特区成立30周年与改革开放30周年,等等类同繁不尽言。本文从两年来的灾难报道、危机报道和盛会报道三个场域着眼,从重大题材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着手,阐述报道理念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新问题。
一、灾难报道之比较
汶川地震可以说是引发了我国灾难报道革命性变化,为之后的灾难报道垂范。当然,此次报道也暴露了我国新闻报道中的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在后来的玉树地震中得到部分修正。
(一)2008汶川地震报道
在2008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国媒介表现出色,开放、及时、高效、客观等素质得到了国际公认,在此我们不赘言。从另一视角进行探析,此次报道仍有缺憾,值得反思。
1.反思缺位缺乏深度追问
灾难性报道讲究思想一律和行动协调,但这并不影响舆论监督。但此次报道中,电视在很多问题上缺乏提问题、做监督的意识。(1)地震预警功能缺位。地震发生后有境外媒体指出,居民和动物都对地震有预知,境外媒体深究地震预测的原理和影响,但我国大部分媒体却草草了事,以“地震预测是世界性难题”终结话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做得好可以安抚震区以外地区居民的焦虑。(2)追踪轨迹“有果无因”。地震属于“天灾”,无法追踪全因,但对其中的“人祸”应该问因。外媒、港媒炒热“倒塌房屋多数为校舍”,质疑校舍属“豆腐渣”工程。我国电视媒体集体失语,把话语权拱手送给外媒、港媒和网媒。(3)善款流向报道笔墨不重。关于善款,电视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捐钱行为和善款数额,每天刷新排名,但是善款流向和善款管理少有问及,而同时网媒早就流传帐篷贪污和善款挪用话题,直接后果是国民对慈善事业的集体不信任。
2.追星成癖凸显电视劣根
2008年以前灾难报道中人物描写的特征是“英雄化”,本质上透射了“重英雄轻平民”的社会心态。2008年开始,“人本位”概念得到重视,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电视的“轻浮”气质又让这种关注走向了极端,甚至有娱乐的幽灵在灾区上空飘游。
不经意之间,电视媒体在这场灾难报道中塑造了不少民间明星。“可乐男孩”被救出来时说的“叔叔,我要喝可乐”,电视让他家喻户晓。在媒体大肆炒作下,这句话的“乐观精神”被无数次解构和重构,使人们对80后青年和对受灾群众的不理解。
“范跑跑”是另一个明星,具有新时期的娱乐精神。“一跑成名”的范美忠多次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这种操作的后果是混淆是非,貌似在行使一种社会责任,澄清善恶,实则是模糊受众的道德判断。何况“媒体在追星思维下,其关注的视角变窄了,造成了对灾区群众这个报道主体的忽视”[1]。
3.定位失当干扰正常救援
在抗震救灾报道中,记者的定位是观察者和记录者。但小部分记者把自己当主角,把灾情当背景,把灾民当道具,迷失了报道初衷,违背了职业道德。“某记者在人命关天的营救现场强行要求暂停营救,协助拍摄;某记者不停追问压在废墟下数百个小时的伤员,要求奄奄一息的伤者配合现场连线,这是缺乏人文素养、职业素养的直接表现”[2]。被埋困124小时的伤者被抬出,记者蜂拥而上,医护人员强调强光会伤眼,制止无效之下无奈喊出“你们抢新闻,我们抢生命”,一针见血指出了记者的定位失当。
(二)2010年玉树地震报道
我国媒体对汶川报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在2010年玉树发生地震之时,电视媒体冷静面对,发扬和修正了汶川报道的风格。其中当然有社会制度逐趋成熟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媒体人自身的清醒和人文精神的重塑。
1.质疑精神回归
玉树抗震救灾报道中,各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重树质疑精神,对汶川地震回避的几个问题都有提及甚至深追。地震发生后不久,有媒体报道,山西地震局工程师余向红在震前三四天就向国家地震局报告了预测结果,但“没被重视”。官方此后做出正面解释,正确引导了舆论。
此次报道还涉及善款流向和校舍状况,比如苏州电视台4月19日的一期报道中有《玉树地震苏州希望小学还好吗?》,追问15年前苏州捐建的“希望小学”工程质量。此外,“另类明星”也没有再次出现在报道中。在自身定位上,媒体重新回归“传播者”本位,影响伤员抢救工作的报道行为发生比率减少,在提问方式的技巧上也有所改善。比如在采访一个学校的学生成为孤儿时,记者并没有采访哭泣的学生,而是与班主任一起坐在教室与学生聊天。
2.地方台发挥特殊功能
首先,报道方式上,地方台报道相对灵活。比如上文提到的苏州电视台,就将15年前捐建的“希望小学”联系起来做文章;杭州电视台在《寻找玉树灾区29个小伙伴》系列报道中,寻找到了情感上的临近点,将两地之间结对好的29对小孩的感情连接起来,既展现了寻找小孩的惊心经历,又烘托杭州人对灾区人民的牵挂。
其次,报道策略上,地方台有所改变。如果说“911”成就了凤凰卫视,伊拉克战争成就了中央电视台,玉树地震可以说成就了青海与湖南两大卫视的合作。湖南卫视利用与青海卫视的合作关系,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搭了一回便车,实现了双赢。从4月14日晚10点始,湖南卫视呼应青海卫视滚动播出新闻,并抽调近200人驰援青海,实现青海卫视历史上第一次新闻直播;湖南卫视记者出现在青海卫视的新闻画面里,其主持人也坐上了青海卫视的主播台,战略上的合作成就了青海电视台突发事件传播的历史突破。
(三)多灾时代悖论及破解: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的平衡
今天的世界自然灾难不断、人为祸事频发,网络又使天灾人祸发酵膨胀,爆炸式扩散负面影响,给世界制造不安全因素。比较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报道,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电视灾难报道的成长,同时也为未来发展提出了全新课题和部分答案,关键之一,就是灾难报道时,宏大叙事和细节叙事的取舍。
从新新闻主义时代开始,叙事学就与新闻学联姻,新闻叙事是指为了完成叙事行为,达到叙事效果的方法。在灾难报道的视阈里,宏大叙事和细节叙事是相悖又相依的两种手段。因为:(1)灾难事件的悲壮主题要求宏大叙事。芸芸万物,生命为大,灾难事件直接指涉人类的生存状况,形成悲壮氛围,要求在空间叙事上涉及人类,在时间叙事上涉及未来等宏大话题。(2)灾难事件的涉事范围呼唤宏大叙事。在地理范围、人口范围、行业范围,灾难事件涉及的利害关系几乎无所不包,需要有自然和社会的多方面文化解读。(3)灾难事件的不可预知性期待宏大叙事。不可预知将人类置于不安全边缘,时时如履薄冰,希望和恐惧要求人们不断进行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所叙话题也涉及到人类历史最终结局的宏大主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电视报道极尽其能刻画细节又是天赋秉性。“细节作为灾难新闻报道的血肉,可以烘托现场气氛,将灾难中不同个体的经历、情感等具体可感的场面和情节自然地展现,重现灾难实况,调动人们的想象和联想”[3]。在灾难报道中,细节描写有独特魅力。我国灾难报道理念的进化过程,实际上是从高屋建瓴式报道到细节描写式报道的转向。
从2008和2010两年的实践来看,宏大叙事容易走向空洞虚无,细节叙事又会导致悲情渲染、惨况再现和二次伤害等负面效果。笔者认为,这对矛盾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全方位尊重,因此追溯人文主义中“以人为中心”的意识,是有效平衡二者的重心所在。
首先,保障宏大叙事,从整体上渲染悲壮氛围,让社会形成共同情绪,产生感情共鸣,并说服社会力量关注和关怀受灾人群,形成集体人文关怀。“电视构成事件的秘密就在于,电视宣传运动在‘孤立的’大众之间促进了形成群体所不可缺少的推波助澜过程。”[4]要形成这个过程,就必须让大众“鸟瞰”灾区的宏观图景,当然“鸟瞰”并非制造模糊和空洞景象,而要处处以“人”为内容,即时公布时间和空间上的背景以及灾难发展情况,客观报道灾区群众的援救和安置情况,即使有负面信息也及时公开和有效疏导,保障知情权。此时不涉及到具体的个人,因此可以放大灾难的悲情和救灾的豪情,并在此过程中注入信念和信心。
其次,巧用细节叙事,从微观上体现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避免悲情放大。以往的报道中,对个人的尊重不够,“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的‘人’是群体本位的抽象物,是五伦关系网络中的虚点,只有社会角色意识而无个体性硬核。”[5]对个体的尊重,体现在帮助他(她)重树信心,重树人格,还予他(她)被灾难剥夺了的尊严。具体到报道工作,记者在采访中要同时保障灾区群众有反映情况的权利和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刻画细节时,反映他们的实际困难,但避免过分描写悲惨境遇,特别提及伤亡的亲人要人性化。
二、危机报道之比较
危机报道是指媒体参与对危机事件的传播,它有两个目的:一是让受众了解危机事件的真相和影响,二是对社会变量进行有效控制。新媒体时代,危机事件激起的涟漪更深,范围更大,危机报道的手段和效果也在发生变化。比如,2008年“三鹿”事件余波未了,两年后“圣元”又再起波澜。
(一)三鹿奶粉事件
“三鹿”事件虽然缘起报纸,但电视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前期缄默,后期跟风,电视的优势和诟病展现无遗。
1.前期失语含糊其辞
2008年6月,中央和地方各级媒体都言及了“毒奶粉”,但“三鹿”二字尚未浮出水面,直到9月《东方早报》才捅破“窗户纸”。这种含糊其辞让人们对媒体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浮想联翩,同时也质疑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和危机预警功能。
媒体与三鹿企业之间的“共谋”、“对峙”、“破裂”三部曲,说明了媒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对自身行为的选择。在自然灾害面前,媒体往往可以不加遮拦的轮番报道,而对于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危机事件,媒体却“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忧虑的“组织化不负责任”和“制度化风险困境”。媒体自身利益取向愈见明显的当下,媒体行为受趋利避害规律所支配,因此“组织化不负责任”和“制度化风险困境”出现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2.调查失衡见风使舵
中央电视台的《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节目曾对三鹿奶粉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报道,并展示了“标杆”。媒体授予“殊荣”之前,并没有做过严谨调查,这种不负责任行为,让媒体自打耳光的同时,也在受众心理失去权威感。
“三鹿”曝光之后,电视又进入另外一种狂欢状态,剑指所有的奶粉品牌,“调查”的功能放大到极限,特别在一些地方电视报道中,遇到家长投诉婴幼儿不适,首先问责奶粉企业,导致信任危机在全国范围内泛滥。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报道方法使电视陷入了非理性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调查”也不可能维持公平公正原则,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功能。
3.跟风起哄借力造势
媒体从开始的三缄其口,到后来的狂轰乱炸。从三鹿个案来看,电视似乎前后都享受实惠,前期得利,后期得名,同时享用了一场媒体盛宴。但是从危机报道的普世维度考察,这种跟风起哄的狂欢式报道,是现代媒介的“死穴”,它证明了媒体只打“死老虎”一种劣态。不过对于电视媒介而言,这种轻松又轻浮的报道方式,更显得适合它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有两个特点:(1)低风险。当人人都在言同一个话题时,这个话题承担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已被分解到了最低限度,因此可以大胆畅所欲言。但同时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风险预警功能也同时遭遇分解。(2)低成本。媒介无需耗费资源挖掘独家,跟风造势同样可以获得轰动效应。因此我们看到三鹿奶粉倒台后,“千夫所指”的媒介景观。但是媒体在享受低成本的同时,也步入“人云亦云”的怪圈。
(二)圣元奶粉事件
无独有偶,2010年发生的圣元奶粉风波,虽然最终被证实为一场误会,但其起因和经过都与“三鹿”有异曲同工之处。相比之下,媒体报道“圣元”时,开放性更加明显,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1.大胆直呼“圣元”其名
2010年8月《健康时报》“武汉3名女婴性早熟”的报道点名“圣元”,随后江西、山东、广东都出现了婴儿早熟现象,电视又发展了一场运动式的报道。不过,这次没有“三鹿”初期的“羞答答”,在对企业点名的态度上毫不含糊。态度的改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经历了“三鹿”事件的洗礼,媒体在同类危机报道中多了教训,开放度和公信度在媒体人的心里有了新的认识;第二就是政策方面的支持更加得力,事态发展之初,圣元事件就获得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这也给媒体报道增加了底气。
2.反思意识仍然滞后
“圣元”危机事件被解释为一场误会,但并非一场虚惊,早熟婴儿和圣元品牌受到的伤害并没有因为官方的“无罪宣判”而终结。作为负责任的媒体,关注的应该不仅是“圣元”的闹剧,而是这些婴儿的命运。尽管卫生部公开声明婴儿性早熟与圣元奶粉无关,但公众对此结论持不信任态度,这证明媒体的危机处理仍是失败的。首先是媒体公信力遭遇质疑,其次是政府在这起事件中的中立角色遭遇否认,企业品牌的污点也没有抹去,最终导致“多败”局面。
如何走出这个看似喜剧、实则悲剧的困境,电视的功能很关键,那就是回到原点,反思起因。回到原点就是重新把焦点对准婴儿,而非“圣元”;反思起因就是从医学上解释婴儿性早熟原因。对此媒体有义务向社会解答。积极有效的社会反思,也能提升媒体自身的权威性和责任感。但实际上很少有电视媒体做到了,而相对而言报纸却做得较好。
(三)风险社会的悖论与破解:舆论监督中“点名”和“不点名”的尴尬
在“三鹿”和“圣元”两起危机报道中,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在事发之初吱吱唔唔不肯“点名”,而后者一开始就大大咧咧直呼其名。从实际后果看,二者都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是否该“点名”,是这个品牌林立,同时又监督盛行时代的一个新课题。
“三鹿”事发之初媒体的暧昧态度可以给出两种解释:第一是广被公众猜测的利益纠葛,广告投入、活动赞助,商业贿赂等疑团进入了公众视野;第二是在真相大白之前,“不点名”是对企业品牌的正当保护。两种解释似乎都能成立,对此我们无从考证。相对而言,“圣元”祸事初露端倪,媒体最初表现像个勇士,但最终证明不过是一个莽撞的孩子,闯了祸撒手就走,但遭遇误伤的的“圣元”却受到致命打击:美国纳斯达克主板上,圣元国际出现“跳水”,一周来市值损失超过20亿人民币。
经对比可以看出,前者因为“保护”名誉权而闯祸,后者则因为“未保护”而闯祸。对名誉权保护,目前我国学界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公民名誉权领域,而对媒介与企业之间的权力与义务鲜有涉猎。《民法通则》对“侵权”的解释仅局限于“传播不真实情况”,或者“运用侮辱、诽谤性语言”。在“圣元”报道中,“点名”传播的情况既是属实的,也没有运用任何侮辱性语言,但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风险社会中舆论监督面临的困境绝非“点名”或“不点名”这么简单,二者在公共利益和商业追求之间游离不定,它们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法律依据,形成一道难以破解的悖论,但仍有迹可循。笔者认为,回归精英主义的独立意识和高贵品质是电视在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纠葛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
第一,收视率决定了公共利益是电视的第一要义,因此一般认为,在企业和公众发生利益纠纷时(一般表现为企业对公众的侵害),媒体先天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须站在公众一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相尚未论断之前,企业的合法权益未尝不是一种公共利益。因此这时电视人应当具备精英的理智,积极寻求第三方(政府)的“论断”,是媒体的首要责任,而非贸然“点名”为自己博取“富贵不能淫”的形象而牺牲企业的形象。当法学上的“有罪推定”成为电视报道的一种习惯,这种冒失行为也就越来越多。还有一种假定是,第三方因各种原因“论断”缺位,这时媒体应保持自身的精英主义品质,“媒体也有一种作用,传递政府不想要人民知道的信息。其中包括:暗中交易、腐败、滥用权力和信任、浪费纳税人的钱、任人唯亲等。”[6]
第二,广告额决定了商业利益是电视的衣食父母,新闻传播学者李希光把现代新闻学的一个特征表述为“公司新闻学取代公正新闻学”虽有偏激之嫌,但影射了当下企业对媒体控制力。在面对“点名”或“不点名”问题时,这种控制会由隐形转向显性。此时电视又必须显现精英主义高贵品质,尊重客观事实,遵守职业道德,按照权威信息直接“点名”,宁可承担经济损失,也要维护自身形象,保证长远发展。
电视在风险报道中角色大众化甚至低俗化,是形成上述悖论的根本原因,当电视人精英主义中的理性、独立、高贵和权威回归,解决之路将渐趋明晰。
三、盛会报道之比较
近两年,盛会报道作为一种国际公关手段受到重视。本文将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剥离出来分析,基于两点考虑:二者同在中国举办(与世界杯区别),二者都在全球范围具影响力(与亚运会区别)。
(一)北京奥运报道
2008年北京奥运报道秉承开放、客观、理性、多元等风格,是开放式报道的成功范例。本文将北京奥运会放在盛会报道的视阈中和对外传播的视野下,从另外一种维度来观照它的功过得失。
1.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报道稍逊风骚
2008奥运会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世界级体育盛会,而且主场设在北京,政治因素和地理因素决定了央视的绝对优先权,“中央集权”的形式让地方媒体处于先天劣势。
在这种语境下,全国各大地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都有严重挫败感。(1)在全民关注奥运的氛围中,几乎所有地方频道收视率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市场份额大幅缩盘。(2)在节目制作方面,大部分地方媒体都无采访权。(3)在一些重要赛事报道中,地方媒体甚至转播权也遭到限制,不仅仅时效性大打折扣,而且画面也充塞各类“补丁”,传播效果大受影响。
地方媒体传播劣态形成也有自身原因。(1)议程设置意识薄弱。奥运期间,赛事是主要议题,但不是唯一议题,但很少有媒体设置奥运以外的议题。相反,我们在地方媒体中看到的都是蔚为壮观的奥运话题,地方报道同时也淹没在“奥运海洋”中。(2)各地方媒体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奥运期间,仅仅辽宁、山东、新疆、湖北电视台发起了CSPN中国电视体育联播平台,但地方台之间的奥运资源共享未形成气候。
2.重视“中国元素”个别报道凸显狭隘民族观
奥运会是一场体育赛事,政治因素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如过度宣扬民族特征,偏执解读民族文化,则会走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事实证明,部分电视媒体在奥运开幕前就已进入亢奋状态。在奥运火炬传递中,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红海洋”,即火炬传递城市的遍地红旗。电视画面更是放大“红海洋”的色域色调,甚至对韩国出现的“红海洋”骚乱也不作避讳。“红海洋”概念让外媒找到了“中国文化侵略”依据。如美联社发文《红旗统领了澳大利亚的火炬传递》,暗示万名华人游行是中国官方特意安排的。“外国人看到的也不是一个理性、开放与宽容的中国走进世界,反而是一个封闭、强势又愤怒的中国闯进了世界。”[7]
赛事开始后,我国媒体对本国选手的“亲情”遮蔽了世界胸怀。有媒体将刘翔出场比喻为人种的对抗。刘翔退赛后,中央电视台记者哽咽出镜。这种行为作为个人感情流露可以理解,但记者出镜时代表的是国民心态,出镜失态显示出风度和胸怀的匮乏。中美女排对抗,媒体取双方教练陈忠和与郎平之名,称为“和平”之战,但在解说中过多强调郎平中国女将的历史背景,使之被受众误解。事实上,“全球化时代,运动员的胜利包含了‘本土英雄’和‘全球明星’两种身份。”[8]
(二)上海世博报道
世博会具有同样的世界影响力,但与奥运相比,持续的时间更长。如何保持长期热度,使媒体面临挑战。从实践来看,上海世博会昭示了以下几个特征。
1.彰显世界胸怀
与奥运的“对抗性”相比,世博的“共商性”更加明显,这一事实决定了世博报道的世界胸怀。仅仅从传播手法上考量,世界胸怀也在奥运报道的基础上跨跃了一大步。
第一,在传播平台上,增加对外传播的渠道和力量。央视英语频道在世博开幕前四天开设《上海世博汇》,“内容上展示世界文明、突出亚洲风采,手法上则力争突出国际视野”。[9]为做得更有国际味道,英语频道还聘请国际文化名人库恩主持系列片《库恩看中国》。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也为世博会量身打造了外语频道——ICS,ICS相对轻松,定位于城市频道,涵盖了新闻、时尚以及各类服务信息。上海台的艺术人文频也加强国际交流,与大阪、温哥华等城市合作,卫星连线双向传输大型节目,
第二,在传播内容上,利用绝大部分资源介绍外国优秀文化,以及为外国游客提供在上海的生活资讯等等。东方卫视《世博达人秀》每天的主题离不开展示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才艺,央视英语频道《城市连线》每天有30分钟卫星连线世界各地城市电视台,另有采访各国馆馆长的40集系列,和采访各国馆设计师的20集系列,此外还加大了对亚洲各国的报道力度,开辟《亚洲风采》专栏。上海台《创意世博》还派记者出国,从该国文化理念上解读展馆的创意。
第三,在传播理念上,淡化“中国元素”,展示友善、虚怀气度。开幕式开篇就问“世界,你好!”,在活动策划和媒介报道中,也看不到“世博中国年”、“中国红”之类的概念,而是在交互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融合中西文化。
2.释放地方能量
与北京奥运相比,上海世博由于在地方城市举办,地方媒体特别是东部城市台获得一定空间,除了空中直播权仍属央视之外,其他方面的报道权利基本享受平等。东方卫视显示东道主地位。开幕当天,东方卫视就展开了360度全方位战:200次记者连线,嘉宾访谈、演播室观众互动。同时,地面频道的世博节目也遍地开花,第一财经的《一财世博指数》、纪实频道的纪录片《上海2010》、艺术人文频道的《世博之旅》,生活频道的《人气美食之世博美食总动员》。南京电视台《零距离》也发挥了东部地域优势,派遣记者常驻上海“挖掘”世博,并现场直播开幕式和其他大型活动。其他城市也有记者临时驻站上海,分别进行了现场连线。
地方台之间还合力作战,共享资源。2010年3月,上海广播电视台发起广电行业联手打造“新媒体世博报道联盟”,来自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的28家广电系统共同组建。“联盟”在世博期间策划新闻、筹办活动,形成了多彩内容和多元角度的媒介景观,历练了地方台应对国际题材的能力,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开放、多元的媒体形象。
(三)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及其破解:“兜售民族”和“融合世界”的交互
每一次盛会,都是一个异种文化碰撞的舞台,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示出来,说服别人在行为上接纳,在心理上折服。但如何使对方相信自己,在当前国际盛会繁多的时代背景下,这个课题又增赋了新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兜售民族”。冷战后西方国家一直占据文化霸权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和国际重大事物上享有优先发言权和绝对独断权,而尚处文化弱势的中国,即使经济地位一再飙升,也很难在文化话语上获得发言权。因此,我们有必要向国外输出民族文化和国家形象。我国政府在这两年已经有了清醒认识。2010年国庆期间,国务院新闻部发起制作的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在CNN、BBC等亮相。国际先驱导报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公关时代的到来。“公关”实质就有“兜售”的意味。
其次,我们需要“融合世界”。以奥运和世博两次盛会的报道来看,前者无时不在强调中国元素和民族精神,如同把标签贴在脸上。而世博报道却在不经意间传递了信念,使自己与世界巧妙融合。一个真正的推销高手,绝对不会摇旗呐喊,而会“润物细无声”。传播学者认为,“学习就是传播”。在世博会上,虚心学习外国优秀文化这种行为本身,就向外传播了中国亲和友善、虚怀若谷的国际形象。
“兜售”与“融合”可以说殊途同归,“兜售”是强势的“融合”,“融合”是温柔的“兜售”,二者看似相悖,实则相依,目的都是输出意识形态和树立国家形象。关键点在于天平向哪方倾斜,“兜售”过度让人产生“文化扩张”的反感情绪,“融合”过度又有可能“被融合”。此时,理性的民族主义成为准确把握二者关系的最佳尺度。
第一,民族主义是国际传播的核心,“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10]民族文化是国际传播的内容,不管是“兜售民族”或“融合世界”,都必须靠紧这个核心。理性的民族主义包含对自民族的自信和对他民族的尊重,这体现了本民族的胸怀和气度,也体现了“兜售”的技巧。
第二,在“兜售民族”中“融合世界”。理性民族主义一个基本理念是,民族的即世界的,民族文化得到世界认可,自然融入了世界。在盛会报道中,“兜售”的内容和方式需精心选择,因为“被兜售”方不是“枪弹论”中的靶子,“传者试图在进行传播时针对某一事件使受众形成一定的‘刻板印象’,其实受众在接受这一‘刻板印象’时,同时对传者的信息也进行了一定的取舍和处理”[11]。
第三,在“融合世界”中“兜售民族”。理性民族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包容”,“包容”本身就是一种形象输出,在奥运报道中,如果更多的报道他国赛事,更多报道失败运动员,更加尊重他国失败者的感受,这种“理性民族”的光环就是“融合世界”的体现,实质也是在“兜售”民族的优秀气质。
总的来看,近年来的电视重大报道在困境中突围,在困惑中成长,显现许多优良品质,但同时也凸显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是当今时代无法破解的悖论,但我们追根溯源,找到了悖论的根源。在灾难报道中重视对个体的人(而非集体的人群)的尊重,报道中也就没有宏大与细节之争;在危机报道中回归电视人的理性、独立、高贵品格,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矛盾也迎刃而解,所谓“点名”或“不点名”实为无谓之争;在盛会报道中树立“理性民族观”,热爱民族的同时也尊重世界,平衡“兜售民族”与“融合世界”,盛会报道更容易被接受,积极性传播效果会更加明显。
[1]罗筑娟.略论记者在灾区报道中的角色定位[J].新闻传播,2010,(2).
[2]徐琳.从主流媒体对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报道比较看新中国媒体理念的变化[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
[3]孟改正.叙事学视野中的灾难报道[J].新闻爱好者,2008,(8).
[4](日)藤竹晓.电视社会学[M].蔡林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32.
[5]杨岚,张维真.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
[6]李希光.畸变的媒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6.
[7]赵灵敏.奥运年的中国民族主义[J].南风窗,2008,(15).
[8]David Andrews etc.Sport Star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porting Celebr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1-19.
[9]郭醇.英语频道因世博更精彩[J].对外传播,2010,(6).
[10](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5-6.
[11]刘继男,何辉.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9.
【责任编辑:陈红】
Some Reflections on TV Reports about Great Events in Recent Years
PENG Hua-xin,OUYANG Hong-s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TV reports about great events in recent years when breaking through predicaments and developing in embezzlements,have produced lots of problems,which seem to become a thorny paradox and find no solution at present.Nevertheless,when going into its whys and wherefores,the basis of the paradox could be found.There should be no debate whether the coverage is grand or minute in nature when humanism is sought in the reports about calamities.When going back to elitism in the crisis reporting,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could be solved instantly.It is a worthless dispute whether an explicit criticism should be conducted by name or by mentioning no name.In the coverage about grand assemblies,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rational national concept”and keep a good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principles of“propagating the nation of the country’s own”and“mingling into the world”,which should run parallel in the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report about great events;coverage about calamities;crisis report;grand assembly report
G 229.27
A
1000-260X(2011)01-0144-07
2010-11-25
彭华新(1978—),男,湖南汨罗人,四川大学新闻专业博士研究生、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记者;欧阳宏生(1951—),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