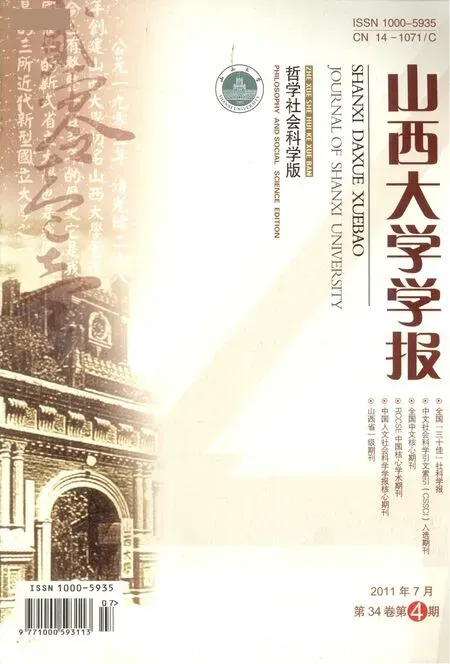“标新”与“立旧”——新世纪小说的双动向
耿传明,李 国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标新”与“立旧”
——新世纪小说的双动向
耿传明,李 国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新与旧的问题实质是价值观的变化问题,激进的现代性也是激进的崇新主义。新世纪社会转型带来了诸多新景观,作为应“世”的小说,就不能摆脱以“标新”的姿态来面对这些新的价值特征及其新的文化格局,但在具体操作上,小说又往往以“后退”的姿态在内容与形式上蕴含着立旧情怀,不仅局限于基本的创作方法与审美立场上,更有小说大环境下的类型化创作倾向。文章就新世纪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民间立场、文学类型等方面进行了整体性归纳分析,从而展现新世纪小说标新与立旧的双向旨归。
新世纪小说;现实主义;民间立场;消费文化;文学类型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日益强大的背后,不管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还是政治的和谐诉求,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是不断高涨的民族文化气息。它以主体性身份承担了抗衡并力求化解这种扑面而来的外在冲突的历史重任,同时也为重塑大国形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而新世纪文学,尤其是起到“排头兵”作用的小说,作为其首当其冲的文化载体,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以一种“后退”姿态的立旧情怀,践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展现着特有的世纪“标新”姿态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格局。
一 现实主义:新保守思潮下的有意味创作方法
新保守主义思潮是在现代化反思的背景下引发而来的,它不仅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思潮,更是一种因自由主义思潮无法应付各种社会弊端而临危受命的政治思潮。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在美英两国出任政府首脑带来了新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促使了新保守主义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内外政策的理论依据愈发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的实践。而新世纪以来,中国“民生”政府的组建及“和谐”政治理念的尝试等内容,从某种层面上说也是主流意识自上而下实施的一种保守立场。因此,在一种“反激情、倡保守”的文化氛围内,新世纪小说创作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便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
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中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典型,它可能并不能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得到彻底的实现,而在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中又肯定会同各种不同的特征,过去时代的遗留,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各种独具的特点结合起来。”[1]在这里韦勒克将现实主义看做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流变概念,他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表征出异样的特征。那么,如何把握这种流变的创作方法呢?在他看来,就要基于时代的现实性,甚至这种现实性存留在预想之中而未取得实践上的意义。这正如当下主流意识倡导的“和谐”主题,必将成为我们现实主义创作所依据的指导原则。因为“现实主义意味着‘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它的主张是题材的无限广阔,目的是在方法上做到客观,即便这种客观几乎从未在实践中取得过。”[1]也只有做到这种与现实的亲密结合,才能实现现实主义的特定属性。毕竟“现实主义是教谕性的、道德的、改良主义的。它并不是始终意识到它在描写和规范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却试图在‘典型’概念中寻求二者的弥合。”[1]应该说,韦勒克是对西方现实主义诸多作品的发展脉络进行全面考察和细致梳理后得出了一个总括式结论,但这也完全适合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特点。从上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文学”,都可以算是狂飙突进式的激进文学运动。它们以与传统“断裂”的大无畏精神,在一种激情与浪漫、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中高歌猛进,并以决绝的态度来对抗历史的痕迹与文化的积累,以反叛的声音和先锋的姿态实现着自我身份的认同。但进入90年代,随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些”等经济口号的提出,国内民众的关注热情逐步由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利益追求,加之诸如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加入WTO直至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等国际大事件,迅速将民众对国内矛盾问题的关注转向了对现代国家民族形象重塑的关注。这些因素都推动了一股新的民族主义热情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而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现实主义创作中所关注的视野由以往的一种现实批判情怀转到一种新的温情保守主义。换言之,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凌驾于生活之上,便有一种规劝并指导现实的社会功利性;追随于生活之中,便凸显出特有的审美功能和叙事策略。所以说,新世纪前后十年里,现实主义创作建构了文学与生活的新关系,那就是在边缘的立场上进行保守性叙事,实行温和而稳健的话语实践。而且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即这种倾向在未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将呈现出一种常态的发展趋势,毕竟“和谐”已成为当前社会自上而下的一种实践性的话题,而“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仍将是一个时代主题长存于世。
在被称为“这是一次大踏步的倒退”的《檀香刑》中,莫言对语言民间化的自觉追求,与当下充溢着“西化式”或“现代式”语言风格的作品相比较,的确实现了以退为进的现实审美策略。《檀香刑》中对异族“杀人盛宴”的陶醉,直接折射出来的便是如何重铸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问题。在随后的《生死疲劳》中,莫言实现了向中国古典小说回归以及民间立场延伸的尝试,呈现了莫言对历史进程中传统农民与土地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余华的《兄弟》中将人的欲望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其价值旨归及所张扬的精神仍旧是《活着》中福贵那样的生存法则——承受现实带来的苦难,不去抱怨并且平静友好地去面对世界。阎连科的《受活》表现的是一个追求幸福生活的荒诞故事,在愚昧中存在着相同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毕竟,“受活”本身就是河南方言,涵盖了忍耐、苦中作乐等意思。毕飞宇继《玉米》之后推出的《平原》亦是消解理想与激情的长篇大作,呈现出来的仍是这种保守式的温情叙事。作者将尊严、爱情、性欲等作为关键词浓缩到典型的中国农村王家庄中,用冷静而没有批判的情感叙述了“带菌者”端方的身体权力、精神权力、欲望权力,并且“摄像机式”地直录了与这些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婚姻、家庭、性爱、情感等现实生活内容。从《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纯真到《方舟》中的激愤,张洁一直在宣泄着自己的情绪,但在《无字》中却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平静与温和。她以个人化默默诉说的方式进入,用80余万言篇幅书写三代女性的命运,却达到了一种群体化的深沉反思。她所倾诉的表面上看是女性特有的痛苦,但实际上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悲剧,是一种无字可抒写的时代沧桑与历史的“伪意义”。
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使人异化的种种诱惑,在以往带有启蒙色彩与理想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看来,必将会是一种道德的扭曲和价值体系的崩溃,但在当下作家看来,这些事情都是太过寻常的小菜一碟,根本不值得进行谴责与批判。格非的《不过是垃圾》是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分子道德变化予以揭示的力作。李家杰是大学时期热烈追求苏眉的爱慕者之一,但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二人之间却发生了彻底颠覆同窗情谊的故事。已是成功企业家的李家杰,最后“潜规则”了苏眉,将我们常常言听的男女同学间的情感故事彻底转变成新时代下男女同学情欲交往的习以为常。巴乔的《阿瑶》写了清纯美丽的农村姑娘阿瑶进城之后逐渐沦落为风尘女的经历。在巴乔的冷静叙述中,看不到任何道德批判的渲染,而阿瑶既没有道德负罪感,也没有觉得命运悲苦,只是简单面对生活和重复着自己的日子。我们感受到的阿瑶的那种生存的无奈、人性的挣扎、情感的麻木却恰恰是对我们现代生活的一种无需情感判断、只需默默接受的无奈现场直录。贾平凹《废都》亦是如此,从1993年因透骨模仿《金瓶梅》所采用的小方框式性爱描写导致被禁到2010年的解禁出版所引发的“废都热”,从当时的批评界对庄之蝶采取的道德谴责到现在的价值判断上的默许认可,这种转变已然说明,市场经济下性爱暴露、男女多角关系、身体权力交易等内容早已成为无需遮掩的“呈堂”之事。这也同样说明了新世纪以来的新保守主义对以往需加指责批判的诸多事情的容纳与接受,而这种立场直接引导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
当然,新保守语境下不能缺失的一环是对主流意识的追随与赞誉,这毕竟是一体两面的呈现。因此,我们还会发现新世纪现实主义创作中有一大批紧跟时代脉搏、展现国家新形象的作品。赵东苓的《21天》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整栋大楼因非典隔离了21天,小说极力刻画的是全楼居民由恐惧、焦灼、惊慌失措、彼此隔离到镇定、从容、彼此关爱、互相理解和互相帮助,在经历了灾难的洗礼和精神升华后,充满了对灾难、生命、勇气和人与人关系的思考。张宏森的《大法官》通过对林子涵、郑小泉、潘军右、范伯年等法官形象的塑造,在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和人生命题等开阔视野下,警醒地说出了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话语中的重要作用。《废墟下的青春》、《生命礼赞》、《救赎》、《站起来》等反映地震题材的小说纷呈不断,直接展现的是小说与时代话题的联姻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透过摩罗的精神转向来剖析当下现实主义的保守情怀。曾经的《耻辱者手记》、《不死的火焰》等书,带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感触与灵魂震撼,那种对强权的蔑视、对自由的渴望,能够如重剑利锋般切开人的心扉。但进入新世纪后,摩罗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之上,推出了新作《中国站起来》,在为民族主义呐喊的同时,也渗透着他努力营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苦心,可以看到他从一个个体本位者,蜕化成一个狂热的国家民族主义者的身影。更甚至我们还可以从中学教材清除鲁迅文学作品这一现象敏锐地察觉到当下文化语境的新保守立场,作为接班人的青年学生知识谱系中缺乏了对鲁迅批判精神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温情、和谐等价值理念的文学作品对教材内容的重新建构,这些都可算是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年青一代所实现的“软着陆”之举。
二 固守民间:现代性反思的“底层叙事”
对民间底层的关注是新世纪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具有明显的“标新”姿态与“立旧”情怀的双动向。对于“民间”一词,在其复杂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背后,离不开一种文化视界与空间的建构,即陈思和所说的,这个空间“和国家的概念相对,在国家权力中心以及它的主流文化的边缘存在和发展。”[2]因此,新世纪小说创作立足民间便成为一种写作姿态与叙事立场,要求知识分子融入地野,审视普通民众的生活内容与生存状态。但我们还应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即主流意识形态为实现巩固自身、壮大势力的政治目的,从来不会放弃对“民间”的干预与掌控。这样,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与主流意识的政治文化双重关注下,“民间”无论如何都将处在一种被关注、被审视的“底层”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成了“底层叙事”事实上也就在践行着民间立场。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锁链将这二者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呢?既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那二者又体现着怎样的互文互动的张力关系呢?可以说,在“反现代性”这一话题越来越成为当下显学的语境中,其对现代性的反思乃至否定的精神立场与价值旨归便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以言说的资源。文学作为精神重塑的扛大旗者,以聚焦民间的视角,将处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困境中的底层民众作为关注的对象,记录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所以,新世纪“底层文学”可以看做是由来已久的大众文学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异变,是在渐失“启蒙”语境后出现的一种“关怀与正义”的价值取向;其关注的对象“底层”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着被压抑、失去话语权力与合法身份的群体特征,难以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角逐;而“底层叙事”往往表现为两种:一是作者以底层身份出现的叙事方式,另一种是客体为底层民众的精英主体化叙事。其中最具文学意义与价值的应该是后者,毕竟这种叙事正视社会转型期从传统到现代、从蒙蔽到开放的现实状况与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和奋斗经历,不仅体现了文学关注现实的良知,同时对当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毋庸置疑,工农大众是革命与改革的主力军,但当下失去土地的农民、离开工厂的工人,却已成为一种新现象。因此,在失去土地与工厂的焦虑背后,存在着一种尴尬的身份认同危机,其社会主人翁的地位已然沦为了社会弱者。为此,作家们不仅以回归民间的视角正视了这些社会新现象,而且能够以立旧的情怀,理性处理这些生活素材。曹征路的《那儿》以下岗工人为题材,展示了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特有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利用“小舅”这个形象通过民众上访的经历反映了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企业机制问题,形成了一种敢于正视和反抗现实的新生力量;但“小舅”的惨死却成了以往我们宣扬的“崇高”、“无私”、“集体”等精神铸炼在市场经济利欲熏心大环境下的最后抗争。刘继明的《放声歌唱》以失去土地的钱高梁进城打工为线索,讲述了他因受工伤讨取赔偿费而不得,在法院顶楼放声高唱跳丧鼓歌并引来无数观众的故事。这种展现民众“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戏剧化场面“以一种悲壮的形式凸显出多重矛盾和错位,是今天农民工尴尬处境的精彩写照。”[3]法官与包工头张大奎在法院门口的权钱交谈宣告了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失败,可以说法律非但没有成为保护弱者的工具,反而因为钱与人情的“参与”使他们成为更甚的“合法”受害者。另一方面,我们又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悖论冲突,即现代化规范对民间秩序的强制剥离。钱高梁作为跳丧鼓的歌师,在乡下是受人尊敬的民间权威,但是在现代的法律面前却丝毫没有价值。法律取代了传统民间固有的“义气、承诺、信任”等内容后并没有给乡下人带来希望,而失去生存根源的农民却不得不在城市空间中回望曾经熟悉的乡土民间。刘庆邦亦是用早期的人生体验,展现了乡土民众各异的生活境遇和苦难的血泪史,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在他看来,“社会从物质匮乏到全面物质化,人的身体成了欲望的盛筵,人对金钱的索取也到了疯狂的程度。”[4]他的中篇《神木》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黑暗煤洞中底层矿工的极其恐怖的故事。宋金明与唐朝阳两人依靠骗取“点子”下井挖煤,然后谋杀他们的生命,再假冒其家属向矿主诈取巨额补偿金来作为发财筹码。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情,是近年来小煤窑频频出问题的新现象。[5]刘庆邦在作品中极力凸显了人性在金钱腐蚀下的扭曲与污浊,对人性之“恶”做了痛入骨髓、震撼人心的描写。但不得不说的是他依旧以回头望的立旧情怀,将“善”作为人性的根本,将“恶”作为金钱操控人性的阶段性过程,毕竟在小说中始终充溢着理解与“向善”的期望。恶人宋金明最后良心发现并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生还机会,救下“点子”元凤鸣而选择与唐朝阳同归于尽。最后,高中生身份的尚未受社会熏陶的元凤鸣放弃“恶人”领取抚恤金的做法而直接说出了矿难实情,仅仅得到几百元钱打道回家。这也明确了“神木”的由来,是“大树老的变成神了,在地下埋藏多年,变成神木了。”[6]这种带有玄冥色彩的神的力量深深埋藏在人的灵魂深处,能使邪恶得到惩戒,善良得到慰藉,而这也成了作者固守民间并以立旧情怀反思现代化的最直接表征。
新世纪小说创作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金钱至上观念对牢固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冲击与瓦解。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大语境中,作家们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没有享受到改革成果却又在承担着诸多改革重任的底层大众们。在他们的人文关怀视角下,直接渲染了金钱侵袭下的情感荒漠世界,刻画了底层大众因经济困窘导致的亲情泯灭,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僵硬、荒凉的生存状态。无论是陈应松的《母亲》所描写的儿女合伙商议并一致同意将自己的亲生母亲灌毒药杀死的故事,还是尤凤伟的《泥鳅》所描写的因工受伤的蔡毅江由于得不到医疗报销又没钱治病,让自己的老婆出卖肉体维系残喘的生命的故事,抑或是王祥夫的《尖叫》所描写的被嗜赌成性的丈夫毒打乃至剪掉手指的妻子米香,在多方求助无门后不得已雇凶杀夫,却被警察责难不求助法律,而发出阵阵凄厉的尖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的故事,这些小说都把底层亲情的极端化推向了叙事的高潮。金钱的缺乏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孝道的缺失、道德的沦丧乃至罪恶的抉择,凸显了底层民众传统家庭观念下的亲情沦落,从而形成一种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民间书写立场。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与以往的民间书写相比较,新世纪小说更能有意识地将人物生存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将这种民间体验置换到了城市空间当中,展现的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民间或蛮荒待开垦的乡土,抑或是民族国家感召下现代性进程中的待启蒙式民间,而是金钱诱惑下的底层民众的尴尬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亲情泯灭。
应该说,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与倡导有利于底层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过去被遗忘、被遮蔽的状态,体现了特有的时代意义。然而在当下的创作体制及风气中,能够深入生活收集原始资料的作家凤毛麟角,尤其是面对大众的生活实录和苦难叙事,大部分作家往往根据转述几手的资料闭门造车,或者依靠自己尚未枯竭的想象力创作文学作品。正如作家杨显惠所说:“这几年文坛上这样的现象很普遍:你读了十本书,发现有八九本都在写着相同的生活、相同的故事和相同的人物。这是因为这些人不深入生活,不调查,而是读了一些别人的书,然后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或互相克隆。这样的作品缺乏原创性,只是模仿和编造。”[7]长此以往,必将会造成一个文学“去伪化”的反扑。另一方面,能为底层群体思考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带着精英意识而不能真正意义上代表底层立场思考,因此,作为底层群众的利益诉求,即便是知识分子能够通过文学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说是非底层立场的难以实现的理想尝试,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这正如南帆所说“知识分子的言说很大程度地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这是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表述底层的冲动之源。”[8]所以说,文学对底层的关注也必将处在一个尴尬的局面当中,而且将会成为一种常态的发展趋势。毕竟文学的边缘身份始终是当下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定断式命题,而文学充当救世主的身份从现在情况来看只能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想象存在。
三 新颜旧貌:小说类型化的拓展与深化
小说类型化创作也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有着“标新”的形式展现,它是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下多元文化格局的文本呈现。不难发现,在当下的阶层分化中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有闲阶层”,他们以游荡的社会青年、懒散的大学生、叛逆的青少年等人群为主,表现为一种“无理想、无深度、无追求、无约束”的“四无”新人形象。而他们的知识结构及多样阅读兴趣促使了小说类型化创作成为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穿越历史、玄幻武侠、盗墓探险、游戏竞技、官场职场、青春成长等题材的小说,有成套路的叙事模式、单一的主题先行、雷同的故事情节以及相近的人物塑造,以一种相似的类型点缀了蔚为大观的当下文坛,并与主流文学、精英文学等展开文学场域与文学话语权力的争夺。可以说,新世纪类型化小说创作是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写作的另一种表现,体现着一种休闲文化的多样性与深度性的特征;同时,它又是文学遵循市场规律、依托网络平台、按照读者阅读情趣进行创作的一种“利润-需求-创作”的文学互动样式,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化的创作风格。
但回溯以往的小说创作,类型化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古典文学尤其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及才子佳人故事中,受封建理学理想人格模式的影响,“仁、义、礼、智、信”成了塑造人物形象的类型要求。至晚清文学创作中,已经涌现出了诸如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类型小说。特别是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已经自觉运用类型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及其发展流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实现了对小说类型化创作进行研究的有效归纳。但这种多元开花的状态却随着“左倾”的政治潮流高涨而逐渐失去了生存的文学场域,在“一体化”的创作要求下,唯一形成的类型化便是一种“好与坏”、“我军与敌军”、“工农大众与走资派”等二元对立式的创作倾向。直到80年代出现的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先锋转向,才形成了文坛上一种理性思考的写作潮流。到90年代及至新世纪后,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及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学的商业化,以往的小说类型化创作又活跃了起来,呈现出了其承传既往的多元性,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它以流行化的文体模式、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异于常态的离奇事件以及轻松不加深思的叙事风格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公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快感,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于安于现状、沉于幻想的精神之旅中。毕竟,过去的小说创作往往将功利性放置于第一位,进行的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以期达到教化读者的目的;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类型化小说创作,更主要将娱乐性与商业性放置于首位,在追逐利润的前提下满足不同阶层大众的审美愉悦。所以说,在“主流意识、市场利润、文学性”三维构筑的当下立体化文学场域中,小说类型化创作的立旧复现与标新繁荣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相反更应该得到作家、理论家及评论家的认可与研究,而不应因其缺少了以往的价值判断及依托网络平台而受到冷落与无视。
除了与传统文学相关联外,电子传媒文化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类型化小说产生的主要温床离不开那些诸如黄金书屋、幻剑书盟、起点中文、榕树下、晋江文学等一系列文学网站。他们较早就意识到这种类型化小说的创作潮流,并自觉地按照小说类型的发展与读者消费的需求积极进行版面重组,引导着小说类型化创作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此外,网络的进入又改变了文学的生产体制,其背后的商业刺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老传媒的联姻,实现了网站与出版社、图书与电子书共同发展的新模式。以成立于2001年的文学书站“幻剑书盟”来说,其成立之初便广聚文学写手,开创了武侠、奇幻等类型小说创作,吸引了一大批文学读者。2003年下半年幻剑书盟开始了由个人网站向商业网站的转型,积极与多家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实现了由网络到纸质相对完整的出版体系。2005年出版的《诛仙》、《新宋》、《和空姐同居的日子》、《搜神记》、《飘邈之旅》等市场上颇具影响力的图书,都是最初走红于幻剑书盟的热门小说。而且2006年4月15日召开的“网络文学发展与出版峰会”也恰恰说明了网络书站与实体出版社密切合作的关系。更甚然,类型化小说与游戏产业、音像产业等亦有着摆脱不了的染指关系,如静官的奇幻武侠小说《兽血沸腾》出来后,短时间内便转化成了网络游戏,而天下霸唱的盗墓小说《鬼吹灯》也即将被杜琪峰导演拍成电影。可以说,这种合作化式的连带关系已然成为当下文学生产的主要流程,甚至于以道德救赎为价值旨归的精英文学也难免受到牵涉,作家创作的作品愈加具有影视剧本的样式与风格。这种情况正如作家刘震云所说:“文学参与电影可以让电影变得更强壮,电影参与文学可以让文学飞得更远、传播得更远。”为此,批评家雷达指出:“未来的文学形态怎么样,与影视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9]。
那么,面对类型化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又将如何与之相适应呢?很明显,以往单一的批评模式似乎很难公正地评价这种异军突起的文学现象。如果说新世纪类型化小说创作是创作主体自由化的一种体现的话,以往的小说创作便可看做是一种“戴着脚镣”式的创作,受到了多种外在环境的制约与限制,因此文学往往成为一种“遵命文学”的创作模式,掩盖并限制了文学类型化的发展与丰富。基于此,新世纪类型化小说如此丰盛,可以看做是以往被压抑文学在当下宽松环境中的以一种“标新”姿态出现的新现象,更是对以往的文学类型化创作的大归结,成为作家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种立旧情结的大演练。毕竟如果仅仅从现当代文学发生与现状两个时期来看,同样是世纪十年的多元共存共生,20世纪的十年因政治原因是一场由思想与主义论争而引发的文本理性多元并存,而新世纪的十年则因经济原因演化成阶层多元及其反映到文学中的小说类型化的情感多元并存。但需要一提的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正视这种文学现象的同时,更应警惕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多元类型化创作背后在现下情况来看往往受缚于市场利润的引诱,如果理论界与批评界不加以正确引导,那多元的发展仍将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单一的趋势,只不过是由旧有的政治约束转化成为当下的经济刺激。毕竟,“文化产业具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和对利益的洞察力,它能从文学作品元素中发现那些最有增值可能性的元素,将其类型化,迅速进行再生产。而另一方面,类型化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有意无意地朝着类型化倾向”[10]发展。
因此,如何引导类型化小说创作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话题。除了用以往“纯文学”观念中的责任或道义等价值理性对其进行相对的文本规范外,改变网络写手的知识谱系以及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应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的分化流变中,很早也存在着小说类型化的创作形态,他们拥有一大批有着历史传统积淀和较高知识素养的知识分子作家,能够在变动不居的文坛中有意识地按照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对类型化小说创作进行实践与开拓,形成独具自我特色的小说文本。如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侦探小说女王阿嘉莎·克丽斯蒂、间谍小说第一人约翰·勒卡雷等,他们都有着独特鲜明的创作个性,能够持久地延续自己的创作类型不随意变更。当然,更不容忽视的是西方类型化小说创作有一个集创作、出版、阅读、传播等于一体的完整的系统,这保证了类型小说合理健康地发展。所以说,纯文学或精英意识作家更应加入到类型化小说创作当中,承担起能够泛起人类内心世界涟漪的严肃任务。此外,随着学者们新老交替的实现,知识话语权力也会随之发生质的变换,有着丰富网络生活经验的大批学者决然不会忽视类型化小说创作这种现象,因此,像玄幻小说《盘龙》、《神墓》、《诛仙》,历史奇幻小说《新宋》、《紫川》,盗墓类长篇《鬼吹灯》、《盗墓笔记》,历史穿越小说《窃明》等类型化小说创作也定会成为文学史关注的对象,它们虽不一定会成为经典文本延续久远,但必将会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囊括到文学史写作当中。因此,大学生作为文学史的接受群体,尤其是对于那些“四无”新人成员中的貌似堕落的且不唯书本为上的学生来说,就应该通过文学史的知识传递更好地体悟到类型化小说创作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毕竟,他们不仅仅是类型化小说稳定的阅读群体,更是能够完善并合理发展类型化小说的创作主体,在改写文学现实的同时实现精神转向。
总之,新世纪小说创作面临着诸多的新景象与新问题,在新的文化格局中既有“标新”姿态的新意展现,又存在“立旧”情怀的传统承续,形成了新世纪文学独有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观念。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继续上世纪90年代的新保守立场,在“和谐”的政治诉求中表现出明显的温和稳健的策略操作;其内容上的对社会转型中的民间底层的关注,则将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人文关怀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类型化小说的形式文本,又将作者、读者与网络,将文学、游戏与影视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了新式的文学生产体制。而在这三方面貌似分离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脚点,即犬儒主义或娱乐主义已经对新一代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新世纪小说朝着这个方向的“分支式”发展似乎并没有止步,反而愈加明显。
[1]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丁 泓,余 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241.
[2]陈思和.理解九十年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69.
[3]李云雷.2006:“底层叙事”的新拓展[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1):55-61.
[4]刘庆邦,夏 榆.作家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N].南方周末,2004-12-30.
[5]骇人听闻的罪恶[N].法制日报,2000-08-19.
[6]刘庆邦.神木,家园何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6.
[7]杨显惠,陈占旭.文学似乎已误入歧途[N].社会科学报,2005-06-23.
[8]南 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J].上海文学,2005(11):74-82.
[9]雷 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J].文艺争鸣,2010(2):6-12.
[10]贺绍俊.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J].文艺研究,2005(3):11-17.
(责任编辑 郭庆华)
“New”and“Old”——the Two Tendencies of the New Century Novels
GENG Chuan - ming,LI Guo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New and old”problem is in essence the value change problem,so the radical modernity is the radical new - adoring doctrine.Th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of new century has brought about many new sights,and as the novel of accommodating to society,it can’t get rid of the“new”posture to meet those new value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culture pattern.But in the specific operation,the novels usually contain old feelings in the contents and form with the“backward”posture.This is not limited to these methods of creation and position of appreciation,but of the creation genre tendency in the environment.So,this paper makes a necessary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realism,standpoint of the populace and the literature genre of new century novels in order to show the two aims of new and old in the novels of new century.
novels of new century;realism;standpoint of the populace;consumer culture;literature genre
I207.425
A
1000-5935(2011)04-0009-07
2011-01-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乌托邦小说研究”(07BZW052)
耿传明(1963-),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李 国(1981-),男,山东日照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book=15,ebook=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