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学术争鸣和名誉侵权界限
采编/海 风

范曾的流水线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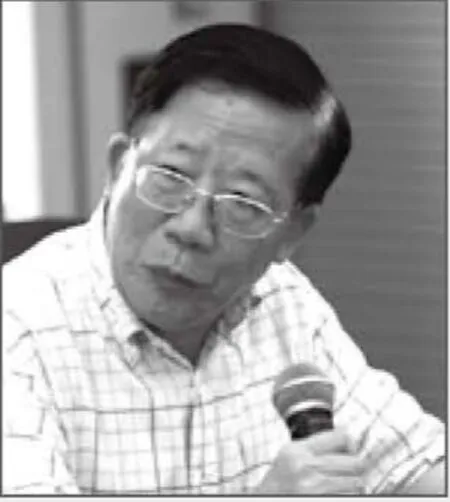
周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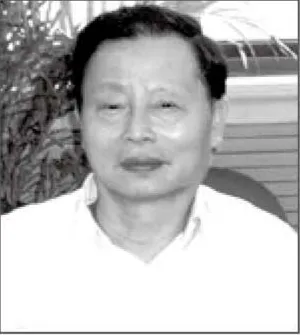
丁法章

凌 河

殷啸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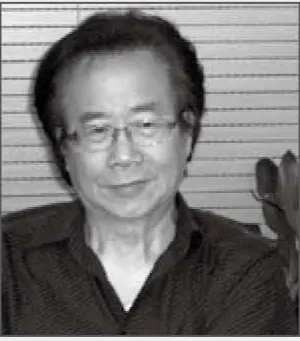
魏永征

江 宏

丁邦杰
事件回顾
2010年3月,收藏家郭庆祥参与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艺术品市场热点对话》栏目,与主持人王小丫及著名书画家石奇、龙瑞热议当前书画界问题。他说:“现在,画家、美术评论家包括搞艺术品真伪研究的专家中,普遍存在一种浮躁心理,一些知识分子,面对金钱诱惑失去了良知,很多艺术品的艺术性不高。艺术家追求的不是艺术创作,见了面就比谁住的房子大,谁开的车好,谁的画卖的价高。有些画家画了几十年的人物,总是几个人物变换着组合,一个形式,一种模式,流水作业了三四十年成了画匠,而画匠决不是艺术家;这些人上了电视,出口必称唐诗宋词,靠传统装点门面,最多不过算个好教师,绝算不上好艺术家。他们或是缺少才气,或是不勤奋,或是存在投机取巧心理。艺术家的创作要融入自身感情,真情实感的创作,才能出有生命的作品,才能去感动收藏家。”郭庆祥在节目中痛批时下蜂拥而出的“艺术怪胎”,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尔后,2010年5月,郭庆祥在《文汇报》争鸣栏目发表署名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文中提到了一位当下“经常在电视/报纸上大谈哲学、国学、古典文学、书画艺术的所谓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他写道:“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谢灵运、苏东坡、钟馗、李时珍等几个古人,都有如复印式的东西,人物造型大同小异。他的人物画虽然是写实的,但其中不少连人体比例、结构都有毛病。他的书法是有书无法,不足为式,装腔作势,颇为俗气。他的诗不但韵律平仄有毛病,而且,在内容上,不少是为了自我吹嘘而故作姿态,不足挂齿。”他还写到了自己当年收购“这位名家”画作的经历:“当年,有朋友找到我,希望我收购200张他的作品。那时候,这个画家境遇不顺,希望卖掉些画度过难关。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尺4000元,不那么离谱。我随即打了200多万元过去。很快拿到了第一批画,展开一看,题材与技法严重雷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是任伯年的,花鸟是李苦禅的,七拼八凑当做自己的了。第二次交货前,我跑到他的画室去看个究竟,出乎意料的是,他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你猜怎么着?每张纸上先画人头,再添衣服,最后草草收拾一番写款,由他的学生盖章。这哪是画画?分明是在画人民币嘛。所以我认为这个人的作品不值得收藏,他对艺术不真诚,对社会不负责任。他多年来一直在重复自己,没有一点创业精神。后来这批画都被我抛出或送人了。”
6月24日,《文汇报》鉴藏专刊同版刊发了美术评论家、画家谢春彦的署名文章《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和署名孙逊的文章《画家最终还是要拿作品说话》。不点名地批评了画家范曾。
2010年9月,范曾及其代理人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郭庆祥、谢春彦及刊登《艺术家要凭作品说话》《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画家最终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三篇文章的《文汇报》。认为《文汇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而《文汇报》是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其刊登的三篇文章先后被谷歌、百度等主流媒体转载,被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地随意贬低原告名誉,侮辱原告人格,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已构成对原告方的伤害。要求《文汇报》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要求郭庆祥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要求谢春彦和孙逊各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
而在案件尚未正式审理期间,郭庆祥一方通过媒体刊出了一组“范增流水线作画”的照片,并称将要在庭审时呈上这些照片作为证据。而与此同时,范增的学生崔自默公开表示,郭庆祥通过媒体发表的这些照片是他拍摄的,是作为研究资料发表在“自默文化网”上的,意在赞扬范增绘画技巧的精湛。崔自默认为,郭庆祥未经允许公布照片是侵权行为。他说:“我早年拍下范增先生画老子和钟馗系列的照片,意思是想说先生可以在瞬息之间创作十来张不同面貌特征的老子,虽然他们形态各异,但精神内质是惊人的相似,‘技近乎道’,就像庄子的《庖丁解牛》里阐述的游刃有余的境界。‘无他,唯手熟尔’,是卖油翁的名言,也是大家形成个人风格和绘画符号的必由之路。”并于2010年底至2011年初在“自默文化网”上发表《“流水作业”不好吗?——替范增先生辩护并驳斥郭庆祥等》《为什么不能“流水作业”?》《关于“流水作业”答报社记者问》三篇文章,反驳郭庆祥。
2011年6月7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郭文》中通篇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格分别做出了贬损的评价,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庆祥的行为已构成对范曾名誉的侵害。另外还认为:因郭庆祥曾收藏范曾的作品,二人系交易的双方,交易行为之中存在商业利益,故郭庆祥称其文章为纯粹的文艺评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被告郭庆祥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七万元。
至于对第二被告文汇报,法院认为:虽然文汇集团对刊载的文章未严格审查,存在一定过失,但其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对范曾的名誉侵权,故对于范曾要求文汇集团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在法定期限内,郭庆祥依法提起上诉,文汇报也提起上诉。
一审判决披露后引起媒体哗然,相关专家学者也表示了不同意见——
专家声音
凌河(解放日报首席评论员、首席编辑):这个案件,案情并非盘根错节,但判决书很有可读性,读了就产生了几个问号,既涉及到民法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新闻法制上的一些基本范畴。我提几个问题求教于大家。
第一,贬损性语言导致社会评价降低就构成侵权的这个法理对不对?事实上,任何批评都是带有贬损性的,任何揭露不符合普世价值行为的言论,都可能导致公众评价降低。是否只要对负面事实进行了描述,就形成了名誉侵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鲁迅先生及其作品是否现在还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受到法庭的制裁?
第二,是否因为言论使人产生了精神痛苦,就构成了侵权?据我们所知,名誉权制度保护的是公民公正的社会评价不受损害,而绝不是不允许批评。如果批评属实,那么被批评者由于社会评价降低而引起痛苦,有什么不正常呢?如果所有正当的“引起对象人的痛苦甚至痛心疾首”的新闻批评都造成侵权,那还有什么舆论监督可言?所谓造成名誉侵权或精神痛苦的认定,究竟是依据推断、推定,还是必须有直接而充分的证据。
第三,认为被告是原告作品的购买者,两者之间有交易,所以不是纯粹的文艺批评,这种逻辑对不对?且不说世界上哪有什么纯粹的东西,按照这种“有交易”的说法,是否更说明了被告是一个消费者?那么他有没有消法规定的9大权利之一的监督权?对商品或服务提出批评,是否属于监督权的范围?因为有过商业往来,所以就不是正常的批评——这样一种司法创新的解释,是否合逻辑、是否有道理?
第四,还是回到文艺问题来。文艺观点是否可以成为司法制裁的对象?被告文章认为流水线作业、复制式的艺术是毫无艺术价值的礼品化。不管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艺术观点?如果是,是否可以戴上侵权的帽子?
第五,文艺作品最后的裁判权究竟在哪里?应该是谁?文艺创作是形象思维,而文艺批评是对于形象思维的再思维,是对于形象思维的逻辑思维,都具有文学艺术的独特内在规律,又是思想和观点的产物,法庭能够规范人的行为,是否也可以规范思想和观点?对于文艺思想的创作和批评,历史上是有过宗教裁判的。到了极左年代,又搞行政裁决。现在是否要走向司法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所在的基层法院来一锤定音?是不是法庭包打天下?其实,我认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后裁判权、真正的终审权,应该属于人民,属于实践,属于时代,也属于历史。所以即便法庭有了终审判决,我们是不是也不必将这种判决当成最后的结论或者最权威的判定?
第六,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究竟有多少?和政治人物一样,我认为公众人物当然有名誉权和隐私权,但按国际通例和政治学通则,他们这些私权应该有所让步。不仅是因为契约本身的缘故,更在于他们和平民、媒体对视中,往往会受到权利偏向、偏袒的很大可能性。这次一审判决是不是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从而再次说明了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因为沾有较多公共资源而应该让出一部分私权,以便让他们受到必要的社会监督、制约,同时显示社会的公平呢?
丁法章(原上海新闻学会会长、著名报人):我建议大家看看7月25号《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名字叫宣言。这篇文章对当前文艺批评界的乱象讲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而且明确讲这三个乱象严重影响了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文艺研究,严重影响了我们当前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里面明确提出“要提倡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多写中肯的逆耳忠言,少写浮夸的褒扬”。现在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研讨会也好,作品研讨会也好,基本上都是唱赞歌的,基本上都是表彰会,歌功颂德会。只说好,不说坏,大家都不见怪,成了一种风气,非常不好的一种风气。所以影响了我们现在文艺事业,包括我们新闻事业,缺少正当、积极、健康的批评。歌功颂德太多,逆耳忠言太少。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艺术品收藏家打破成见,敢于撰文,不点名批评了范曾这名画家对文艺创作的不负责任、不讲质量的表现。文汇报在学术专版发表了这样一篇争鸣文章,我觉得正当其时,这种文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可贵了!对文汇报的这种勇气,对郭庆祥同志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应该受到我们的称道,应该得到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是搞新闻评论的,什么叫新闻评论?有新闻再有评论,没有新闻无所谓评论。或者说,先有事实再有评论,新闻第一位,评论第二位。事实绝对要准确。现在郭庆祥同志讲范曾的一些事实,我相信是符合事实的,文汇报肯定非常审慎地决定要发表这篇文章,而且没有点名。如果这个事实准确的话,那么就是在评论了。范曾创作生产作品的过程,郭庆祥认为其中有不负责任、不讲质量、对公众利益有损害的地方,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我认为完全正常。范曾讲侵犯了他的人权,但我看了全文,好像沾不上边。尽管郭庆祥的用语是尖利的,是有战斗锋芒的,但这是个人文风,谈不上名誉侵权。而且我看材料,事实上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以后,范曾并没有因文章而受到影响,他照样升官加爵,当了一个什么院的院长,他的作品价格也是一路飙升。我看了郭庆祥的答辩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文汇报在判决书下来以后,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说服力。我看了这篇文章,心服口服,因为它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是能够说服人的。范曾和昌平区法院的同志不了解什么叫文艺批评,他们不懂。
范曾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看范曾的状纸,给郭庆祥戴了多少帽子啊?那个语言,比郭庆祥的要尖刻多了,上纲上线。而且曾几何时,他写文章讲黄永玉,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黄永玉告他了吗?没有。你可以对人家恶语相加,诽谤攻击,人家不可以对你文艺创作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进行批评?
丁邦杰(金陵晚报副总编):如果依照昌平区法院的逻辑,中国媒体要统统关门。文汇报刊载郭庆祥不点名批评范曾流水作业的文章,被告上法庭,这件诉讼案一度被新闻界传为笑柄,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法院一审判决文汇报因对刊载文章没有进行严格审查而败诉,创下了打击正当媒体批评的恶例。从法律角度看,媒体刊登文艺批评需要“严格审查”什么呢?首先批评的事实是否凭空捏造或歪曲?这一点原告自己并没有否认,流水作画是其所带博士生亲证的,而且郭庆祥当场出示了范曾墙上十几张挂的宣纸在流水作业的铁证。第二个,“严格审查”的内容,是该批评文章有诽谤和侮辱性语言。判决书上所列“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四个词语,连稍有常识的弄堂大妈也能辨别出,这不过是一种公民评价或者充其量叫买家抱怨,堂堂法官大人怎么可以“歪着斧头砍”,开罪新闻媒体呢?文汇报的争鸣文章除了通篇没有指名道姓,还在其用词造句方面比较严谨,它并未说你自诩“坐四望五的大师”是癞蛤蟆坐秤盘自称自贵;它也没骂你“流水作业”批量生产国画是糟践文化贪财不顾命;它更没批斥你横眉冷对公众指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么平和的争鸣都不让生存,非要吃一场官司赔钱道歉才能罢手,我国法律如何保护媒体及其新闻从业者正当的舆论监督权、新闻传播权、报道采访权,以及公民的言论自由呢?
范曾作为一个艺人他可以不知,但昌平区法院的法官大人不可以不知:尽管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都明确写上了舆论监督权和公民名誉权受到同等保护,但是,前者属于公权而后者属于民事权利,舆论监督由于公权的特殊性,处于法律优先保护的地位。况且,范曾是国内外知名的公众人物,这个身份决定了他的名誉权往往和社会的舆论监督权、普通公众的知情权等互为消长。自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后,公众人物在媒体批评的矛盾冲突中,他的名誉权已经受到显著抑制——这是大陆法系与欧美法系司法共同的判案原则。范曾平日里通过新闻媒体出尽了风头,享有了极大的社会关注资源。如果拿他的名誉权和一般公民相关保护使用同样标准的话,这显然是极不平等的。所以,社会各界普遍主张对于范曾这样的公众人物,舆论监督和批评适当从严,这具有利益平衡的基础,也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昌平区法官作出如此判决,其对正当舆论监督的杀伤力很大。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早就说过: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道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道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追究媒体责任。可以构成名誉权纠纷或诽谤罪的,只能是新闻报道,而不可以是评论性的文字。对社会中存在的某一类现象的抨击,对某种政府机关或某个行业及其社会名流的批评,无论言辞如何激烈,都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更不能构成诽谤罪。对于公众人物诉媒体的名誉权案件,法院在决定受理之前须对案情作初步的审查,只有媒体可能存在实际的恶意时,受理才是正当的。昌平区法院的这桩判决,之所以值得全国新闻媒体强烈关注,是因为它具有典型的扼杀言论自由、打击舆论监督的示范效应。如果照昌平区法官的逻辑,新闻单位见到范曾这样的名人就只能屈膝恭维,稍有不敬动辄得咎,必被拉上公堂赔钱道歉。长此以往,中国的新闻媒体就只能关门打烊了事。
江宏(上海书画院前院长、著名美术评论家):我们的文艺批评现状,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说好话,很少有对艺术作品提出批评的。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了。如今郭先生碰了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就是绘画界人尽皆知的范曾。本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给文艺批评打了一针强心剂,把歪风邪气变成正风、变成好的东西,居然被法院判了败诉。这是法律的问题,还是文艺批评的问题?一件好事情,怎么给法律一弄,弄成了我们都应该说好话,都应该歌功颂德,都应该把真正的批评压下去?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深挖一下,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批评才能往正确的方向走。
周瑞金(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画家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的一审判决结果令人惊诧。文艺批评家郭庆祥被判向原告范曾书面致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七万元——虽然这与范曾索赔的500万元相距甚远,但已经构成对本已命悬一线、极其脆弱的文艺批评的致命一击。因此,这一判决的影响力远超两位当事人的个人恩怨,或将成为一纸正常文艺批评与学术争鸣的“封口令”,使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再一次雪上加霜。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判例,倘若文艺批评的双方从此不再以理服人,而要由法院来做仲裁人去判断孰是孰非,这样下去,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文艺批评只会走向末日,而本已危乎殆哉的言论自由空间也会由此越来越逼仄。
仅仅因为对画家的“作画方式”及“人格”做出“贬损评价”,便是名誉侵害,文艺评论便不再“纯粹”了,这让我立即“为古人担扰”地想到了鲁迅先生。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鲁迅恐被罚得倾家荡产。当年鲁迅在文章中对梁实秋、顾颉刚、林语堂、郭沫若等一众文人均作过很多的“贬损评价”,比如鲁迅对梁实秋先生的指斥,指其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甚至说“凡走狗,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这样的话,其“贬损评价”的烈度,岂不是远超郭庆祥批评范曾?然而,这样的骂战,并不曾有损于梁实秋先生的清誉,也不曾见梁实秋先生将鲁迅诉诸法律。像曾与鲁迅论战过的林语堂先生,却在《鲁迅之死》中称,“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什么是大师的气度,林语堂可为表率。
鲁迅也曾经承认,“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然而,倘在今天,鲁迅若还敢这样常用尖刻之笔,一定会屡遭官司的罢?
其实,范曾先生本人也曾对沈从文、刘海粟、吴冠中、黄永玉等在行文有过“贬损”之讥,何曾见这几位与他对簿公堂呢?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时人对民国气象的景仰时有流露,这当然不是景仰当时的军阀混战,而是文化界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氛围。
由是反观此案,如果是放在民国,放在鲁迅先生的时代,被批评者要么一笑了之,要么也拿起笔来反诘、反攻击,但绝不会创造性地想到去“呈堂供述”,我们能想象鲁迅与林语堂、与梁实秋对簿公堂吗,请法官仲裁他们的笔墨官司吗?
既然文艺批评已经闹上了法庭,那么且让我们回到现行法律。
应该说,宪法要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与民法通则要保护的公民名誉权,确实在现实中时有矛盾之处。捍卫名誉权,常常是认定对方有侮辱和诽谤等侵权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保护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不受侵害,确实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道大题目、难题目。目前,在立法上对此还缺乏明确的界定,比如没有区分官员、公众人物与非公众人物,这便给了司法实践以很大的运作空间,本应对这些矛盾、冲突和立法空白折冲樽俎,在保护言论自由与公民名誉权这两种基本权利之间找到某种符合公平正义的平衡。
在一些国家的判例中,往往遵循这样的司法原则:对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案的判决要慎之又慎,谨防伤及公民言论自由。这是基于公平正义原则。1964年美国发生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亚拉巴马州法院判《纽约时报》侵权,赔偿50万美金。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认为亚拉巴马州法院适用该案的法律规则不足以从宪法上保障第一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此撤销州法院的判决,《纽约时报》胜诉。沙利文案后形成的实际恶意原则、事实与评论分离原则、公共事务原则,都成为审判名誉侵权案的重要司法原则。所以,在美国新闻侵权案中新闻单位的败诉率只有8%,而中国却高达80%以上。沙利文案中法官的一席话成为司法判例的经典:“我们以这样一个全国深刻认同的原则为背景来考虑本案:关于公共问题的辩论应当是不受抑制的、活跃的,和充分开放的,当然也包括激烈、尖刻的、有时是令人不快的严厉抨击。”
公众人物的言行直接影响公共事务,应当接受公众监督。虽然公众人物也享有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在内的人格权利,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有更多为自己辩解的话语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实行弱化保护。这是做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已经得到足够的补偿,所获社会尊重远超普通人,其社会地位、权力和影响也使他拥有较强的抗御侵害能力。
可惜的是,目前在这个领域我们却不得不同时面对立法缺陷和司法混乱。在现实判例中,往往是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被“强化保护”,较之普通百姓更能打赢所谓名誉权官司。范郭案又是一个新的例证。这一判决如果生效,恐怕所有批评性的舆论监督都将噤若寒蝉,或者怀揣人民币才敢进行写作。这样的如履薄冰,如何能让我们迎来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这也让我们在缅怀民国先贤的时候,不能不别是一番滋味:时隔一个世纪,我们在言论自由方面,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为了保护文艺批评、学术争鸣,我们至少应当确立这样几条原则,与名誉侵权划清界限:1、批评依据的事实是客观真实存在,并非虚构捏造;2、批评对象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并非个人之间恩怨;3、批评出于诚意,并非出于主观恶意;4、允许进行反批评,并非阻挠反批评。我认为这4条应该是划清界线最基本的。
政治文明建设行进至今天,守卫言论自由的宪法底线,防止司法滥权,是时候了!从这个案子起应该警醒了。
魏永征(汕头大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去年北京有记者问我对这个案子怎么看,要采访我,我说那你得把资料给我,要把证据给我,不好干预司法。他就给了我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也就是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范曾流水作画的照片。我说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谈的。为什么呢?看了这张画,我想我们都会提出不同的疑问:这个画都差不多,一张要卖几万,十几万,值不值?荣宝斋的水墨画一张也就一千块。当然你可以问,你画得出来吗?你能一下画这么多张吗?这个就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争论,在我们社会上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电影、戏剧、小说,讲大一点,政治家的演说、措施,大家都可以评论。小而言之,我们吃一顿饭,这个厨师做的菜好不好,有的人说太好吃了,有的说太差了,说差的,难道都侵犯了厨师的名誉权吗?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来说,我们在座的明天都要做被告,因为我们都攻击了范先生,甚至说不定还攻击了法院。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基本道理——如果发生诽谤案件、或者名誉案件的审判,要把意见和事实区分开来。这个基本的原则,可能是国际通用的。比如普通法、英美法里,三大抗辩理由的一个,免责抗辩理由,就是公允评论。今年3月15日英国司法部对国会提出一个《诽谤法》修改的草案,草案里建议把公平评论、公允评论改为“诚实意见”,这个意见即使是偏激的甚至片面的,都不能成为诽谤。甚至意见错了,也不能构成诽谤。因为意见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是英美法。
欧洲人权法院在审判名誉案件或者诽谤案件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把事实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如果是价值判断,法庭不能判断你这个价值判断是错或对。所以如果是价值判断,他不构成诽谤。
法庭判决只能根据事实判断,只能判断事实的有无,不能判断意见的对错。判断意见的对错,不管是政治的对错还是文艺的对错或者是对厨师烧菜好不好,这是通过公众讨论或者学术研究来加以认定的,得出一个大致一致的意见,法院、法官不能判决这些问题,不能判决意见的对错。因为意见是不可证明的。这同我们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一致。言论自由的基础是意见自由。就是说,言论自由里包括事实和意见两部分,我们没有造谣的自由,没有诬蔑的自由。传播虚假的言论,是没有自由的,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但是,我们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意见和事实分开,这是一个国际惯例。
我们中国怎么样?我们中国事实上是有这样的规范的。这个规范,就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这里边说,因为批评文章而引起名誉权纠纷应该如何处理?三条。第一条,如果批评的有关事实基本内容属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不构成侵害名誉权。第二条,如果文章的基本内容真实,但有侮辱他人的内容,构成侵害名誉权。第三条,基本内容事实构成侵害名誉权。也就是说,两种情况是可以侵权的。第一种情况,传播了虚假事实,损害了他人名誉。第二条,传播了侮辱他人内容的有关词句。这里边没有意见,没有讲到意见的错误会构成侵害名誉权。所以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批评性的意见不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在我们1993年的司法解释里边已经有了。
这个案子涉及的“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这些话就要看他是不是针对一个事实。有没有事实?他前面有一大段事实。这段事实已经写进判决书里。法院认定他有举证“流水线作业”这个事实。他是根据这个事实来做评论的。我们看郭先生的文章,是一片说理的文章。我们现在对侮辱的问题研究太少。好像有些激烈的词句就是侮辱。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言词性的侮辱到底怎么界定。但是尽管研究不多,可以肯定这个案子的四个词不是。
这个案子为什么应该拿来讨论?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新闻评论、文艺评论、学术研究和其他各种媒介传播的发展。
殷啸虎(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上海市政协常委):这个案件涉及到两个权利,一个属于文化权利,一个属于人身权利。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了,怎么办?我的理解,名誉权的界限和文艺批评的权利界限放在一起,中间就剩下一个模糊地带。我们今天探讨的,到底是中间的一个线,还是这个阴影部分?这个法律要搞清楚。线条的线,就很清楚。就像我们跟日本主张的东海,中间就有一个阴影部分。他说的中间线,我们不承认的。这个部分中间,就是我们讲的模糊地带。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线条弄清楚了,起码从法理上我们可以理清问题了。文艺批评的尴尬,恰恰在于边界的模糊。
我认为文艺批评权和名誉权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不是模糊地带,那就是一条线条的线。线在什么地方?就是人品和作品,就是文艺批评权指向的对象是什么?我觉得法院的判决非常不聪明,从法院判决来看,首先法院已经认定了一个事实,就是说郭庆祥所批评的对象是范曾的画、诗、书法以及作画方式。这个属于作品的范畴。我批评的是作品,作品属于什么范畴的?属于文艺批评权的范畴。我们说,作品是由人创作的,肯定要涉及人的问题。如果我这个批评是从你的作品包括你的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包括创作方式等出发的,很清楚,这个还是作品,不是人品。就是批评作品的时候,附带对人品进行批评,这是符合文艺批评的界限的。所以我批评作品,肯定要涉及到人品。名誉权和文艺批评权的界限,我们要界定清楚。一旦界定清楚以后,你再来看,法院判决书认定的,绝对就是范曾的作品,而不是纯粹的人品。而名誉权的侵害,绝对是对人品的。
道理上讲,你有名誉权,我有言论自由权。但从判决书上看,这个说法并没有被法院所采用。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我们国家从宪法层面讲,言论自由的指向对象主要是公权,对政府的批评。一般对个人之间的批评,我们很难用言论自由去对抗民权。如果言论自由了,恰恰证明你是诽谤他的。美国讲言论自由的界限,叫“明白而即刻的危险”。没有地震,你说地震,大家短时间内跟你跳下楼了,你构成的是明白而即刻的危险,造成了后果。从这个来讲,我们说名誉权也好,文艺批评也好,把中间的线分好,一边是作品,一边是人品,他批评了什么。如果用言论自由的话,可能比较模糊,有些话确实说不清楚。他说言论自由,你说你不能诽谤我。但文艺批评权也是我的权利。一个是权利,一个是自由。权利和自由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是积极权利,一个是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我可以积极行驶某种权利。消极权利就是我不让别人做这件事情,或者我做了这件事情别人不来追究。这中间是有一个区别的。
法官可能也意识到文艺批评权利可以对抗名誉权。言论自由很难对抗名誉权,难度比较大,用文艺批评权去对抗名誉权,这就是两种权利的冲突。如果我们主张文艺批评权赢了,那么我们就赢。所以法院很清楚的,他做了一个界定,他说“郭庆祥的文章为纯粹的文艺评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但他依据是“双方基于交易行为,双方之间存在利益,所以你不是文艺批评”。这个就非常荒唐了。很简单的道理,你是作家,有一本书,我凭什么批评你?首先得我看过你的书。我看到这本书有几个途径,一个你送给我,第二个是借给我,第三个我去买一本。我收藏你的作品,不符合我的预期,所以我才提出批评,这个预期包括对你作品艺术价值的预期,也包括对你作品的商业价值的预期。正因为艺术价值高,所以商业价值也高。为什么买范曾的画?范曾的画肯定比我的画艺术价值高,所以值钱,这是肯定的。法官这个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通过双方的交易行为否定文艺批评的观点,这个法律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个一两句话就可以驳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