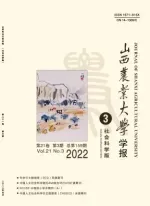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
——对季卫东 《宪政的复权》的解读
亓捷,任才峰
(1.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2.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
——对季卫东 《宪政的复权》的解读
亓捷1,任才峰2
(1.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2.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宪政是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制度基础,不同的时代背景应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在当今全球化、地域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宪政在许多方面都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 “新论”。法学家季卫东先生从新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法社会学的视角,用复眼式的观察方法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的新内涵,同时也指出政治变革乃中国当前避免权力合法化危机的必由之路。
宪政;修宪;护宪;政治变革
宪政也叫民主宪政、立宪政治,是体现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的政治制度。可以说,实行宪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作为法治国家的中国,更应该依宪法来治理国家。但将宪政问题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却难免有些失落。尽管中国宪法历史已近百年,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追求也近百年,但是基于有识之士共同认同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宪政文化资源的缺乏,中国的宪政建设一直尚未成功,宪法学人对宪政道路的探索也异常艰辛。
而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全球化、地域化的趋势,政治民主、经济进步、文化多元的背景,都对普遍性法治秩序提出了挑战,因而新背景下的宪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如此价值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中国的宪政道路将往何处去?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仔细阅读了著名法学家季卫东先生的《宪政的复权》与《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变革》,这两篇文章从新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法社会学的视角,用复眼式的观察方法探讨现代宪政的新含义、法治秩序如何定位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宪政的出路——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季先生深刻而严谨的论述为我国艰难的宪政之路确定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一、多只眼睛看宪政
季先生首先带领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宪政:前苏联、东欧各国的 “宪法革命”,形成了新的宪法秩序下的一整套制度;西欧社会批判理论的宗师哈贝马斯立场转向维护 “民主法治的国家”,提倡 “宪法爱国主义”,这提示人们现代法治主义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是各种制度创新的基本参照物。而且自由主义宪政的制度安排的复权也影响到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 “政治承诺”,对“依法治国”的宣称使我们对宪政运动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研究宪政,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首要前提是要弄明白何为宪政。但学界对宪政的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将宪政解释为 “民主的政治”;[1]许崇德教授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民主政治,“如果再加上形式要件,那么宪政应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2]另外还有学者别出心裁的将宪政作为宪法逻辑运动的状态来解释。[3]但纵观整个宪法学界学者们对宪政的解读,基本都涵盖了 “民主政治”的内涵,这无疑是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论断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和延伸。“事实上,有民主政治并不等于实现了宪政,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中世纪城市民主制以及近现代不少国家的民主实践都能说明这一点。”[4]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再作详细解释。通过以上表述,我们了解到宪政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国家管理的理想状态,尽管宪政不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在找到更好的制度之前,我们必须极力推崇其优点并为我所用。但克服教条主义,在中国语境下赋予其新的含义,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
在如今 “价值判断相对化,普遍主义的、绝对的规范体系渐趋瓦解”的时代背景下,极需脱离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 “虚无主义”的情绪,对现代宪政及现代法秩序进行重新定位。伯尔曼曾经指出,“没有信仰的法律将蜕变成僵死的教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5]“对于美国人民,宪法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祖国的象征,是他们美好生活的清晰表达,是他们自由的宪章。”[6]“我们有很多理由庆祝美国宪法,特别是因为它是我们权利的保护神。”[7]而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我国现行1982年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规定有18条,内容充实、合理、具体,因而宪法学者将宪法称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宣告书”。然而,美好的宪法文本规定是否就意味着民众也建立了对法律尤其是宪法的信仰呢?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它规定了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所必需的权利和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必须履行的义务,法律作用的发挥并不能完全仰赖于国家的强制力,更应该寄托于公众对法律的一种基于内心的服从和崇拜而形成的信仰。哲学家康德认为,信仰是一种“确信”,但这种 “确信”和意见、知识的确信不同:意见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没有充足理由的判断,知识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有充足理由的判断,而信仰则是人们在主观方面有充足理由,也就是在信仰者看来是确实可靠,而在客观方面却得不到充足证明的一种 “确信”。[8]而法律信仰是 “根源于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进而所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9]具体到宪政领域谈法律信仰,就必须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使宪法权威不仅仅体现于对国家机构的设计、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且要使 “宪政与宪法精神成为整个社会公民内化的生活信仰”。[10]但是毫无疑问,在中国 “有人治无法治”的历史传统以及 “权大于法”的政治现实的国情下,要树立全民对法律的信仰,是 “极其艰巨的作业”,“它既要解决尚未完成的现代化问题,也要解决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现代性问题,因而面临解构与建构并行的两难”。[11]但是若要希望推行宪政之路顺利平坦,仍要 “毅然决然地与法律虚无主义进行格斗”。[11]
美国公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提到:“我们的公法,就其效力来说,依赖于广大人民对其基本生活条件的接受。人民的接受,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机构,是法律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力量。”[12]因而,真正树立宪法权威应当成为宪政建设的要务。中国语境下的宪法权威的树立,一方面应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视野,总结人类的经验教训,借鉴西方制度文明的合理成份;另一方面宪法权威和宪政建设更应该考虑中国政治现实因素,将宪政建设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二、路径之一:尚需宪法文本的完善
最早明确提出 “法治”一词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 《政治学》一书指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应该包括两重含义: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到了17、18世纪,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治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逐步扩大,并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这已经成为共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宪法至上可以说是法治的根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战胜封建专制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和颁布资产阶级宪法,以巩固其民主法制。英国1689年的 《权利法案》、1787年美国制定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法国1789年 《人权宣言》,开创了资产阶级以宪治国的历史。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法制建设和多部宪法的通过和完善,对于宪法在法治之路中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正如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法治 “是人们提出的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以实现的政治理想”。[13]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文正邦也认为:“现代法治应与宪政的涵义同一。”[14]可以说,以宪治国已经成为一切民主法治国家坚持的基本原则。
然而正如季卫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的,“无论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宪政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来看,都很难说中国宪法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达到了它应该达到的水准”,从而为我们提出了及时修宪的任务。尽管从宪法的地位来看,为了确保其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应该保持其稳定性,但是经济建设的加快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又要求宪法逐步完善才能跟上时代步伐,也才能保证其应有的效力和得到实施。修宪的要求提出以后就必然涉及修宪的模式问题。是 “推倒重来”还是 “部分改宪”?这要基于立法成本、立法技术以及对政治秩序的影响的考量。季先生基于维护政治秩序的连续性、节约制度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主张推动国家在近期内按照既有的法律程序进行比较大幅度的改宪,并为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改宪方案。“正如及时的改革对政府有利那样,温和的改革对人民也是有利的。之所以对人民有利,不仅因为温和的改革具有持续性,还因为它具备一种生长的原则。”[15]宪政观念指导下的 “改宪”即是这种 “温和的改革”。
要体现宪法的权威性,要求我们不仅仅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文本上的完善,还要求我们以实际行动保护宪法。“在中国推行宪政的第一步应该是护宪运动”,“虽然现行宪法在内容上的确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毕竟政治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弊端都是以违反宪法的方式而存在的”。[11]因而,基于在短期内不能通过修改宪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护宪”更为当前的主要任务。“经验表明,百姓以其最朴素的生活逻辑体验到法律和法律实践给予他们的利益实现和权利关注,这是最大的宪法和宪政意义,宪法和宪政这个词在不识一字的老农那里可以不获得抽象性理解,如能获得最大拥护,岂不是宪法和宪政最大的价值体现。”[16]
三、政治变革:避免权力合法化危机的必由之路
上文已提到过,有民主政治并不等于实现了宪政。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人民可以基于平等原则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并可以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政治决定。但但凡读过托克维尔的人都会对这一完美的制度构建提出疑问,在 《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17]“多数人专制”的理论对我们坚信无疑的民主政治提出了挑战,从而使得一部分人从对民主的赞叹走向对民主的否定,其实这存在对托克维尔的误读。按照古典的民主理论,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当多数人做出错误决定时必然会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出现多数人的专制。托克维尔在看到社会民主的趋势时首先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但托克维尔并未因此而走向对民主的否定,而是力图使民主更加完善,防止多数统治的无限权威。
宪政概念的引进又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与宪政结合下的民主 “通过根据自由和人权的法理对权力进行制度性约束方式,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多数派专制的弊端”,宪政内含的 “分权”的原理和 “人权”的原理,旨在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来限制国际的强制力,保障统治的正当性,“避免牺牲弱者的自由以及脱轨的民主”。[11]
在当前全球化、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的宪政之路不得不借鉴别国的经验。单看亚洲邻邦,尽管金融危机使得许多国家权力结构发生分化,社会秩序崩溃,但是 “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虽然还不很完善但却正在逐步走向稳定和成熟”。但在中国却往往存在借口成本巨大、条件欠缺而反对政治变革的声音。但他们更应该看到 “由于缺乏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的制度条件”,使得 “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其能量之大使得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任何重大改革措施都难以付诸实施”。2006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中曾强调指出:“上层建筑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今后,我们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中国政治变革已迫在眉睫!
借鉴亚洲邻国的成功经验,“把违法的权力之争转变为依法的程序之争,把一纸具文的宪法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宪法,是民主化得以成功的经验”。因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任务是推行法治和宪政,并进而建立一种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少数者权利的民主制度。发展民主就要完善法制、依法治国,而宪政则是国家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制度基础,二者缺一不可。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726.
[2]许崇德.学而言宪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3.
[3]莫纪宏.宪政是宪法逻辑运动的状态 [J].法律科学,2000(5):28.
[4]周叶中.宪政中国研究 (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7.
[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M].北京:三联书店,1991:47.
[6][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 (导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6:1.
[7][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 [M].北京:三联书店,1996:524.
[8]康德著,许景行译.逻辑学讲义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7-62.
[9]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3.
[10]刘和海.宪政基本问题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44.
[11]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52,53.
[12][美]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洪德,杨静辉译.美国法律史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60;转引自杨海坤.中国走向宪政之路 [J].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编.东吴法学文粹 [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69-170.
[13]米勒,波格丹诺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675.
[14]文正邦.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80.
[15][英]伯克著,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自由与传统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40.
[16]刘奇耀.中国语境下的宪政之路 [C].刘和海.宪政基本问题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05.
[17]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7.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of Constitutionalism——Decoding Ji WeiDong's Constitutional New Theory
QI Jie1,REN Cai-feng2
(1.LawSchool,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2.LawSchool,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China)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based on different backgrounds should be given its different meanings.In today's globalization,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the new era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many ways has been given new meanings,an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new theory" .Mr.Ji Weidong's jurists start from the new background,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law,with the compound eye style with observation methods of a new era for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new content,but also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change is to avoid legitimizing the power,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Constitutionalism;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Protect the constitution;Political reform
D90
A
1671-816X(2011)02-0113-04
(编辑:程俐萍)
2011-01-08
亓捷 (1986-),女 (汉),山东莱芜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