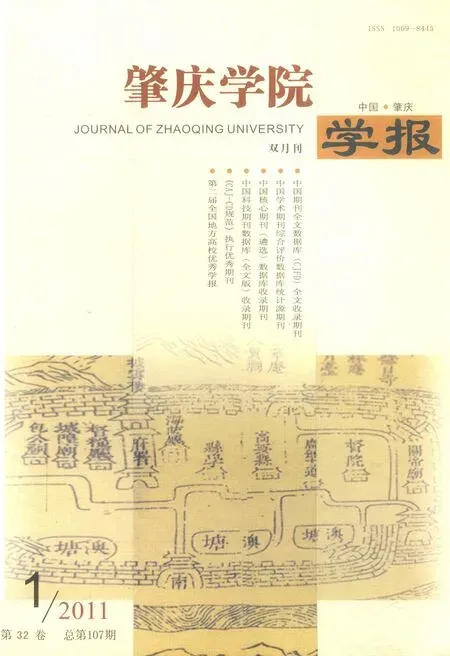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艺术论与郭润文油画创作的“归家”主题
韩 靖
(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艺术论与郭润文油画创作的“归家”主题
韩 靖
(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郭润文“归家”主题的油画创作体现出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艺术论的某种程度的契合。其作品在“归家”的呼唤中流露出的存在关怀、人文关怀,以及古典主义的艺术追求,既是对于艺术表现的社会化、政治化模式的超越,又是对于当下流行的形式游戏和娱乐精神的纠偏,重建了艺术和生命的联系,具有永恒的价值意味。
郭润文;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艺术论;“归家”
在当代艺术的众声喧哗中,郭润文的油画创作始终坚持对于艺术和生命关联的正面追问,坚持艺术引领人重返生命家园的艺术宗旨,其具有古典主义品格的油画创作,看似“不入时”,却有着永恒的价值意味和对于当代艺术创作的纠偏意义。此外,在研究郭润文“归家”主题的油画创作中,我们发现其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艺术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这体现出郭润文油画创作的“世界品格”。本文透过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艺术论的视角,从内涵与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对郭润文“归家”主题的油画艺术展开考察。
一、聆听“归家”的命运之呼唤:艺术家的使命
关于艺术与“归家”,与人类救赎的关系问题,谈得最深刻,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海德格尔了。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人所回归的家园就是“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什么叫“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呢?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命家园中,天、地、人、神“以统一的四位的单一状态而彼此依存。四者中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映射出其余三位的在场。此外,每一位又在此四位的单一性中以自己的方式映现自身,进入自身。 ”[1]因此:“‘在大地上’已经意味着‘在天空下’。这两者也意味着‘留存在神面前’,还包括‘居于人的共在’这一层意思。”[1]186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命家园里,没有哪一位是中心、主宰和绝对者。而就“人”来讲,也只有处于这“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里,与脚下的大地,天上(心中)的神灵建立起和谐的联系,人才是在“家”的,也才是“自由”的。这也就是存在的“无蔽状态”,海德格尔又形象地称之为“澄明”或者“林中空地”。

图1 《梦归故里》1995年作
海德格尔认为,回归“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里是人类唯一的“命运”。然而,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现代化“去魅”在将人从被自然和神灵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又使人成了可以对一切为所欲为的“主人”,如此“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也就解散了。伴随着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海德格尔展开了他的艺术“归家”之思。在海德格尔看来,今天,也只有艺术可以重新引领我们“归家”。那么,为什么艺术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来看海德格尔对于艺术之本质和存在意义的规定,他说:“艺术在其本质上既不再现、表现和象征什么,也不单单是将存在者带上前来,艺术‘创建’(Stiftung,Founding)存在者的‘真’(无蔽状态)。”[2]既然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创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更确切地应该说是“记录”,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家无须在艺术中“表现”或“象征”什么),从而它能开启存在的澄明,使欣赏者沿着艺术所开启的归家路,重新返回生命的家园。而艺术家的使命就在于聆听归家的命运之呼唤,并将这“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之美好记录在他的艺术中。
海德格尔的艺术论,不仅明确了艺术的使命在于引领人“归家”,而且也否认了艺术是对外在社会现实的“再现”和对主观自我的“表现”,也不是什么观念的“象征”。艺术所表现的就是流浪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苦苦寻找归途的人的存在。这样便使艺术的视角重新转移到了个体之普通存在。并且对于单纯之“再现”和“表现”的否定也使海德格尔的艺术趣味趋向于古典主义的和谐。总之,海德格尔的艺术论是其存在主义哲学在艺术上的体现,是对在传统主客二元对立哲学观念影响下的艺术论的颠覆。也就是在以上诸方面,郭润文的新古典主义的油画创作,体现了与海德格尔的艺术论的某种程度的契合。
二、《落叶的季节》等女性系列:失家的感伤
从郭润文的油画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很明确的对于“归家”的呼唤。这突出地表现在郭润文的以《落叶的春天》(图2)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题材的油画创作中。当艺术家企图书写他的“归家”之思时,女性的存在——这“家”之主要的象征,便成为他艺术表现对象的首选。

图2 《落叶的春天》1996年作
在郭润文的成名作《落叶的春天》中,在貌似神龛的散发着神秘气息的背景前,一位年轻女子坐在“如刑具一般的椅子”[3]上,她面色苍白,神情哀伤,一只手无奈地摊开,而另一只手向虚空伸出的四个手指,似在暗示她死去的孩子只有四岁。在她的周围,飘零的春天的落叶在回旋翻舞。而在她的怀中,停留着一枝折落的树枝。此情此景,都不仅让人联想到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哀悼耶稣》中那位怀抱着自己死去的儿子的少女圣母。《梦魇》和《疲惫》描绘的都是在真实的生命困境中挣扎的母亲形象。母性的伤痛,是家之不幸和解体的征兆。在《童年的游戏》中,少女如玉般纯净温润的面孔和她身后暗黑的背景形成对照,恰如她手中儿时的游戏所表征的童年世界的美好与成人世界的残酷对照一样,让我们为终将失去生命中最为快乐澄明的部分而喟叹。同样的表达也出现在《本命年》中,少女明艳的红衣无法驱散徘徊在窗外的不祥命运的阴影。据画家讲,他在创作这副画时,正受到忧郁症的折磨,可见其中凝聚了艺术家的极端绝望的生命体验。《梦归故里》(图1)和《缝纫女工》表现的是最终被驱逐出家园的女子。在《梦归故里》中,表现了由于劳累和困倦而伏在缝纫机上昏睡的少女,在梦中又回到了家乡。《缝纫女工》中的女孩子独处在一间库房般的空间里,她面色苍白,衣衫单薄,眼神单纯无助,在她四周,流淌着冰冷、陌生的水泥气息——这就是在异乡的生命体验。这两个女性形象都令我们联想到离开故乡来到城里的打工妹。在此郭润文表达出了和海德格尔同样的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世界的批判。《出生地》中,女孩子虽然重又得以亲近故乡的土地,但画面上所流露出的感伤情绪,却更让人体会到她曾经在异乡的漂泊和无可归依。
三、“缝纫机系列”等静物作品:回归大地亲情
对于人之“失家”的描绘使郭润文的油画创作弥散着一种浓重的感伤,然而“归家”的呼唤就此响起。郭润文的“归家”之思,首先重建了人与“大地”松弛了的关联。对于亲情的怀念与向往是郭润文油画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综观我的作品,人们并不难发现,我的题材千变万化,内在的主线却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相互依赖。”[4]亲情对一个人的存在来说,则属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四方共同体”中的“大地”部分。“大地是那既显出又隐蔽的东西。大地自持自立着,无为而无怠。正是在此大地上和此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才获得了栖居于世界之中的基础”[1]41。但是另一方面“大地”又意味着“从此出现的东西由此收回,并隐匿一切自行涌现之物。在此涌现出来的万物中,大地是作为隐匿者出场的。”[1]36也就是说,大地既是我们得以存在的背景和根据,又是我们的所由来和最终归宿。而亲情对一个人的存在来讲,就具有如此的“大地性”。
对亲情的怀念和向往在郭润文的“缝纫机系列”等静物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永远的记忆中》(图3),那斑驳的墙面、流泪的红蜡烛、脚踩缝纫机和剪刀,高超的写实手法造成的强烈视觉效果足以激发起曾经将生命的一部分丢给那段岁月的人,对于童年、母爱和手足情深的怀想和追忆。正如作者所说:“我画《永远的记忆》是把缝纫机当成了体现亲情和母爱的一个媒体,一种符号。我想,凡是经历了那个特定年代的人,都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些东西。”[4]《痕迹》所描绘的似乎是一间老屋:式样老旧的桌子和木箱、破纸箱、煤油灯,散发着辛酸而追忆的气息。还有《碗》,那只粗砺的、边缘已经破损的大碗,令人想起童年饭桌上散发着母亲味道的稀粥。

图3 《永远的记忆》1993年作
然而,综观郭润文的“归家”主题的油画作品,我们发现,向大地亲情的回归成为他归家之思的最强音,对亲情的怀念和向往也是他作品中最具艺术感染力的因素。也就是说,在郭润文的归家之思中,重建人和大地的联系不仅是创作起点,也似乎成为了创作终点。
与郭润文不同的是,对海德格尔来讲,人要重返“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并不只要和其中的某一个元素有关联,而是同时要建立起和大地亲情以及天上诸神的关联。没有脚下的大地,人就不会有根基;然而,没有神性尺度的指引,人也不会有创造力和超越性,也就最终不能够将这个世界变成人的家园。海德格尔的归家之思凸显的是一个既有大地性,又有神性追求,参与着大地和世界的去蔽和遮蔽之斗争,真正自由自觉的个体。与此相应,他所肯定的艺术都是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存在之无蔽状态之呈现。像古希腊神庙,是“神的形象”和“人类的命运”的合一,它屹立在山岩之上开启着世界。而梵高笔下的那一双农鞋既“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也有“死亡逼近时的战栗”。
和海德格尔相比,郭润文的“归家”之思忽略了神性尺度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以亲情的回归为最根本,体现了中国传统血亲伦理文化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中国特色的归家之思影响他的“缝纫机系列”的油画创作,就是:“家”的形象虽然温暖感人,然而艺术境界还不够阔大开敞。
四、《教堂》系列:迎接神性之光
人要重返家园,不仅要重建和大地亲情的关联,神性的光辉也要照临到他的存在之中。何谓“神性”?在海德格尔的视阈中,“神性乃人借以度量人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栖居的‘尺度’。唯当人以此种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按其本质存在”[5]。天空之神为人提供了衡量生存的尺度,在这个尺度下显示出大地和天空,现实和理想,遮蔽和澄明的距离。人的存在若没有神性的尺度,便不能够追求和超越。
在郭润文的感伤而温暖的画面上,隐现着一种神秘意味,这种神秘来源于宗教因素。然而如果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在郭润文的笔下,宗教的悲悯情怀要多过宗教的超越因素。画面上的那些有着宗教气息的美丽女性,她们那一张张苍白的、孩子气的、散发着玉般光泽的面孔,既显示出内心的纯洁,又流露出对命运的忧伤;既显示出信仰的忠诚,又流露出对救赎的渴望。而她们那些有着宗教意味的手势,既是一种寻找和方向,又显示出无助和迷茫。笔者认为,醉心宗教的悲悯情怀依旧和艺术家深埋心中的对大地亲情的向往有关。
《出生地》(图4)被视为郭润文的代表作,画面寓意贴切地表达了郭润文的主体的 “归家”思想。一个女孩子经历了太多的流浪,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故乡的大地正承载、安慰着她生命的伤痛。阳光透进来了,洒在她身上,这不仅仅是故乡的太阳,也是神性启迪的光辉。但她现在还太疲惫了,她把头偏在一边,微闭双目,还没有力气去接受这神性的启迪。

图4 《出生地》2004年作
但人必须将天空神性的澄明纳入到自己的存在中去,这个天地合一的世界才可以叫作我们的家园。2008年以巴黎圣母院为题材的油画《教堂》(图5)系列,显示出了郭润文后期“归家”之思的变化。在这些作品中,神性的超越因素明确了,宗教之光坚毅地照亮了黑暗。人物形象虽然很小,然而那明亮的光束执着地穿透黑暗,正是精神世界信心和力量的体现。而在几乎创作于同时期的《排练》和稍后的《聆听》(图6)等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超越的精神力量。归家之思的新变化为郭润文油画艺术带来了新的美学因素:一种深沉坚毅的力量感和阔大开敞的气象。

图5 《教堂之二》2008年作
五、“单纯的宁静”:古典风格的追求
就像天、地、人、神在生命家园中没有哪一个是主宰一样,在海德格尔的视阈中,艺术活动中也没有哪一个是主宰,无论是社会力量,还是艺术家的个体欲望。因此,艺术既不是“再现”,也不是“表现”,更不是什么观念的“象征”,艺术只是对存在的“无蔽状态”的忠实记录,是呈显。“在艺术作品中,是真理而不仅是真实的某物在活动”[1]56。因此,海德格尔所推崇的艺术风格,既不同于“极端的现实主义”,也不是“极端的形式主义”,它同时拥有“伟大的现实性”和“伟大的抽象性”,那是一种“单纯的宁静”。海德格尔将其命名为“伟大风格”,也称之为“古典风格”。“尼采所谓的宏观风格最接近于严峻的风格,古典风格。”[6]海德格尔是这样来描述“伟大风格”的:“伟大风格是一种单纯的宁静,它来自于对生命之最高丰满的自持与支配。它是生命的原始解放而又有所节制;它是可怕的对立而又是单纯的统一;它是生长丰满而又是稀世之物的永恒。凡艺术之作最高形式,凡艺术之作为宏伟风格而被把握的地方,我们就必定回到了生命显现的原始状态……”[6]250。也就是说,这“伟大风格”或者说“古典风格”是存在的各种元素的又一次和谐统一,是存在的澄明在艺术上的体现。
郭润文一直被视为古典油画品格的执着追求者,而他的古典主义美学风格的追求与他对艺术之本质和使命的理解相关。在回答对于“古典主义”的理解时,郭润文说:“一个是人文,一个是宗教,我觉得是这两点。”[7]他的新古典主义的艺术也表现为,与其归家之思相应的,向着海德格尔艺术论视阈中的“伟大风格”和“古典风格”努力和趋近。
在郭润文作品的画面上,有着一种克服了“对立统一”之后“单纯的宁静”。谈及对于古典主义油画形式的理解时,郭润文认为,“透过一层珐琅般晶莹剔透的物质形成的空间,探视到深厚结实的色层”[3]是古典主义油画的形式秘密,是纯正的“油画味”之所在,也是郭润文执着的艺术追求。其实,郭润文油画创作的动人之处,也正是画面上浮现出的幽暗与光辉交织出的神秘高贵气息。而那一片幽暗与光辉交织的所在,就是郭润文的归家之思的形色停驻。在这一片幽暗与光辉交织的沉静中发生着遮蔽与去蔽的斗争,是向着澄明家园的无限趋近。那“深厚结实的色层”里有着大地和深渊的诱惑与安慰,有着存在的沉默和锁闭;又有着救赎和超越的光明,透过那锁闭的存在射进来,才形成了这一片“珐琅般的晶莹剔透”的光彩。因此,正如郭润文自己所说“技术不仅仅是油画质地,它包括所有绘画本体的因素”[3]。
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在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历史和文明进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的解体。与此相应,艺术不是以“‘创建’(Stiftung,Founding)存在者的‘真’(无蔽状态)”为己任,而是表现人的存在的片面性,这时的艺术就无法承担起引领人归家的重任。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艺术论相一致,郭润文的油画艺术创作,将视角转移到存在中的人,是与他脚下的大地,头顶的星空,与他的卑微和信仰关联着的有着自我命运的个体的人,这既是对于艺术的社会化、政治化模式的突破,又是对于当下流行的形式游戏和娱乐精神的纠偏,重建了艺术和生命的联系,重建了艺术的价值,这是郭润文“归家”主题的油画艺术对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贡献所在。
[1] 海德格尔.系于孤独之旅:海德格尔诗意归家集[M].成穷,余虹,作虹,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22.
[2] 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53.
[3]郭润文.我谈我画——与老锅的对话[J].美苑,2002(2).
[4]鲁虹.对亲情的向往与怀念——鲁虹与郭润文对话[EB/OL].[2007-06-14].http://guorunwen.artron.net/main.php?newid=29482&aid=A0000214&pFlag=news_2.
[5] 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504.
[6] 刘旭光.海德格尔与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48.
[7]谈话——古典性也是一种当代性(郭润文VS张晓凌)[EB/OL].[2009-03-05].http://art.china.cn/mjda/2009-03/05/content_2772510.htm.
(责任编辑:杜云南)
J05
A
1009-8445(2011)01-0077-05
2010-12-01
肇庆学院2010年校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01012)
韩 靖(1970-),女,山东菏泽人,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