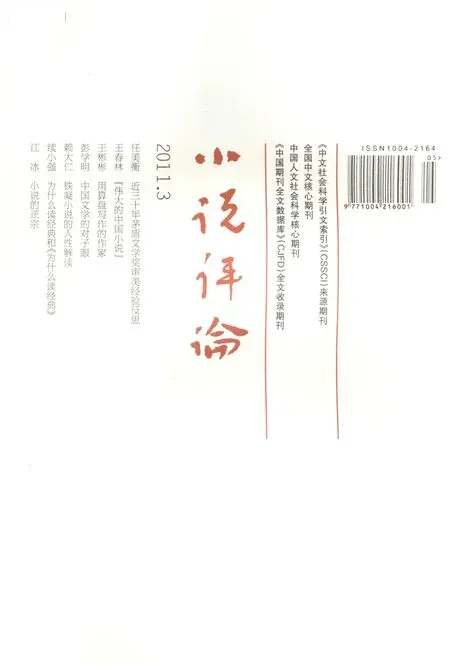小说的正宗
江冰
小说的正宗
江冰
何谓小说的正宗?往小里说是追问一种文体,往大里说又是追问整个文学。今天错综复杂的文学形式,今天渐现颓势的文学教育,促使我们开始这样的追问,即为我们的职业需求,也为文学的生存。
一、主流文坛支撑着一种小说正宗
不必讳言,主流文坛对小说的正宗其实相当清楚,这可以从以茅盾文学奖为首的各种主流评?奖的标准中看出,即便是自诩为“学院派”的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和学会奖,也依然相去不远。离读者比较近的各种文学期刊排行榜和年度奖,虽然也考虑了读者喜爱的因素,考虑了小说作品的社会影响因素,但由于刊物的体制、经费的来源,以及它本身就是主流文坛的地盘,其评奖标准也是正宗为主,略略掺入一些非正宗的元素,比如消费化的元素,比如另类文化的元素。
总体来说,评奖的主办者都是相当谨慎,他们对小说正宗的维护,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有对以中国作家身份为自觉的精英立场的维护,假如把话再说的白一点,也是对自己所熟悉所依赖的一套文学标准一套话语体系的出于本能的维护,何谓本能?立场、理想、审美、趣味、爱好、职业感、话语权,都有,都有那么一点——可以从几个文学事件中看到“小说正宗的反弹”:麦家的长篇小说入选茅盾文学奖,其作品的类型化大受争议,评委被界内人士质疑,作品质量被批评,相关的批评文章甚至被收进学术性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且不说麦家小说的质量和分量是否上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台面,关键还是这一类收到读者喜爱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作品艺术路数,有别于正宗的标准;另一起事件虽然来得猛也去得快,但留下的问题仍然值得回味,即被文坛公认为纯文学正宗刊物的《收获》,2010年发表了80后作家郭敬明的小说,文学界反应强烈,评论家多有评说,加之媒体推波助澜,四面反响的文章篇幅大大超过“小四”的作品,几乎是为这位文坛内外游走的翩翩少年做了一个大大的免费广告,使人回想起数年前郭敬明等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的轩然大波,其内在原因之一也是触及了小说的正宗乃至文学的正宗。
二、大学文学教育:从支撑到质疑小说正宗
中国内地大学也从文学教育方面支撑着小说的正宗。
建国六十年来,经过多少次政治运动,经过多少次教学改革,但文学教育的方式,文学课程的模块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文学理论中的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史中的三大块: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从文学标准看,西方文艺复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苏俄的、中国古代的、五四新文学的、延安文艺的,都成为小说正宗和文学正宗的参照,近二十年来,还有两个参照: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伴生的新时期文学。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教育中的正宗地位在动摇。其原因可以到文学教育的大小环境中去寻找。
大学现场的现实是,内地大学文学教育背景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
首先,价值观由一元向多元变化。社会逐步开放,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网络草根化,意见领袖民间化,国外思潮的冲击,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对松弛和相对宽松,社会包容风气的逐步形成,城市市民的兴起,世俗欲望的肯定,日常生活美学的流行,崇高理想主义的消解,社会精英的沉沦,传统伦理的质疑,宗教信仰的缺失——所有这些社会变化,使得价值观由一元趋向多元,其次,社会结构由体制内向体制外变化。1997年以后,大学生不包分配,体制内地盘的缩小与市场化地盘的扩大,铁饭碗被打破,终身制被放弃,人生依附性同时也被消解。当然,另一种情况在于社会不公的现实依然如故,“考碗族”超过“考研族”,大学生自主创业不到1%,大学生“蚁族”遍布一线城市,80后大学生实际上面临比前辈更加严酷的生存环境:工作、房价、物价、医疗、环境污染、信息爆炸——
最后,也是最不可忽视的是文学教育的对象:80后90后“网络一代”在变化。代际差异空前凸显,教师权威迅速消解,青年一代对家长及成人世界和现行教育制度的抵抗情绪愈加高涨。信息世界的开发,使得大学生熟练掌握两套话语系统:对付教育者,中规中矩,就取分数;面对自我,则游戏狂欢,本我毕现;集体主义的放弃,个人主义的崛起——“我时代”到来,青春期的叛逆,青年亚文化形成对一切正宗的天然抵抗。具体到文学教育领域,表现为一冷一热“两极情绪”明显:对文学经典冷,对青春文学热;对传统作家冷,对非主流作家热;对大学讲台上的教授冷,对网络青年“意见领袖”热。一句话,对传统正宗的近于不讲理由的一律排斥,似乎有一种“断裂”的文化现象存在。我在各大学几十场演讲,几乎都遇到一个相近的问题:为什么教授讲的我们都不喜欢,而我们喜欢的教授都不讲?
受制于大社会环境的大学教育的小环境,同样出现变化和动荡。传统的标准,经典的示范,受到质疑,文学教育的明显滞后,使得讲台上的说教变得愈加苍白无力,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沟通也在形成障碍。
三、中国大陆文学形势变化挑战小说正宗
一直处于文学现场的评论家白烨是敏感于时代的先知之一,他的“文学三分天下”之说,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当下文学的天下大势,也许,我们的学者可以用更加完备的论述加以更加准确的描述,但评论家白烨的强项就是一直与大众传媒保持亲密的接触,在如何利用传媒传播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方面,他是当代文学评论家中做的最成功的几人之一。看看白烨的说法——
“在进入新世纪由整一的体制化文学分化为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之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成形并日益稳固。在这种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之中,不同板块都在碰撞中有所变异、有所进取,但发展较快、影响甚大的,却是新兴的以文学图书为主轴的市场化文学和以网络文学为主题的新媒体文学。”①
“梁晓声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反问我,你说‘80后’‘走上了市场,没走上文坛’,也许这些‘80后’作者、作品和读者已经构成了一个另外的文坛。这话对我也有启发,他们也许还构不成一个文坛,但至少构成了属于学生阶层所独有的一个自足的文化现象。‘80后’的悄然崛起和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密切相关,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反省很多东西。”②
“但种种迹象都向人们表明:各国文坛的‘80后’们,确实在很多方面与此前的写作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在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因而,他们的纷纷登台亮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文学改朝换代的一个信号。”③?
文学现场的现实情况可能比白烨的描述还要错综复杂,还要斑驳陆离,主流文坛一块靠作协系统支撑,依然自成格局,尽管主流纯文学期刊已是举步维艰;市场化文学靠广阔的市场利润和庞大的消费者形成竞争力,其中人口基数也是优势之一,比如仅仅历史小说一块就有很大的图书市场前景;新媒体更是我们远没有清晰了解的一块原野,横跨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借新技术日新月异,赖青少年“网络一代”热捧,无论是空间的张力,还是时间的冲劲,均是无以伦比,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令人眼花缭乱,真所谓太给力太神马太浮云。传统的主流的文学评论家们,如何招架的了啊!
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阅读包括艺术消费的人群已经开始分流,全球化市场化的年代,任何计划任何指示包括指令都在弱化,层出不穷的新现象,瞬息万变的新信息,都是我们原有知识系统涵盖不了的新领域,甚至是我们视野所无法抵达的新原野。比如网络上的“王道女”、“腐文学”,你很难想象有上百万的青少年女性读者,在近于狂热的创作和阅读一种同性相恋但又不是“同志小说”的文学作品,这个庞大的网络小说人群,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大学宿舍的电脑里,就在中学生的书包里。这样一类具有非主流文化特征的小说在创作阅读之中,必然会产生对正宗小说艺术观的全面质疑、挑战和冲击!而我们的教育者和批评家常常处于或批评指责或居高临下谆谆教诲的位置,跨越代沟消除隔阂有效沟通的可能性很小,效果甚微。
还应当看到的是80后90后网络新一代自身的变化。除了精神上的变化以外,他们的身体也在变化——而这一点常常是成人社会所容易忽视的——假如与80后进行一下“换位”,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关于“身体”的观察角度,即人类的身体如何面对急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④大量的研究表明,无论从肯定还是反对的立场,科学家们都承认网络一代由于接受新的信息方式,使得他们的大脑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孩子们的神经系统已经具有了新的质的变化。一句话,他们已经不是同父母完完全全一摸一样的人了,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玄,但不离谱,是事实。关于这些,主流正宗的人们,所知甚少啊!一个是观点不变,唯我独尊;一个是目力不及,一叶障目。
结语:文学转型时代如何把握小说正宗
试图在一篇短文中谈清楚何谓小说正宗,几无可能,更何况其本身就是当下文学艺术界一大难题。不过,文学研究大家钱穆先生的态度和观点倒可以借鉴。在他看来,文学的正宗是存在的,比如中国文学的“雅化”进程,比如中国诗歌“作者第一”即作品中必须有作者自己等等。这位大家同时也承认文学有不同的层次,有上下之分,但即便是“文人之文,亦文中之一格”而已⑤,他一方面不赞成以一种取代另一种,但又肯定“下层文学亦必能通达于上层,乃始有意义,有价值”。⑥由此揣摩,由此启发良多。面对转型时代,我们当有包容精神,通达态度,宽广视野,在不断学习和不断探求去维护和发展小说的正宗、文学的正宗。说易行难,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信仰和境界问题。
江冰 广东商学院
注释:
①②③参见白烨:《我看“80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
④参见江冰:《80后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
⑤⑥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