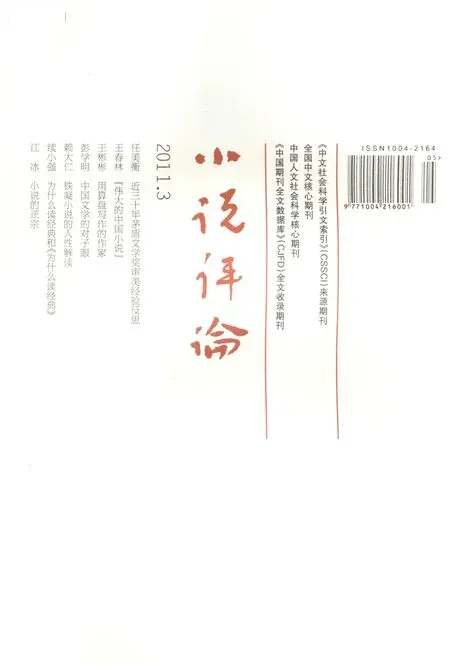巴尔扎克主题:人是怎样被毁灭的
李梦馨
巴尔扎克主题:人是怎样被毁灭的
李梦馨
有人说,巴尔扎克是物本主义者,把“物”的临摹放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超越了对“人物”的塑造;我要说,我不否认“物”——作为金钱和欲望的代表——是巴尔扎克观察世界和展开叙事的一个重要凭借和载体,但是,巴尔扎克的文学创作绝不是为了描述物体本身,他的最后的目的和最终的指向,是人,是人的境遇和命运。他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之所以能够让他被后世铭记,绝不单纯因为他对于“物”的纤丝毕现的精确描写,而是因为他的作品里有鲜活的生命,有性格各异的作为“人”的文学形象。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自古以来都是以“人”为中心。高尔基说过一句至今都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文学就是人学。的确,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人”,也就是对生命的关注。在古代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有象征着爱与美的维纳斯,也有象征着力量与勇敢的阿喀琉斯;有凶狠而决绝的复仇者美狄亚,也有热情而善良的堂吉诃德;有为爱而生的朱丽叶,也有为责任而焦虑的哈姆雷特。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之中的极为丰富的人物形象,据研究统计大概为两千四百七十二个人物,这其中有被金钱迷惑的葛朗台,也有那个被拜金主义和畸形父爱折磨的可怜父亲高里奥,也不缺乏让人为之流泪、为之恼怒、为之反思的角色。
在巴尔扎克的文学长卷中,有封建贵族的痛苦与可悲,有资产阶级的罪恶与得势,有苦难农民的无奈与贫苦。恩格斯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所以,我选择两个最能够代表上流社会的冲突双方作为切入点,深入讨论巴尔扎克笔下的生命。
一、拜金主义者的幻灭
19世纪末,尼采惊呼“上帝死了!”这反映出19世纪沉积已久的旧有文化体系趋近崩溃,顺应历史的新生的文化体系还未建立的特有的痛苦、空虚、焦虑以及怀疑。在封建体制中,人们有稳定的社会安全感,而资本主义的出现打破了旧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要求人们强化自我意识,但是在要求释放的同时,人们似乎也找不到边界,所以在放纵的竞争观念等欲望的支配下,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在巴尔扎克笔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内心充满贪欲。他们眼里只有金钱。金钱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把财富当做一切,认为世界的全部价值、人生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攫取和拥有金钱和物质财富。就是这样的极度自私的拜金主义者,成为新时代的“英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内心没有健全的人性和正常的情感,只有冰冷的钞票。在他眼里,妻子、女儿其实也是资产。金钱高于一切,这就是葛朗台的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他人生的最高准则。对其女的态度的几次转变将其特质描写的淋漓尽致。在遗产争夺中,葛朗台几次为了金钱转变态度,扭曲自己的人格。初时,囚禁自己的女儿、恐吓自己的妻子;知道有遗产可获得后又立刻和母女二人讲和;妻子尸骨未寒,就有使用各种手段逼迫自己的女儿放弃遗产,女儿不像父亲那样可悲,对钱财天生冷漠,放弃了遗产;孩子放弃遗产之后,他这样说道:
“得啦,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我的还了我,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场交易。”(《欧也妮·葛朗台》)
在这里,人性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则是与一切动物性的欲望毫无二致的贪欲。人必须依赖物质条件维持生命,但是,更重要的,人倘若要成为更高意义上的人,他就必须在“物质”之上,确立真正属于人的道德基础和生活理想。如果一个人只停留在肉体、本能、无意识之中,那么,他并不是健全意义上的人,只能说这是一种物性意义上的的消极的存在物。而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大肆侵占人们内心的时候,多数人忘记了理性、精神与意识的存在,甚至忘记了宗教的力量,即使他们没有忘记西方精神根源的宗教,每天依旧祷告、信奉,宗教也变成了镀着黄金光芒的寻求安慰的方式。在物质的冲击下,资产阶级最先沦陷在黄金的迷梦之中,体验着金钱所带来的快感。《共产党宣言》中有言:“资产阶级撕下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一判断确实有助于诠释《欧也妮·葛朗台》等巴尔扎克作品的主题。
巴尔扎克的作品,写出了资产阶级如何富有激情地追逐财富,如何为自己的成功而激动不已,也写出了他们成功背后的不光彩的交易,写出了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们的幻灭。
二、贵族阶级的黄昏
资产阶级在崛起,而在贵族阶级的头上,黄昏降临了,黯淡的夕阳投下了凄凉的余光。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广泛而深入的描写了落寞的贵族阶级的迷茫和颓亡。从外省到首都、从乡村到城市、从家庭到社会、从亲情到爱情、从经济到政治,到处都可以看到贵族阶级的失意与挣扎。虽然贵族阶级的没落属于客观历史的规律,但是巴尔扎克还是展现了面对弱者所特有的同情心。巴尔扎克对贵族阶级的境遇做过大致的概括:
到王政复辟时代,一般贵族都记得吃过亏和财产被没收的事,所以除了一二例外,她们都变得节俭、安分、思前顾后,总而言之,庸庸碌碌,谈不到伟大的气派了。……这一切都带着时代色彩。(《贝姨》)
而这样的时代色彩就是波旁王朝时期,封建贵族就在极力的修补重建她们昔日的家园,为了能够维持曾经的生存方式,他们尝试着各种改变或者妥协,但是,历史的潮流难以逆转。面对野心勃勃的资本家,他们无能为力,一掷千金的奢华的生活成为往日的荣耀,政治上的特权也正一点一点被迫放弃。
在充满悲剧感的《高老头》中,我们认识到了鲍赛昂夫人。她是巴黎上层社会力独领风骚的人物。在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她翩翩起舞,游曳在不同的客人之间,心花怒放,飘飘欲仙,目无一切。然而,这一切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她被情夫抛弃。阿瞿达侯爵为了更多的金钱抛弃了她。她只能辗转到乡间,去过隐匿的日子。渐渐地,她在恬淡的日子中,找到了安逸的生活。然而,又有了男人为了金钱,热烈地追求鲍赛昂夫人。这完全打破了她的恬静生活,激起了她压抑已久的激情。不过,最终,这个男人也为了更多的金钱,离开了鲍赛昂夫人,和别的女人结了婚。门第高贵的妇女,一再被抛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金钱。资产阶级的暴发户在与旧贵族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妇女以金钱击败了只有头衔的贵族妇女,并替代她们开始演绎新的时代“喜剧”。
在《高老头》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被金钱折磨得不知所措的父亲。高里奥是牺牲品,是拜金主义和畸形父爱的牺牲品。高老头是个发福的退休商人,在大革命中,他积极利用时机发了一笔横财,依靠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暴发户,但是在他肥胖的身子里还有浓厚的信仰观念制约着他。
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两个女儿。她们是他全部的寄托和希望。他爱钱,在那个时代里在那个环境下他必须爱钱,可是他更爱自己的女儿,他用钱满足女儿的几乎一切愿望。而正是这种扭曲的父爱,让两个女儿成了欲壑难填的拜金主义者。她们两个,一个心满意足地成为了伯爵夫人,一个自得其乐地成为了银行家的太太。而高老头在满足女儿的欲望之后,只能带着自我安慰和所剩无几的钞票住进公寓。而这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起始:他的钱越少,他的女儿们来见他的次数越少,为了给予她们更多的“父爱”,而最终,高老头一无所有。
我们要惊叹于巴尔扎克对于历史的敏锐的洞察力,透过很多现象直接抓住本质的能力,并且在创作主线上排除同情心的干扰,解释了贵族阶级的本质和命运。当然,这也得益于他的极度客观的创作手法。其实,巴尔扎克面对贵族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剖析资产阶级的残缺时,巴尔扎克总会不自觉地奔向贵族阶级寻求支撑点,挖掘社会存有的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又深刻认识到这个阶级的软弱和无能,而这种软弱与无能也让巴尔扎克明白,贵族阶级最终是要被淘汰的。
三、悲剧是怎样诞生的
“悲剧的诞生”,尼采这句话深刻地概括了西方十九世纪文学的本质。19世纪的西方文学充满了悲剧。故事里充满了眼泪、悲叹、绝望与死亡。
那么,为什么19世纪文坛会具有如此规模的悲剧文学的产生?
这是因为,首先,资本主义社会还未定型。19世纪,封建制度不再强大,资本主义还未定型,资本主义作为未来的曙光隔着云层朦朦胧胧,让人憧憬、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是,光亮还未刺透云层的时候,人们却为他流血牺牲,当无数的鲜血换来了牢固确立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却哑然发现,新的矛盾里有更多陌生的苦难和冲突,人们必须去面对他,但问题棘手,自此消极的情绪开始积淀。
《高老头》中,面对着新世界和下层社会,拉斯蒂涅内心的变化,是极其典型的。作为大学生的拉斯蒂涅,聪明热情,富有才能,内心激荡着强烈的向上爬的欲望和追求。这个时候,他的性格还未定型。但是,当他进入社交界的灯红酒绿,他叹羡不已。如果说,鲍赛昂夫人把极端利己的人生价值观灌输给他,那么,伏脱冷就是他的第二个“指路人”。他开始改变,向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在认识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去追逐攀爬。
其次,资本主义的生存竞争造就了“社会弃儿”。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建立竞争对手,让竞争无处不在,在优胜劣汰的制度中成就金字塔的高端精英。资本主义是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而是使人击退对手成为孤立的个体,单枪匹马奋斗挣扎,而这样的境遇很容易产生孤独感以及被抛弃的失落感。
第三,在激烈的竞争中,过度的竞争状态机容易产生仇恨心理和情感的两极分化。个人的核心观念是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个人利益不惜伤害其他人的利益,并且自认为理由充分。据哲学家说,“人类的悲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察觉到个人的欲望和追求往往不可能得到满足”,一类人在物质欲望的占有上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另一类人则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陷入惶惶不安的绝望和痛苦境地。
巴尔扎克以极其敏锐和广阔的视角,俯察着十九世纪法国拜金时代的诸多问题,诊察他们的伤疤,分析他们的病况。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悲剧性。他真实而生动地叙述了各种人物的不幸的生活。如果没有他的冷静的观察,没有要做“书记官”的人化自觉,那么,这些充满“悲剧感”的伟大作品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李梦馨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