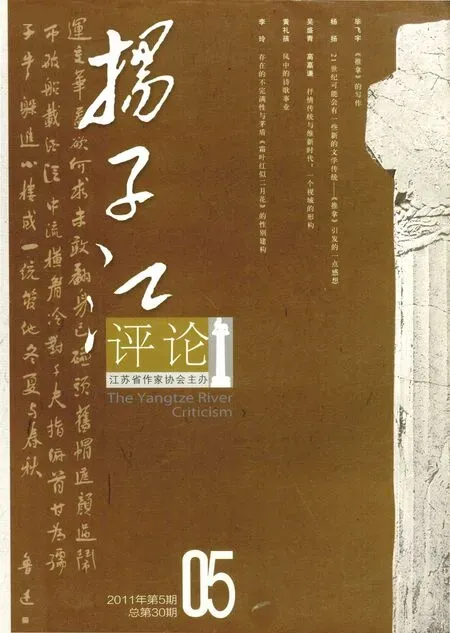黄礼孩访谈录
黄礼孩 明飞龙
明飞龙:这份刊物是什么时候开始创办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诗歌与人》产生的影响。
黄礼孩:《诗歌与人》是1999年底创办的,到现在也10年了。《诗歌与人》先后推出“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诗学概念,在诗歌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70后诗歌”已被作为概念收入《大学语文》一书,而由洪子诚、刘登翰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亦把“70后诗歌”、“中间代”编入新诗史。多所大学把“70后”、“中间代”作为诗歌新概念进行研究。《诗歌与人》已成为被转载最多的大型诗歌民刊,并被国家图书馆及国内外名牌大学图书馆所收藏。每年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新诗年鉴》、《北大年选·2005诗歌卷》等年度选本都从《诗歌与人》中选载优秀诗歌。《诗选刊》、《诗刊》、《人民日报》、《文学报》、《新闻周刊》等报纸杂志曾经做过专题报道。2001年获《诗选刊》颁发的“最受欢迎和关注的民间诗刊奖”;2003年获“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奖·优秀编辑奖”;2004年获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颁发的“2004年度国际最佳诗刊奖”;2005年《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获第三届龙文化金奖(优秀编著奖);2008获“第二届最佳报刊诗歌编辑奖”。《诗歌与人》的影响力用陈晓明先生的话是:“《诗歌与人》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史文本,是活的当代诗歌史和精神史。”沈奇先生说:“《诗歌与人》已经构成21世纪当代中国诗歌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坐标。”这些年《诗歌与人》得到很多赞誉,并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民刊”,我更多地把这看成是一种追求的目标。一个正在途中的刊物比已到达目的地的刊物更有力量。我想《诗歌与人》是不断抵达又不断出发的刊物。
明飞龙:请问《诗歌与人》的编辑方针是什么?
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办刊理念或者说编辑方针是做别的诗刊不敢做或遗忘的部分,从而竭力呈现一个不可重复的诗歌现场。
明飞龙:《诗歌与人》的发行方式是什么?
黄礼孩:《诗歌与人》主要以赠送的方式来交流,只是交流的对象有所选择,赠送给“有影响力的人”多一些。因为诗歌刊物的读者面相对其他文学刊物来说是更小的,而这有限的资源要能够影响这小部分人。一本刊物除了诗歌质量之外,杂志本身的质量也至关重要,装帧、设计、用纸等都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这样,杂志的接受者即使不看,也不会随手把它扔进废纸篓,会把它收藏起来,当杂志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对接受者的影响也就自然产生了。
明飞龙:《诗歌与人》的办刊经费来自哪里?
黄礼孩:办刊的费用基本上来自我自己的收入,主要是给一些机构办晚会,写台词、串词,在一些报刊写专栏文章的稿酬。平时为几个出版社做些版式和封面设计什么的,但主要由设计师来完成,我顶多出些点子。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女诗人江涛,她提供过资助。诗人陈陟云如兄长一样关爱我,给过我慷慨的资助。对此,我一直铭记于心。
明飞龙:您认为《诗歌与人》与其他民间诗刊相比,它最大的办刊特色是什么?
黄礼孩:走专题取胜之路。《诗歌与人》创办之初,我没有明确想过要走专题这条路,是做了“70后”和“中间代”这两个选题后所带来的启发和思路。
明飞龙:《诗歌与人》的专题我都很熟悉,比如“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概念专题,及《最受读者喜欢的10位女诗人》、《中国女诗人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女性诗人专题。这些专题里,您认为哪个是不如意的?
黄礼孩:最不如意的一个专题是《1927-2007中国诗歌漂流书》,这本书我们只用手工做了十五本,在佛山的“诗歌与人·诗歌节”上漂流,想就此进行流动式的漂流阅读,半年或一年后回到我的手中,我把大家的阅读札记一起附在书上再正式出版,但两年过去,没有一个人把书给我寄回。这是一次非常浪漫的诗歌行为,可惜最终夭折,估计诗人都赖得去邮局或者想据为己有,这个游戏没有玩下去。
明飞龙:诗歌界对《诗歌与人》的一些命名存在争议,比如“70后”这个诗学命名,您如何看待命名?
黄礼孩:其实,我知道在诗歌的前面加任何定语都是多余的,我也知道“70后诗歌”不是一个诗歌流派,顶多是一个概念。但在当时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背景下,七十年代写作的诗人如果自己不去争取自己的位置的话是很难引起关注的,可能会遭遇被淹没的命运。“70后”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尽管如此,这个概念还是逐渐被文学史所接受。我并非热衷于命名,所有的命名都带有功利的色彩。诗歌命名一直为人诟病,诗歌命名也就为他人树起靶子,但我们好像又难以摆脱命名的宿命。命名是权宜之计,它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宣传,便于批评家和史学家就这一诗歌现象进行梳理、概括、批评、肯定或否定。
明飞龙:您作为“70后”的代表性诗人,您的诗歌观是什么?
黄礼孩:我最初的诗歌观念是想在诗歌中尽可能呈现美的一面,现实如此不堪,有时不愿意触动这些题材。一个诗人对某类题材天然具有可塑性,也就是诗人跟某种气息之间天然有着微妙的关系。我对人性温暖、怜悯、关怀、人道、爱、勇气、明净和纯粹的事物都有着说不出的亲近,也许是童年的母爱,也许是赞美诗的纯净,也许是自然的美给了我这些。但我的诗歌中也写到死亡、阴暗、腐烂和分裂,只不过这部分没有放大来写,所以这中间黑暗的力量没有壮大起来。对黑暗和残酷命运的书写需要一个人内心有更大的控制力,也就是说,你的内心足够强大才能控制这个魔力为你所用。阴暗也是一种力量,唯有内心的光明才能与之产生冲突,才能构成复杂的精神世界。相对于之前的写作,我试图在文本中植入更多的思考,唯有以此才有更大的感受力。
明飞龙:您在办刊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来自官方的阻扰,毕竟《诗歌与人》是没有刊号的。很多民间诗刊出一两期就停刊,其中就有官方的干扰。还有,您如何看待广东的诗歌?您对广州有何印象?
黄礼孩:广东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地方,文化氛围也比较宽松,办《诗歌与人》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没有遇上什么麻烦。要说麻烦的话有一次,那就是在2005年做《诗歌与人:柔刚诗歌奖专号》时,因为里面有首诗歌涉及到毛泽东,有人举报,而被广东有关部门列入检查范围,但后来也没什么,不了了之,后来也就没有遇到类似的事了。整体上说来,《诗歌与人》诞生于广东是幸运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东诗歌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这是因为广东诗歌没有为华语诗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广东诗歌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广东诗歌集聚了一批有实力的诗人,他们是外来的,也是从本土成长起来的。他们写作、办刊、办网站,把诗歌广东弄得风生水起。但广东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这里的人都很现实,也很实在。广东对诗歌并不重视,如果说这些年有影响的话也是民间搞起来的。诗歌在民间,而不在谁的手中,这正是诗歌活跃的因素吧。广州是一个没有品味的城市,在这里生活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在这里做事还算可以吧。很多时候,我觉得诗歌没有地域之分,所以做刊物也就少了地方意识。诗歌是自由的,从刊物的层面来说,它不是思想或哲学,它是一个刊物的精神气场。只有自由的刊物才能呈现自由的诗歌。
明飞龙:《诗歌与人》编选了许多外国诗歌,请问您在选编过程中有没有某种标准?
黄礼孩:如果说在译诗的选择过程中,有某种理念的话,那就是对好诗的推介。翻译诗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个人便是其中的收益者。所以想多推荐一些当下国外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品给中国读者。
明飞龙:《诗歌与人》颁发的几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奖金来自何处?
黄礼孩:主要靠自己出,没办法时也找朋友帮忙。
明飞龙:您怎样看待《诗歌与人》的未来?
黄礼孩:我也不知道《诗歌与人》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情景,十年来我从没想到会走到今天,同样,我也不去想未来会怎样,只是竭尽全力地做好每一个选题。
明飞龙:您怎样看待民间诗刊与官方诗刊的关系?
黄礼孩:最初的时候,民间诗刊与官方诗刊是两个不同的阵营,民间的是边缘的,官方的是主流的,他们基本上不怎么往来。后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松弛,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现在的民间与主流诗刊差距越来越小,我觉得是官方诗刊在向民刊靠拢,但民刊的锐进势头在减弱。
明飞龙:您是一个集诗人、批评家、编辑家为一体的综合型人才,您是怎样成为这样的人才的?
黄礼孩:非常惭愧,说我是诗人、批评家、编辑家,这是朋友们和媒体的美意,我愧对这样的称呼。我的理想是努力去做一个诗人。在我看来,写出一些自己满意的诗篇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一个诗人毕生的精力是要去写出优秀的诗篇,但一个诗人如果还能用不同的形式说出更多,这对于丰富自己的心灵也是必要的。诗歌的写作和其他文体的写作毕竟不同,所以我试着写写别的文字,比如诗歌笔记。诗歌札记的写作让我的文字有了穿透力和思辨的精神,虽然我没有严谨的学术背景,但诗人式的评论有更多的诗性情怀。而作为一个编者,更需要写作的经验和阅读的敏锐,需要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文字。最近把这些文字收集起来,出了一本评论集《午夜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这里的,但我知道当一个诗人是我最高的理想,而一个优秀的诗人自然也是一位好作家。一个只会写诗而不会其他文体的人多少是可疑的,同样一个诗歌刊物的编者应该具有想象力和整合能力。我想,可能是这些想法,让我尝试着去改变。
明飞龙:在您的博客上我读了您大量的诗评、画评、影评等,您对艺术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您这么忙,怎么有时间写下这么多的东西?
黄礼孩:除了诗歌,我还喜欢艺术。这跟我在艺术界工作有关。诗歌之外的艺术世界同样是丰富多彩的。我觉得人生分多种境界,文化人生大概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借助杰出的思想,你可以感触到更为宽阔的世界,你的心灵因之丰盈。这正是我对艺术感兴趣的原因。每天,我都在忙一些琐碎的事情,时间变得鸡零狗碎,这对于阅读和写作都是一种伤害。但作为作家不写作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再忙也争取时间记录点什么。
明飞龙:在世人眼中,诗人一般是比较难相处的,诗人之间也互相瞧不起。但你在诗歌界却获得了诗人们的一致好评,您有一种怎样的个性?
黄礼孩:一个人的内心精神资质直接影响到他对世界的判断。我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是善良的,在与人相处时,付出自己的真实和真诚,即使你因此受到欺骗也没有损失什么。我想,你给这个世界报以什么,这个世界也会回报你什么。我没想过要去做一个人人都满意的人,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委屈自己,也不迁就别人,尽可能做到大家都舒适。在生活中,我只想做一个爽朗的人,清爽明朗,自然自在。
明飞龙:问您一个私人问题,您的婚姻爱情如何?
黄礼孩:如果说与诗歌相遇是一种缘分,那么婚姻爱情也是一种缘分。希望有一天,我能套用《圣经》的话对一个女孩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在等待这一天。
明飞龙:衷心祝愿您找到一位理想中的爱人,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祝愿《诗歌与人》越办越好,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
黄礼孩:也非常感谢你对《诗歌与人》的研究,感谢你对民间诗刊的关注,相信你一定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