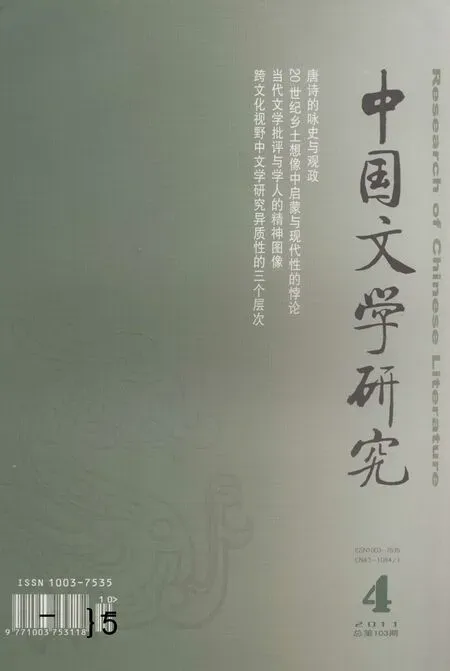作为文化认同的抒情美学传统
刘毅青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中国的抒情传统对港台以至西方汉学的中国文学与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随着海外汉学家的作品在大陆的刊行,其研究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注意。旅美华人学者陈世骧是最早提出抒情传统的人,他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最早从比较文学视角提出,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中国文学的特征就整体而论是一种抒情的传统。自此,“抒情”这一来自西方文类的概念,成为概括中国文学特质的重要术语,并从文学研究扩展到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成为一种具有审美内涵的概念。从1960年代至1990年代,抒情美学传统成为台湾和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最有成果的研究取向。抒情美学的建构之所以在海外华人学者那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影响,并延绵到现在,乃来自其深刻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文艺美学本身的阐释。本文的着眼点即在于希望通过文化认同这一视角,揭橥海外华人学者此一抒情传统建构里所开掘的文化认同之内涵。兹概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认同的中西文学之比较建构
陈世骧初步揭示中国文学传统在本质上是一个抒情传统的提法,并由此而展开抒情传统与西方史诗和戏剧传统相互并立、对观的论述系统。正如陈世骧所说,抒情美学之传统是在中西比较美学语境中做出的一种美学类型定位,“当我们说某样东西是某种文学特色的时候,我们的话里已经含有拿它和别种文学比较的意味。我们要是说中国的抒情传统各方面都可代表东方文学,那么我们就已经把它拿来和西方在做比较了。我们所以发现中国的抒情传统相当突出,所以能在世界文学的批评研究中获致更大的意义,就是靠这样的并列比较。”〔1〕(P3)抒情与叙述本是西方文论对文学的类型划分,进而获得各自类型的美学特质。从美学上看,抒情与叙述正可以作为代表。陈世骧认为,与滥觞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的西方文学不同,中国的文学传统始于以音乐为其要髓的《诗经》和《楚辞》。《诗经》“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楚辞》是“文学家切身地反映的自我影像”和“用韵文写成的激昂慷慨的自我倾诉”,〔1〕(P6)因此都是抒情诗歌的典范。
随后,高友工就以“抒情精神”对应“悲剧精神”的理论架构来勾勒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内在精神与理想:“抒情精神”是以中国抒情诗为范例,代表艺术创作中主体心境所能体现的与外在“心象”和谐一体。中国诗歌中的“情景合一”的传统,就是具体体现。在抒情传统里面,既然诗的创作是以诗人的情志为导向,是诗歌情志表达活动中的一环,则诗的语言经营固然可以有其独立自足的意义层面,但诗的意义总不免是浮现在诗的语言表层之外,而指向诗人主体情性的表露。由此,中国古典诗歌论述传统在情感意念此一面向上的思考,就具体表现在“情感的内容与质量”这个论题。再者,就古典诗论的历史发展而言,诗人或批评家所亟欲宣示的批评观念或理论术语,为数颇多。然而,这些看似不同的批评观念或理论术语,其实深切反映古典诗论传统中对于诗歌审美特质此一议题的追寻与探问,而在这些看似不同的提法中是可能有着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因此,不论是“境界”、“沉郁”或“神韵”,其目的都在于为古典诗歌标示一种独特的审美典式,甚至藉此阐明诗歌所得以完成的一种理想的审美旨趣与审美效果。因此,“用最粗浅的话来说,中国的抒情精神正和西洋的戏剧精神分别在它们文化中同样居于一个中心的枢机。换句话说,中国戏剧正如西洋抒情艺术多多少少是要受其主导精神影响。中国文人要转戏剧为抒情的形式,也正似今日西洋文学批评要以戏剧性的张势与冲突来解释抒情诗。”〔2〕(P92)
以抒情和叙事并举首先凸显的是这样的文化类型设想,即中西文学在抒情和叙事这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中是各擅胜场,没有优劣之分,中西从传统以来即具有自身的文学特征。可以说,陈世骧所说的“这样的并列比较”背后乃是出于一种文化认同,即希望通过将抒情标举为中国文学的特长,以树立中国文学在西方叙事文学传统优势中的地位,这显示了:海外华人学者抒情美学的建构是一种文化自觉,自觉地希望通过将自身的研究归入到传统当中,而获得自己的文化认同。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马上显露出来。人们惊异伟大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造成希腊文学的首度全面怒放,然则有一件事同样令人惊奇,即,中国文学以其毫不逊色的风格自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崛起到和希腊同时成熟止,这期间没有任何像史诗那类东西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不仅如此,直到两千年后,中国还是没有戏剧可言。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1〕(P2-3)
而高友工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西洋艺术中艺术的综合性自然也是传统中的热门题目。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六因素就已提出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如何在语言和模仿代表的戏剧中能合为一体的问题。因此,从宏观的整体着眼,“他的整个美典是建立在一个外投性的、代表性的戏剧美典,也即是我常提及的描述美典上。这种美典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中的矛盾与冲突是与我们文化中抒情美典中憧憬的人生的中和性真是有天壤之隔。瓦格纳的《魔环四部曲》是没法和倪瓒的山水来作比较的,但各自反应它们文化中的理想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P93)
陈世骧和高友工的中西美学类型的比较,首先以平行比较为基点,突出中西文学各自的传统特色,表彰了抒情作为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其用意就在于反对一味地以西方人的审美作为标准。如高友工所说:“所以文化的比较有个人的好恶取舍,但无法作高低的评价。也许我们可以说只能执着于一端的文化在现代是一种缺陷。理想的美典该是兼容并蓄的。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像今日美国的一些评论家完全失去了立场,来者不拒地滥收,而是说我们能超越局限自己的美典而设身处地想象其它的经验。只有在这种想象的扩展开拓后,我们的艺术经验才能更成熟,更丰富。也许在遍尝之后,我们仍然回到自己的旧癖。但愿意进入其它人的条件和目的,也是培养人本精神的唯一阶梯。”〔2〕(P93)在这里高友工更进一步强调,此一文化比较凸显了文化传统自身的内在兼容性。
二、连续性与兼容性:以文化认同为中心的历史观建构
如上所述,抒情美学的文化认同乃是建立在文化自身的连续性和兼容性基础上的文化比较,现进一步申论。
首先是连续性:抒情传统的文化认同强调了文化是民族集体共同意识的连续发展,张淑香认为:“中国抒情传统是源自本身文化中,一种强固的集体共同存在的感通意识。”〔3〕(P41)而这种集体存在的感通意识,便是诗人不断回顾生命的历程。因此,按照张淑香的看法,整体的、同情共感的生命意识乃是中国抒情诗的本质。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承以致形成传统,其发展就像大江,从源头开始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不同的支流汇入,大江奔流直下,表面看起来是浩浩荡荡,直泄千里,但是在其河床当中还是有着各种潜流,各种曲折,这只有深入这文化传统的大江的深层才能探清楚。但是相比较而言,就像两条不同的大江之间它们的走向比较起来总是大相径庭的,作为大江的自身而言,它自身的变化曲折并不影响它与另一个传统比较起来,在走向上是不同的。就抒情传统而言,“中国文学传统的本质与荣采完全在其抒情传统”〔3〕(P41),而“中国传统中所体会的悠悠宇宙,原是个有情天地,生生不已的根源,因此才有‘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之说”〔4〕(P43),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本质是作者对生命片段的感伤、叹逝,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是无法完全将作品与作者割裂来阅读,因为作者在作品中展现强调的是当下瞬间的内心活动,即生命个体“情”的描述,是当下感受的推移。到了孙康宜那里,则认为这个抒情的自我是放置在复杂的情境中,诗人创建的是“戏剧”、“叙事”的客观形式,但他所要表达的是戏剧化的面具下,书写下他所经历的情感,这使是诗人自我抒情的艺术表现。这在其它抒情传统的论者那里有着相似的表述。
比如,孙康宜则突出地将传统诗学中“情景交融”的观念作为抒情美学的内在化形式,标举抒情美学“表现自我心境”的意义,她认为抒情:“是诗人面对此刻的情景所感受到的情感的持续表达,以至于外在的现实被重新塑造和构建,成为自我和情景的艺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份。”4(P256)而蔡英俊则认为:“以抒情的模式呈现个人内心生活的种种印象与感知,创作活动所着意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保存并表现经验的‘自我感’(subjectivity)与‘现时感’(immediacy),也就是经验(意念或意向)在其原有的脉络中的纯粹性与完整性;至于在语言的操作上,则是以‘意象’为基本单位而发展出一种‘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直觉形象的典式’,并且能够体现每一个当下片刻的‘自然、自足、自得、自在’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即是一种‘和谐’与‘归于一’的理想。”〔5〕(P77)总之,抒情传统特别重视抒情所具有的共同审美特质在中国文学史的不同文类中的呈现。
其次是兼容性:抒情美学的内涵在陈世骧那里并没有做很完整的表述,在整个抒情美学研究的学术传统里面,高友工为抒情美学传统的建构做了最关键的努力。抒情美学,按照高友工的说法即“抒情美典”的审美内涵,在抒情美学的学统里,阐释并不相同。其中高友工的论述影响最大。高友工的观点可以用抒情美典的四个要项来概括,即内化(internalization)、象意(symbolization)、自我、和当下。即我们面对外界的种种,有所感知,经过内化的过程,以象意的符号呈现出来,重点是,呈现之际,必须与当下和自我结合,也就是说在呈现那一刻,时间是定格凝止的,转而成为在固定的空间回荡回顾。这说明,中国抒情美学乃是沿着使审美对象内在化和意象化的方向发展,而艺术形式的意义在于积淀了主体诗人的内在情感,成为具有深刻情感和历史内涵的有意义的形式。高友工进而指出,抒情传统“不仅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种主题、题素。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属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6〕(P23)正因为此,抒情美学成为整个中国文学艺术所共有的审美意识,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涵盖了绘画书法和音乐,同时也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从诗歌到小说和戏剧,无不体现了抒情的审美意识。
这就是认为,对于一种文化传统而言,其内部的变动,不管怎么变得厉害,总是在传统的脉络当中,而不可能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另起炉灶。除非发生大的变故,河道更改,它丧失了自身的河道,干枯或者汇入其它的河道。而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我们的传统变革虽然厉害,但并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也就是说,中国美学中虽然不仅只有一个抒情传统,还有其它的传统,但是总体而言,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这个类型表现出来。正如高友工所说,“我在前边所讲的也许是有太大的局限性,所谈只限于中国艺术中的抒情精神。但我希望在高处看,所讲的还可以在理论层次上与西洋文化有一种比较。我个人一直以为比较文学在欧洲文学限制之内是可以有很大贡献的,但若就两个迥异的文化,其比较只能在理论的层次上进行。而中西艺术精神的比较正只能从两种不同美典在两种文化中的比重来看。”〔1〕(P92)
因此,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比较,只是一种总体上的取向和特征的比较,而不可能是很具体的,局部的细节的比较。两种传统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细节上和局部上的一致性,但在总的走向上,在精神气质上往往还是存在着根本差异。这就是认为,抒情传统的形成由中国艺术的内在规律决定,抒情美学的内在规定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征,抒情美学的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一脉相承。
三、抒情传统的现代性
抒情传统一经提出,就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海外华人学者和艺术家都自觉地将自己归入到抒情传统中去。这就说明抒情美学成为他们自觉恢复自身艺术和学术的传承,以获得自身文化认同的象征。这首先是因为这样中国现代文艺和美学思想面临着这样的文化认同危机: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艺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在时代的变革中割裂,以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面临着一种困境——我们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价值体系来对其进行评价,中国现当代艺术在中西碰撞,各种艺术观念大杂烩中丧失了其自身的审美批判标准。与西方人相比,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艺术评价标准。历史的断裂造成了文化断裂,而这种断裂使当代中国人失去了统一的历史感,历史感的缺失推动着他们向传统寻找精神源头。
而正因此,抒情传统具有很强的内在向心力,使得各种门类的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着文化精神的核心聚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艺术都受到文学的影响,呈现诗意的境界,其原因就在于抒情性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当然所谓抒情传统只是艺术传统中的一个源流,但却是一个绵延不断支脉密布的主流。虽然有其它的传统与之争锋,但直迄今日仍然壮大。也许这是由于它正体现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文化理想。至少可以说它透露了一套很具体的价值体系,触及了文化的根本。”〔1〕(P90)海外的学者自觉地将抒情美学视为中国传统中具有强大概括力的学统,将其视为“源自本身文化中一个强固的集体共同存在的感通意识”〔3〕(P45),完整“体现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文化理想”〔1〕(P90),阐明抒情美学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之中,是中国人的“共同意识”,其意义就在于“本质上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可向哲学美学延伸的解释框架,以及一个普被接受的关于中国文化以诗为主体之自身逻辑的合法化叙事。”〔3〕(P90)因此,在笔者看来,抒情传统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它建基于文化认同之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历史感,延续了一种中国文化的精神,让我们可以回溯自身的美学传统。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如果不存在美学价值,艺术史将只是一个堆积作品的巨大仓库,作品的年代延续将毫无意义。反过来说,只有在一种艺术的历史演变背景之下,才能感受到美学的价值。”〔8〕(P6)抒情美学将中国文化内在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建构起来了,寄托了海外学者复兴中国文化的自觉。
从现代文学的学术层面上,有美国华人学者王德威自觉地接收抒情美学的道统,从现代文学角度,将抒情传统从学术层面延续下来。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看来,现代文学的抒情主义是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相关,但是,其实这个抒情传统应该向更深远的中国文学史传统追溯。不过他认为:“我想要强调的抒情主义,恰恰想回到我所召唤的中国传统文学或文论里面关于抒情的表述,我想到的线索至少包括了《楚辞》《九章》里面诗‘发愤以抒情’的问题。这个抒情不再只是简单的小悲小喜,当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时候,已经是一种愤怒的抒情,他中间有强烈的张力,值得我们来扩充。”“我在用‘抒情’这个词的时候,不再只是把它当作抒情诗歌,也把它当作一个审美观念,一种生活形态的可能性。”可以看出,王德威的抒情概念并没有脱离高友工的阐释,究其实质,抒情美学所揭橥的乃是一种文化理想。他认为,魏晋南北朝在混乱的历史时局中焕发出一个最精彩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美学空间。“在那个时空中,‘抒情’是一个生活实践的层面,也可以是一个政治对话的方式。”〔8〕(P5)王德威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看作是牵涉面广大,但又深深影响到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他认为,从现代文学角度,抒情传统与史诗传统是相对立的,抒情代表的是个人,而史诗则代表了集体话语,时代的政治。在王德威那里,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相关,他说:“但我做这个抒情主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和抒情主义的另一个面向作对话,也就是史诗。”〔8〕(P6)王德威的抒情和史诗的二元话语体系来自捷克的汉学家普石克构建的抒情和史诗,他总结道:“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文化的转变,正是从抒情的阶段转换到史诗的阶段。所谓抒情,指的是个人主体性的发现和解放的欲望。所谓史诗指的是集体主体的诉求和团结的革命的意志。据此,抒情与史诗并非一般文类的标签,而是可以延伸为话语模式,情感功能,以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想象。在普石克看来,这两种模式的辩证形成一代中国人定义、实践现代性的动力,而现代中国史记录了个别主体的发现到集体主体的肯定,从‘抒情’到‘史诗’的立场。”〔8〕(P6)因此,现代文学史里面,抒情美学成为小说追求的美学目标。意境是抒情美学的核心概念,到现代,意境被自觉地引进小说创作。在抒情小说中,意境更是成了作家追求的美学目标。废名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陈惠英以抒情美学传统对现代文学进行作品分析,认为,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质,使现代小说这种文类,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以诗(主要是抒情诗)的发展探视,其中“兴”的作用,给文学作品灌注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即以当代的作品为例,在不同的文类之中,可以看出其中的“抒情”特性,使作品呈现特殊的语调与气氛。她说,“作者在把握自己独有的声音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同时间地掌握了某种内在的抒情,正如高友工所说的‘如真’的呈现。张淑香以‘诗可以怨’为抒情传统的理论基础,指出诗人如何把实际人生的经历,转化为艺术的经历,这是文学所以长存的理由了。诗人所觉的“怨”,流露着生命的悲剧意识,则是永恒的文学题材。从文学面貌的演变,可以看出,当代的文学,既有传统的脉络,又有现代的元素,此亦足以说明现代社会的多元与多义。”〔9〕(P63)
陈惠英的分析多以小说与诗为例,正如她自己所说,主要是她对这两种文类的表现较为注意。而实际上,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从电影创作上,自觉地接续到抒情传统。侯孝贤的电影出来之后,研究者就发现很难将其放在叙事传统的审美坐标系里进行评价。如果按照叙事的审美标准来评判,侯孝贤电影的价值将遭到贬低,因为它不符合其基本的审美原则。而在研究者看来,只用将侯孝贤放在传统以来的抒情美学传统,侯孝贤的电影美学才能得应有的理解。和侯孝贤有着长期合作的小说家朱天文将侯孝贤的电影归于诗歌的传统,并引用陈世骧的抒情理论作为论证,她说,“于悲剧的境界,西方文学永远是第一手。而于诗的境界,天可怜见,还是让我们来吧。”〔12〕(P12-13)
侯孝贤在欧洲的艺术电影市场上有较大的影响,许多电影学者认为,侯孝贤开创了一种电影的美学风格,在电影里面进行了抒情的美学实验。侯孝贤有意颠覆电影的戏剧性而凸显其抒情性,这已经沉淀到了侯孝贤对电影的审美直觉中,成为其审美判断的标准:“我常常看一个国片,外面都说很不错,我看半天就是觉得没办法看。……人物的设计也好,或者氛围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一个叙事。因为电影从西方来的,所以我们学会了他们的叙事,这个叙事就是所谓俗称的戏剧性。”〔13〕(P46)尤其侯孝贤晚近的电影,有意削弱电影的叙事和淡化戏剧张力,他要凸显的是一种诗意的氛围。他说自己构思往往是先有人物,然后才去勾勒整个故事。比如他拍《红气球》,就是先找到巴黎的一处房子,“然后我就想假使西蒙是朱丽叶(指比诺什)的小孩的话,他们住的附近的环境,他的学校在哪里,菜市场在哪里,我会问他们什么地方的面包最好吃,打钥匙在哪里什么的”〔13〕(P146)。《咖啡时光》在东京也是如此。因此,侯孝贤的电影不重视逻辑性很强的戏剧冲突,也不通过冲突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通过长镜头对客观景象的描述。而他的镜头所呈现的往往是一种氛围,一种生活感受,一种生命的情调。在这种类似传统诗歌对客观的再现中,融入主体的情感,达到情景交融。
侯孝贤的电影在叙述结构上具有很强的跳跃性。其影像镜头可以随着情感和意念的流动,而不去进行故事的叙述,略过一般过程的交待。其电影往往甩开按部就班的叙述,在不同场景、不同历史之间大幅度地跳跃,把时间相距较远的事物放在一起,通过暗示,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味。侯孝贤的影像结构具有深刻层次与隽永绵长的美感。因此,侯孝贤的电影营造出一种意境,将人与自然环境用一种中国古典诗学中和谐感融合在一起。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人的生命状态只因着太阳的起起落落而变化。这种尊重环境的电影形态与传统诗歌所崇尚的意境是一致的。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中,诗意化的叙事和诗句的造型直接出现在影像中,文清所书写的文字弥漫着浓郁的诗歌味道。比如文清在监狱中所写的:‘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文清在古典名曲《罗蕾莱》中跟宽美讲述的童年故事,都是在一种诗的基调里来造型的。”〔14〕(P201)朱天文回忆了侯孝贤在拍《恋恋风尘》时说的一句话,侯孝贤说:“(影片)应该是从少男的情怀辐射出来的调子,纯净哀伤,文学的气味会很浓。是诗的。”可见,侯孝贤的电影具有抒情美学追求主观的情感抒发,突出个人内在的心灵意境,侯孝贤被影评人认为“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10〕(P16)在侯孝贤的电影里面,电影意境更加丰富,具有深广的内在张力。他用抒情改造叙事,使抒情美学的内在心象与和西方的叙述再现完美的糅合起来,形成新的抒情美典。从而开拓了电影的新的影像世界,使得抒情美学的美感能够通过影像结构直观地呈现出来。
结 语
每一代作家,都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体现其艺术理想;每一次文学运动,也都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体现其发展方向。而对传统的不同评价,揭橥的是自我之理论主张。因此,抒情传统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建构了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绵延不断支脉密布的主流”,它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确立了中国艺术的典范,为我们进行文艺批评构建了完整的审美座标体系。抒情传统在中国文化严重断裂的今天起到了回复我们传统的历史感功能,从而为我们对传统的叙述提供一个可以支撑的脉络。同时,抒情传统具有开放性,即使在当代,抒情美学的传统也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抒情美学成为忠于中国人自身美感意识的艺术家自觉继承的文化观念。
〔1〕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A].陈世骧文存论文集〔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A〕.美典:中国文学论集论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2008.
〔3〕张淑香.抒情传统统的本体意识-从理论的“演”解读<兰亭集序>〔A〕.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C〕.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4〕孙康宜.吴伟业的“面具”观〔A〕.文学的声音〔C〕.台北:三民出版社,2001.
〔5〕蔡英俊.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A〕.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一—抒情的境界论文集〔C〕.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6〕高友工.文学研究中的美学问题: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A〕.美典.中国文学论集〔C〕.北京:三联书店,2008.
〔7〕米兰·昆德拉.帷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访谈录之一〔J〕.书城,2008(6).
〔9〕陈惠英.抒情传统与现代社会〔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4).
〔10〕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M〕.台北:台湾三三书坊,1989.
〔11〕侯孝贤.侯孝贤.导演电影讲座〔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12〕郭小橹.东方影像: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电影特征比较〔A〕,电影理论笔记〔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