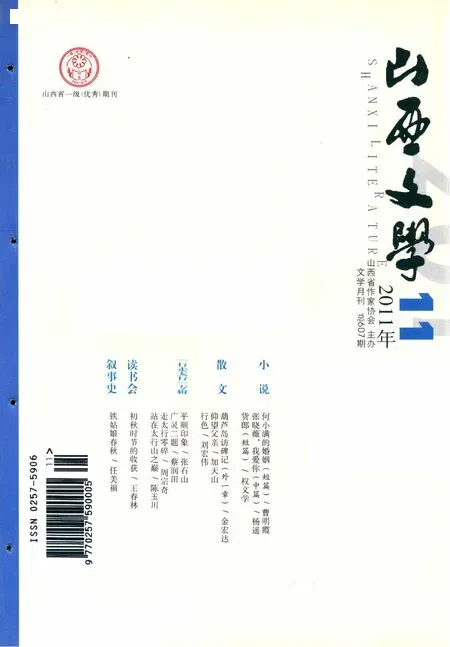葫芦岛访碑记(外一章)
离开已经很久了,葫芦岛那辽阔而雄深的云天,似乎还一直悬浮在脑际,确切些说,还有那几处昂昂然矗立在云天下的碑刻,它们共同构成的绵亘于时空的无限恢弘的画面,以及透示于其中的诉说与证明的巨大表现力,还在心中深“刻”难泯。
其实,此刻我就是直奔那里的碑刻而去的。几年前,葫芦岛渤海造船厂五十年厂庆,要立碑为记,找人代撰碑文,我“不揣谫陋,腆然承乏”。碑成之日,厂方曾邀我前往参观,却因俗务难拔,又念往返千里之遥而婉拒了。殊料留下一缕悬想,就是那几段粗拙的文字,装扮之后,“立”起来,会是一副何种形象呢?如今正好有一机会,便专程来探究竟。
耸立在船厂大门前广场上的这碑,果然伟岸可观。说是碑,其实是一座纪念性建筑物,上方有几个凌云而起的人物塑像,下方则是乘风破浪的舰船型。“船舷”两侧为碑文,一边中文,一边英文。中文题曰“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五十周年记”,粗粗阅过,很“尊重原作”,未见改动,起笔云:“葫芦岛港阔水深,碧波万顷;陆路水道,雄扼要冲,既为北方天然不冻之良港,亦是古来兵家必争之要塞。……”接叙船厂兴建之艰难历程,复叙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与辉煌,终述壮志与企望云云,俱是据厂方提供的资料与要求而写,可谓中规中矩。现在看来,神韵欠缺不说,文字也嫌过长,漫漫铺开,竟是一大篇。大理石面,电脑刻字,正所谓“刻”板划一,殊少神采,又由于非一整块,拼接处痕迹历历,整体美感大受损害。即令如此,主办者郑重其事,投入不小,不难感知。尤其将碑文全译成英文,勒于另一侧,提供外宾阅赏,此种创制,似乎别处尚少,颇显胸襟。
早从网上得知,离此不远,还有两处现代碑刻,趁天光尚早,一便去看了。
一是建于1930年的“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此碑有碑亭,亭盖四面陡坡,飞檐上翘,下临石崖,面朝大海。石碑为汉白玉制,材质坚而莹润,造型沉稳庄正,碑身正面阳刻隶书“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9个大字,背面阴刻张学良将军撰写的八行正楷碑文。年代并不迢遥,而字迹己漫漶难辨。为此,碑亭外立有一黑色大理石碑,将张文移刻于其上,系近年文物部门所为。此碑之外,又“衍生”一碑,乃当地政府所立,详述该纪念碑“失而复得”之经历。原来,十年浩劫中,它曾被推入海中,为海水浸蚀甚久,后打捞出来,复归其位。这就不由人不再打量一下这通纪念碑了:它如此伤痕斑驳,饱经患难,不仅见证了当年的历史,也见证了后来的历史,这位“寿翁”,该有多么深广的阅历和睿智。也不禁让人骋目海天,遥想当年撰写碑文的英武少帅,今已驾鹤西去,不经意留下这几行文字,尚与故国后人时时对话,成就了一段“不朽之盛事”,幸甚幸甚。
葫芦岛筑港开工未几,“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葫芦岛港亦沦入日本人之下。就在纪念碑后方,有三个废弃的巨大的储油罐,是当年日本人用来向其海上“动脉”输血的。走近看去,空荡无物,唯有几摊苍黑的渍水,和一片飘零的荒草。如果说碑是有字的历史见证,那么,它们即是无字的历史记忆,只是这种记忆,早露出太多的朽败和秽滓罢了。
冥冥中似有一种安排,越过这象征日本侵占与掠夺的储油罐遗址,数十米外的公路旁,赫然又横卧一巨石,上书“日本侨俘遣返之地”大字,且有“1050000”字样,异常醒目,其后有碑文云:
从1946年5月7日至1948年9月20日,共遣返日侨俘1051047人,历史在这里为日本侵略中国以失败而告终画上了一句号,也在这里为中国人民的宽容和善良留下了一座人道主义的丰碑。……
从爱国军民筑港兴国,到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占,再到抗战胜利,宽容遣俘,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百步之间,凝缩一线。(后来得知,此处拟建“和平公园”——正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此碑选用巨石,融艺术造型与碑刻于一体,刚劲浑朴,稳重如山,碑文虽用现代语体,亦简练有力,言浅意深,也难得的是,以中、日文对照,年年来此纪念的两国人民,同诵此文,能不感怀万端!
历史沿着这些碑刻延伸,次日上午,又去看了塔山阻击战烈士纪念碑。时间就在遣返日本侨俘完毕不数日,发生了这场塔山阻击战。此战解放军在一个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带,浴血鏖战六昼夜,歼敌六千余人,挡住潮水般敌军的去向,战况极为惨烈。纪念碑即筑在当年的前沿指挥所,上有陈云题词“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阴亦有一碑文,记叙战史及立碑缘起等,惟此碑文为防受损,竟被特意用铁丝网罩起,不能通读,也是一小小“奇观”。其侧又有一块墓园,许多当年身历此战的解放军名将,如吴克华、莫文骅等,均葬于此。然而,墓园规制、碑石制作,似嫌草草,与他们的功勋、地位,殊不相称。
苏东坡曾写过一篇《墨妙亭记》,记当时有位地方官很喜欢碑刻,专门修了一个亭子,将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的石碑集藏起来,有人就说,凡物必归于尽,“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意思是不必太看重和依恃碑石的久长性。苏轼却力挺这位地方官,他认为虽然要“知命”,知道一切都不会绝对久长,却也还是要尽“人事”。碑刻这样的东西,尽管也终会为岁月所销蚀,但是还是较为坚固、长久,我们生息的地面上,多一些这样的标志,会使人们的历史记忆更加鲜活、深隽,何况,如果设计、制作经心、精湛,富含美学价值,使人流连、涵咏,怀想不已,岂非善莫大焉。
寻访花坞
问了若干老杭州,都告以不知道有个花坞,但老东岳是知道的,却大抵也没特地去过。可是“风雨茅庐”的主人郁达夫确凿地写过一篇花坞的游记,第一次游花坞留给他的印象是那样的好,再说,花坞这名字又是多么诱人。
从灵隐登上北高峰,在毛主席诗词纪念碑亭,稍事停留,时间大约是下午两点多。是个冬阳高照的日子,登了一段山路,虽然都是一级级的石阶,阳光的热力也催出了我一身汗,在山顶微风的吹拂下,披襟伫立,极目远眺,倍感舒畅。在此之前,真不知道润芝老先生竟数次登临此地,而且,有资料说,他自定都北京以来,驾临杭州达四十余次,平均每年两次,共住过八百多天。九州各城除北京外,怕都无此荣幸。偏爱此方山水如此,无怪乎他吟出如下诗句:“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风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五律·看山》)
不过,他老人家飘飘而下的,恐怕还是依来时的路径。我向亭边一位中年人打听了一下,得知山的北麓,确实还另有一条路,也就是郁达夫所说的“自北高峰后,向北直下的这一条坞”。然而,当时郁达夫并未走过,倒是另寻了一条路,“坐了黄包车,过古荡,过东岳,看了伴凤居,访过风木庵(是钱唐丁氏的别业)”,而后才被车夫“拉到了花坞的中间”。
我便选定走这条路下山。这路并不难行,一路也是石阶,只是比从灵隐上来的路要稍陡,石阶破损较多,如果走的人少,是不会有如此损坏的,可如果走的人多,那么就不该没有维修,这么想着自己也无奈地笑了。而此时毕竟人少,多少显出一些冷落荒旧的味道来,很符合一种寻幽访旧的心境,悠悠然就似走近了郁达夫的那个年代。
北高峰林木蓊郁浓密,山前山后一般,只是山前新修了一条上山的缆车道,现代的机器设施搅乱了宁静和谐的自然景观,而山后这边则一如往昔,保存了一派天然风貌,回首一望,苍苍莽莽,整个山峦如覆盖在一层厚厚的绿袍之下,而眼前的一片树林的参差叶片,则在阳光下呈现出绚烂多彩的画面:赭红、浅黄、深紫……颇有些恣意和活跃。天空中悠游盘旋着一两只鹰,不知还是不是曾有幸迎过驾的那只“晚鹰”,这让你顿生连绵的回想,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有很深的历史根底。
又走过一截,就看见了山下的屋舍,达夫先生当年探访的幽静的尼庵何在?美丽动人的花坞何在?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其实,郁达夫当时最欣赏的还是这里林间散点着的小小的茅庵,一派安闲静凝的样子,又加以见到风度霭然的老尼,言行举止,竟像是俗世外的高人,这一发现,几乎就像进入了桃花源一般。
然而,现在任我走走停停,张目四望,却见不到一个茅庵,也没有竹叶杂树中间透露出来的屋檐半角,更不用说是风度翩然的老比丘尼了。走了许久,不见有其他人影,只是临近半山腰,才见有几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子喘吁吁往上走来,向她们打听一下,都说不远了,过了东岳庙,有一小巷,再拐出去,即可到古荡。到这时,我才怏怏地认定,花坞是消失了,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就在郁达夫的那篇游记中,他也提到,十余年后再一次去时,人情与风物均已改换了面目,更何况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现在的山脚下,正兴修一座堂庑宏大的庙宇,名曰“法华寺”,这寺名似乎很熟,不是别处也有,即是在古典小说中见过,杭州法华寺的原址莫非就在此地?郁达夫的游记没有提及,可能是他访过尼庵就打道回府了。而东岳庙呢,也还有,在一条窄窄的小道上,却很冷落,卖香火的人看见有人从山上下来,投过来期待的目光,我便在他的这种目光中行走过去。
尼庵没有了,花坞也没有了,但我想我还是走过了它,尽管它只存留在作家的文字中,隐没在历史的烟云里,这一路它们都确凿地在我的想象里展现过。